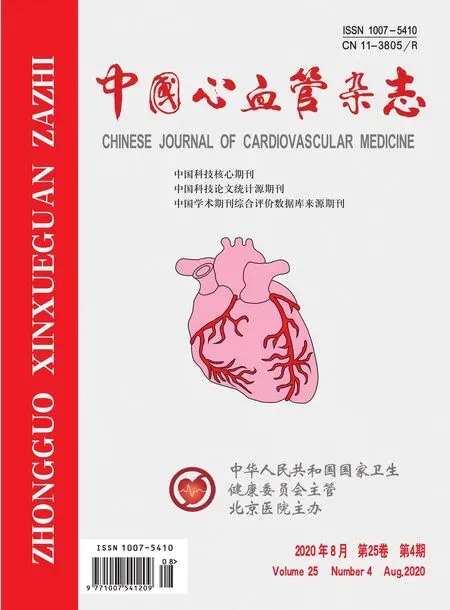心房颤动相关的生物学标记物
李春兰 裴丽娟 侯鹏
730020 兰州,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心内科(李春兰、侯鹏),神经内科(裴丽娟)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一种很常见的心律失常,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在50岁以下人群中房颤的发生率为0.5%,50~60岁为1.5%~2%,70岁以上则高达3%[1]。2010年美国的报告显示,65岁以下人群2%患有房颤,而65岁以上为9%[2]。房颤时房室同步丧失,导致心排血量下降,严重损害心脏功能,合并房颤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心排血量下降可达25%[3]。另外,在非瓣膜病和瓣膜病房颤患者中,缺血性脑卒中的年发生率分别是无房颤患者的2~7倍和17倍[4]。因此,预防房颤发作是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了一些预测和干预房颤发作的相关生物学标记物,本文综述如下。
1 神经体液内分泌性标记物
1.1 B型利钠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
Miake等[5]对254例非瓣膜性房颤患者进行了单次射频消融术后房颤复发的前瞻性随访研究,在65例房颤复发患者中,其基线BNP显著高于未复发者,不论是在单变量还是多变量Cox危险回归分析中,仅有基线BNP与房颤复发显著相关,而年龄、性别、左房内径和左室射血分数、房颤类型、肾功能(eGFR)、β受体阻滞剂和襻利尿剂应用,以及心力衰竭、高血压、糖尿病等病史均与房颤复发无显著相关性,提示消融前BNP水平可用于评估消融后房颤复发的风险。另有学者也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结果[6]。BNP是一种主要由心室肌细胞分泌的多肽类激素,心房肌可分泌少量BNP。BNP通常标志着心脏血流动力学的压力,反映心肌对神经体液的敏感度,当心力衰竭时血浆BNP升高,推测房颤时的BNP可能主要来源于心房,提示心房压力增高、心房功能不全,且心房功能不全是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无独有偶,谭颖[7]研究发现,BNP可能为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卒中危险分层及抗凝治疗提供有益指导。由此可见,BNP是预测房颤射频消融术后复发的独立指标之一,还可用于房颤的危险分层和指导抗凝治疗。
1.2 肾素-血管紧张素
研究表明,肾素-血管紧张素与房颤的发生以及复发之间存在着一定相关性。肾素-血管紧张素主要具有心脏的正性变力作用,使心肌肥大,导致心脏大小、形状和功能发生变化、心肌细胞电活动紊乱,从而发生房颤[8-9]。
2 炎症及氧化应激性标记物
2.1 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
Ehrlich等[10]研究发现,房颤组患者的CRP水平较对照组高出两倍,而且在左心耳组织样本中显示有炎症细胞、活化的T细胞、巨噬细胞及组织因子浸润。还有研究显示,CRP升高能增加房颤风险[11-12]。CRP是一些在机体受到感染或组织损伤时血浆中急剧上升的蛋白质,能激活补体和加强吞噬细胞的吞噬而起调理作用,清除入侵机体的病原微生物和损伤、坏死、凋亡的组织细胞。传统观点认为CRP是一种非特异的炎症标记物,但近十年的研究揭示了CRP直接参与了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以上结果表明,炎症刺激可能对左心房结构产生影响,促进房颤发生发展。
2.2 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
IL在传递信息、激活与调节免疫细胞、介导T和B细胞活化、增殖与分化及在炎症反应中起重要作用。IL-6可刺激生成多种急性期反应蛋白,如CRP,调节肿瘤坏死因子α和IL-1β。IL-6启动子基因变异可能调节炎症反应,增加发生房颤的风险[13]。在该项包括191例非风湿性房颤患者的研究中,与窦性心律组相比,房颤组患者的血浆IL-6水平升高。李根林等[14]认为,IL-6与房颤的发生和维持有关,在电复律或射频消融后复发风险也增加。由此可见,房颤的发生与炎症反应密切相关。
2.3 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和尿酸(uric acid,UA)
HCY作为一种常用的氧化应激标记物,其血浆水平与房颤的发生及复发均具有相关性[15-16]。HCY参与体内各种重要的氧化还原反应,其自身氧化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和过氧化物,增加活性氧含量,活性氧直接影响钙调蛋白引起细胞内Ca2+超负荷,心房离子通道改变,进而导致心房电重构;同时还可诱导IL-6等炎症因子的表达,二者共同促进房颤的发生与发展。另有研究提示,UA是房颤发生和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17]。分析原因可能是UA作为体内嘌呤代谢的最终产物,反映黄嘌呤氧化酶活性,而黄嘌呤氧化酶激活可导致活性氧产生过多,引起心房结构重构,促进房颤发生。
3 心肌纤维化及心房重构标记物
3.1 基质金属蛋白酶2、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2 and 9,MMP-2、9)
研究发现,心房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重构伴随着MMP-2上调,以及随后间质胶原蛋白的增加,在永久性房颤患者中表现更为明显[18]。袁书国等[19]研究发现,与窦性心律组相比,房颤组的微小RNA-233和MMP-9表达明显升高,而且与左房内径呈正相关,原因可能是影响胶原代谢,造成心房结构重构,促进房颤的发生与维持。
3.2 半乳糖凝集素3(galectin-3,Gal-3)
Gal-3可作为预测导管消融术后房颤复发的生物标记物,在接受房颤消融治疗的非结构性心脏病患者中,其血浆水平升高[20-24]。其作用是刺激静止状态的成纤维细胞分化为肌成纤维细胞,产生和分泌基质蛋白,包括胶原蛋白、纤连蛋白。Gal-3除产生胶原蛋白外,还参与胶原蛋白的成熟、外化和交联过程,最后通过与基质蛋白结合,实现心肌纤维化;另外Gal-3被激活后,与其他Gal-3的残基结合形成二聚体而形成网状结构,从而使ECM堆积,心肌僵硬度增加,引起结构重构,促进房颤的发生发展。
3.3 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1,TGF-β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 1,IGF-1)和松弛素(Relaxin)
TGF-β1通过Smads信号通路刺激心房成纤维细胞生成胶原组织,导致心肌纤维化的发生[25-26]。IGF-1可通过激活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通路,增加结缔组织生长因子和血管紧张素Ⅰ型受体的表达,发挥纤维化作用[27]。而Relaxin可抑制成纤维细胞激活和胶原蛋白合成,从而抑制心房纤维化。低水平Relaxin的患者,房颤导管射频消融术后,房颤不易复发[28]。因此,Relaxin可能是一个预测房颤危险分层的标记物。
3.4 内皮素1(endothelin 1,ET-1)
Nakazawa等[29]研究发现,高水平的血浆ET-1是经手术治疗后房颤复发的重要预测因子。罗晓亮等[30]发现,ET-1是肥厚型心肌病房颤复发的预测因子。当心房肌细胞肥大和左房压力升高时,心房肌细胞、心房纤维母细胞及血管平滑肌细胞分泌释放ET-1,启动了左心房的结构重构;此外,ET-1能够调节L-型钙通道和毒蕈碱型钾通道电流,缩短心房肌的动作电位和绝对有效不应期,参与了心房的电重构,心房重构导致房颤发作。
3.5 Ⅰ型胶原羧基末端肽(type Ⅰ collagen carboxy-terminal peptide,ⅠCTP)、Ⅲ型前胶原氨基末端肽(procollagen Ⅲ N-terminal peptide,PⅢNP)和微小RNA基因(microRNAs,miRNAs)
研究发现,房颤复律后复发组和接受心脏手术后发生房颤的患者血清中的ICTP和PⅢNP水平高于窦性心律组,提示二者可能成为预测临床心脏手术治疗后发生房颤的相关指标[31]。目前血液循环中可测定的胶原肽成分包括Ⅰ型前胶原氨基末端肽(PINP)、ICTP和PⅢNP等。PINP反映Ⅰ型胶原合成速率,ICTP反映Ⅰ型胶原降解速率,PⅢNP综合反映Ⅲ型胶原转换。而ECM主要由Ⅰ、Ⅲ型胶原组成。在生理情况下,仅有少量的前胶原肽维持ECM的胶原结构,大部分的前胶原肽被迅速降解;在病理情况下,Ⅰ型胶原降解减少,ECM增多,导致心肌纤维化和房颤发生。另有研究表明,在Grave’s病合并房颤的患者中,其血清中有8种miRNAs水平明显高于不合并房颤的患者[32]。miRNAs主要影响ECM,故可作为房颤治疗靶点的生物标记物[33-34]。
4 其他
4.1 高敏肌钙蛋白T(high sensitive cardiac troponin T,hs-cTnT)
研究发现,房颤患者血清中hs-cTnT水平升高[35]。Roldán等[36]研究发现,93.5%的房颤患者hs-cTnT升高,而且其是独立于CHA2DS2-VASc的房颤患者的脑卒中、心血管死亡等发生率增高的预测因子。hs-cTnT升高的机制可能是房颤伴快速心室率使心肌受损、心肌纤维化、炎症、氧化应激、心功能不全,心房心室的容量和压力负荷加重。
4.2 血清心锚重复蛋白(cardiac ankyrin repeat protein,CARP)
黄晓娇等[37]研究发现,血清CARP在房颤组高于窦性心律组,持续性房颤组又高于阵发性房颤组。CARP在房颤患者心肌中的表达呈明显正调节,它的过度表达直接影响心肌细胞间信号的传导,导致离子通道复极不一致,明显增加不应期的离散,进而诱发折返径路形成,促发房颤。
4.3 肺静脉解剖变异
肺静脉解剖异常可以被定义为房颤的图像生物标记物。右肺附加静脉是在房颤患者中发现的最重要异常,此外,左房和肺静脉口直径增大也是房颤发作的危险因素[38]。
5 小结
综上所述,房颤的发生不外乎以心内膜损伤、炎症、纤维化、重构、血流动力学改变和局灶性电异常作为基础,与房颤相关的生物学标记物大致可以分3类:参与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相关的因子、与心房纤维化和重构相关的因子以及与房颤相关的神经体液因子。研究上述生物学标记物对预测房颤的发生、复发、并发血栓栓塞的风险,以及房颤的管理有着临床指导意义。
利益冲突: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