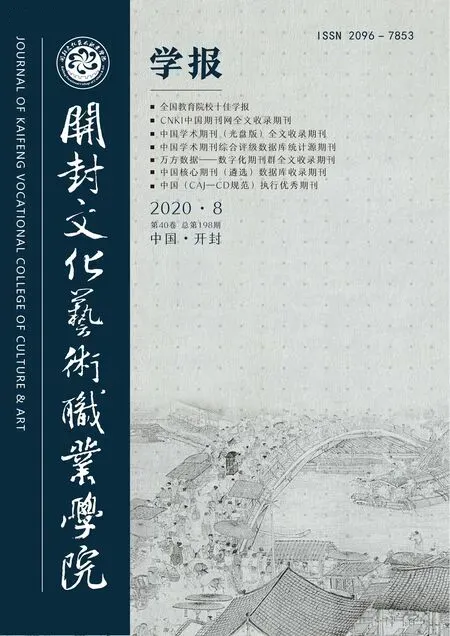《秀拉》中奈尔的身份建构
刘小姣
(石河子大学 外国语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秀拉》是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莫里森曾表示:“我一直认为,《秀拉》这本书的思想是我所钟爱的,而且其写法是独一无二的。”[1]作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黑人女作家,她的作品大多描写黑人社会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困境,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以一种独有的方式为黑人的民族事业和文化发展找寻出路。在蓄奴制被废除后,黑人的生存境况并没有得到极大改善,仍旧处于弱势地位,经济上受到白人剥削,精神上忍受白人折磨。在这当中,黑人女性的地位尤为低下。20 世纪早期,贝尔·胡克斯曾指出黑人女性的“双重不可见性”。“在美国,没有人能像女黑人那样没有社会存在与社会认同,当黑人被谈论时,谈论的焦点是男人,当女人被谈论时,谈论的焦点是白人女性。”[2]不言而喻,黑人女性是“弱者中的弱者”,她们不仅要受到来自白人的种族歧视,而且会受到黑人男性的性别歧视。双重歧视的压迫让黑人女性丧失了追求自我的权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越来越多黑人女性选择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打破双重禁锢。小说《秀拉》的主角秀拉蔑视周围的男性,无视黑人社区的规则,走出了一条原本不属于她的道路,而小说中另外一名重要女性人物——奈尔,就在这股历史的潮流中彻底失去了追求自我的机会,成为千千万万底层社会黑人妇女的代表。
一、“底层” 社会——奈尔身份的底色
面对种种社会不公,黑人的集体反应对于奈尔身份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黑奴默然接受白人农场主赏赐的土地;面对白人乘务员的责骂,奈尔的母亲海伦娜挤出一丝挑逗的微笑来试图获得同情;丈夫裘德面对事业上的挫败,只能从奈尔身上来找寻自己的男子气概。所有“底层” 黑人面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黑人男性尚且如此,将婚姻和家庭看作是最好归宿的黑人女性当然更加惟命是从。由此看来,在这种压抑的社会环境中,奈尔很容易为了与环境融为一体而放弃自我需要的追寻。
在这个“底层”集体中,奈尔的身份被打上了“依傍男性而生存的黑人女性” 的烙印。幼年时,她和秀拉就认识到她们“既不是白人又不是男人,一切自由和成功都没有她们的份”。白人对黑人张扬跋扈,黑人男性把这种压迫潜移默化地转移到黑人女性身上,种族与性别的双重压迫也成为奈尔身份建构的底色。奈尔的母亲海伦娜既性格骄傲又任劳任怨,这样的母亲形象对于幼小的奈尔来说是压垮自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母亲面对乘务员露出挑逗的微笑也让奈尔明白“一生一世都要警觉着”,这也从侧面说明奈尔一开始具有追逐自我的强烈意识,“‘我不是奈尔。我就是我。我。’每当她说一次‘我’这个字眼,浑身就聚集起一种像是权利、像是欢乐、像是恐惧的东西”[3]194。
然而,这种追求自我的冲动在海伦娜的言传身教中渐渐化为乌有,成年后,奈尔选择了一种传统的“崭新的感情”——与餐厅招待裘德步入了婚姻殿堂。但对于裘德来说,奈尔的人生价值仅仅在于满足他的男子气概,“有了她,他就是一家之主……两人合在一起,才是一个裘德”[3]194。对奈尔来说,婚姻是最好的避风港,裘德认准了奈尔会飞蛾扑火般为他和这个家庭付出所有,就与梅德林其他的女性如出一辙。
二、他者“秀拉”——身份建构的催化剂
如果将社会和历史环境看作是奈尔身份的底色,那么奈尔身份建构中出现的重要他人和他者则是促成身份的“催化剂”。秀拉的桀骜不驯和独立自主代表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是奈尔身份建构中遇到的“他者”。作为“他者”,秀拉从小就表现出与奈尔不同的品性:在面对白人小孩的欺负时,秀拉用水果刀划伤自己来震慑对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汉娜被火烧死却无动于衷,甚至与各种男性关系混乱。“秀拉可以被称作标准的‘美国存在主义者’……其实质是反社会的激进主义行为。”[1]秀拉的所作所为不仅仅让她与奈尔的友情破碎,还使其被整个梅德林视为敌人,整个“底层”的人们厌恶她、害怕她。秀拉的反抗过于一意孤行,脱离了黑人大众的民族文化事业,同时伤害了自己的亲人与朋友。奈尔履行着自己作为女儿、母亲和妻子义务的同时,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与追求自我的秀拉分道扬镳,终于变成了另一个有着“牛奶糊皮肤” 的海伦娜,这与秀拉的离经叛道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按照卡伦·霍尼对于人格的分类,奈尔属于顺从型人格。顺从型人格者的特点是倾向于依赖他人,将自己看作比他人弱小或者无力的存在,需要他人的呵护。奈尔一开始将秀拉视作她生命的希望,在秀拉的庇佑下,她也曾想过成为和秀拉一样的女性,但与秀拉关系破裂后,奈尔不得不选择和“底层” 的人们站在一起,亲近他们来孤立秀拉,表面上看是出于憎恨秀拉破坏她的家庭,究其根源是她想要从社区这个大环境中寻求呵护与依赖。这是霍尼人格分类中顺从型人格所具有的特点,即亲近人。这类人会依靠他人来获取自身所缺乏的爱与保护,同时要避免疏远他人以确保这种依赖的持续。秀拉的背叛直接推动了奈尔回归到“底层” 社区,奈尔认为,只有她屈服了,才会获得大众的爱与呵护,才可以避免受伤。自此,奈尔就只能囿于社区的规则,任由社区湮没了她“一生一世都要警觉着” 的愿望。
三、奈尔顺从型人格的演变
幼年的奈尔涉世未深,对自我的认识还处于萌芽阶段,而在跟随母亲一起搭乘火车上错车厢后,奈尔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也下定决心要一生一世都警觉着。“如果奈尔的一生因为绝对服从黑人社区的规矩而失败,那么,这一刻也是她形成错误观念的起因。”[4]此刻的奈尔是挣扎着的,一方面想要循规蹈矩,另一方面也想成为和母亲不同的人。后来,奈尔的经历证明了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与秀拉成为亲密的朋友,是奈尔顺从型人格的开始,根据霍尼对顺从型人格的定义,这一类人“习惯性地将别人看作比自己更优越,更迷人,更聪明般的存在”[5]18。奈尔对于他人有着近乎病态的依赖,认为自身是卑微渺小的,因此,需要靠近人来获得自己的朋友、爱人或者伴侣。这一点在奈尔的心理分析中可以得到印证:“是秀拉使她欢笑,是秀拉使她用新眼光看旧事物,有秀拉在身边,她感到自己聪明了,文雅了,而且还有一点自惭。”[3]201可以说,奈尔对于秀拉的依赖缓冲了黑人社区的双重压迫。而奈尔顺从型人格的病态依赖在婚姻中进一步表现为对家庭和丈夫的“殉道士” 精神:不求回报地默默付出,认定裘德“爱她就不会伤害她”,但发现裘德与秀拉的一夜情之后,奈尔彻底崩溃了。
经历了内外环境的催化、自我意识的泯灭之后,在与他人关系的发展中,奈尔的性格特点由一开始的病态依赖进入到依附性的盲目依赖,“如果家里的人发生争执,她就站在最强有力的一边,通过与强的一方保持一致,获得一种归属感,支撑感,这就使她不再像过去那样软弱无力,那么孤独无助。”[5]18在社区的包围中,奈尔通过与社区的人在行为和思想上保持一致来获得归属感,最终再也无法离开底层社区这个大环境了。
结语
对于亲人、友人和爱人的依赖本是人类存在于社会中具有的正常的性格特点,奈尔的依附却因为时代的烙印而显得格外悲哀。她的身份建构从一开始飘忽不定的自我意识,到对亲人、友人和爱人的病态依赖,再到依附和迎合大众以求获得归属感的盲目依赖,导致了奈尔作为黑人女性的悲剧人生。
——《无名的裘德》中隐含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