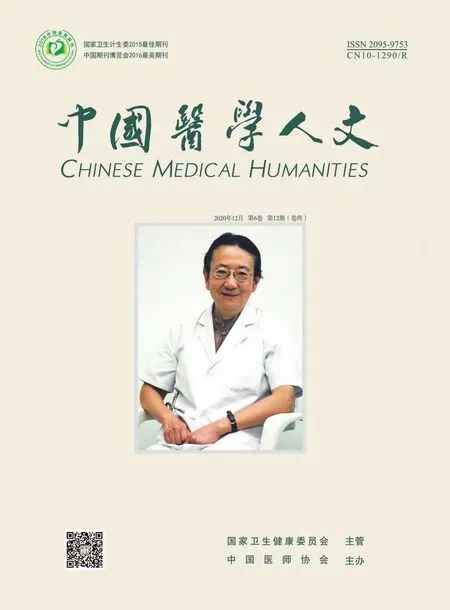临床是什么
——从“奥斯勒命题”说开来
文/王一方 耿 铭
现代医学越来越精细化,却患上了母题空洞症,如同脊髓空洞症,母题的空洞带来观念行为的迷思与乏力,譬如“医学”“健康”“临床”“疗愈”,并非百度搜索引擎或者百科全书给出的解读。医学并非只是一门科学,而是源自科学,高于科学,健康也并非躯体无疾,而是身心社灵的平衡与和谐,以及生命全程、社会全方位、产业全链条的关怀与服务,同样,临床并非只是简单地回到患者身边,“离床”的远程会诊与虚拟现实技术再造的临床实训基地都是对临床概念的拓展,但临床的真谛是什么?仍然需要我们深思,需要我们熟虑,需要我们回归“奥斯勒命题”。
临床是什么?这不是一个问题,却是一个需要深究的命题,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奥斯勒没有抽象地论述临床医学的学科建构(不同于基础医学、预防医学的范式),而是朴素地告诉他的弟子们,临床就是把更多的时光安排在患者的床边,去观察、去聆听、去触摸,去思考,随着现代技术对临床医学的介入,他又提出要将实验室建在病房,仪器拉到床边,让技术最大限度地为患者服务,以实现“患(弱)者为尊”的人道主义夙愿。
临床的背后是学历与阅历,专业知识(技术)与综合素养(人文),能力与魅力的关系,医护成长境遇千差万别,但必须重点强调其临床实践的历练(如规培的门槛,执业医师考试门槛)。价值导向必须把解决问题的实操能力放在论文发表、外语素养等要素之上。中国现代临床医学泰斗张孝骞、林巧稚不是论文大王,而是临床大师。在他们的感召、示范、引领下,协和医院产生了一批“痴迷临床,以解决患者疾苦为乐趣”的临床大夫,许多人后来成为了临床大师。
重实践能力是一个价值风标,其背后隐含着对临床真谛(即著名的奥斯勒命题)的认知与理解。早在一百年前,奥斯勒就提出:“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与可能性的艺术”,这是一个充满实践理性的命题,临床的本质是病床边的陪伴、见证、抚慰、关怀。实验室也需要建到病房里(要验证的应该是人文的力量)。在奥斯勒看来,如果不是个体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医学也可能是科学,而不是艺术。多变性是生命定律,世界上没有两副面孔是一模一样的,也没有两个生命个体是一模一样的,因此,在疾病的异常条件下,也不会有两个病人表现出同样的病理反应和病态行为。相反,奥斯勒认定越无知,就越教条主义,越迷信书本和既有的指南。所谓“好医生治病,伟大的医生治病-人”,当代临床大师胡大一教授十分欣赏奥斯勒的这一名言,反感那些“看病不看人,懂病不懂人,治病不治人”的所谓名医,因为医学是人与人的故事,而不只是人与机器的故事,人与金钱的故事,叙事医学的创始人丽塔·卡伦更进一步发展了奥斯勒的临床智慧,认为疾病、死亡不是一个事故,而是一个故事,疗愈、疗护的努力让这些故事有了温度。现代医学不应该高冷,而应该高暖。
为何医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是因为生命境遇具有永恒的不确定性与无限的可能性,正是因为这些可能性导致的疾病复杂性、多样性、艺术性塑造的患者个性,医护人员必须尊崇主体性,对冲客观性、齐一性、标准化。医学存在艺术性,旨在对冲、稀释、软化医学的科学刚性,希望在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保持张力。于是,医学从业者必须具有双重职业性格:科学家+艺术家,而这份历练来自临床实践的磨练。
著名医学家,耶鲁大学医学院前院长刘易斯·托马斯认为:医学是最年轻的科学,医疗技术只是半吊子技术,病因治疗的比例并不高,而必须辅以发病学治疗、症状学治疗与安慰剂治疗,医生常常需要在诸多不确定的信息下做出正确的判断。许多疑难疾患面前,医生做出正确判断的前提不是检测报告,而是经验与直觉。如果将特鲁多(墓志铭)箴言“有时去疗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抚慰”改为临床路径的启悟,应该是“有时去循证,常常去叙事,总是去体验。”
三百年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经嘲讽那些只在书本中钻研医学的人,他们开知之甚少的药,治疗他们知之更少的病,治疗他们完全不知的人。因为,医护只有经过临床的实践摔打之后,才明白药理知识是相对确定的,疾病(病理)知识不确定性增加(个体性,混沌性),病人的境遇是千差万别的。
毫无疑问,医护人员对临床意义与价值的认知决定他们的眼界与境界,职业进阶的高度与深度,也决定着他们的职业回馈,临床大师永远是年轻,永远最快活。
首先,临床是科学与人文,技术与人性的深度融合,詹启敏院士认为医学有两只翅膀,一只是飞速发展的医疗技术,另一只则是生命关怀的人文秉性。仅凭一只翅膀发力肯定飞不高,飞不远。韩启德院士将医学人文比喻为“方向盘”与“刹车片”,决定着职业生活(行车)的方向与节奏,避免翻车(人生事故)。
其次,临床交往是医者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源自马克思的名言“认识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包括医-患关系(相爱-相杀,温暖-冷漠,悲悯-傲慢),也包括医-医关系(同行沉默与文人相轻)、医-护关系(是支使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医-药关系(相互补台,相互疏离)、患-患关系(同病相怜,相互支撑,相互攀比、埋汰),每一对关系的背后都是职业艺术的细细流淌。临床也是人类苦难境遇的总和:医者每天都面对疾病、残障、衰弱、死亡、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心灵的投射,社会关系的倾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残酷性,反美学(活色生香,死朽衰臭),反生活(饿/渴不思食/饮,恩将仇报),反常识(人财两空,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临床更是实践难题,医患之间存在着永恒的无法相知之幕(医者的专业知识与判断力优势于患者与家属,信息的泛滥增加了医患之间相知的障碍与难度),医患陌生亲密关系,面临着快速亲密关系缔结的难题,只有在慢病语境中,才有所缓和,久病成良医,久病成知己,医患之间才会有更多的理解和认同。
其三,临床也是医护体验的总和:有人兴奋(嗜血性),有人压抑/沮丧(晕血、晕尸),平衡感最重要(理性与经验,美与丑,权威性与亲和力,知利害-得失,高下清浊,进退-收放),因此,临床是综合技能(胜任力)的集合:共情,沟通,关怀,照护,手术,药物。临床还是气质的外展:医护必须具有开放性,亲和力,宜人性,正念(积极心理)与包容性。
最后,临床是哲学,充满了辩证法,讲求对立统一,保持张力与平衡。需要不断地进行实践中的反刍、反思,或称之为否思性思维,既是自我否定的批判性反思,也有建设性反思,包括对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反思,摆脱各种决定论(基因决定论),机械论(刻舟求剑),从疾病到疾苦,生物到生命,心理到心灵,现象到意象,干预到顺应要完成一次次转身。也就是说,临床干预的反思不仅要拓展思维半径,还要致力于方向的转折,从躯体干预到心理干预,灵性干预,从战争模型(病因消杀)到姑息顺应模型(安宁疗护),知是非难易,轻重缓急到进退收放。具体的临床范畴包括五个方面,可简称为“五要五不要”:要干预,不要干预主义,适度而不过度干预,着眼于扶弱,而不是助强、助狂,不仅在躯体层面干预,还要在心理-社会交往-灵性层面干预,不仅要救助,还要拯救-救赎,接纳姑息妥协,顺应生命的自然归途;要技术,不要技术主义,手中有技术,也不滥用,有高新技术,依然保持对生命的敬畏;要科学,不要科学主义,科学不是万能的,接纳、探究临床中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偶在性,艺术性;要规范,不要教条主义,追求个性化,适度讲规范,适时讲变通,因人应时因地制宜;要创新,不要猎奇主义,拒绝“新就是好,老就是朽”。
最近,在韩启德院士《医学的温度》新书发布会上,韩先生用一段箴言来揭示临床医学的真谛,那就是“医学亦人学,医道重温度”,这也是奥斯勒命题最贴切的当代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