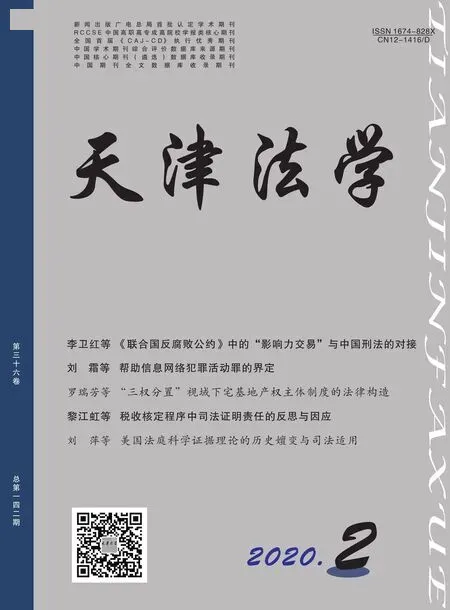《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影响力交易”与中国刑法的对接
李卫红,许振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政法学院,北京 100089)
一、问题的提出
2003 年10 月31 日,世界第一部得到国际普遍认可的反腐败专门规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第58 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审议通过,我国于2005 年批准加入《公约》后,已先后参加了七届缔约国大会,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对反腐败工作的重视程度,为反腐败治理以及反腐败国际合作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参加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 条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第27 条规定:“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这表明,缔约国对于所有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内容具有履行的义务,即使它在与国内法不一致的情况下,也要尽可能地修订国内法,而不能以没有规定为理由不履行,当然前提是国内法接受公约的规定。
问题是我国是《公约》的缔结国,但《公约》第18 条规定的“影响力交易”条款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完全对应的罪名,它与《刑法》第388 条规定的受贿罪,第388 条之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第390 条之一规定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以及第392 条规定的介绍贿赂罪均有异同,我国刑法并不能完全契合“影响力交易”的规定,以下面两个案件为例,同一的案件事实,依照《公约》中的影响力交易条款,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但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司法机关难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或者是比较牵强地认定。
案例一[1]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曹某在任期期间,先后两次找到北京某公司经理罗某,要求罗某为其解决老乡孩子的北京户口问题。罗某在其客户中找到了有进京指标的公司进行解决,而曹某分别收受老乡钱财40 万元与30 万元。本案中,曹某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要求与其不存在工作关系的罗某为其老乡解决北京户口能否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本案属于“影响力交易”范畴,但我国刑法对此难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案例二[2]:
北京A 公司老板李某为承揽到B 国企的业务,为国企总经理谢某的妻儿解决北京户口问题,在此期间李某向负责落户的某镇长行贿几十万元。在该案件中,谢某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通过有求自己的李某的行为为自己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在该过程中,权利与不正当利益产生了交换,谢某利用本人职权换取妻儿的背景户口,并非利用权力换取财物。若立法对贿赂内容的规定不仅涵盖财物与财产性利益,还能将其他所有的好处涵盖在内的话,在司法机关认定时则不存在困难,可直接认定为受贿罪。但本案的贿赂内容为“北京户口”这一不正当好处,不能直接认定为受贿,间接认定行贿或受贿皆可。但它属于“影响力交易”范畴。
上述两案例的结论是同一案件事实,根据“影响力交易”认定构成犯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认定不构成犯罪。其具体问题如下:《刑法》第388 条规定的“斡旋受贿”是“受贿罪”的特殊类型,与“影响力交易”相同之处在于均利用的是本人的“影响”而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但差异之处在于:第一,在行为方式上,“斡旋受贿”利用的是“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该“便利条件”存在制约关系①,“影响力交易”利用的是“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影响力”并不必然存在制约关系;由此推出第二,关于受托人的身份,“斡旋受贿”要求中间人须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影响力交易”的受托人是“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第三,在成立条件上,“斡旋受贿”要求“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结果犯,《公约》第18 条第2 款规定的受贿行为“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是行为犯;第四,“不正当好处”有别于“财物及财产性利益”;第五,关于定罪上,我国《刑法》对请托人和受托人分别认定为行贿罪和受贿罪,而依《公约》请托人和受托人均应依第18 条认定为“影响力交易”;斡旋受贿罪与影响力交易在适用上存在上述不同。如何协调处理这些不同,是落实《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一个挑战。
本文将从“影响力交易”规定出发,对其关键词进行释义,并探究关于“影响力交易”方面《公约》与我国《刑法》适用上的异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影响力交易”条款与中国刑法规制异同
(一)“影响力交易”条款关键词释义
1.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
《公约》第2 条第1 款将“公职人员”解释为“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人员。这一解释没有争议,关键是对于“其他任何人员”的范围,我国刑法的规定不同于《公约》。前提在于对“腐败”概念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方可对“其他任何人员”的范围进行界定。
在腐败现象已成为全球热点的当下,由于各个国家对“腐败”的定义不同,导致了在法律上规定的差异性。在对于“腐败”的定义莫衷一是的情况下,笔者试图通过不同角度对“腐败”应涵盖的范围进行讨论:在词义上,“腐败”一词在《辞海》上的释义为“腐烂;思想陈旧;行为堕落”;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的释义为“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托人违反职责和损害他人权利,非法地运用其地位或者声誉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②。在实践中,当今世界反腐败体制大致可以分为议会主导型和行政主导型两种基本类型,不论是以芬兰为代表的议会主导型国家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行政主导型国家,反腐败的对象也都是国家机构和所有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的合法性[3]。与《公约》“影响力交易”规定类似的,欧盟委员会1999 年通过的《反腐败刑法公约》第12 条③所规定的涉及到《反腐败刑法公约》第2 条、第4 条至第6 条、第9 条内容的主体亦未超出“公职人员”、“公共成员”的范围。在《公约》中,除对“公职人员”、“公共部门”进行规定外,也要求“防止涉及私营部门的腐败”,在规定上有“经济反腐败体制”④的色彩,但《公约》规定又不仅限于此,对“窝赃”、“妨害司法”的行为同样进行了规定[4]。因此,结合《公约》规定,通过以上角度对“腐败”的理解,笔者认为“其他任何人员”是指可以作为“受托人”的任何人员。
2.“直接”和“间接”
“直接”和“间接”是指的行贿和受贿的方式。“直接”,从字面意思上来说,请托人将“不正当好处”给予受托人,未经他人转手。从规范上理解,若请托人与受托人合意由请托人将不正当好处转移给受托人以外的第三方的,也属于“直接”范围之内,因为请托人与受托人两者决定的,并无他人意志的影响,该不正当好处的转移是由受托人的意志决定的。争议点在“间接”,其范围多大?笔者认为,在行贿行为中,请托人未与受托人达成合意,即向受托人的配偶、子女、父母给予不正当好处的,可以认为是“间接”关系。若向受托人的其他关系人,如:亲密的朋友、同乡等行贿的,是否属于“间接”,应当根据关系亲疏程度对接受不正当好处的关系人进行区分,若关系人为社会一般观念所认可的共同生活的父母、子女、配偶的,以默示为原则;若超出一般观念所认可的共同生活范围,须以受托人明示为补充。“间接”索贿,笔者认为是介入了第三者,受托人自己并未明确表示收受好处,而是通过默示或通过其他人的明示或者暗示提醒请托人给予不正当好处的行为。
3.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
由于《公约》第15 条规定了“贿赂本国公职人员”,所以在对此处“实际影响力”进行释义时当然不应包括公职人员的职权,因为公职人员的权力一目了然,无需解释。有学者认为,“本人的实际影响力”包括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5]。笔者认为,前者是当然的影响力,难点在对“本人的实际影响力”如何理解,是否可从英文“station”和“character”的字义来探讨。“station”侧重因职位或地位带来的影响力,强调该影响力是由其所处的位置决定的,与人格无关;“character”侧重自然人因其身份所带来的,如血缘、地缘、感情纠葛等带来的影响力。由此界定“影响力”,它是由其所处位置决定或者自然人身份带来的足以对他人的职务行为、权利行为或者义务行为造成改变的能力。对于“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的理解,有观点认为与“实际影响力”对应,即为不存在但却被误认为具有的影响力。笔者反对此种解释,《公约》第18 条成立“影响力交易”要求为请托人“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不正当好处”为条件,若受托人不存在但却被误认为具有影响力,此时并非腐败问题,而是可能构成“诈骗”,因此该种解释是不合理的。笔者认为,“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是通过其地位决定或者自然人身份无法直接确定而假定或者推定其具有的影响力。如受托人曾为某公职人员子女的家庭教师或邻居,受托人能否影响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无法通过二者关系直接反映,从而推定或假定其具有的影响力。但不论“本人的实际影响力”还是“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均应当是客观事前存在判断[6]。
4.不正当好处
《公约》第2 条第4 款将“财产”解释为“各种资产,不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动产还是不动产、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此处的“不正当好处”既包括积极的好处的增加,如获得实际的好处或者交易机会,亦包括消极的债务的减少。“好处”的范围明显大于“财产”,应当是给人带来的“益”,所有满足个人需求的内容都应当在好处的范畴之内,如理想的工作、受托人认为的个人价值的实现等等。
(二)“影响力交易”在我国《刑法》中的实现
《公约》第三章“定罪与执法”第15 条至第25条,要求“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将该一系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我国《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罪”是我国关于腐败犯罪的主要规定,其他章节还有部分规定。“影响力交易”所涉及的犯罪行为,在我国《刑法》第八章及其他章节的规定中有所体现。
1.行贿行为
关于请托人的行贿行为,请托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利用国家工作人员“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而获取不正当好处的,依《公约》第18 条“公职人员”“滥用本人实际影响力”和我国《刑法》第389 条行贿罪均可规制。“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并非推定或假定的影响力,应当属于“本人实际影响力”。请托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以财物,利用其“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为谋取不正当好处的”,依《公约》第18 条其他人员与我国《刑法》第390 条之一“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均可规制。《公约》与我国《刑法》的规定,均要求以获得不正当好处或利益为条件,均为目的犯。
2.受贿行为
关于受托人的行为,受托人是国家工作人员时,“滥用本人实际影响力”,“为该行为的犯意产生者或者其他任何人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不正当好处”,依照《公约》第18 条第2款处罚;此种情况下,依我国《刑法》第388 条,“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斡旋受贿”,构成受贿罪。受托人为我国《刑法》规定的三类人群时,可依《公约》第18 条第2 款与我国《刑法》第388 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进行处罚。
关于被利用的公职人员的行为,依受托人请求为请托人办事,当然成立受贿罪。在未依受托人请求为请托人办事的情况下,属于间接受贿范畴,公职人员依受托人请求以职权之便作为或者不作为,公职人员知情后未退还或上交的,依《公约》第15 条第2 款“间接”收受不正当好处处罚。依据2016 年4 月18 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贪污贿赂解释》)第16 条第2 款的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如果同时存在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和不正当职务行为,应当构成受贿罪。
(三)我国《刑法》未规定的“影响力交易”内容
1.任何人员与特定人员
《公约》规定的“影响力交易”中的受托人可以是“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即为“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人员以及具有实际影响力或者推定影响力的可以作为“受托人”的任何人员。而我国《刑法》通过“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将受托人的范围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2007 年7 月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 条规定,“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我国《刑法》以“其他共同利益关系”这一模糊概念对该罪主体进行限定,其范围能否覆盖“可以作为受托人的任何人员”,以及是否由于范围较小而形成法律漏洞,值得讨论。
司法解释中,将特定关系人的范围规定为“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近亲属、情妇(夫)是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亲密关系或者紧密的情感纠葛的人。“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从字面上理解是可以体现为共同经济利益的关系。因此,不具有共同经济利益关系的同学、同乡、战友等关系就无法归属在该范围之内。我国《刑法》对于受托人范围的规定,小于《公约》规定。若同学作为受托人请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即便国家工作人员对作为受托人的同学收受好处知情,依2016 年《贪污贿赂解释》由于受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不属于特别关系,因此也无法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在该滥用职权行为未“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与受托人均无法受到刑法处罚,而我国无法规制《公约》规定的犯罪行为。
2.影响力的范围
《公约》规定公职人员利用本人实际影响力以及其他任何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都构成犯罪,但我国《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未进行明确规定,被当作其他任何人员进行处理。受托人对请托人“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承诺是否只能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来实现?
依《公约》规定,对于受托人所能造成的影响不应仅局限于国家工作人员“斡旋受贿”或者三类人群的行为,受托人本人的“影响力”也可使请托人或其他人从“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伪证行为为例,若“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其“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的权利或义务,从法庭审判时获得从轻、减轻、免除刑罚或者被判无罪的“不正当好处”为条件,该行为亦完全符合《公约》第18 条的规定。依我国《刑法》仅能对上述行为以第305条“伪证罪”进行定罪处罚,对其收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未进行评价。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的行为影响到法院审判,因此对其收受好处不正当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行为进行充分评价。
3.“给予”的阶段性
我国对“行贿”行为表述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意味着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不正当的报酬,或者说,将财物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正在、将要或者许诺实施的职务行为的对价,使国家工作人员接受[7]。给予体现在其主动性,“收受”体现在其被动性,不论是行贿人的拉拢、收买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为自己谋利益,或者是对于后者为自己谋利益的酬谢,都不影响行贿受贿的性质[8]。因此,我国对于行贿中给予行为的理解应当是实际给予,而《公约》规定为“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
4.“不正当好处”与“财产性利益”
关于不正当好处的表述,在《公约》中体现为请托人给予或者受托人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及为他人“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我国相对应的表述为,行贿人给予或者受贿人索取或者收受“财物”,以及“谋取不正当利益”。依2016 年《贪污贿赂解释》第12 条规定,“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我国对于贿赂犯罪对象的规定小于《公约》规定,这是否符合人性的规律及个人的需求值得探讨。
5.被利用的公职人员的处罚
如果受托人利用了公职人员的职权行为,从而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公职人员对受托人接受不正当好处的情况不知情或者知情后要求其退还或上交的,依《公约》第19 条“滥用职权”的规定处罚;但我国《刑法》第397 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要求必须有实际损害并非《公约》规定的“违反法律”。
我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一章规定了“滥用职权罪”,2012 年12 月7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3 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同时构成受贿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渎职犯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除滥用职权罪外,可能相关的还有《刑法》第九章“渎职罪”规定的徇私枉法罪、枉法裁判罪、私放在押人员罪等,以上犯罪均符合《公约》第19 条“滥用职权”的规定,但在我国《刑法》中并未在“贪污贿赂罪”一章规定。
三、我国刑法不可能与“影响力交易”完全对接
《公约》对于“影响力交易”行为的规定,不论从内涵还是外延上都超出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刑法》第388 条之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第390 条之一规定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并非完全为《公约》“影响力交易”条款在我国刑事立法规定的体现,我国《刑法》规定亦无法全部解决《公约》涉及的“影响力交易”问题。为了更好地规制我国的“影响力交易”问题,减少可能存在的处罚漏洞,以及更好地、更妥帖地加强与国际反腐败交流的衔接,在当下应当对于我国“影响力交易”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由于犯罪观不同,犯罪概念不同以及在立法上划定的犯罪圈不同,我国刑法不可能与“影响力交易”完全对接。
(一)犯罪主体不可扩大到任何人
“影响力交易”中的主体可以是任何人,但我国所有相关腐败犯罪的主体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否则犯罪圈太大,不利于将有限的司法资源集中用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我国现行刑法及司法解释对受贿罪主体的规定恰到好处,即国家工作人员及特定关系人或有共同利益的关系人,受贿罪的主体如果扩大至《公约》“影响力交易”条款的的任何人,逻辑上不畅通。
1.我国《刑法》对于受托人范围的规定小于《公约》的规定,将除公职人员外的受托人员限制在三类人群,而非具有实际影响力或者推定影响力的任何人,这一规定具有合理依据。即便该三类人群较为容易影响其他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但若其他任何人能够实际影响到公职人员或者行政部门或公共机关的行为致使他人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均应受到处罚,在我国的刑法体系中,依其他相关规定处理,而不是使其成为贿赂犯罪的主体。因为《公约》与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体系不同,“影响力交易”中的任何人有些在我国《刑法》的另一些章节有对应规定,如伪证罪,如果证人被收买后作伪证,其行为构成《刑法》第305 条规定的伪证罪,而不是被认定为“影响力交易”行为。
2.宏观上,我国《刑法》第13 条规定犯罪需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等于从否定层面做了说明,在分则的具体规定中有所体现,在若干的司法解释中也可得出相同的结论,如盗窃罪、诈骗罪等财产犯罪的数额较大,寻衅滋事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的情节严重,这些与西方国家的违警罪不同,违法与犯罪之间有一道明显的界限。同样,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也应当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其中,主体应当受限,重点打击手握国家权力的人的以权谋私行为。
3.受贿罪所侵犯的法益应当是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职务行为的廉洁与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都不足以概括,如果利益成为贿赂内容,那只能由交换一词准确说明,交换可以囊括所有的贿赂内容,而不仅仅限于财产性利益。至于公务活动的正常进行,更不足以说明受贿侵犯的法益,因为部分贿赂犯罪并不影响公职人员正常的公务行使,不悖职受贿常常为受贿者所为。因此,当受托者手中没有权力或与其有共同利益者没有公权力可交换时,该项犯罪难以成立。
(二)“贿赂物”的内容应当改为“不正当好处”
我国当前“贿赂物”的范围,仍被限制在“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这一规定不利于对于腐败犯罪的控制。当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扩大“贿赂物”的内容会产生因为缺乏具体量化标准而使得司法实践中出现难以操作的现象,这一担心显然是多余的。一方面,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对贿赂范围的规定采取的就是“利益说”;另一方面,我国刑法中的许多犯罪并没有规定数额标准,司法机关照样惩处了这些罪行[9]。另外存在的问题是,将“贿赂物”的范围扩大,但扩大到何种程度?我国关于“贿赂物”范围的界定,已突破“财物说”,适用“财产性利益说”,即包括财物和财产性利益。继续扩大“贿赂物”的范围则适用“利益说”,“只要是能让人的物质或精神得到充分满足,则不论利益是有形还是无形、物质还是非物质、财产还是非财产,都应视为贿赂”[10]。
有学者认为,非财产性利益在逻辑上可以成为贿赂犯罪的媒介,我国未将其入罪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贿赂犯罪计赃论罪的处罚方法,另一方面是因为以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媒介的案件极为罕见[11]。然而,在以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媒介的案件并不罕见甚至多发的当前,将“贿赂物”的范围扩大,既有效呼应人民群众呼声,又能有效打击腐败犯罪,是应然之举。贿赂物范围的扩大适用于第二个案例,北京户口可以被视为“益”,即在本案中属于不正当好处,直接认定受贿即可,而不是间接认定,避免证据上的被置疑。
(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当扩大到“间接利用”
法律的生命在于解释。如何释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由《公约》第18 条规定“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可以得出该罪与公务活动或者公共权力相关,公务活动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作出的行为,我国《刑法》将“影响力交易”相关行为限制在受托人利用其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之内。但我国《刑法》并未规定受托人利用本人权力影响“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的公共权力的行为,如证人伪证影响人民法院的审判权的行使等。即便是开篇的第一个案例,受托人利用的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影响力,它是公权力的延伸,换言之,他在部里担任办公厅副主任一职,其辐射的权力直接影响到部里的所有部门,即使是对部里外包业务的北京某公司,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间接的,但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上他曾经对该公司的主管部门打过招呼,让其关照本公司的业务等等,行为人手中的权力被用于个人私利,其权力被利益收买。这种公权力的影响不同于公民权利的行使,其界限就在于公权力的影响度,如本案的制约关系,虽然不是直接的权力制约,但间接的权力制约依然可以作为惩罚的根据。因此,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可扩大到私权利,但可以扩大到间接性的公权力的影响力。
当以上述三个方案为依据时,文章开头的两个案例就不再存有争议,认定其为受贿罪顺理成章。
(四)“给予”行为不可提前
我国行贿中的“给予”行为是“实际给予”,而《公约》规定为“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将“给予”行为扩大到“许诺给予”和“提议给予”,这样提前“收受”行为的成立时间,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难以认定“许诺给予”和“提议给予”。我国刑法总则规定了故意犯罪过程中的阶段,即预备、未遂、中止,分则是以既遂形式规定的,而“许诺给予”和“提议给予”应当属于犯罪预备阶段,而犯罪预备难以认定,因为预备行为可推论出许多主观方面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如最简单的买刀行为,是为杀人而为还是为日常生活所为,即便结合行为人的平常举动,也难以作出唯一的杀人预备的判定。“许诺给予”和“提议给予”只是贿赂犯罪的预备行为,给还是不给无法在这一阶段判断出来,在实体上无法判断,在程序上无证据证明贿赂行为的发生,因此,我国刑法还是应当以“实际给予”为准。
注 释:
①2011 年11 月13 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1 条规定“刑法第385 条第1 款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
②《布莱克法律词典》中对“corruption”进行检索,释义为“Illegality; a vicious and fraudulent intention to evade the prohibitions of the law.The act of an official or fiduciary person who unlawfully and wrongfully uses his station or character to procure some benefit for himself or for another person,contrary to duty and the rights of others.”
③《反腐败刑法公约》第12 条规定,“直接或间接地为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人,故意地许诺、给予或者提供任何不正当的利益给任何断言或者确认能够对本公约第2 条、第4 条至第6 条、第9 条所提及的任何人的决策施加不合适的影响,以及索求、收受或者接受给予或者允诺不正当的利益时,考虑到该种权势,无论其行使与否,也不论假定的影响是否导致预期的后果,各当事国均应采取确定其国内法下的刑事犯罪所必需的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
④在北欧、尼日利亚和法国,为有效打击经济犯罪和公共官员腐败,应运而生的一种反腐败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