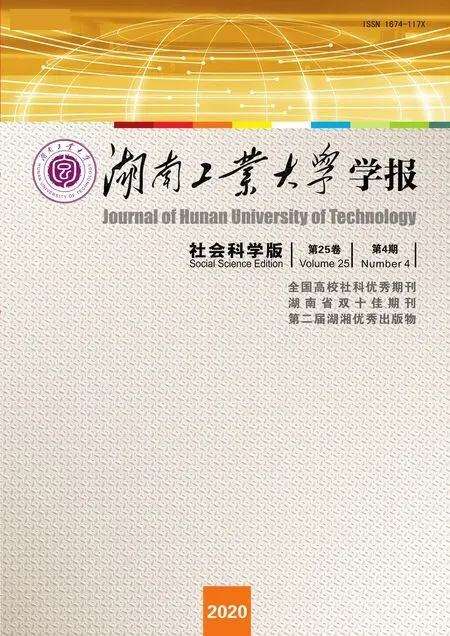反讽、荒诞与“和解术”构型
——《送我上青云》叙事实践与文化意蕴论析
张益伟
(安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送我上青云》作为80 后导演滕丛丛执导的处女作,颇能代表新生代导演对当下社会秩序和人们主体精神的思考,电影获得第22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之亚洲新人奖最佳导演奖提名。不少评论者已关注到该部作品的女性叙述视角及对女性意识的表达。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之作,这部作品事实上已远远超出了女性主义电影的范畴,它的悲悯的意涵与主题指涉着当下中国的每一个个体,这种主题的不断衍生与电影叙事手法的独特调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电影叙事理论上来说,《送我上青云》扎根于当下中国现实,通过使用反讽、荒诞、和解术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让一个原本苦涩的故事具备了多重蕴涵和张力。
一 反讽——青云路上的困顿描绘与挣扎诉说
克利安思·布鲁克斯在《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一文中表述过“新批评”派对反讽的看法:反讽就是“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1]376,是作为意象或者材料的陈述的“‘部分’接受语境压力的修饰”[1]379的产物。由此看出,“新批评”派非常强调语境对一个完整的陈述语的“施压”或修饰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施压”可以改变陈述语本身的指涉方向,从而造成“这句话的意思恰巧与它字面意义相反”[1]379的效果。在此基础上,他又对反讽的样态给予分类:“我应当提醒读者一句,甚至明显的、习惯上承认的反讽形式也包含广泛的多样性:悲剧性反讽,自我反讽,嬉弄的、极端的、挖苦的、温和的反讽等等。”[1]380沿着“新批评”派为“反讽”研究提供的致思路径,我们可以发现,不仅诗歌之中存在着反讽,在大量现实主义艺术作品中,反讽也是普遍存在的,它经常借“人物行动——语境——目标(理想)”这一动态关系的变化来呈现文本显性抑或潜藏的意义。在这里,人物行动和目标的实现本身如果被看作是一个陈述语(过程),语境则通过错置、隐瞒、混淆、延宕等手段使“行动”与“目标”二者产生偏离,从而让该陈述语发挥其惊人的讽刺效应。其中语境是布尔迪厄意义上的“场域”(关系束)[2],充满着浓郁的权力色彩。在现实意义上,它可以指向社会、族群、集团、机构、党派等。《送我上青云》这部电影便充满着诸多反讽,反讽叙事构成了其主题生发的关键,也是进入该影片的重要步骤之一。
首先是片名和电影故事内容之间的反讽。“送我上青云”引自《红楼梦》第七十回《临江仙·柳絮》,为小说中薛宝钗所作:“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3]柳絮本是寿命极为短暂之物,但在薛宝钗的笔下,却可以“上青云”,这种情状描摹颇符合宝钗善于“借力”的形象内蕴。这一特征与电影中的主人公盛男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反讽效应,从而指引观众不自觉地将两个分属不同时代的女性进行比较鉴赏。宝钗咏柳絮,她本人正是凭借其家族实力的庞大而借力再别霄壤。但影片塑造的有原则有追求的大龄未婚女记者盛男却得了卵巢癌,她的青云之路被阻滞,行动变得不可持续,自然其“目标”也很难实现,这样目标与行动之间的相悖与矛盾便出现了。如果说盛男的疾患是导演的一种“主控思想”[4],其带来人物命运的戏剧性转折,那么好风能否寻到?盛男能否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便关联着电影对盛男所处语境的合理调度及其故事如何讲述的处理。
其次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反讽。电影中的盛男是一个女强人形象,像多数新时代的新女性一样,她有着自己独立的事业追求。身为记者,她一个人在城里租房打拼;同时,她不藏污垢,任何肮脏之事都逃不过她的眼睛。电影刚开始,她发现山林失火事件是李总为邀功纵火所致,便立即打电话告诉同事;随后她主动揭发小偷并被小偷突袭。可以说,盛男就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样具备一种“只傍清水不染尘”的天然的高洁品性。可是她的出身却并不能为她保持“高洁”的情操提供太多的支持。电影中不断出现的高耸入云的大楼似乎都在表呈盛男内心的惶惑:“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却找不到我的家。”家中父母互相背叛,30 万元的手术费需要自筹,这都是摆在盛男面前的绕不过去的难题。她是记者,“挑错”是她的职业病;她性格耿直,有些类似男孩子那样不惧不怕;在钱和尊严面前,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当她听到李总嘲笑她“给钱就是衣食父母”,贬低记者不过是“跑业务”之词时,她当场撕毁合同。这些行为与事件都传达出这位都市女性在追求“青云路”上所遇到的语境的反讽。
再次,是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之间的反讽。电影除了讲述盛男的故事之外,也穿插讲述了与其对照的次要人物在“青云之路”上艰难跋涉的故事。如书生气浓郁的刘光明,他被岳父李总喊着当众背诵圆周率成为一种奇观和乐趣,一家人都把他这种“天赋式表演”视作消遣。刘光明有志向,喜欢阅读,却又懦弱无奈,只能独自吞噬着理想幻灭的痛苦。遇到盛男以后,他才在一个陌生的异性身上找到了些许尊严,但是这种自信很快又坍塌了。即使最后他决定从别墅跳下去,“勇敢”地做一次自己,似乎也不过是给他受尽屈辱的人生徒增了“残疾”二字而已。他的身份和位置无任何改观,他在众人眼中依旧“毫不起眼”。极具反讽意味的是,他唯一有“骨气”的作法,是借岳父之父的葬礼,坐着轮椅,带着卑微的一点骄傲让所有人对死者(似乎是对他)三鞠躬。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再比如企业家李总(李平),坚决认为金钱是最重要的,知识在当下已不值钱,因此,他胡吃海喝,贪图享受,利用手中的资源和权力成为当地的一个“款爷”。他在背后不断戏弄式地消费他的父亲,在其父亲的眼中,他是十分“愚蠢”的。从其父子二人的对照式性格形塑中可以发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沉迷于在自我的凝视中不断膨胀。其表面上很有尊严和自信,但是在别人眼中却未必如此。这些反讽叙事呈现出个体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差异,也构成了对怀揣“青云之志”的当代都市人悲剧性生存的隐喻。
二 荒诞——现实让人无处遁逃
改革开放40 多年来,中国在物质经济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国人的精神是否与这种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相匹配,导演显然对此有所怀疑。沿着这样的问题继续向前思考,我们发现电影使用了荒诞的手法去呈现人物与现实语境的碰擦与龃龉。法国作家加缪在解释“荒诞”的涵义时说:“当一个世界可以用一般的理论方式来解释时,即使这种解释有其失误的一面,这个世界归根结底还是我们所熟悉的。但是,当一个世界突然失去了幻想和光明,人们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怪物。对于人们来说,这个世界就成了一个无可挽回的流放地,因为就像人们已经丧失了对未来的天堂所抱的任何希望一样,他们又被剥夺了对已经失去的家园的任何美好的回忆,这种人和生活、演员和剧中世界的分离就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感觉。”[5]社会的快速发展并不能掩饰人类精神上的创伤和疼痛,而只会加深这种变异,其恰如荷兰华人作家林湄所说,人们“失去主心骨似的不知所措,不是随波逐流,就是逆向而行或原地旋转,只在乎功利和实惠。”[6]显然,导演滕丛丛着眼于描绘正是这样一种矛盾化的不均衡的现实。在她看来,“时代社会的阴暗面是他们的痛,而他们哭的是那些不幸的人。”[7]她接触到了这样一些原本很优秀却命运多舛的人后,将聚光灯对准了他们。
首先,荒诞表现为物质的繁荣和精神的式微的矛盾。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可以呈现在很多方面,诸如千年未变的男权标准和性别范式的制衡效用,男性以金钱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四毛、李总),等等。物质的繁荣和精神的式微二者之间的错位和游离是盛男命运荒诞感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金钱的增多并不代表知识的增多或认知的深刻。电影中,盛男这样向来一帆风顺的女孩,也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存有诸多疑问。对她而言,在没有弄清楚自己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之前,是绝对不会像她母亲那样轻易地和男人发生婚姻关系的。
其次,荒诞表现为都市的发达与文明的进步并没有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疗治躯体和精神的良药。电影中的盛男成长在一个物质比较殷实的家庭,除了父母亲长期的婚姻不顺之外,她在经济上并没有受过太多的困扰。至于外界流行的“剩女”标签之说,她对其更是不屑一顾。世人眼中的所谓的成功,对盛男而言,没有任何意义。面对开公司的老板父亲,她也敢于撕破脸皮,揭穿其道德丑陋的本性。她在朴素风雅的山水民居中希冀凭借写自传自筹手术费用。借这个过程,她完成人生价值观的蜕变并思考了生死的奥秘。
盛男母亲梁美枝虽然长得漂亮,却一直活在男性支配的阴影下走不出来。面对丈夫出轨,她非但看不清自己的位置,竟还几次三番说要通过“出轨”来报复对方。我们从她的低能式选择和自欺式行为中可以看出,她的思想反映了一部分中国女性对女性自我价值的模糊认识。这些女性认为,她们的价值必须“被纳入男人生命的轨道,为男性的生存和成长服务”[8]163,似乎只有这样,她们才能昂起头来做人。我们在亦舒小说《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君、黑孩小说《樱花情人》《惠比寿花园广场》中的秋子身上都能看到同样的男性附庸这一形象链条的延续。“她们的主要行为都是向男性奉献或牺牲,而这种献祭注定使她们走向死亡。”[8]163这些女性深陷男权统治的藩篱中,自己却浑然不觉。“她们付出的女性爱是无意义的,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最终使自己沦为物。”[9]盛男正是在母亲身上看清楚了这一点,因而她不愿重蹈覆辙,再走老路,她一直在努力地找寻自我。
更为荒诞的是刘光明。他有理想,有抱负,但大学毕业后便匆匆结婚,从此便过上了被金钱豢养却不断挣扎的生活。他原以为只有在金钱的滋养下,他才能施展他的志愿和抱负。可惜对他来讲,“精神的这场独立运动是充满了惊险与痛苦的,甚至是非常恐怖的。”[10]这一点在电影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刘光明在财大气粗的岳父面前,为了赢得一点面子,在家庭入户玄关处悬挂一面镜子,只要岳父一进来换鞋,就相当于给他磕头一次;甚至在老爷子的追悼会上,刘光明自己推坐着轮椅去接受所有人对死者(似乎是对他)的鞠躬,以此找回他所期盼的那一丁点儿可怜的尊严。刘光明的跳楼自杀行为同样具有很强的荒诞意味。加缪在《局外人》中塑造的“社会的弃儿”莫尔索,被社会规则折磨至外表冷漠、身陷囹圄,其性格与刘光明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事实上,“他远非麻木不仁,而是被一种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执着而深沉的激情所鼓舞。这种关于我们的本质以及情感的真实也许不那么高蹈,但是少了它,任何对于我们自身或者我们这个世界的追寻就是不可能的了。”[11]存在主义文学中的人物的戏剧性在刘光明这个人物身上再次显映。
再次,荒诞也体现于自然风物的勃勃生机与人物生命的残败凋零的对比上。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贵州,画面唯美清新,大河弯弯,云舒云卷,西南边境氤氲旖旎的自然风光,道教气息浓厚的深山老林,这些美景可感可知,暗合着明代陈继儒笔下“编茅为屋,叠石为阶,何处风尘可到;据梧而吟,烹茶而语,此中幽兴偏长”的诗意兴味[12],充分展示出中国西南边陲地区的地景风貌。这种构思雅致的“文人画”般的审美趣味与人物交相辉映,形成了独特的电影美学符号。但影片中的每一个人物却都挣扎在美景之外,都在做着与自然心性相反之事,欲望的悬浮和权力的计算让社会成为一座活着的“炼狱”。四毛一心想巴结上李总,以此为事业的飞黄腾达打下基础;李总“浑浑噩噩”恪守并享受着自认“最识相”的一套生存法则,称王称霸。盛男和李老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前者是疾患的折磨,后者是时间的考验。这种“山水间”的故事却并不与山水间的诗性栖居、生机勃勃相随相依,人类如蝼蚁般的生存在野蛮生长的大自然中更显得微乎其微,那种“看不见”的属于人类的惶惑和恐惧,更显其神秘。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电影表现了了人类的可怜处境。“人一旦在平庸无奇、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提出‘为什么’的问题,那就是意识到了荒谬,荒谬就开始了,而人也就清醒了。”[13]盛男正是处于这样一个荒诞的险象环生的环境之中。电影通过这种悖论式的故事讲述,传达着导演对当下国人精神疾患的重重忧虑。这种忧思也转化成一种警醒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把荒诞故事当作警世寓言,是我们面对电影时最基本的态度之一。”[14]
三 “和解术”——灵与肉、自我与他者的相处之道
反讽和荒诞叙事终究是一种手段,其折射出来的人类的处境最终还是要在一种平实的镜像和审美中获得提升。电影使用了“和解术”这一故事和技巧双重层面上的处理手段,从而决定了影片主题的指向和意义的生产。影片最后描述了盛男躺在病床上被推到手术台上的情景,可以说,这一和解式处理在技术上显得意味深长。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女主角的一种幻觉,这种幻觉表达着盛男内心的一种期望。盛男在与自我、与父母、与社会“和解”之后的唯一选择便是配合医生的治疗,选择对父母的宽宥,而不是对峙。我们也可将这种幻觉视为故事的延伸,盛男选择让其柔软的躯体接受诊疗,其性情自然也获得了一次“手术”处理,进而充满重生的可能性。无论盛男的青云之路多么高蹈或渺远,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肉体上来,因为精神始终是离不开肉体作为支撑的。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是精神和肉体、理性和感性的完美结合,人间烟火并不构成对精神追求的必然障碍。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导演的悲悯用心,她用特殊的视角俯瞰众生。在叙述姿态上,她强调了“给出”,而不作过多的“判断”或“解释”,因为生活本身足以凭借其突兀和复杂特征动人心魄,富有戏剧色彩;相反,过多的阐释或者解释都是多余的。唯有“和解”,可能是个体与世界以及自我相处的唯一合法性方案。
我们在电影中不断看到人物之间或者人物自我从对立冲突到和解的过程,这种和解并不是电影故事最后团圆结局的必然走势,而是基于现实本身的一种艺术化考量和设定。在一定程度上,这种选择既符合当下现实中国人日常生存伦理的诉求,同时也极富艺术性,不断感染着观众。就前者而言,我们可以联系导演和当下中国的现实来进行考察。该片的编剧、导演的滕丛丛是“80后”,其本身的成长经历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同步的,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曾经对于‘无根’的自我安之若素的80 后们开始反思,自我真的可以脱离历史与现实而独立存在吗?在历史的长河中,‘我’的位置到底在哪?‘我’之所以长成现在的样子,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来路?”[15]在将近40 年的人生历程中,一方面,作为导演的滕丛丛感受到了中国社会井喷式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她也看到了传统中国以及道德中国在现代语境中的尴尬位置——传统文化如何存续和继承,古典中国和现代化中国之间的断裂如何缝补,这些问题在导演的视域中是触目惊心的。作为一个社会和时代的敏锐观察者,她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电影中以盛男、刘光明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焦灼和无奈,他们卑微的生长,他们希望的落空;也可以看到金钱至上观念给另一些人物诸如“李总们”带来的心灵的空虚和畸变。由此,人物色调上的灰暗与凝重之气扑面而来。但是在影片中,导演并非一味用力于兜售和投喂苦难与批判,她把镜头集中于“展示”这一人性裂变的能指环节和动作。作为导演,她想诉说的是40 年来中国的物质发展变化与中国人主体精神发展的偏离造成的疼痛感。至于如何重建这种主体精神,电影主要通过“和解术”给出答案。
一是灵肉合体,与自我和解。影片中,盛男走过了从灵肉分裂到灵肉合体的一段旅程。电影一开始,她对自己的身体是毫不在乎的,正如她名字所隐喻的那样,她虽然身为女性,但是却比男人还要刚强。她可以和男人一样可以做拼命三郎,有勇气有担当。面对一个精神病人,她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恐惧,而是见怪不怪,尽管因此招来横祸。她对母亲依赖症的厌恶、对父亲出轨的鄙视等情节表现出:她是一个外表看似坚强、内心也不服输的女人。当盛男在刘光明身上亲眼看到了一出滑稽的人生悲剧上演后,她又是无比痛心的。她的哭泣证明她也有一颗脆弱的心灵,她也同情那些卑微的生命,她也同样对这个世界无奈且常怀揣恐惧,她甚至一度想过跳崖自杀。可以说,盛男内心的蜕变过程清晰地反映了她与这个世界的“和解”的过程。从开始她对母亲的不屑一顾,到后来对刘光明的失望,体现出她内心的不断成熟。她不断在他人的世界中看清和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断从与他人的对立冲突中过渡到与他人的和解与宽宥他人。
影片中,盛男开始认为李老给她提供的一套健康方案是很滑稽的,并不信以为真,她权作敷衍之事相待。但在和李老接触之后,她开始不断地对生命的意义进行参悟。李老的那句“爱欲之门,我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勘破了那些虚妄的灵魂假说,为她开启了思考生命和欲望的大门。李老对“爱欲之门”的解说渗透着传统中国哲学中身心合一的观念。由此可见,“爱欲之门”既包含着精神的丰盈,也离不开肉身的打开,而这正是她20 多年来苦苦寻觅的一个答案。因此,电影最后呈现的盛男在断壁残垣悬崖边上的三声“哈、哈、哈”,其实也表征着她看透人生之后的一种坦然和豁达。它既是对自我灵与肉之间沟壑的一次“弥合”,同时也是她和李老之间矛盾的一种和解。
电影呈现了盛男于情欲高潮中颤栗不已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恰恰在于证明每一个人的青云之路的抵达都是他人不能替代的。女性不能代替男性来完成,同样,男性也不能代替女性来完成,只有自我才能完成对自己历史的清理和意义的抵达,并最终明确自己人生的位置和方向。《送我上青云》这个电影片名很容易误导人的一个地方在于,似乎追求精神深邃和追求肉体享乐是天然对抗的。有精神洁癖的盛男充满一种智识的傲慢,她嘲笑母亲的愚蠢,但从来没有试图理解过母亲的恐惧。其实,母亲的那种恐惧是对时间的恐惧,但因为那恐惧太过本能,以至于被盛男放置在不屑的位置。她用“哈、哈、哈”大笑嘲笑李老,但她最后才明白那三声大笑是对自己紧绷人生的疏解。她被谈哲学、看云彩的刘光明吸引,她嘲笑他,却没有理解过他的绝望。刘光明拼命离开她,纯粹是出于对她的恐惧,因为盛男的欲望本能而且实在,表面看来粗俗且违反礼俗,扭曲到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最后,盛男站在城墙上发出三声“哈、哈、哈”,可以看作是,她终于理解了欲望和肉体的合一对精神的原初状态的支撑是多么的重要。
二是接受他者,与社会和解。《送我上青云》中的一个核心词汇是恐惧,这种恐惧气氛弥漫在每一个人物身上。梁美枝一直对丈夫的出轨耿耿于怀,她恐惧岁月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痕迹,50 岁时生理上的绝经让她倍感紧张。因此,她想方设法要走出去,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知音”。在年迈的李老那里,她终于找回了曾经被尊重和被崇拜的感觉,似乎这是自身青春梦想的一次召回。还有李老,他也试图使自己灵与肉和解。辟谷期间,他清心寡欲。遇见梁美枝后,他彻底醒悟,懂得了放下与解放自我,明白了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是对人间美的留恋。此时,一味的“幽禁”和“闭关”已经不再重要。相较之下,盛男最初对世界激烈的对抗尽管呈现出一种“不坠青云之志”的英雄气节,却在李老这里显得盲目而傲慢。李老说,爱欲乃生死之门,爱欲的生发取决于一个肉体支撑着的个体。人的意义固然在于精神的不断成长,但是这个成长需有一个肉身化的生存作为铺垫。如果离开了这个肉身,去追求精神,最后只能是觅得空中楼阁。那并不是理想,那只是一个虚幻的梦。和解不是目的,却是人性魅力得以彰显的最好方法。
我们当然向往上青云,但是青云绝非精神的飘忽,它是肉体和精神的协奏曲。个体的幸福建立在精神和物质的均衡发展基础之上,而非建立在女性主义视角的自我美化中。自我“孤岛化”和对抗,不是求生的唯一法则。事实上,这部电影的启示恰恰在于,无论男女,由“和解”而生的通透之力是我们唯一的救赎。倾听别人,互相理解,才是救赎之路。故而,绝对不要陷入那个一味追求自我价值属性的死循环之中。加入大爷大妈买鸡蛋买大米的队伍,和寻找知音、讨论哲学,从来不应是冲突的。《送我上青云》的最后,表现出人物与自我、世界、他者之间的和解。这种和解不是一种失败或者妥协,其看似无力与无奈,却不失为一种不屈或豁达之良策。
《送我上青云》充分挖掘中国古典文化资源,以富有诗意的叙事布局呈现出一种视觉美、张力美,进而衍生出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是电影写意手法的使用。画面中云蒸霞蔚,青山绿水,烟雨蒙蒙。盛男寻找李老的过程发生在一个诗意的深山老林之中,这里有着浓郁的道家意味,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远离了现代都市,清净明亮。李老仙风道骨,言谈之中充满中国道家仙人的智慧。李老喜欢写字作画,其辟谷行为本身也是中国传统中的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其书法文字折射出千年中国书香文化的光芒,也反映了这个古老的文明在当代的生存困境:只能藏之名山,不能留存在大都市之中。其次是电影中对古老中国民间文化遭遇现代科学后所衍生的问题的呈示。如电影中的那个练气功的精神病人,其头顶一个铁锅目的在于方便接收来自宇宙的信号。这个悲剧化形象显然就把中国民间气功符号放置到电影之中,其精神疾患关联着传统思维与现代思维之间的撕扯,表征着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悖论。当代社会,一方面是大都市商业的发达和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极力追逐,另一方面是人们依然面临很多无法解决的生命之谜和精神困境,一些人不得不从古代中国文化中寻找灵丹妙药;另外,还有一些人试图以荒诞不羁的行为与世界对抗。影片中,古典风韵、传统中国符号与都市现代化符号的尖锐对峙,代表着两种文化观念之间无法弥合的矛盾,这种布局也反映出导演对古老中国文化如何发展和存续问题的反思。
与电影《送我上青云》这位女导演对中国传统道学思想的援用一样,不少中国当代女作家也在不断寻找向古老中国甚至域外探寻、征引疗愈良方的路径。她们或是试图将古老的中国经验纳入到现代化的轨道中来,从而在一种比较视域中审视现代化的局限;或着意于探索现代化之外的新的可能性;或醉心于整合古典资源与现代中国文化。如作家庆山在散文《月童度河》,尤其长篇小说《夏摩山谷》中,就表达了她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强烈质疑和反思。在小说中,主人公不停地游走于现代化的边缘地带诸如中国的西藏、喜马拉雅山脚下、尼泊尔、加尔各答、不丹等,寄情于山水、寺庙和佛教,注重主体精神的自修和完满,在一个褪去都市浮躁欲望的纯净空间中,寻找精神和生命完善的多种可能性。旅日女作家黑孩的《贝尔蒙特公园》,则是将对现代化的省思指向了一个动物群落,并由此提炼出人类社群的生命政治与伦理正义问题。这些女性作家与滕丛丛导演对如何救治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分裂人性给出的方案异曲同工。《送我上青云》直面现代社会中的顽疾和痛楚,直击文明的痛点,用反讽、荒诞的艺术手法描绘出文明的断裂感和无常感;同时,也借人物的命运把脉、讲述古老中华文明在当下的可持续性命题,并希冀用“和解术”这一软处理方式弥合物质和精神之间的沟壑,从而为我们反思文明的症结提供了一种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