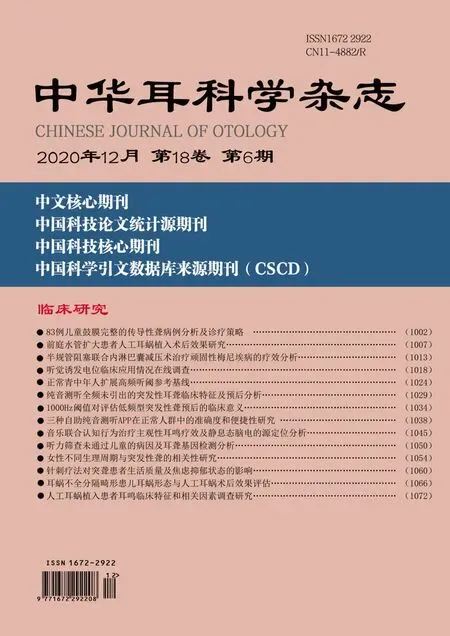耳鸣相关脑电研究
张驰王晓光蒋晴晴马晓彦曹伟王方园 申卫东杨仕明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学部
2国家耳鼻咽喉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3聋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聋病防治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5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京中医疗区旃檀寺门诊部
耳鸣是指在没有外界声音刺激的情况下,正常意识所感知的异常信号,通常也被称为“幻听”。全世界有大约10-15%的人群遭受耳鸣的困扰,在突发性感音神经性聋的患者中,耳鸣的发生率甚至能达到80%-95%[1]。耳鸣可导致失眠,难以集中注意力,甚至会出现严重的焦虑或者抑郁,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
目前对于耳鸣的机理研究尚不十分明确。由于许多耳鸣个体可以将耳鸣明确定位到单侧或者双侧耳,因此最初众多学者认为耳鸣由于耳部病变导致。但是Silverstein等将听神经切断后发现患者仍然存在耳鸣,提示耳鸣可能不仅仅与内耳有关。后续研究发现,耳鸣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外周听觉信息传入异常后,导致频率分布重组及听觉皮质神经元异常放电,进而引起相关脑区结构和功能重塑。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部分学者也提出耳鸣可能是由于噪声消除机制缺陷导致[2]。此外,关于耳鸣相关的中枢研究还发现,耳鸣的功能改变不仅发生在听觉皮层区域,同时还发生在非听觉皮层区域,例如边缘系统、额叶、顶叶等[3]。但是迄今为止,关于耳鸣发生的具体机制仍未明确。
脑电是一种将电极置于头皮上记录脑电势的技术。常见的脑电信号大体可分为δ频段(2-3.5 Hz),θ频段(4-7.5 Hz),α频段(8-12Hz),β频段(13-30Hz)以及γ频段(>30Hz)。在耳鸣相关研究中,可以将频段划分的更加精细。α频段可分为α1(8-10 Hz)和α2(10-12 Hz),β频段可分为 β1(13-18 Hz),β2(18.5-21 Hz),β3(21.5-30 Hz)三个频段[4]。不同的脑电频段预示机体的不同精神状态。
1 耳鸣相关脑电特征
耳鸣对人体的影响,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层面的影响:特异性的感觉层面(即耳鸣响度)以及非特异性的情感层面(即焦虑、痛苦等)[5]。在特异性感觉层面,部分学者认为耳鸣响度的感知是由听觉皮层γ频段活动的增加导致,并且通过听觉区域和内侧颞区(如海马旁区)之间的连接调节[6]。另有部分研究结果认为耳鸣响度的感知与θ频段编码的去传入量有关。还有部分研究结果表明响度的感知与γ频段嵌套在θ频段上有关[7]。
关于非特异性的情感层面,部分学者认为耳鸣痛苦主要由背侧和亚属前扣带皮层,海马旁回以及内侧颞叶等结构组成的网络调节,主要发生于α频段,而这一现象同样与其他神经病变比如慢性疼痛相类似[8]。Ahn等人通过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耳鸣患者在前额部缺乏较强的δ相位/γ振幅耦合(这种耦合反映认知过程中的区域间交流),作者认为这一缺失现象反映了损伤的前额叶自上而下的抑制控制[9]。陈宇辰等学者也发现耳鸣相关痛苦是由于在α频段的额边缘回路之间功能连接减少导致[10]。Mohan等人基于有效性连接—格兰杰因果分析,分析310例耳鸣患者与256例健康人,发现额边缘系统和内侧颞区之间的信息传输强度和效率下降,他们认为这反应了整个耳鸣网络的重组,而额边缘系统和内侧颞区共同形成耳鸣网络的主要中枢。他们同时还发现耳鸣痛苦网络的核心表现为从左海马/海马旁回到亚属前扣带皮层的有向联系强度减弱[11]。
随着对脑电信息的深入挖掘,脑电微状态作为一种较新颖的脑电分析方式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脑电微状态是大脑自发意识认知活动的基础[12]。众多研究已经证明脑电微状态的时间序列特征在行为状态、人格类型以及神经精神障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13]。近年来,脑电微状态在耳鸣中的诊疗价值也逐渐体现。蔡跃新等人采用128导联的脑电检测发现耳鸣患者从微状态D向微状态B的转换较对照组减少,耳鸣的响度与微状态C的平均持续时间表现为正相关的关系[14]。他们进一步研究突发性感应神经性耳聋(SSNHL)伴耳鸣的患者与正常人的脑电微状态差异。SSNHL伴耳鸣的患者表现为微状态A的振幅、覆盖范围、平均持续时间、出现频率均减少,而微状态B呈现为增加的趋势[15]。因此,蔡跃新等人认为脑电微状态可以作为评判耳鸣的一项有意义的科学指标。Sven等学者同样有针对性地观察了耳鸣与慢性疼痛患者的脑电微状态,耳鸣患者微状态C主要涉及左侧前颞中回,以δ和γ频率活动为主,健康人主要涉及中央的后扣带皮层以及脑岛。作者认为左侧颞中回通过影响声音的检测和抑制来对耳鸣产生影响[16]。而以上所有结果均提示,脑电可作为一项比较客观的神经生理生物指标来评估耳鸣。
2 基于脑电的耳鸣相关因素研究
2.1 耳鸣与年龄
SONG JJ等人发现迟发型耳鸣患者(平均年龄52.3岁)与早发型耳鸣患者(平均年龄29岁)相比,脑电活动与功能连接更多集中在前扣带回和海马旁回。在迟发型耳鸣患者的亚组比较中,高痛苦组患者比低痛苦组患者在前扣带回表现为更多的β 1、β2和γ频率带活动;在早发型耳鸣患者亚组中,高痛苦组患者比低痛苦组患者在左侧额眶皮层和左侧腹外侧前额叶皮层表现为更多的δ/β以及γ频率带活动。作者认为即使耳鸣痛苦类型相似,不同发病年龄导致脑部区域激活的范围不完全相同,提示耳鸣的发病年龄可能也是对耳鸣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17]。
2.2 耳鸣与性别
Erlandsson等的研究发现,虽然耳鸣患者中性别之间痛苦等级无明显差异,但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容易受到耳鸣等负面情绪的影响[18]。基于此,Vanneste等人探究了不同性别耳鸣患者的大脑区域活动差异。结果发现女性与男性相比,在额眶皮质到额极区域的β1和β2频段活动存在差异。而在α频段,女性额眶皮层、岛叶、亚属前扣带皮层、海马旁区和听觉皮层之间的功能连接增强。这种增强的功能连接将听皮层活动与耳鸣诱发的情绪活动连接起来。从而使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耳鸣负面情绪的影响[19]。
2.3 耳鸣与听力损失
最初,众多学者一直致力研究耳鸣与听力损失的关系。伴有不同性质听力损失的耳鸣患者其耳鸣发生机制可能不完全相同。耳鸣患者伴有轻微听力损失的大脑反应主要表现为听觉皮层的活动,传入缺失的信息通过相邻的皮层区域补偿,表现为正常静息状态下皮层的α活动向θ活动转变,并且降低侧方抑制,形成γ带活动环。但是当听力损失较严重时,传入缺失的信息主要从海马旁区以θ-γ耦合的形式从听觉记忆中提取,即伴有重度听力损失的耳鸣患者表现为听觉皮层和海马旁区共同的活动[6]。
既然耳鸣与听力损失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为什么有些听力损失的患者不伴有耳鸣,而有些耳鸣患者没有听力损失呢?De Ridder等学者指出去传入机制可能是产生耳鸣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耳鸣的产生可能与自上而下的缺陷噪声消除机制有关[7]。正常情况下膝前部前扣带皮层以θ频段活动为主,激活自上而下的噪声消除机制后,膝前部前扣带皮层主要表现为α频段活动。当这种噪声消除机制受损后,膝前前扣带皮层主要表现为θ和γ频段的活动[20]。对于有听力损失而没有耳鸣的患者,患者可能通过调高自身噪声消除系统,即调高前扣带皮层的α频段活动抑制耳鸣的产生。而对于耳鸣不伴有听力损失的患者,有些学者指出某些形式的去通路/去传入并不会导致明显听力下降[21],部分耳蜗神经切断术却能有效的保留听力[7],即患者虽然传入通路受损,但并不表现为显著听力损失,却能造成耳鸣;另有部分学者则认为耳鸣的产生是由于噪声消除机制受损有关,导致前扣带回皮层持续以一种非激活的θ耦合γ频段活动,而这种活动导致听觉皮层γ活动增加,进而产生耳鸣[22]。
2.4 耳鸣与惊恐障碍
Pattyn等学者通过流行病学分析发现伴有惊恐障碍的患者耳鸣发生率是正常人的5倍以上[23],而耳鸣伴惊恐障碍的患者比单纯耳鸣患者有更高的痛苦指数。进一步分析发现耳鸣伴有惊恐障碍的患者比纯耳鸣患者在楔前叶(BA7)表现为更低的θ活性;而与健康人相比,在楔前叶/楔状叶延伸至后扣带皮层的后皮质部分(BA31)表现为更低的θ活性。同时耳鸣伴有惊恐障碍的患者与健康人相比,在α1频段上表现为背侧扣带回和其他三个兴趣点(脑岛,杏仁核,亚属前扣带回)之间的功能连接减少。虽然这一点在单纯耳鸣患者与对照组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而这可能与复杂的图像处理流程以及耳鸣人群的异质性有着密切的关系[24]。
3 基于脑电的耳鸣治疗
3.1 习服疗法
耳鸣的习服治疗是基于Jastreboff经典的神经生理学模型,Jastreboff认为耳鸣的产生是通过神经网络机制产生,而习服治疗的目的则是通过消除听觉、边缘和自主神经系统之间的功能连接来抑制耳鸣,并形成对耳鸣反应的习惯[25]。它将心理干预与疾病治疗结合起来,是当今国际上比较认可的一种新方法[26]。
Shin等学者发现耳鸣患者THI评分的改善情况与治疗前左岛叶、左前喙前扣带皮层和膝前部前扣带皮层的活动成正相关;耳鸣响度的改善情况与右侧听觉皮层和海马旁区的活动成负相关;耳鸣数值评分的改善情况与双侧前喙前扣带皮层和膝前部前扣带皮层的活动成正相关。作者认为前喙前扣带皮层和膝前部前扣带皮层区域是耳鸣消除机制的核心区域,并且短期习服治疗的的改善情况与上述几个区域的活动密切相关[27]。Lee等人则发现与习服治疗前相比,习服治疗后左侧初级和次级听觉皮层的γ频带能量减弱。而右侧岛叶和额眶皮质α1频带能量的变化与耳鸣痛苦的变化呈现为正相关。说明习服治疗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调节听觉系统与边缘和自主神经系统之间的功能连接来改善耳鸣相关的痛苦[28]。
3.2 神经反馈疗法
神经反馈治疗在1960年末开始出现,已经是癫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以及其他疾病的一种成熟的治疗方式。已经有许多研究者将神经反馈治疗应用在耳鸣治疗当中[29]。Crocetti等人发现提高听皮层的α活动并降低听皮层的δ活动,能显著改善耳鸣的相关症状。而γ频带的活动在耳鸣的神经反馈治疗中应用较少,主要原因是目前对γ活动的研究还不明确,它对耳鸣是一种促进或是抑制作用仍未可知[30]。
Vanneste等学者发现神经反馈治疗前后的后扣带皮层与海马旁区的有效性连接的改变与耳鸣患者痛苦降低的程度成正相关,提示神经反馈治疗是通过过影响不同脑区之间的联系而改善耳鸣,而并非通过影响兴趣区域神经元的活动达产生作用[31]。Dominik等人进一步改善神经反馈治疗方式,采取个性化疗法,选取患者特异性的α峰值频率作为奖赏频率,他们发现在经历了15周的个性化神经反馈治疗后,患者的耳鸣痛苦程度和耳鸣响度均有明显减轻。且脑电监测的α/δ的增加率与耳鸣痛苦程度的改善情况相关,主要与α频率的增加有关[32]。
3.3 经颅磁刺激和经颅随机噪声刺激
经颅磁刺激是通过放置在头皮上的线圈发出的短暂磁脉冲,刺激神经元,以达到缓解耳鸣的目的。Noh等人曾发现给与患者颞区与额区的联合经颅磁刺激的效果会优于仅仅给与额区的单独经颅磁刺激。但当时研究者仅仅是通过量表评分来进行评价。对具体机理并不明确[33]。后来研究者基于脑电发现耳鸣患者THI量表的改善情况与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楔状叶的功能连接呈负相关,而与楔状叶和扣带皮层的功能连接呈正相关[34]。而这些,研究者认为是造成联合治疗优于单独治疗组的原因。
经颅随机噪声刺激则是通过放置在头皮的表面电极,给与皮层低强度的随机电流进而调节皮层活动,电流水平在特定的平均强度附近呈正态分布。Moshsen等人首先验证经颅随机噪声刺激治疗耳鸣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同样发现前额联合听皮层复合刺激组的治疗效果优于单纯听皮层刺激组[35]。该研究者进一步研究两种不同的刺激方式对大脑电信号的影响程度。最终证明了额前区和听觉区复合刺激可以通过调节耳鸣患者的痛苦网络和多个耳鸣个中枢达到改善耳鸣的目的[4]。
3.4 迷走神经刺激
De Ridder等研究者发现迷走神经刺激音调匹配治疗能够改善患者的难治性耳鸣。Vanneste等人则在其基础上探究其改善耳鸣的潜在的神经机理,他们发现迷走神经刺激音调匹配治疗能够降低左侧听觉皮层的γ频段的同步化活动,增加α频段的同步化活动。治疗前后耳鸣响度的降低与γ频段的同步化程度的降低呈正相关。迷走神经刺激音调匹配治疗同时还能降低听觉皮层和与耳鸣相关的区域(包括扣带皮层)之间的相位相干性。这一结果提示迷走神经音调匹配治疗可能是通过直接调节神经元的可塑性来达到治疗耳鸣的目的[36]。
3.5 人工耳蜗植入
许多研究已经报道过耳蜗植入后能够改善耳鸣的病例。Mielczarek等学者试图通过给与患者耳蜗电刺激,探究其对耳鸣的影响。他们发现电刺激治疗后,患者的耳鸣情况明显改善。通过脑电检查,发现患者在左侧中央颞区和左额叶区域α频段的上下限显著增加。认为耳部电刺激可能通过改善皮层活动来达到改善耳鸣的效果[37]。但是Jae等学者选取4例单侧聋伴耳鸣的患者,比较人工耳蜗植入术前后的行为学评分以及定量脑电图。他们发现植入耳蜗在打开的情况下,与术前基线相比δ频带在右侧听皮层和眶额皮层的活动明显减少,并且δ/β2频带在听觉皮层和后扣带回皮层之间的连通性减少。而植入耳蜗开机与关机相比,右侧听觉皮层/额眶皮层表现为减少的δ频段活动,双侧听觉皮层、左侧额下皮层/额眶皮层表现为减少的γ频段。耳蜗植入术后会导致整体皮层活动和功能连通性下降。研究者认为导致皮层活动变化的主要因素还是由于传入通路的作用,而非单纯皮层可塑性。但是总体而言由于本研究样本量太少,所反映的数据可能比较片面[38]。
总之,脑电作为一种无创且具有高时间分辨率的研究工具被广泛应用于脑功能相关研究中,基于脑电的耳鸣相关检查治疗研究也日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有些学者对脑电在耳鸣诊疗过程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Pierzycki等学者曾经分析耳鸣患者12周前后的心理声学、社会心理学以及脑定的相关测量,发现脑电图功率谱与耳鸣症状学、生活质量和听力损失程度无关,认为全头皮脑电不能有效的反应耳鸣的客观情况[39]。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耳鸣本身异质性比较大,研究者们对耳鸣的性质、分类以及耳鸣的评价指标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另一方面基于耳鸣模型的脑电分析,究其根本是一种算法及数学模型的改良,因此在进行统计分析的过程中,所使用的算法、计算方式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尽相同。目前对于耳鸣脑电的诸多研究仍处于研究的初步阶段,未有完全明确的结论。相信随着对耳鸣研究的深入,随着耳鸣诊断的明确及数学模型的进一步优化,脑电会在耳鸣的诊断治疗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