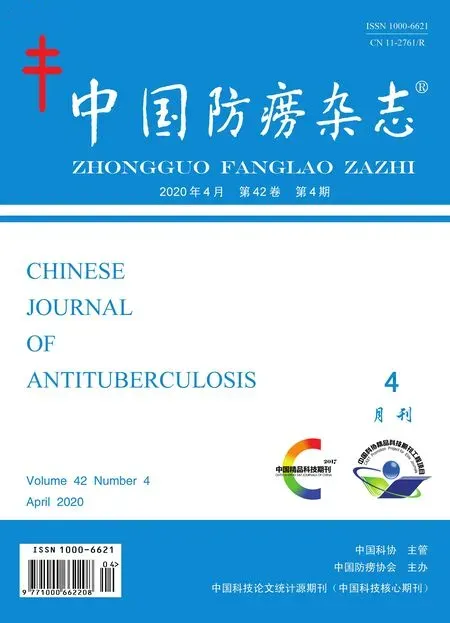“终止结核病”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刘健雄 钟球
继全球“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1991—2005年)和“遏制结核病策略”(2006—2015年)之后,WHO又于2014年提出了“终止结核病策略”(2016—2035年)[1]。其主要目标是:(1)相比2015年,结核病发病率下降90%(<10/10万)、死亡率下降95%;(2)没有因结核病而面临灾难性支出的家庭。但从2016年以来的实践结果看,人类要实现2035年终止结核病目标极具挑战[2-3]。我国作为30个结核病高负担、30个耐药结核病高负担和14个 TB/HIV高负担国家之一[2],加上仍是发展中人口大国的现实国情,更是任重而道远。但是,我国正在进行且取得重大战果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壮阔实践则向世界充分彰显了中国优势、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我们认为:只要人们能够直面下述一些重大问题,并着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问题解决方案,在中国实现“终止结核病”之梦并非难以企及。
一、促成政府主导、部门合作、医防协同和社会参与政策的高度融合
结核病为人类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已经举世公认,WHO历来的结核病控制策略和我国结核病控制策略[1-2,4]均将加强政府承诺列入首要位置,可以说没有政府主导或行政干预不力,结核病控制前景绝对不会向好。多年来业内多方呼吁的防治经费投入不足、2017年湖南省桃江县两所中学暴发严重结核病例聚集性疫情所折射出的部门合作状况、结核病定点医院等新型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建设的举步维艰、人们对结核病患者复杂心理与经济重负的漠不关心甚或视而不见等诸多重大问题,若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任何政府承诺、任何防治规划最终都只能是一纸空文。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运行模式为我们给出了通向成功的范例。结核病与其同属呼吸道传染病,控制路径必定有众多相通之处。当然,我们不可能照抄照搬这一模式,也不能奢望在短时间内提出解决问题的完美方案。但是要坚信: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地做好面向各级领导、面向医务人员、面向广大群众和面向结核病患者的全面结核病健康促进工作,新型中国结核病控制模式就一定会在不远的时间内呈现于祖国的大地。
二、强化疫情报告、疫情分析和分类指导机制
早在2005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建立了《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目前该系统已根据《中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工作指南(2008年版)》进行了优化。在其操作手册中就其目的的表述是:“以便能够更好地满足当前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需要,帮助各级结核病防治机构和各级医疗结构积极发现和治愈结核病患者,达到控制传染源、减少死亡和发病、保护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这个目的是否真正达到了?我们不能妄加评论,但以下事实应该能够窥斑见豹:2017年湖南省桃江县第四中学和桃江县职业中专学校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发生了多达90例确诊为结核病的学校结核病聚集性疫情,而在《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中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反映;自1997年起WHO每年都有全球结核病报告全面展示各成员国的结核病流行情况与控制状况,但于国内结核病流行疫情官方所能给出且公众所能查见的数据绝大多数只能是1979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结果;Khan等[5]根据我国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6—2013年结核病统计数据,发现约32%的结核病患者经历了超过3个月以上甚至长达1年的诊断延误,并归结为结核病流行疫情居高不下的主因。可见,《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并未充分发挥。Theron等[6]认为不基于数据进行决策不可能达到终止结核病的目标,我们高度认同。因此,笔者建议:(1)充分利用《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的大数据,向公众发布内容全面、适合国情的中国结核病年度报告;(2)充分利用结核病流行疫情分析数据,做好结核病健康促进中的领导开发工作;(3)充分利用各种流行病学新型技术手段,深层次挖掘和分析网报数据信息,实时总结不同地区结核病控制工作的成败得失,督促广大从业者不断改进工作。
三、提高现症结核病患者的发现水平
现症结核病患者能否被发现和被及时发现,是结核病控制中减少传染源存量、遏制传染源增量的决定性事件,因此,也成为所有结核病控制策略的核心要素。但是2019年WHO[2]全球结核病报告指出:估计2018年全球新发结核病患者约1000万例(发病率为132/10万),实际发现新发结核病患者726万例;中国的结核病患者发现水平为估计值的90%,但对耐多药结核病(MDR-TB)的发现却仅为估计值的21%、对0~14岁年龄组人群的结核病患者发现率则不足估计值的5%。这些数据加上Khan等[5]的研究结果,充分说明如何提高患者发现水平和提高早期发现水平均为我国目前结核病控制中的难题。从技术层面看,几十年来的“抗酸杆菌涂片检查+分枝杆菌培养+影像学检查+临床表征”的主体诊断模式在结核病诊断能力提升上仍未取得质的飞跃;虽然近几年来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7-8],但迄今为止结核病患者的病原学确诊率仍不及60%[2];各类影像学检查以其快速、易行的优势在结核病诊断中固然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较低的特异度一直困扰着临床诊疗[9-10]。从策略层面看,30多年来,我国主要采用因症就诊的被动发现方式,但其短板已经凸显;人们也早已认识到被动发现方式的局限,并探索患者主动发现方式[11-12]。对此,笔者建议:首先,准确理解结核病归口管理的真正内涵,充分发挥综合医疗机构的技术优势,在结核病患者发现上实现“高水平,广覆盖”;其次,加速医防合作的新型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的建设进程,强化医防主体责任落实和公共卫生政策配套;第三,从“法”的高度营造全人群参与结核病防治的社会氛围,稳步推进以社区、用人单位为基础的结核病患者主动发现、治疗管理与疫情监测工作。
四、及时、成功治疗结核病患者
结核病是人类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但归根结底需要在临床层面得以实现根本性的解决。然而,近几十年的具体实践又高度警示人们,结核病患者的成功治愈绝非单纯的临床诊疗问题。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毛泽东主席科学论断“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结核病治疗上,我们应该能够说“治疗方案确定之后,管治就是决定的因素”。在临床诊疗上,人们对各类结核病的治疗一直都在进行艰难的探索[13-15],结核病已由原来的“十痨九死”转变为85%的患者得以治愈[2],成就辉煌;但是MDR-TB、TB/HIV双重感染的产生与蔓延[16-17],又使患者缺医少药、不治者众[18-19],形势严峻。在治疗管理上,我国全面推行的医务人员直接面视下的短程化疗(DOTS)曾被WHO誉为全球结核病控制的典范,但也并非完美无缺[20-21];基于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目前人们在遵循DOTS中心要义的前提下对如何利用“互联网+”等新型工具以加强对结核病患者的治疗管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2-23]。面对如此复杂的临床实际,笔者总结实践经验建议如下:(1)破除行政区划壁垒,对所有结核病患者的诊断与治疗实行首诊单位及首诊单位所在地结核病防治机构负责制,并建立利于工作开展的经费拨付制度、职责考评与问责制度,这样即可化“流动人口”挑战于无形;(2)建立结核病强制性治疗法律制度,并出台相应的医疗保障、生活救助及疾病保险政策,这对于MDR-TB患者、TB/HIV双重感染患者来说尤其重要;(3)及时吸纳世界优秀科技成果,并尽快应用于我国临床实践,鼓励先行先试;(4)对于复杂、疑难、重症患者,倡导个体化的精准治疗和多学科的综合治疗,并在患者知情同意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治疗;(5)对结核病患者的治疗管理,在患者及其诊治医院必须同时接受当地结核病防治机构指导与监管的原则下,不必拘泥于具体的实现形式,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
五、提升研究工作创新性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效能
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科研项目多、研究论文多、学术专著多、成果转化少”的“怪圈”现象在我国已是司空见惯、备受诟病。近日来,针对现行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顽瘴痼疾,教育部、科技部开启了“破”的征程、确定了“立”的目标。目前,人们对于“破”总体争议不大,但至于如何“立”则疑虑不少。对科学研究成果究竟如何全面评价,笔者学识、阅历有限,提不出系统性的方案,但我们觉得可以从钱学森的“两弹一星”、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屠呦呦的青蒿素、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等获得全球认同的评价要素中得到启迪。我们更加希望看到“立”好之后,中国的广大科研工作者能有钱学森之“他们可以译登我在国内发表的文章”的自信与气度。具体论及结核病领域的科学研究,我们固然希望专业意义深远、足以引领世界水平的中国成果横空出世,如破解抗结核新疫苗、抗结核新药研发难题乃至成功突破。但从现实出发,我们则热望能有更多的应用与基础研究成果解决结核病控制工作面临的实际问题,如基于药理学与微生物学的新型治疗方案研究、基于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检测系统提高胸部X线摄影诊断性能的研究、应用分子影像学手段指导用药与疗效判断等。
六、结束语
WHO“终止结核病策略”提出了要做些什么,继之要求我们深入思考的就是如何去做[24],这绝无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方案[25],但最根本的有两点:精准施策,狠抓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