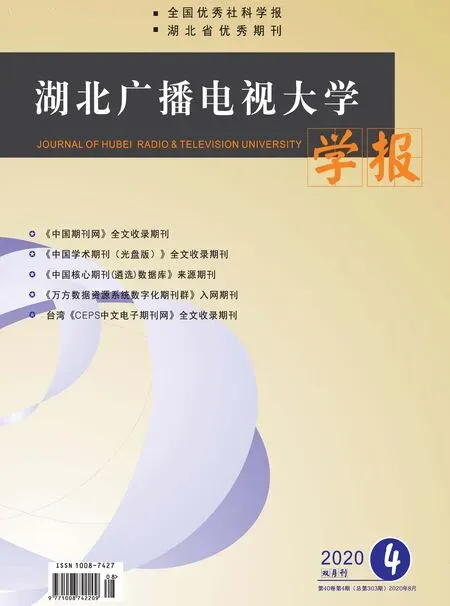《玛蒂尔达》中国巡演成功对我国戏剧文学外译与传播的启示
(重庆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2160)
2019年7月2日,由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制作的音乐剧《玛蒂尔达》(Matilda The Musical)在东莞玉兰大剧院首演,拉开了中国13个城市巡演的序幕,12月10日于上海完成了在中国的第100场演出,掀起了观剧高潮。这部改编自英国作家罗尔德·达尔同名小说的音乐剧,彻底征服了中国观众。该剧在剧本改编制作、巡演宣传推广、价值理念输出等方面,都凸显了艺术传播,尤其是戏剧传播的核心要素,值得我国戏剧文学外译和传播工作者学习借鉴。但目前对该剧成功“走出去”并“走进去”传播模式的研究尚未可见,本文拟从音乐剧《玛蒂尔达》中国巡演成功所体现的传播学特质及各要素间相互作用达成理想的传播效果探讨我国戏剧文学外译与传播的可操性原则。
一、《玛蒂尔达》中国巡演成功
《玛蒂尔达》每到一地都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掀起一场传播热潮。这部荣获有着戏剧界“奥斯卡”称誉的托尼奖的大作在中国的成功巡演绝非偶然,它是“佳著与佳作”的完美结合,既有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打底”,又由专业的戏剧表演团体精心打磨,再加上契合精神主题的外宣造势,“网红神剧”就此诞生。
(一)著名作家作品
儿童文学名著《玛蒂尔达》是英国作家罗尔德·达尔的力作。这位被誉为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的作家,终其一生创作出了《查理与巧克力工厂》《查理和大玻璃升降机》《詹姆斯与大仙桃》等优秀作品,先后斩获了世界奇幻文学大会奖等一系列世界文学界的知名奖项。《玛蒂尔达》(又有版本译为《小魔女》)[1],是罗尔德·达尔在1988年创作的童话小说,它以一位名为玛蒂尔达的女孩的视角,为无数读者揭开了一个奇幻又美妙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玛蒂尔达好像是带着上帝的眷顾出生,她是一位神童,不到5岁就博览群书。但玛蒂尔达又好像专门经受着上帝的考验,天资聪颖的她不得不忍受着庸俗、势利、反智的父母,以及学校里以恐吓、折磨小孩为乐趣的恶毒校长。就在与父母和校长斗智斗勇的过程中,玛蒂尔达带动蜜糖老师和其他同学们以正直勇敢去抗争复仇,最终收获了宝贵独立的自由和纯真永久的友谊。因此,《玛蒂尔达》采取的叙事视角和叙述立场,都十分适合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
(二)顶级制作团队
成功的戏剧作品,除了需要“佳著”外,更需要“佳作”。《玛蒂尔达》由成立于1961年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以下简称皇莎剧团)推出,该剧团是世界级的专业戏剧演出团队,有着庞大的演员规模、健全的组织体系、完美的演出水准,是英国乃至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剧团之一。《玛蒂尔达》的成功离不开顶级音乐制作团队。本剧的词曲由著名音乐鬼才蒂姆·明钦(Tim Minchin)一手包办,他为《玛蒂尔达》量身打造的音乐和歌词,优美而灵动、贴切又唯美,凸现其主旨和精神内核,效果惊艳。他也凭借该剧音乐斩获2013年托尼奖最佳词曲创作奖及2015年格莱美最佳音乐剧专辑奖。《玛蒂尔达》的舞台舞美设计完美呈现罗尔德·达尔的奇思妙想,拿下戏剧界最高奖项——奥利弗奖和托尼奖的最佳舞美设计奖,并在奥利弗奖中揽获全部舞美类奖项,创下2013年吉尼斯世界纪录。演员们有着极为专业的演出素养,百老汇版本的4位玛蒂尔达的扮演者还一起荣获托尼奖“杰出戏剧表现奖”。其他关键人物如川奇布校长(Miss Trunchbull)、蜜糖老师(Miss Honey)、布鲁斯(Bruce)等角色也是个性鲜明,表演精湛。
(三)专业宣传推广
在将原版音乐剧《玛蒂尔达》引入中国的过程中,英国皇莎剧团、中国保利文化集团和音乐剧品牌“七幕人生”携手进行了极为专业的策划和组织:
首先,巡演启动仪式在英国驻华大使馆官邸举行,通过官方机构的造势,传递给中国市场十分隆重而明确的讯息。英国驻华使馆公使、保利和“七幕人生”负责人、音乐剧《玛蒂尔达》制作人及巡演代表等嘉宾现身发布会现场,目的是“通过整个国际化团队的共同努力,巡演的(中国)观众们将获得和伦敦西区驻演版音乐剧一模一样的感受”[2]。在巡演中,中英双方通过多种渠道最大限度宣传《玛蒂尔达》。皇莎剧团在新浪微博上开通官方公号,采用中国网友熟悉的语言表达方式,及时宣传其巡演安排和剧目本身。“七幕人生”通过官媒、电台、微博、微信、剧场展板、海报、明信片、原声歌碟等形式全方位拓宽宣传路径。同时,巡演的城市都是中国各省市的中心城市,人口密度大、经济实力强,一般都是一定区域内的文化传播重镇,为剧团成功巡演奠定了坚实的受众群体和数量的基础。可见,《玛蒂尔达》这部剧在中国的成功巡演,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以一种全方位多元化的密集宣传“攻势”,传播效果十分显著。
(四)核心价值一致
音乐剧《玛蒂尔达》以生动、形象、感性的形式,将原著中展现的有关童年成长的难题、痛苦、不解、曲折以及克服困难之后的欣喜、收获、幸福,都一一铺陈在观众眼前。玛蒂尔达和蜜糖老师相互依靠,共同成长,当剧末最后的音乐响起,备受生活压迫的她们紧紧相拥,把一种敢于直面生活困难的勇气生动传递给了在场所有观众,正如歌词中反复唱到的“尽管你很弱小,也能拥有力量”。玛蒂尔达反抗的不仅仅是父母和校长具体人物的蔑视和迫害,还有以权威来定正误的惯性思维以及用地位而非正误来定权威的本末倒置的观念。该剧基于原著,丰富了剧中的人物形象,使整个故事更趋现代意义,其中展现的原生家庭、亲密关系、阅读与教育、压迫与反抗等议题是中西文化共性,激发观众强烈的共鸣。因此,该剧展现出反抗的勇气和力量是世界共识性的,令人思考话语权平等、读书有用论等,这些都与中国的核心价值趋同,也是这部音乐剧能够得到中国乃至全世界观众认可和点赞的根本原因。
二、《玛蒂尔达》成功传播的要素分析
跨文化传播从来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尤其是艺术传播,因为“艺术传播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系”[3]。传播学奠基者拉斯韦尔率先提出著名的“5W模式”[4],勾勒出传播学研究的范围和基本内容。理查德·布雷多克在此模式上提出7W传播模式[5],传播的主体、内容、媒介、受众、效果、情境和动机等七大要素的互动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后续学者针对文化艺术传播的相关研究都绕不开这一基本框架,因此,从传播学的本质特征以及影响传播效果的传播过程诸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等多方面深入分析音乐剧《玛蒂尔达》在中国巡演传播的成功具有启示作用。
(一)多元传播主体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传播主体是文化作品对外交流传播的能动载体,是推动文化传播的直接驱动因素。《玛蒂尔达》在中国巡演成功是职业化拓展化的传播主体共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
该剧的传播主体呈现出职业化和多元化的特征。首先是作品创作方,即《玛蒂尔达》原作者罗尔德·达尔及音乐剧的出品方皇莎剧团。作者的文学著作已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风行全球,推动了世界儿童文学的向前发展,同时也成为众多影视作品和音乐、诗歌等艺术作品的创作“母本”。而皇莎剧团是目前世界上的顶尖剧团之一。他们代表了作家作品和音乐剧创作的最高水准,体现出最高的职业素养,是该剧成功的基石。其次是皇莎剧团根据音乐剧表演的特质对在原作基础上进行的舞美设计,改编的关于蜜糖老师身世的情节,和脍炙人口的音乐曲目共同把音乐剧《玛蒂尔达》推向“近十年来最杰出的音乐剧”(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最后是该剧传播主题中最关键的一环,即全体演员,尤其是主演们专业生动投入的表演,其歌声、其对白、其神形、其姿态,完美演绎并引领观众深深陶醉于故事情节,如痴如醉,最大程度展现了传播主体的能动性和对传播效果的积极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从《玛蒂尔达》启动中国巡演,传播主体的范围进一步拓展。英国驻华大使馆,中国保利文化集团、中国音乐剧品牌“七幕人生”,包括活动赞助方上汽集团都成为不可或缺的传播主体,尤其是负责策划宣传中国巡演的“七幕人生”,其全方位密集型的推广活动确保了该音乐剧的传播成功。在该剧全国巡演过程中,中国戏剧界的权威人士、微博大V、微信公众号等“观后感”的及时推送,加上陆续观剧的广大群众引发的好评热潮和朋友圈状态更新,也自觉成为传播主体的一环,为该剧接下来的巡演积攒了超高的人气,对传播效果的作用不言而喻。
(二)传播内容核心思想的普世性
传播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传播效果,特别是在跨文化跨国界传播过程中,传播内容是否符合受众地域民众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心理习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传播活动的传播效果。
《玛蒂尔达》的传播内容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一部戏剧是不是能够打动人心,要看其能否瞄准焦点问题进行深入阐发。该剧集中从孩子的内心感受、外部环境、成长境遇、心理变化等多个视角去描写儿童成长中遭遇“不被渴求、谩骂歧视”进而“奋起抗争、互相激励”最后“幸福相拥”的故事,成长困惑、教育与环境、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等内容在舞台表演中一一展现,明晰而动情。因此,传播内容的聚焦指向,能够让文艺作品可以用更多的艺术表现手法去多视角展现,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文艺作品的传播效果。
《玛蒂尔达》的传播内容萃取自人类文化的共同特质,其核心思想的普世价值观催生良好的共情效应。所谓共情,就是让在场的观众能够全身心融入剧情发展,情绪跟随剧情的变化而起伏。产生共情效应,就说明一部戏剧作品现场的演出是基本成功的。该剧对渲染共情效应的设计特别用心:从舞台设计到舞美打造,一开场就让观众置身于小女孩玛蒂尔达独特而丰富的内心世界,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唱演专业醇熟,一系列分场景的演唱曲目,如“School Song” (学校“赞”歌)、“My House”(我的家)、“This Little Girl”(这个小女孩)、 “When I Grow Up”(当我长大)、“Revolting Children”(革命,小孩!)等完美诠释了跌宕起伏的剧情,优美悦耳又烘托主题;剧末台上演员向台下观众抛送纸飞机的场景,更能让人感受到玛蒂尔达成长后走向幸福生活的内心喜悦。这些细节的打磨吸引了更多的观众,二刷三刷该剧者络绎不绝。因此,满足传播受众期待和需求的传播内容将获得高认同度,是传播致效的重要因素。
(三)多元传播媒介融合推广
传播媒介是在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之间接收双方沟通交流信息的渠道和路径。《玛蒂尔达》在中国巡演成功是网络媒介、电子媒介和印刷媒介等多元化传播路径的融合发力的成果。
该剧在巡演伊始,皇莎剧团就适时开通官方微博,不断推出有关《玛蒂尔达》巡演的讯息以及此前表演的剧照图片,赚足了网友的眼球;随后“七幕人生”也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让该剧相关信息持续发酵,据新浪微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20日,由帐号“七幕人生音乐剧”作为主持人发起讨论的话题“音乐剧玛蒂尔达”,阅读总量已达6143.8万,发帖讨论数量3.2万,参与原创发帖人数3932人,数据显示出较强的传播热度和广泛度。除此以外,每到一个城市,主演们就会参与当地电台电视等访谈节目,进一步拓宽传播渠道,所以,广播、报刊、互联网、手机等现代新兴传播媒体为该剧的传播造势增色。当然,最直接有效的传播媒介还是舞台的现场表演。观众们被演员们精湛激情的演出所折服,自发在小女孩玛蒂尔达经典“叉腰”姿势的巨幅海报和展厅设计前驻足欣赏,购买原版音乐CD、表演剧照等。同时,该剧的舞台设计也极具创造性和想象力,既有舞美灯光营造的神秘感和空间衍生感,又通过各类道具的轮换转场和拼接对剧情形成强大的烘托,让观众从走进剧场的那一刻开始,就被整体的舞台效果带进了玛蒂尔达的世界里,开始了一段两小时的奇妙体验历程。这种舞台表演与新兴社交媒体的相互配合、共向发力,既有效地克服了戏剧作为传统传播媒介在当下面临的受众面窄、影响范围小等不足,又充分借助了社交媒体“瞬时、量级”传播的巨大威力,让该剧的传播效果超越了剧场的物理空间。
(四)传播效果关照下的传播受众和传播环境考量
艺术的传播应当将其效果放到关键位置,因为“艺术的目的在于它的传播,而传播的达成则有赖于传播者与受众的情感同一”[3],而传播效果是通过传播受众体现出来的。音乐剧《玛蒂尔达》在中国巡演整个过程中都主动寻求受众的共识,为了受众能理解、体会该剧的意思表达及精神实质,不但演出现场的大屏幕提供了与英文台词唱段一一对应的中文,还在故事结尾处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出现了一句中文台词,体现了艺术传播特有的娱乐性和“同理心”。而且该剧根据受众心理特点和生活方式进行积极创新,从剧本的编撰开始,就大胆删繁就简、突出主线进行剧本的二次创作,力争在两小时的表演时长内,将原著的逻辑脉络、故事主线、人物特质、精神内核等关键元素全部表达到位。该剧在内容上所呈现的丰富内涵如家庭观、读书有用论、女性的角色定位与独立思想、抗争意识等引发了观众的广泛讨论与深入思考,而正义、勇敢和友爱这样的价值观也是中国人所讴歌追求的核心价值观,因此传播受众能形成强烈的“认同感”,自觉自发为该剧喝彩推广,甚至有观众10刷该剧,传播效果立竿见影。
该剧的传播也依赖于良好的传播环境,包括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等,传播环境与传播效果具有重要关联。目前大国间虽有摩擦与纷争,但总体态势是和平发展,互通有无,为文化艺术传播构建了较宽松的政治环境。该剧在中国巡演前,已经通过原著小说与电影版《玛蒂尔达》积累了一定的人气。皇莎剧团的音乐剧版《玛蒂尔达》自2011年在伦敦西区首演就取得巨大成功,并持续演出至今,英美主流媒体均给予最高评价。除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和美国《时代周刊》,也被《纽约时报》称为“从古至今英国创造的最令人满意、最颠覆性的音乐剧”,并斩获英国戏剧最高奖奥利弗奖7项大奖以及美国戏剧托尼奖5项大奖。随着国民经济总量大幅提高,我国兴建和改建的国内剧院总数已超过2000余家[6],几乎每一个省会城市都有大型剧院。普通观众有意愿且有能力去剧院观赏各类文艺演出,这些都为该剧在中国的传播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不可忽视的是,以戏剧为媒介的传播形式,对其传播效果的评判也逐渐在从单一的经济因素走向综合甚至更为宏观的文化影响力因素层面。音乐剧《玛蒂尔达》在中国广大观众心中成功种下了一颗对西方经典戏剧以及西方儿童文学所向往喜爱的“种子”。随着这颗“种子”的生根发芽,中国观众群体特别是以孩子们为主体的年轻一代观众群体,一定会对西方戏剧和文学等各类文化载体产生更大的好奇心和更易接近的心理认知,达到预期传播效果,符合传播学中“使用—满足模式”,即个人需求与动机→对传播媒介的期待或选择其他活动→使用类型→满足→反馈。[7]
综上,音乐剧《玛蒂尔达》中国巡演是跨文化传播成功的典范,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等主要因素分析,对我国戏剧文学外译和传播有巨大的理论启示和借鉴作用。
三、对我国戏剧文学外译与传播的启示
(一)我国戏剧文学外译与传播
作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中国戏剧源远流长,曲目繁多,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瑰宝。改革开放以来,除传统的戏曲艺术,话剧、音乐剧、舞蹈剧场、实验演出等多元戏剧形式均在中国迅速发展。我国戏剧对外传播的历史由来已久, 18世纪上半叶,《赵氏孤儿》等元杂剧被译介到欧洲,经过19世纪中国戏曲典籍的传播,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京剧大师梅兰芳分赴日本、美国、苏联、欧洲等主要国家进行京剧表演与国外戏剧考察,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京剧热。
近年来,我国戏剧也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频频现身于国际一流剧院艺术节,如英国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德国柏林艺术节、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等。中国戏剧与时俱进, “有意识地利用科技手段创新讲述中国文化与民族艺术,得到国际戏剧界的认可”[8]。一方面,我们为中国戏剧“走出去”欣喜不已;但另一方面,我国戏剧外译与传播的步伐显得“步履蹒跚”,离“走进去”的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有些学者已注意到这一困境,并开展了相关研究。林一、马萱[9]回顾了中国戏曲从古至今的对外传播历史,并列举大量对外交流演出中西合作的实例证明西方民众对我国戏曲正形成新的兴趣高点。张安华[10]和朱斌[11]都采用经典的“5W”模式提出我国戏剧文学对外传播策略,但落实到外译和传播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的操作缺乏更实际有效的理论指导。因此,通过分析音乐剧《玛蒂尔达》在中国的巡演经验有助于探索我国戏剧文学的外译模式和对外传播原则。
(二)我国戏剧文学的外译与传播原则
中国戏剧文学“走出去”不是指仅把中国戏剧文学作品翻译出去,而更重要也更难的是中国戏剧文学译著能在传播对象国通过文本或舞台表演产生影响力,得到传播受众的认同和接受。如何较好地穿越族群种类和文化差异的隔阂去达到彼此的认同,一直以来都是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12]。下面笔者将从传播学视角以音乐剧《玛蒂尔达》的译传实践为基础,提出中国戏剧文学的外译与传播原则。
1.传播效果优先原则
艺术实现价值的本质是达到预期传播效果,音乐剧《玛蒂尔达》从作品、剧团、演员、推广、译者、剧场的遴选都以传播效果为依归,充分调动能提升该剧传播效果的一切要素。即剧团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分析传播环境、研究传播受众、借助传播媒介等,使该剧能在传播受众国演出顺利,取得高认同度,并最终带来预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效益。具体来说,有以下措施:
首先,要着力打造演员个体的传播主体身份。京剧大师梅兰芳在西方的演出、张火丁访美文化活动,昆曲的青春版《牡丹亭》和《临川四梦》在海外的演出交流等都是典型的外译传播成功案例。演出、访谈、讲学等形式让传播受众近距离了解大师们的风采,领略中国戏剧的精美绝伦;各大媒体的专栏介绍和演出广告特别注意挖掘演员的个人魅力,打造明星演员,提升票房号召力。因此,西方民众加深了对演员个体的认识,形成“明星效应”,自然起到较好的传播效果。近年来,张火丁、俞玖林等各个剧种的“名角儿”与时俱进,纷纷成立个人工作室,这是适应市场化,吸引国内外受众的有效举措。
其次,戏剧的外传仅仅依靠个人魅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积极拓展对外传播主体,不能单纯地以政府机构、官方组织和专业团体为主体,而是应更好地借助和依靠多元主体的作用。除剧目制作团队,国内包括政府相关文化机构,各地兄弟剧团、剧本翻译、评论家等,还有来华留学的外国学生;国外主要涉及中国驻各国大使馆、我国新闻机构在境外设立的记者站、孔子学院等相关文化机构、各大剧场、主流媒体、友好大学、海外华侨等,还有国外戏曲爱好者。多元主体联动不但能扩散传播速度,还能拓宽传播渠道。上海昆剧团不但将《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梦记》四部大戏推向国际舞台,还将折子戏、实验新作和戏曲电影等不同类型的作品推送到海外高校、一流剧院、顶尖艺术节的舞台,丰富“走出去”的作品与路径,擦亮“百戏之师”的国际标识度。[13]
最后,要实现我国戏剧外传效果最优化,还得积极寻求有效传播渠道。音乐剧《玛蒂尔达》除了传统的剧场舞台,还充分运用了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是除剧场演出外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具有去中心化、数字化和十分显著的多媒体特征,互动性极强[14]。我国戏剧文学外传要利用现代化传播工具和技术手段,要特别充分地利用以网络平台为载体进行信息和文化传播的“第五媒体”——新媒体。相对于演出、展览广播、出版、电影、电视、论坛等传统意义上的传播方式,数字报刊、数字广电、手机短信、车载电视、幕墙广告、触摸媒体等新媒体,具有无可比拟的传播速度和功效。尤其值得借鉴的是,通过将戏剧元素融入在国际享有盛名的影视作品能取得出其不意的传播效果,驱动国外受众对中国戏剧的好奇心,心生美感和向往,如电影《霸王别姬》中穿插了大量的京剧元素;《青蛇》中白素贞和小青穿着京剧青衣的服饰;《卧虎藏龙》中的武场音乐;《花样年华》中穿插了多种戏曲唱段如京剧、粤剧、越剧、评弹等作为背景音。
2.传播内容优化原则
传播内容是实现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传达的信息是传播受众直接接触和理解的要素。音乐剧《玛蒂尔达》的传播内容富有意义,能很好满足传播受众的期待和需求,获得高认同度。以此为鉴,我国戏剧的外传必须坚持传播内容优化原则,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一是以剧团编创、演员、剧目推广方等为主的多元传播主体要充分发挥“守门人”作用,对传播内容把关,主要是对曲目内容、时长、舞美设计、宣传材料等把关。我国传统戏剧可以用慢节奏、多场次、长时间的形式来从头到尾充分阐释经典剧目的完整内容,但现代社会的民众却没有办法“忍受”如此漫长的“文化休闲”,曾有欧洲观众抱怨,看昆曲的文戏“有些慢”。事实证明,由中外优秀剧院携手编创、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且寓教于乐、互动性强的曲目更容易获得传播受众青睐。我国戏剧外传的几个经典案例都充分说明这一点:1930年梅兰芳访美期间,每场演出均有女司仪现场介绍中国戏剧传统,演出的宣传材料均由名家撰文,如胡适、齐如山和梁社乾,他表演的戏剧和舞蹈呈现了京剧中青衣和旦角的最高境界;2007年,昆曲《牡丹亭》在比利时演出,角色的身段情感引人入胜,所体现的细腻、典雅、高贵,以及精美绝伦的舞台背景与服装造就了“绝佳的视觉效果”;2013年,中国国家话剧院与苏格兰国家剧院联合出品的话剧《青蛇》,以全新的视角解说中国传统神话“白蛇传”的故事,由德国和英国设计的舞美灯光采用三面高墙、多台投影等技术手段,带观众领略了独特的江南风情与气韵。这些举措都体现出传播主体对传播内容方方面面的优化以实现最佳效果。
二是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建立“戏剧文学外译模式”,推动我国戏剧文学外译与传播齐头并进。这是一个长期工程,需多方持续努力,我国学者近年来展开了相关研究。孟伟根[15]基于西方主要戏剧翻译研究者Patrice Pavis 和Susan Bassnett等的观点,聚焦戏剧翻译争论的核心问题,即“可表演性”和“可读性”。吕世生[16]指出戏剧文本的翻译要基于目标语戏剧系统,对原文本进行翻译改写。戏剧大家英若诚就是坚持“可表演性”和针对舞台表演对原戏剧进行改写的典范。杨祎辰[17]通过梳理近年来国内外戏剧翻演过程为对象的描述性研究,个案研究向经典剧目和重大演出事件倾斜,《赵氏孤儿》《贵妃醉酒》《茶馆》《西厢记》《牡丹亭》等经典剧目在海外的成功演出就充分阐释了这一观点。
总体而言,我国戏剧文学要实现成功外传,首先要遴选戏剧文学作品的译者。朱斌通过分析《牡丹亭》的各类译本,提出“中国戏剧的译介主体最好包含在目标国享有盛誉或具有权威地位的译者”,因此,华裔学者和国外知名汉学家是译介效果的最佳人选,因为如果译者是“自己人”且可信度高,在种族、文化背景、价值观和宗教信仰与传播受众一致或相似,传播受众更容易接受传播主体传播的信息[18],而且此类译者更能针对国外欣赏中国戏剧的受众甄选演出曲目,对曲目内容进行合理增删或调整,并以此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
其次,引入“戏剧文学代理人机制”,演出前基于对受众的分析负责寻找合适的译者,有针对性地对曲目译文进行调整。演出中负责宣传资料、展览、演员介绍、演出字幕等翻译工作。演出后要及时调查受众满意度,根据反馈意见进行适度调整。这是目前较为薄弱但又极为迫切的一环,需要国家政策、官方机构、剧团等多方合力,共同促成。最后,加强中外合作,通过孔子学院和来华留学生挖掘热爱中国戏剧的大学生团体,培养戏剧外译和传播的人才资源。
3.传播受众导向原则
外宣翻译的核心在于给目标受众以引导。凡传播效果上乘的精品力作,无一不蕴含了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双向交流互动。我们的戏剧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也必须把受众作为重要因素考虑进去,深刻研究如何对受众形成充分的影响和文化冲击,让受众在欣赏作品的同时不知不觉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浸润和熏染。音乐剧《玛蒂尔达》和我国戏剧外传成功的案例充分体现了传播受众导向原则的重要性。坚持传播受众导向原则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重视传播受众“意见领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传播学的“两级传播”理论指出,观念的流向呈现出“意见领袖—一般受众”的规律[19]。对我国戏剧外传而言,将剧本和首演向政要、明星、主流媒体、戏剧评论家等意见领袖倾斜,再通过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将作品的口碑传递到一般受众,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般传播受众的观剧决定,甚至可能影响其对剧作的认同,意见领袖的观点对我国戏剧外传的宣传推广效果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梅兰芳72天访美就是齐如山这个实际的“戏剧代理人”通过“意见领袖”一手促成并大获成功的,其中包括美国公使芮恩施、纽约剧作家哈布钦斯、旧金山詹姆斯·罗夫、卓别林等政要名流,更离不开美国主流媒体如纽约《时代》《世界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等的大力推介。近年来,我国戏剧“走出去”亦是如此,通过参加国际一流剧院艺术节、文化节,重视与各国戏剧顾问的交流沟通,追踪媒体报道,积极捕捉“意见领袖”的评价,努力提升国际标识度。
二是契合传播受众的需求。传播受众对传播信息的接收是有选择的,也是有记忆的。传播内容必须契合其需求并适时调整优化传播内容,才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进而打动受众。比如,梅兰芳在美演出中根据观众的建议取消了检场的京剧传统,虽然“丢了一项传统仪式”,但收获了观众的认可和对京剧的热爱。2007年,昆曲《1699·桃花扇》瑞士的演出,从海报宣传、舞美灯光设计,还有英文翻译等,都是匠心独运地为海外演出所量身打造。2017年,上海昆剧团在希腊国家歌剧院大受欢迎,其成功点在于选择了《雷峰塔》这部文武戏码兼具的经典折子戏而非《牡丹亭》。2018年,昆剧《临川四梦》四台大戏赴欧洲巡演,上海昆剧团提前“预热暖场”,先让欧洲观众对昆曲常识有了基本认知后,再通过多种字幕、图片展览等形式让观众可以进行多渠道的信息接收,最终达到了观众能够较好地欣赏昆曲的传播效果。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西合璧式的表演形式收到受众青睐。如川剧《凤仪亭》2004年在荷兰演出,将原生态的川剧“高腔”和西方交响乐融合,惊艳全场。将中国戏曲元素应用到国外影视作品或戏剧表演中也值得提倡,如德国电影《阿纳托米·泰特斯》、中法戏剧《丑角中国行》、中意喜剧《破产》,还有京剧版《夜莺》《悲惨世界》等。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并要求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跨文化传播从来就不是一件易事,“即便是在本国家喻户晓之事,对他国民众而言也不啻于难解天书”[20]。我国戏剧文学的外译与传播历史既有成功的典型案例,也有“带着作品乘兴而出,市场遇冷扫兴而回”的深刻教训,更面临多元文化冲击下的新的挑战和压力。我们要以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方向,以音乐剧《玛蒂尔达》在世界的成功传播为参照,以传播学理论为实践指引,坚持传播效果优先,发挥多元传播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根据目标受众要求优化传播内容,与时俱进利用传播媒介,实现传播效益最大化。因此,我们要在加强中外戏剧交流的基础上,既善于“借船出海”,在西方戏剧、影视等创作中融入更多的中国戏曲元素,又坚持“为我所用”,由国内相关机构邀请国外名导合作排演中国故事,中外优秀剧院携手打造更多在世界范围内脍炙人口的中国题材戏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