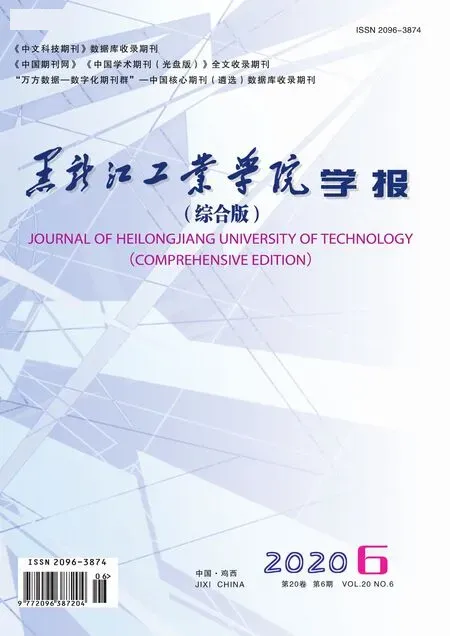浅谈迟子建的小说创作与东北民俗文化
张思远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民俗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作家的审美观和创作观,也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文化动力之一。“民俗文化是评价一个作家及其作品是否具有永恒魅力的重要价值标准,甚至影响到特定区域读者对其接受状态。”[1]如沈从文作品中对湘西民俗文化的融入,使他以鲜明的区域特征和人文气质区别于其他同代作家。老舍、张爱玲、师陀等人的作品之所以能自成一派,独具风格,也和他们小说中的民俗文化书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作家对于特定区域的民俗了解程度和融汇能力直接影响到其作品的艺术价值。民俗元素在文学作品中大多以具体的象征事物表现出来,比如饺子、汤圆、腊八粥等等。此时的民俗事象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着作家的思想情感。作家在表达和表现的过程中把主观情感与思想意识寄托在这些民俗符号中,并通过具体的民俗事象传达出作家内心的情感信息。迟子建笔下东北民风民俗便在她的精心安排和演绎中,使平民百姓生活中的民俗事象通过适当的表达样式实现了其整体精神世界和情感结构形式的最终表达。她也通过对民俗文化书写传达着自己的审美理想和价值判断。
一、民俗文化的多维呈现
民俗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缩影,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同时它也是渗透物质和文化的精神再现。民俗事象复杂多样,大致可以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几大类。民俗是在民间发生并成长起来的,因此无论是平民还是作家都无法逃遁于民俗文化的笼罩。迟子建作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她在构建其艺术世界时也不自觉地将她经历过的民俗文化灌注其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世界。
1.生态民俗
在迟子建的文学创作中,生态民俗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对象。迟子建对东北地区的自然风景以及生态习俗的描写非常丰富,特别很多民间流传的关于动物的传说。如在《伪满洲国》《白雪乌鸦》《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提到的狐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于动物禁忌、动物保护神的描写,如对黑熊、驯鹿的崇拜。在其小说《越过云层的晴朗》《候鸟的勇敢》《一匹马两个人》中,动物甚至成为了小说的主人公和重点描写对象,动物和人共同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共同反映出了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她小说中这些生态民俗文化显然受到了东北地区生态民俗的深远影响,除此之外她实际上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二者结合共同体现出了作家深刻且富有人道主义的思想。迟子建小说中蕴含的生态民俗不仅传达出了她对当代社会的忧思,同时也反映着她本身具有的复杂的文化心态。在迟子建笔下,苍茫的北国风光有着鲜明的民俗指向,在关注她的作品的同时,可以将民俗和自然二者之间的界限淡化。在一定程度上将她笔下的自然书写看成是展示民俗文化的另类表达,自然环境也成为了民俗意识的载体。正是迟子建饱含着温情的对东北自然风光的描写,才使民俗文化在她的文本中实现了症候式的表达。
2.物质民俗
物质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包括饮食、服饰、出行以及住所等方面。在以往的现代作家或者当代作家中,并没有一位作家如迟子建一样将东北的物质民俗文化描写得如此全面。迟子建笔下对于衣食住行的描写,显示出了鲜明浓郁的东北文化民俗特征。在服饰方面,她对东北地区服饰描写最为全面的应是《伪满洲国》,其中对服饰颜色款式描写多达77处。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在对鄂温克人的嫁衣进行的详细的描绘,伊芙琳为金得和杰夫琳娜做的嫁衣:“上身紧,下摆宽的长裙,半月形的领子,马蹄袖,腰间镶着翠绿的横道,非常漂亮。”[2]迟子建对服饰的描写不仅揭示了地域特色,同时又暗示出了人物的身份、性别、年龄以及生存际遇。迟子建对北方的吃食也描写非常丰富,土豆、酸菜、玉米饼、腊八粥等具有浓郁东北风味的吃食在她笔下比比皆是。在《故乡的吃食》中,她提到了在立春这天北方人吃春饼、啃萝卜,腊八节的腊八粥、年前宰猪等习俗,她对这些习俗的描写不仅写出了东北民俗的魅力,同时也写出了北方人民对传统民俗节日的热爱以及凝聚在东北人心中的亘古不变的文化情结。迟子建对东北的民居也进行了详细的描绘,如在《房屋杂谈》中,详细描绘了东北传统房屋的特点,《原始风景》《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对木刻楞这一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房屋进行了细致地描绘,这些用木头垒起来的高大房屋坐落在北国苍茫的土地上,显出了一种沉静庄重之美,迟子建在这些具有民俗特色的房屋中阐释着对生活和美的理解。
3.社交民俗
迟子建的作品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社交民俗文化。由于迟子建写作重心大多在农村,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有着很多东北农村社会的社交民俗文化。这种社交民俗文化主要受到了东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移民和游牧生存经营方式的影响。社交民俗文化的融入使迟子建的小说体现出来的主要特征便是民间色彩浓厚,情感色彩突出并且人情味浓厚,使小说呈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具有东北人情味的朴拙的人性之美。她在《没有夏天了》中写到如果哪家出了丧事,无论谁家都要去,尽管是平时有过仇怨的,也需要去祭奠亡灵。《守灵人不说话》中,也写到如有人家办丧事,村里的人需要轮流守灵。《逝川》中:“阿甲渔村有一种传说,泪鱼下来的时候,如果哪户没有捕到它,一无所获,那么这家主人就会遭灾。”[3]但是吉喜为了给爱莲接生放弃了捕捉“泪鱼”的最佳时机。阿甲渔村的村民也默默地在吉喜的盆中放满了“泪鱼”。《群山之巅》中,为了帮助傅家甸度过鼠疫的难关,傅百川、于晴秀等人自发制作口罩,王春申则免费帮助运输死尸,喜岁和周耀祖为了救助火车上的难民甚至被感染致死。互相帮助和相互协作是东北地区社交民俗文化的重要特征,迟子建的文学作品中书写的这种互帮互助社交民俗文化深深地体现了真正的东北精神。
二、多重民俗叙事视角
不同的叙述视角在作品中有不同的作用,叙述视角的变化会取得不同的审美效果,也会给读者带来不同的审美体验。通过考察迟子建作品中的民俗元素的措置、构成及民俗文化的表现角度,发现迟子建作品中对民俗采取了全景叙事、民俗事象叙事以及民俗民性叙事三个叙事视角。叙事视角的选用直接反映出了作家的创作姿态和立场,迟子建通过不同的民俗叙事角度展现了东北复杂多变的文化心态和具有鲜明东北地域特色的气质精神。
1.全景式叙事
迟子建在小说《白雪乌鸦》《伪满洲国》中在人文、自然、历史、政治多种背景下对东北民俗文化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白雪乌鸦》中迟子建在交代傅家甸名字的由来时,直接展现了傅家甸的城镇街道、酒馆、商铺、教堂、剧院等一系列建筑民俗文化,同时也交代了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又在每一个小节中对傅家甸的节日民俗、社交民俗、民间语言、民间游艺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描绘。如在小说第十八节《灶神》中详细地描绘了在祭灶神这天傅家甸每一家都要烀肉、炸丸子和剁饺子馅的习俗。第四节《烧锅》中提到了秦八碗烧的烈酒,这酒浓郁热烈,傅家甸的人都热爱这带有着浓郁酒香具有东北特色的烈酒。具有浓郁东北风味的方言的运用,也使人深刻地感受到了特定时代下东北小城的风土人情。尤其是在这部作品中,迟子建全面地展现了在特定时代下多民族多民俗文化融合交汇的特征。《伪满洲国》可以被称之为是一部“地方史”,这部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是“史”,是因为迟子建对伪满洲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的全方位的介绍,当然对东北文化习俗也进行了全景式地描绘。她在写平顶山屠杀时对东北传统房屋进行了介绍,房屋周围围着的大蒜、玉米、农具带着浓浓的东北风味。她在小说中也提及萨满跳神、丧礼婚嫁、社交礼仪等风俗习俗。正是她在这部小说中对风俗民俗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才使小说的生活细部肌理非常贴近当时东北地区的生活语境,从而使这部小说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
2.民俗事象叙事
五四时期很多乡土作家将民俗事象作为小说主要的叙事线索和结构框架,很多民俗事象如冥婚、冲喜、典妻虽具有地方特色,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现状,很多作家并不偏重于表现这些民俗事象所具有的区域文化特征,而是将写作中心放在暴露封建社会的黑暗上。文学史发展到当代,迟子建虽也使用民俗事象,但是却不将完整的民俗事象作为写作的主要线索,她笔下不同的民俗事象有着不同的功能。各种民俗事象穿插在她的作品中,成为她民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迟子建通过对东北地区各种民俗事象的点染和铺陈,营造出独具东北风味的民俗氛围,从而表现出东北地区的民间风物和民情事态。在此类叙事中,东北地区平民百姓的情感、心理和文化心态等成为了迟子建作品表现的重要内容。迟子建笔下的民俗事象,在适当的时候便隐退到了文本深处成为了一种铺陈和点染民俗氛围的叙事工具。她笔下民俗叙事多采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民俗元素通过这种方式发挥着它的叙事功能。如在《白雪乌鸦》中翟桂芳被纪永和典妻的情节,实际上写的是在特定时代下以纪永和为代表的市侩小人,他们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甚至出卖尊严和灵魂,侧面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迟子建的作品中独具东北风味的民俗事象比比皆是,诸多民俗事象的描写使她的作品与东北地区的历史、文化、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迟子建的作品并不宏大壮阔,她通过民俗事象这一独特的叙事视角使我们从平民的角度了解东北地区独特的民情特质,这正是迟子建作品的伟大之处。
3.民情民性叙事
这里所言的民情民性叙事指的是迟子建作品中对民生事态和民性民情的整体氛围的营造,正是因为这些民情民性和民生事态我们是不可感和无法触摸的,所以我们应该在整体上把握迟子建作品中的东北民俗文化的意义。迟子建的作品毕竟不是纯民俗作品,因此她对于民俗事象的关注并不如民俗作品一般系统且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她在作品中更多呈现的是具有鲜明的东北民间气息的人和物,在神韵上展现特定时代中各色人物的民间气质和生存际遇,因此迟子建小说中的民俗叙事明显指向的是“人”而不是单单止于对“俗”的关注。《伪满洲国》《群山之巅》《白雪乌鸦》《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以及在短篇小说《逝川》《葬礼》《守灵人没有眼泪》等作品中,迟子建对东北地区的民俗民性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她在对民情民性描写的过程中关注着人物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东北人民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生活态度在迟子建的民情民性叙事中直接显现出来。如在长篇小说《伪满洲国》中,她通过对动荡年代东北地区民间的民情民性的描写,塑造出了一群无所谓抗争也无所谓附逆的人,也塑造出了面对生活苦难隐忍坚强的人,呈现出了当时东北地区的民生众态。迟子建的这种叙事方式一方面展现出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具有鲜明的生活气息。另一方面展现出了人生事相,表现出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和人的生命意识,具有深刻的意义和内涵。
三、民俗化倾向成因初探
迟子建自八十年代步入文坛,至今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在当代文学史中,迟子建不属于任何一个创作流派。三十年来她始终坚持将自己的创作支点深深地扎根于东北这片黑土之中,坚持描绘东北地区的生存状态,使她的作品呈现出了不同于同代作家鲜明的地域化民俗化倾向。她为何如此坚持关注东北地区的命运,并执着地展现这片黑土地的民俗文化是值得我们研究探讨的。
1.童年经验
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曾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说过:“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他的经验与行为。”[4]人在生活中缔造着民俗文化,同时民俗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人。迟子建自幼生长在黑龙江最北端的漠河山村,儿时便接触到各种东北农村社会的风俗民俗。她在《北极村童话》《原始风景》《北国一片苍茫》等早期作品中描绘了她的童年生活。事实上童年记忆对作家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莫言小说中有着大量的对饥饿的描写,实际上就来源于童年时期的生活经历。童年经验影响着作家的情感态度、审美倾向、想象能力和艺术追求。在迟子建的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出她童年时期接触了很多东北民间风俗,如元宵灯节、东北婚丧嫁娶的风俗等等。迟子建曾言:“我的亲人,也许是由于身处民风淳朴的边塞的缘故,他们是那么善良、隐忍、宽厚,爱意总是那么不经意地写在她们脸上……这几乎影响了我成年以后的人生观。”[5]可以看出迟子建是在一种质朴的社会和人际关系中成长起来的,在这种纯粹的民俗环境中成长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她文化阅历和审美经验的形成,黑土地淳朴的民风民俗成为了她之后文学创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奠定了她创作的基本格调,也形成了她文学创作民俗化的气质特征。
2.乡土情怀
迟子建笔下的黑土地苍茫旷远,热烈而沉静。我们可以在迟子建的文字中感受到她对东北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也能体会到她对家乡神话传说、民情风俗的热爱。实际上,迟子建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东北民俗文化特征,蕴含着浓厚的乡土情怀。乡土情怀隐含在她内心世界并且内化为精神世界中最深层次的底色,也正是这种乡土情怀使她不断地走进自己的家乡,用充满温情的文字去描写东北这片土地的风情民俗,她用乡土原型的方式诉说着对精神家园的寻求。“我对文学和人生的思考,与我的故乡,与我所热爱的大自然是紧密相连的。”[5]迟子建并不是一个民俗学家,只是一个作家,但是她却像一位民俗家一样关注着东北大地上每一种民俗文化。在创作《额尔古纳河右岸》之前,迟子建到根河市(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点)进行了实地考察,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事项进行了详细地记录。所以我们能在这本书中充分领略到鄂温克族多样的民俗文化。她始终坚持走在东北这片土地上,不畏辛苦与艰难,用行动体察着东北人民的日常生活。行走在黑土地上的迟子建在小说中用诗意的笔调将东北文化习俗呈现出来,体现出了她浓浓的乡土情怀。正是她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才使她如此执着地站在东北这片土地书写最真实的东北民俗文化,使东北这片土地成为了她精神的栖息之地,同时她的文字也使无数生存在这片土地的人找到了灵魂的归处。
3.审视—回归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为创作宗旨的“伤痕文学”出现,很多作家对民间文化和民间传统进行批判和反思。八十年代中期步入文坛的迟子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此时风潮的影响,她开始对自己走出去的黑土地的民间生活进行反思和审视。如作品《左边是篱笆,右边是玫瑰》中批判民间封建道德伦理对生命的戕害。《无歌的憩园》批判了民间落后思想。《旧土地》批判了民间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这些作品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是其影响力远没有迟子建其他作品具有影响力。直至她成年后离开黑土地进入城市后,才了解民间生活的珍贵和民俗文化精神的可贵之处。《原始风景》是迟子建在成年后对童年感受的反刍,她在这部作品中重新审视民间生活和民俗文化,通过此次反思她唤醒了自己沉睡的灵魂,完成了灵魂的返乡。迟子建在《我伴我走》中说到:“我想看看窗外的夜色,然而又怕见到的仍是满城灯火,同我心中的夜色大相径庭而更加失落。”[6]她见证了城市中的繁华和喧嚣,再次返回家乡,她对家乡的民俗文化和社会风情有了更加深沉的了解。不同于鲁迅的“离乡—还乡—离乡”模式中,对家乡传统文化习俗和封建伦理的批判,迟子建再次回到家乡,便沉浸在了家乡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中,写了许多展现民间风俗的作品如《逝川》《亲亲土豆》《腊月宰猪》《五丈寺庙会》等等。迟子建在这些作品中用自己诗意化的文字,描述着和谐的民间生活,用这种乡土诗意化的方式来对抗城市文明所产生的人性异化现象,面对着人性异化现象和以此产生的人类的生存困境,在乡土民俗文化中寻求了一种精神救赎的方式。
结语
研究迟子建的作品与东北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为了研究迟子建小说的文化特质,更是透过迟子建的文学作品领略东北地区的民族文化,体验东北文化中蕴含的深层涵义。在迟子建三十多年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东北民间基因并未走向萎缩,而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出迟子建笔下的东北民俗文化描写具有东北地区特有的厚重感,她对东北民俗文化书写的独特意蕴有助于提升东北当代文学的审美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