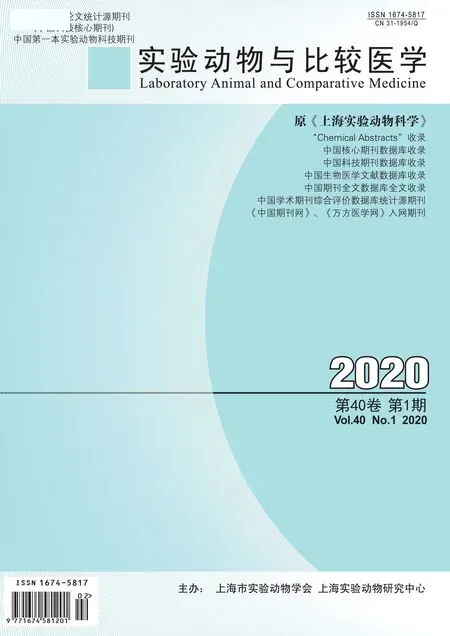小胶质细胞在焦虑症发病过程中作用及其机制研究进展
陆登成, 石安华, 陈 帅, 韦姗姗
(云南中医药大学, 昆明 650500)
焦虑症是以情绪体验、自主神经功能失调及运动性不安为主要症状的精神障碍性疾病[1,2]。黄悦勤教授[3]团队于2013~2015年对中国除港澳台地区外的18岁以上人群进行调查发现,焦虑障碍是我国最常见的终身精神障碍性疾病,患病率高达7.6%。然而,目前对焦虑症的发病机制不清、治疗效果差等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近年的许多研究表明,小胶质细胞与焦虑症的发病存在密切的联系。
小胶质细胞(microglias, MG)作为中枢神经系统免疫防疫的第一道防线,缺血、感染或神经退行性病变等均可激活MG[4]。研究[5]表明,MG激活导致的神经免疫系统失调可能是精神健康障碍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在患有精神疾病(如: 焦虑)的人体和动物模型的海马、前额皮质、杏仁核和室旁核激活的MG呈现出相对较高的密度,且与焦虑程度成正相关[6-9]。Gonzalez-Perez 等[10]发现,经泼尼松诱导的焦虑大鼠前额叶皮质MG数量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用米诺环素(一种小胶质细胞调节剂)对围产期patDp/ +小鼠(高焦虑的小鼠)治疗后发现, 小鼠出生后第7日基底外侧杏仁核中的离子化钙结合衔接分子1(ionized calcium-binding adapter molecule, Iba1,在研究中常将其作为MG激活的标记物)的表达量有所减少,第37日时明显减少,且焦虑相关行为也得到缓解。这些研究均表明MG可能与焦虑症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深入了解小胶质细胞在焦虑症中的作用机制,对揭示焦虑症的发病机制具有重要意义的。
1 MG概述
MG作为一种广泛分布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固有免疫细胞,约占脑内细胞的10%,早期主要起源于中胚层的骨髓造血干细胞,之后以单核细胞的形式随血液循环进入大脑。正常生理状态下,MG处于静息状态,静息状态的MG胞体虽不运动,但具有高度的动态能动性(dynamic initiative),它们有很多的细胞突起向周围环境不断伸缩探索,从而起到免疫监视的作用[11]。当中枢神经系统发生神经炎症或脑损伤时,MG迅速被激活并向损伤部位募集,参与神经的免疫过程。人们根据激活的MG功能、表面抗原及所分泌的细胞因子的不同, 习惯将其分为经典激活型M1(classically activated microglia)和延迟型M2(alternatively activated microglia)两种极化表型(polarized phenotype)[12,13]。M1型MG高表达组织相容性复合物Ⅱ(major histo compatibility complex-Ⅱ,MHCⅡ)、CD86和CD80,并分泌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 IL) -1β、IL-6、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OS)等促炎细胞因子促进炎症的发展、产生神经毒性,与神经网络功能障碍密切相关;而M2型MG则高表达壳多糖酶3样蛋白1(chitinase-3-like protein1, YM1)、精氨酸酶-1(arginase-1, Arg1)、CD206、细胞血红素氧合酶1(heme oxygenase 1,HO-1)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 1, IGF-1)等,以及分泌IL-12、IL-10等炎症抑制因子,其中CD206主要涉及抗原呈递与处理,YM1和Arg1参与神经修复与再生[14]。
2 MG在焦虑症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MG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机体处于应激状态时,MG被极化为不同的细胞表型,并通过神经免疫、神经元及内分泌系统等多种途径影响焦虑症的发生发展。
2.1 不同极化表型的MG对焦虑症的影响
MG不同的极化表型为我们揭示焦虑症的疾病本质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15]表明, MG激活和极化可能是焦虑症潜在分子机制。
2.1.1 M1型MG促进焦虑症发展 MG极化表型M1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促进神经炎症,改变神经元的功能,最终诱导焦虑的产生。相关[14]研究显示,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 LPS)或干扰素-γ(interferon-γ, IFN-γ) 诱导M1型小胶质细胞活化时,可产生大量的促炎因子如IL-4、干扰素α(interferon α, IFN-α)、IL-1β、MHCII、iNOS和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等,促进炎症反应、加重神经元损伤从而导致神经功能障碍。陆浩慧等[16,17]发现,经LPS脑内注射的实验小鼠表现出明显的焦虑样行为,且观察到模型组小鼠MG的M1型活化、神经元树突棘密度改变,以及海马DG、CA1、CA2区表现出了更多的M1型MG的激活。这可能是由于过度激活的M1型MG通过对神经元的修饰介导焦虑样行为的产生。Li等[15]研究了不同焦虑特征的4种近交系小鼠的MG的炎症谱,发现高焦虑小鼠具有明显更多的M1型MG标志物MHCII(+)、CD206(-)的表达;此外,他们还发现在免疫激活(MIA)的妊娠期焦虑雌性小鼠后代的中枢神经系统中也出现较高的M1表型表面标志物CD11b的表达,及相对较少的M2型MG,与焦虑行为呈正相关。
2.1.2 M2型MG对焦虑症的抑制作用 M2型MG分泌的抗炎细胞因子、神经营养因子和蛋白酶等具有吞噬病原体、增强免疫抑制的作用,甚至改善M1型MG带来的炎症反应,对神经再生、血管生成和髓鞘再生均有积极的作用[18]。研究[19]表明,选择性的诱导MG的M2极化可缓解实验动物的焦虑样行为。陆浩慧等[20]用髓样分化因子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 Myd88)抑制剂(MIP)增加实验小鼠M2型MG的激活,改善了焦虑小鼠的焦虑样行为。Zhang等[21]研究发现,应用LPS抑制剂(crocin)后BV-2 MG分泌的NO、TNF-α、IL-1β和ROS显著减少减少,且crocin显著下调iNOS、NF-κBp65和CD16 / 32及提高BV-2细胞系中CD206(M2标记物)的表达,降低了LPS诱导的实验动物焦虑样行为,其机制可能是由于NOD样受体pyrin结合区域3(NOD-like receptor pyrin domaincontaining three,NLRP3)和核转录因子κB (nuclear transcription factor kappa B,NF-κB) 信号通路得到有效的抑制,从而促进MG表型M1向M2表型转化。此外,极化的M2型MG分泌的IL-10可抑制前炎性因子如TNF-α的产生, 从而减轻神经炎症[22]。研究[23]证实, IL-10还可以缓解经前期焦虑患者的焦虑体验。Zhao等[24]通过激活母体过氧化酶增殖物激活受体γ(peroxisome proliferation-activated receptor-γ,PPARγ)的方式,诱导M2型MG促进神经前体细胞增殖和分化,改善免疫激活(MIA)焦虑小鼠后代的认知障碍以及焦虑行为。
总的来说,MG极化表型M1具有促进焦虑发生发展的作用(下文阐述的MG对焦虑症的促进作用主要指MG极化表型M1),而极化表型M2的表达可通过多种途径缓解焦虑症。因此,极化的MG表型M1向M2转型可能是焦虑症焦虑症缓解的重要机制之一。
2.2 MG通过诱导免疫紊乱促进焦虑症的发展
神经炎症及细胞因子失衡可能是焦虑症发病的重要机制。过度激活的MG释放促炎性细胞因子可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炎症反应,最终导致神经元凋亡[25]。Meetu 等[9]研究发现,睡眠剥夺期间实验大鼠的焦虑程度与促炎细胞因子和活化的MG计数呈正相关,且海马中促炎细胞因子(TNF-α,IL-1β和IL-6)呈显著倍数增加,而抗炎细胞因子(IL-4和IL-10)却明显减少。Yin等[26]在焦虑小鼠的海马中观察到神经炎症,MG激活和神经元凋亡等现象。Wang等[27]对慢性轻度应激(chronic mildstress,CMS)所致的焦虑行为大鼠观察发现,模型大鼠中枢神经系统存在NLRP3炎性体及MG激活、IL-1β、IL-6和IL-18等炎性介质上调及神经元凋亡等病理生理变化。此外,Hari等[28]研究表明,增加MG炎症抑制因子干扰素调节因子2结合蛋白2(IRF2BP2)的表达可以缓解实验小鼠的焦虑样行为。因此,激活的MG释放的中枢炎症因子诱导神经免疫紊乱与焦虑症的发病有密切的关系。
神经元是神经系统信息传递的重要途径,过度激活的MG通过分泌促炎性因子进一步影响神经元的正常功能促进焦虑样行为。如TNF-α可能通过调节纹状体兴奋性突触后电流(EPSC)调节纹状体兴奋性突触传递介导焦虑样行为[29]; IL-1β可刺激脑内皮细胞上的IL-1β受体(IL-1R1)及抑制纹状体中GABA突触的大麻素受体1(CB1Rs)的敏感性, 诱导实验小鼠的焦虑样行为[30,31]。此外,集落刺激因子1(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1, CSF-1)由单核吞噬细胞谱系的造血生长因子和巨噬细胞分化, 是巨噬细胞的主要调节因子[32]。MG的增值与存活依赖于CSF-1受体(CSF1R)信号的传导[33]。实验研究[34]表明,慢性不可预知性应激(chronic unpredictable stress,CUS)可诱导焦虑动物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上的CSF1信使RNA及该区MG表达增加,使mPFC的神经元树突棘密度降低,并出现神经元元件的吞噬作用,同时实验动物表现出高焦虑的状态,当敲除mPFC中神经元CSF1时减弱了MG介导的神经元重塑及由CUS引起的焦虑样行为。
因此,当MG过度激活时产生大量的促炎性因子,这些促炎性因子通过中枢神经毒性、神经元重塑等途径进一步促进焦样行为的发展。
2.3 MG通过影响神经递质释放促进焦虑症发展
除免疫受体外, MG还可通过影响神经递质受体的释放及获取各种各样的突触信号,促进神经元-胶质细胞的交流,介导相关行为的变化[35,36]。
研究[14,37,38]表明, 激活的MG可影响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合成,促进焦虑的发展。Couch 等[39]发现,长期慢性应激诱导的焦虑小鼠前额区域TNF-α和5-HT转运蛋白(SERT)的表达升高,同时存在更多的激活神经胶质细胞。此外,激活的MG还可导致6-羟基多巴胺(6-OHDA)介导的多巴胺能黑质纹状体通路的损伤,促进实验大鼠的焦虑样行为[40,41]。GABA是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 焦虑时起到抑制焦虑样情绪的作用。Ramirez等[42]用苯二氮卓类药物劳拉西泮和氯硝西泮通过增强大脑中的GABA能活动,有效抑制了反复社交失败诱导的焦虑小中枢神经炎症信号传导,并抑制了MG的表达及逆转焦虑样行为。
2.4 MG改变神经元信号传导促进焦虑症的发展
突触可通过分泌神经递质实现信号传递及信息交流, 当神经元的功能及结构发生变化时可使突触传导异常。近年来研究[43]表明, MG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对突触的修剪来维持神经元形态和功能的稳定性, 当神经元形态的稳定性和突触可塑性异常时则可能导致行为的异常。CX3CL1-CX3CR1信号通路由神经元上的fractalkine(CX3CL1, C-X3-C基序配体1)和MG上fractalkine受体(CX3CR1)共同构成,CX3CL1-CX3CR1系统实现了神经元—MG信息的交流及MG对突触的修饰,维持正常的信号传导。目前认为该系统在神经系统疾病中可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4,45]。Rogers等[44]敲除小鼠海马CX3CR1后,观察到小鼠海马中不成熟的树突棘密度的增多,并表现出明显的记忆减退和情绪焦虑。
MG被激活时可诱导星形胶质细胞释放大量ATP[46]。大量的ATP积累可刺激位于中枢神经系统MG的ATP门控跨膜阳离子通道的嘌呤能2X7(purinergic 2X7 receptor, P2X7)受体(P2X7R),进一步激活半胱天冬酶1(caspase-1),并诱导NLRP3与衔接蛋白和caspase-1的低聚反应,导致IL-1β前体的成熟[47-49]。Yue等[50]应用CUS的方法对大鼠施加应激时发现,随着应激积累,海马中细胞外ATP、IL-1β和ASC显着增强,NLRP3炎性体的组装,caspase-1的裂解等炎性组分增加,当给实验动物应用P2X7R的激动剂时,实验动物表现出明显的焦虑样行为,但是当运用P2X7R拮抗剂或敲除P2X7后将无法诱导实验动物的焦虑样行为。此外,Furuyashiki等[51]实验表明,P2X7受体的嘌呤能信号传导也可引发MG中的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 PGE2)的产生从而介导实验动物焦虑样行为。
上述研究表明,MG通过CX3CL1、P2X7等途径改变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导,促进焦虑症的发展。
2.5 MG通过激活内分泌系统促进焦虑症发展
研究[52]表明, 激活的MG释放ROS诱导神经元丝氨酸/苏氨酸蛋白磷酸酶2A (protein phosphatase 2A, PP2A)活化,而PP2A活性增加可导致海马损伤、神经细胞丢失、神经树突萎缩、突触点减少、糖皮质激素受体(glucocorticoid recepter, GR)减少, 进一步损伤海马对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HPA)轴反馈抑制中的作用, 引起皮质酮分泌,进一步触发氧化应激标记物的释放, 引起各种神经功能的损害,表现为血清皮质酮水平显著升高, 增加的皮质酮水平改变GABA能信号传导, 促使焦虑行为的产生[53-55]。此外,有研究[56]表明,激活的MG还可能与下丘脑-垂体-性腺(hypothalamic-pituitary-gonadal,HPG)相互作用促进焦虑症的发生。
综上所述,MG是中枢神经系统常驻的免疫细胞,正常生理条件下主要发挥免疫监视的作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在焦虑症中的作用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首先,机体处于应激状态时,MG表现为不同的极化表型M1、M2,以M1型占优势的MG极化状态具有促进焦虑症发生发展的作用,而选择性的诱导M2表型的表达可以缓解焦虑。然而,目前对MG与焦虑症的关系多处于表型的探讨,焦虑症发病过程中MG激活后引起的病理生理变化错综复杂,对MG表型在焦虑症发病中的机制研究可能是解释焦虑症发病机制的新视角;其次,过度激活的MG通过神经免疫、神经递质、内分泌及神经元重塑等多种途径促进焦虑症的发展,这可能是MG促进焦虑症发病的重要机制,因此,进一步探讨MG与神经免疫、神经递质、内分泌及神经元重塑及其各个机制之间的联系,将有助于阐释MG在焦虑症发病中的作用机制;在抗焦虑治疗及药物研究中,鉴于MG表型M2表达时具有缓解焦虑的作用,有目的抑制MG表型M1过表达诱导MG向M2型转化,可能是治疗焦虑症的新思路。总而言之,进一步探讨MG及其表型在焦虑症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机制,将为揭示焦虑症的发病机制及治疗靶点的选择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 实验动物与比较医学的其它文章
- 屏障环境的哨兵动物应用
- 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动物模型的病理特征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