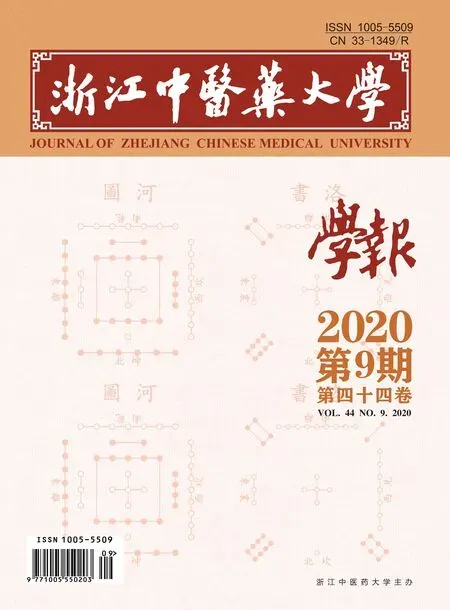郑启仲教授应用脏腑辨证治疗小儿睡眠障碍经验
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儿童医院 郑州 450003
睡眠障碍为儿科常见疾病之一,具有较高的发病率。有研究表明,我国2~12岁儿童睡眠障碍合并报告率为35.1%[1]。小儿睡眠障碍可分为睡眠失调、异态睡眠和病态睡眠3种类型[2],其常见临床表现为夜醒、梦呓、磨牙症、夜惊症、难觉醒、睡行症、恶梦、失眠、晚睡、周期性肢体运动和发作性睡病等[3]。西医对儿童睡眠障碍的治疗,一般不采用药物干预,而多选择调整生活方式、改变睡眠习惯及心理疏导等,其临床有效率较低。对于部分重症患儿则常用镇静催眠类药物治疗,虽可短期取效,但常出现药物依赖、药物耐受,远期疗效不佳。而且此类药物多缺乏儿科临床用药研究基础,可能发生肝肾损伤,对患儿的认知、行为、生长发育方面也可能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当前西医临床上对于此病的治疗尚缺乏安全有效的方法。中医学对本病具有丰富的认识,多将其归为不寐、多寐、梦游、夜啼、遗尿、鼾证等[4],其治疗方法散见于诸多文献,并有较佳的临床疗效。郑启仲教授为河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第三、四、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从事中医临床50余年,善治小儿急、重症及小儿内科疑难疾病。笔者跟随郑师学习多年,现将郑师治疗小儿睡眠障碍的经验介绍如下。
1 病因病机
郑师认为小儿睡眠障碍发病的核心病机为五脏失调、五神不安,而痰湿之邪既为五脏失调的病理产物,又为小儿睡眠障碍发生的最重要致病因素。外邪侵袭、饮食积滞、情志所伤(特别是暴受惊恐)为发病的常见诱因,病程中可见虚实夹杂或虚实相因为病,使症状多发,病机复杂。
1.1 五脏失调,五神不安 《续名医类案》曰:“人之安睡,神归心,魄归肺,魂归肝,意归脾,志藏肾,五脏各安其位而寝。”[5]指出睡眠与五脏、五神有密切联系。唐容川[6]131云:“寐者,神返舍、息归根之谓也。”《景岳全书·不寐》载:“寐本乎阴,神其主也,神安则寐,神不安则不寐。”[7]指出睡眠受五神支配,五神安居其所、舍五脏则睡眠正常,反之则睡眠异常。《灵枢·本神》曰:“肝藏血,血舍魂……脾藏营,营舍意……心藏脉,脉舍神……肺藏气,气舍魄……肾藏精,精舍志……”指出五脏藏五神,五脏之精气充沛、生理功能正常为五神安居之基础,而五神为五脏功能之外在表现,故睡眠障碍疾病发生的直接原因为五神不安,其本质为五脏功能失调。若外感、饮食、情志、劳倦等各种致病因素使心、肝、脾、肺、肾之功能失调,出现精气耗伤、津血亏虚、阴阳失衡、气机不利、痰湿内生等病理变化,致神、魂、意、魄、志失养或被扰,就会发生睡眠障碍。
《素问·六节藏象论》:“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灵枢·邪客》:“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心神统摄魄、魂、意、志,对睡眠有重要调节作用,如外邪侵袭、痰热内扰、瘀血内阻、心之气血阴阳亏虚,可致心神扰动或失养,致神不守舍,从而发生睡眠异常,表现为入睡困难、烦躁、神倦、心悸、胸闷等。
《灵枢·本神》:“随神往来谓之魂……”又云:“肝藏血,血舍魂……”《类经·脏象类》云:“魂之为言,如梦寐恍惚,变幻游行之境,皆是也。”[8]52魂与神协同对睡眠起到了重要的调控作用。外邪侵袭、情志内伤、精血耗伤均可致肝疏泄、藏血功能失常,如肝失疏泄,气机不畅,阳郁化热,则热扰肝魂,使肝魂不安;而肝血不足,阴虚阳亢,肝阳浮动,则魂随阳升,失其所舍,飞扬于外;肝血亏虚亦可致心神失养,而血虚生热亦可扰乱心神[9]。肝魂不安者表现为多梦、梦游、梦呓、不寐、烦躁、狂躁、惊恐等。
《灵枢·本神》:“……心有所忆谓之意……”《素问·宣明五气篇》“脾藏意……”忆通过辅助心神,起到安定思绪和记忆的作用,进而影响睡眠。如外邪侵袭、饮食不节等使脾失健运,致脾不藏意,可见失眠、记忆力减退、思绪烦乱、纳差、腹胀;亦可波及他脏,导致土虚木乘、心脾两虚、气血亏虚、肝不藏血、痰湿内生之证,而致睡眠异常。
《素问·宣明五气篇》:“肺藏魄。 ”《灵枢·淫邪发梦》:“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血证论·卷六·卧寐》载:“梦乃魂魄役物……魄为病,则梦惊怪、鬼物、争斗之事……魄梦多恶。然魂魄之所主者,神也。 ”[6]133《类经·脏象类》:“动在魂,而静在魄也;梦能变化而寤不能者,乃阴阳之离合。”[8]53魄与魂协同调节做梦及寐寤,而助神调节睡眠。如外邪袭肺、肺之气阴不足、痰浊阻肺致肺不藏魄,则表现为恶梦、夜寐轻浅、易寤、频寤[10]。
《灵枢·本神》:“肾藏精,精舍志……”《素问·解精微论篇》:“水之精为志,火之精为神。”水火相济,则神志安和,睡眠正常,反之则睡眠异常。如肾阳不足,寒饮上逆于心,心阳被困,心神失养,则见欲寐不寐、倦怠、恶寒、易惊、易恐;如肾阴不足,虚热上扰,则见烦躁、失眠。
1.2 痰湿内生,脏腑失调 小儿脾常不足,饮食不节,伤及于脾,脾失健运,津液失布,聚而化湿生痰。痰湿之邪阻气伤阳,流窜不定,症状多变,为儿科睡眠障碍最常见的致病因素。痰湿之邪阻滞中焦,犯及于胆,胆失中正则善惊易恐;痰随气升,上犯于心,浊阴蒙窍,则见头晕、记忆力差、易睡、嗜睡;痰邪上贮于肺,肺气不利,则见呼吸不利;痰郁日久,胶结为有形之物,则见扁桃体肥大及腺样体肥大,而出现睡眠打鼾;痰邪停聚化热,痰热犯胆扰心,则见烦躁、睡眠哭闹、易惊吓;痰为阴邪,久则伤阳,致脾肾阳虚,则喜静、困倦、嗜睡。
1.3 饮食停滞,心神被扰 《素问·逆调论篇》曰:“胃不和则卧不安。”《儿科萃精·卷七·积滞门》曰:“乳积之儿,其候睡卧不宁,不时啼叫,口中气热,频吐乳片,肚胀腹热,大便酸臭,古法主消乳丸。”[11]患儿饮食不知节制,且多食肥甘,停滞中焦,化生湿热,致胃失和降,见腹胀、腹痛。而胃经经别络心,胃气不降,浊气、积热上犯于心,心神被扰,则失眠、夜卧不安、易惊、哭闹、磨牙。
1.4 外邪侵袭,脏气受损 外邪侵犯,肺卫受伤,肺失宣降,鼻窍不通,咽部不利,吸入清气受阻,呼出浊气不畅,则见鼻塞、打鼾、睡眠不安、多梦。肺失宣降,痰湿内生,结于咽喉,则见扁桃体肥大、腺样体肥大[12]。亦有阳气不足患儿,寒邪直中太阴脾经,则见“脾主困”[13]7及痰湿内生之证;寒邪直中少阴肾经,则见“但欲寐”及心肾阳虚之证。
1.5 情志致病,脏腑失调 情志与五脏的生理功能密切相关,脏气平和则七情得调,五志安和,反之则会导致情志失调;而情志失调,亦可致脏腑气血的运行失常,而使五神不安,出现睡眠异常。儿科最常见的情志刺激为惊恐、过思、忧虑,如小儿暴受惊恐,可使肝失疏泄,胆失中正,而致气机逆乱,痰邪内扰;由于学习等原因导致思考过度,可使脾运失健,而致生化无力,气血乏源;所欲未遂,忧虑过度,使肝失疏泄,导致气机郁滞,化火扰神。
2 辨证思路
郑师认为,治疗小儿睡眠障碍应遵循脏腑辨证法则,重视痰湿之邪,兼顾病因。因小儿特别是婴幼儿问诊困难,切诊亦常不能配合,故接诊时当明晰要点,依据主症加以辨证。心肝实热者其辨证要点为烦躁、易怒、哭声有力、舌边尖红;脾胃虚弱者其辨证要点为面黄、乏力、纳少、食后易腹胀、关脉无力;心脾两虚者其辨证要点为面色萎黄、纳少、乏力、失眠、多梦,脉左寸无力、右关无力;脾肾虚寒者其辨证要点为纳少、乏力、恶寒、手足不温、多寐或不寐或寐浅、脉沉细;胆郁痰扰者其辨证要点为易惊、易恐、多梦、苔腻;痰湿阻滞者其辨证要点为乏力、头目昏沉、多睡、纳呆、便溏;乳食积滞者其辨证要点为不思乳食、口异味、腹胀、大便酸臭、苔厚;外邪侵袭者多有外感病史及风寒、风热表证;情志所伤者则有惊恐等病史,并因其所伤脏腑而有不同症状。
3 治疗经验
治疗时应调整脏腑寒热、虚实,辨别有无痰湿之邪,必要时结合辨病及病因治疗,酌加安神、镇惊、醒神、通窍、解表等药物,如酸枣仁、柏子仁、合欢皮、龙骨、牡蛎、石菖蒲、远志、蝉蜕、钩藤等以提升临床疗效。对心肝有热者,可用龙胆泻肝汤、导赤散;对脾胃虚弱者,可用六君子汤、补中益气汤;对心脾两虚者,可用归脾汤;对脾肾虚寒者,可用附子理中汤、肾气丸;对痰邪犯胆扰心者,可用温胆汤,兼有心气虚者可用十味温胆汤。对痰湿蒙窍的发作性睡病,可用神术散、涤痰汤、藿香正气散、麻黄附子细辛汤等方加减;合并脾虚者可合用六君子汤、理中汤、白术散;合并肾阳不足者,可合用四逆汤、肾气丸。对痰邪结于鼻咽兼有外邪,见鼻塞、打鼾者,可用消瘰丸合苍耳子散加减;对夹郁热者,加射干、连翘、板蓝根;对夹血瘀者,可加赤芍、郁金、莪术。对乳食积滞者,可用保和丸加减;伴腹胀者,加厚朴、枳壳;伴便秘者,加大黄;热重者,可加黄连、栀子[14]。对惊恐伤神者,可用远志丸。
4 病案举隅
4.1 睡惊症案 吕某某,男,3岁,2018年8月10日初诊。主诉:夜间哭闹半年。半年来夜间睡眠时常突发哭闹,每晚发作,常反复持续达数小时,后半夜较重,大声啼哭,易惊、易恐,不易安抚,家长抱入怀中方能入睡。血生化正常,脑电图及头部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均正常。 予钙剂、营养神经药、小儿七星茶颗粒、醒脾养儿颗粒及镇惊安神中药治疗,效果不佳。诊见:精神一般,面色稍黄,山根青,纳食一般,入睡时汗出,舌尖红,苔白稍腻,脉滑,右寸无力。西医诊断:睡惊症;中医诊断:夜啼,辨证属痰热内扰、心虚胆怯,治法:化痰清热、益气宁心。拟方:十味温胆汤加减,方药:太子参6g,法半夏6g,茯苓6g,陈皮6g,麸炒枳实6g,生姜3g,五味子6g,熟地黄10g,远志6g,炙甘草3g,蝉蜕6g,炒酸枣仁10g,黄连3g。中药颗粒剂共6剂,每日1剂,分2次开水冲服。
8月16日复诊。服后哭闹明显减轻,每次时间缩短,惊恐减轻。舌淡红,苔白稍腻。上方去黄连,加石菖蒲6g。共6剂,每日1剂,分2次开水冲服。
8月22日复诊。近3日来睡眠正常,无哭闹及惊恐。上方去蝉蜕,共6剂,服法同前。其后随访2个月未发。
按:《素问·灵兰秘典论》:“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灵枢·邪客》:“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心胆气虚,脾常不足。饮食伤及于脾,痰浊内生,阻滞气机,气机逆乱,协痰游走,横逆则犯胆,上行则扰心;亦有患儿突受惊恐,致肝失疏泄,气机逆乱,津液失布,聚而生痰,痰随气逆,犯胆扰心。因心不藏神,胆失决断,见睡眠不安、易醒、多梦、善惊、易恐、哭闹。《世医得效方》载:“十味温胆汤,治心胆虚怯,触事易惊,梦寐不祥,异象感惑,遂致心惊胆慑,气郁生涎……心虚烦闷,坐卧不安。”[15]方中半夏、茯苓燥湿化痰,太子参健脾养心、安魂定魄,枳实、陈皮调气行痰,熟地、五味子滋养心阴,远志、酸枣仁养心安神,甘草和中健脾。全方理气化痰、养心安神,扶正与祛邪兼顾,与温胆汤相比较,更加切合儿科虚实夹杂之病机。对夹热者,可加黄连;对惊恐明显者,可加蝉蜕;痰浊重者,可加石菖蒲。
4.2 发作性睡病案 刘某,女,10岁,2018年5月15日初诊。主诉:睡眠多3个月。3个月来睡眠增多,病初夜间入睡早,晨起难醒,1个月来上课时常入睡,伴乏力,头沉,纳食减少,大便溏。平素喜食肉食、甜食、饮料。血电解质、生化均正常,脑电图及头部CT正常,口服营养神经药物及中药效果不佳。诊见:形体胖,精神萎靡,面色黄暗、虚浮,恶风、恶寒,时有头目昏沉,纳食少,食后易腹胀,手足不温,大便溏,舌淡,苔白腻,脉沉细。西医诊断:发作性睡病;中医诊断:多寐,辨证属脾肾阳虚、寒湿困阻,治法:温肾健脾、化痰祛湿散寒。拟方:麻黄附子细辛汤合七味白术散加味,方药:麻黄6g,制附片6g,细辛3g,党参10g,炒白术10g,茯苓10g,炙甘草3g,木香6g,藿香10g,葛根10g,干姜6g。中药颗粒剂共7剂,每日1剂,分2次开水冲服。
5月22日复诊。近2日多睡症状稍减轻,舌脉如前,上方加炒苍术10g。继服一周,精神明显好转,睡眠时间缩短,纳食增减,手足温。上方继服2周,症状消失,以参苓白术散加藿香,服用2周。随访3个月,未再发病。
按:患儿面色黄、纳少、腹胀、乏力、便溏为脾虚之象,手足不温、脉沉细为肾阳不足之象,形体胖、面色暗、虚浮、头目昏沉、乏力、苔腻为湿浊困阻之象,恶风、恶寒为外感寒邪、卫阳郁滞之象。《小儿药证直诀》云:“脾主困……”[13]7李东垣[16]《脾胃论》云:“脾胃之虚,怠惰嗜卧。”《丹溪心法·中湿》曰:“脾胃受湿,沉困无力,倦怠嗜卧。”[17]《伤寒论》:“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本例患儿喜食肥甘,伤及脾胃,痰湿内生,痰浊上扰,清窍失养,则头目昏沉、多眠;痰浊中阻,则纳呆、腹胀、乏力、便溏;痰浊为阴邪,久则伤阳,肾阳不足,心阳疲惫,见手足不温、易寐、神识朦胧;正气不足,外寒易侵,故可见内外合邪之症。麻黄附子细辛汤可温肾阳、振心阳、宣肺气,阳气升则阴霾之痰浊化,肺气宣则痰湿及外寒散。七味白术散出自《小儿药证直诀》,由四君子汤加葛根、藿香、木香而成[13]51-52。四君子汤益气健脾,其中炒白术燥湿醒脾,藿香化湿辟秽,木香燥湿温运三焦、芳香辟秽,葛根升清阳达头目。两方配伍,复肺、脾、肾之运化水湿功能,使三焦通畅,阳气得复,邪气自散。在外邪与内生之痰湿化后,则健脾扶正,以绝痰源,而防病复。
5 结语
睡眠障碍在儿科具有较高的发病率,本病具有一定的自限性,但部分患儿症状持续时间较长,可长达数月甚至数年,对患儿学习、生活及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中医学治疗本病有独特优势。郑师认为造成本病的根本原因为五脏失调、五神不安,而外邪侵袭、饮食积滞、情志所伤、痰湿内扰均可造成小儿五脏失调、五神不安,尤其以痰湿内扰为最常见的致病因素。治疗时应遵循脏腑辨证法则,依据主症辨脏腑寒热、虚实,兼辨有无痰湿之邪,及有无外感、积滞、情志所伤,必要时结合辨病治疗,酌情使用针对具体病种的治疗药物。同时亦应注意有无诱发睡眠障碍的不良生活习惯及环境因素,及时祛除诱因,一方面可提升临床疗效,另一方面亦可防止疾病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