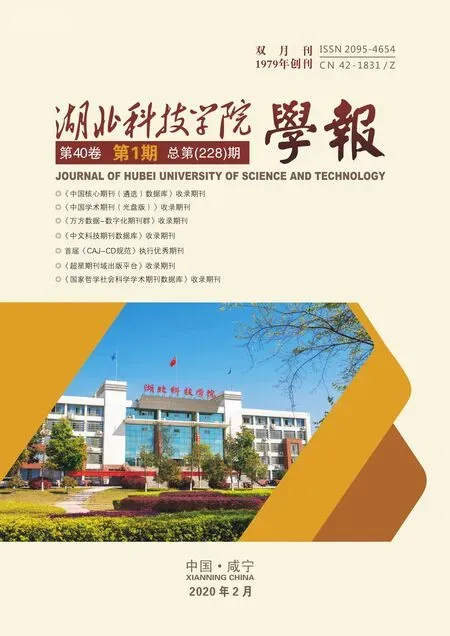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中的彼得一世形象探析
——以《反基督:彼得和阿列克塞》为例
公冶健哲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作家、思想家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865—1941)创作于1895—1905年的《基督与反基督》(Христос и антихрист)“三部曲”作为“融入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丘特切夫等经典作家的思想与形象”的“俄罗斯与西欧两种文学传统融合的产物”[1](P292),在发表之初即获得了俄罗斯文艺界与思想界的普遍关注。在“三部曲”系列的收官之作《反基督:彼得和阿列克塞》(Антихрист: Петр и Алексей)中,梅氏将目光投向了17—18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历史,在小说中成功塑造了彼得一世独特的艺术形象,并在作品结尾公开阐明了“基督必定战胜反基督”[2](P520)的思想立场。自“三部曲”问世以来,学界对于《反基督》中彼得一世形象的解读至今仍莫衷一是:研究者们或是从作品人物的象征意义出发,将彼得视为“集中代表了自己时代‘人性’的巨人”[3](P140)和俄罗斯文学中“人神”形象的典型范例[4](P8),或是以梅氏的宗教哲学思想为依托,称其为“人类历史阶梯上进行宗教精神探索的一个环节,是探索宗教真理的曲折道路上的一个否定性因素”[5](P135),抑或是将作品情节与史实加以联系,赋予彼得以“抱负远大的君主”[6](P32)或“破坏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历史罪人”[7](P32)的两极评价。然而,《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作为表达梅氏宗教哲学观的“思想小说”,正是通过作家对历史人物的主观阐释,描绘主人公的“精神、心灵和情感之类的内在特征”[8](P17)来宣扬其所倡导的“第三约”哲学思想。本文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解读《反基督》中的彼得一世形象,发掘这一形象中蕴含的作者伦理观念以及梅氏宗教哲学思想中的人本主义特征。
一、斯芬克斯因子作用下的“双面君王”
在《反基督》中,彼得一世一改19世纪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笔下器宇轩昂的“青铜骑士”形象,被梅列日科夫斯基描绘成了一位结合了坚定与脆弱、善良与残酷、冷静与疯狂等诸多对立特点的“双面君王”。在对彼得一世的性格进行描写的过程中,作家借助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之一、德国女官阿伦海姆的日记,以“通过虚构人物的视角来表现历史人物”[9](P115)的方式,凸显了彼得性格中“人性与兽性两种极端的结合”[10](P107):彼得果断地下令将几千名火枪兵处以极刑,却因不忍心看到燕子被当作科学实验的牺牲品而将其放生;他既能毫不畏惧地面对涌进舞会大厅的洪水,也会在心力交瘁时投入妻子的怀抱寻求安慰;尽管沙皇时常严厉地责备太子的守旧与无能,但他仍在儿子身患重病之时甘愿用十年的生命换取爱子的康复。然而,彼得一世的精神世界中最为尖锐的矛盾则表现在信仰层面:他既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却同时公开崇拜在当时被视为“异教”的多神教神祇。这两种看似水火不容的信仰在彼得的身上同时并存,并使其在不同信仰的主导下做出种种各异的行为,甚至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面貌。实际上,彼得的复杂性格以及在其精神世界中交替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督”与“诸神”,正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所指出的人物性格中“斯芬克斯因子(Sphinx factor)”[11](P38)发挥作用的鲜明体现。
“无论是社会中的人还是文学作品中的人,都是作为一个斯芬克斯因子存在的”[11](P38),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每个人物都是象征理性意识的人性因子与代表动物性本能的兽性因子的结合体,而彼得在“双重信仰”的制约下的不同表现,正是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不同比例所造成的结果[11]((P38~39)。“兽性因子是人在进化过程中的动物本能的残留……其外在表现形式为自然意志及自由意志”[11](P39),梅氏在《果戈里与鬼》(Гоголь и чёрт)一书中指出,“根植于大地和肉体”、“向往‘可感知的现实’”[12](P59)的多神教信仰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重要源头之一。“多神教真理的核心精神是酒神式的欢愉,如同奥林匹斯山上众神在掌握无限神力之外,还要感受身体的愉悦……它始终和人的本性相关”[13](P38),随着社会的发展,“诸神崇拜”开始逐渐脱离宗教的范畴,被解读成一种“主张光明与欢乐,主张生活的完美,提倡最大限度地强调人类自我”[1](P287)的处世态度。彼得在为庆祝多神教神祇之一的维纳斯雕像进入彼得堡而举办的舞会上与臣仆们一起跳舞作乐、纵酒狂欢,完全放下了沙皇高高在上的身份,表现出一种无拘无束、自由放任的天性,而这正是“斯芬克斯因子”中象征原欲(libido)与自由意志的“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占主导的结果。与当时封建刻板、主张禁欲主义的东正教相比,以希腊诸神为代表的多神教更加关注“人”自身的生活需求,其所宣扬的人类“生命的欢乐”和“肌体的强健”[12](P61)也是对人的生命基本价值的肯定。因此,梅氏正是借助彼得一世对“诸神”的崇拜,批判了历史基督教极端主张禁欲、轻视肉体的虚伪道德[10](P40),并通过描写沙皇如同战神马尔斯一般英武俊美的外表,强调“人是配得上女神的”[2](P24),充分肯定了人类自我实现的愿望和张扬生命热情的权利。
如果说,彼得信仰世界中的“诸神”更多地彰显了人类的自然天性,那么力图克服自身局限、主张自我完善、追求为道德的提升而做出牺牲的“基督”则是代表道德与理性的“人性因子(human factor)”的象征。与多神教相比,基督教主张为了精神和道德的完善而对人的自然本性加以克制,是人类理性日趋成熟的产物,通常被解读为“人与自我求圣关系的精神教义……是人向上帝的提升,也是通向神圣的蓝图”[14](P51)。当彼得遭遇精神的苦闷和重大的抉择时,他始终求助于象征理性的“基督”而非代表肉体需求的“诸神”。彼得将俄国的改革视为“上帝放在我们眼前的普遍好处”[2](P32),他渴望自己能够拥有基督般完美的献身精神和道德高度,成为基督式的拯救俄国百姓于愚昧落后之中的强者。在象征理性的基督信仰的帮助下,彼得虽历经重重痛苦的考验,却依然感受到了“类似于奇迹的幸福”[2](333)。此外,“基督”所赋予彼得的,还有对祖国、人民和亲人发自内心的爱,以及随之产生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梅氏认为,“爱”是“基督‘三件礼物’中最重要的一件……爱不是智慧的信念,而是存在的一种状态。知道真理是不够的;人必须在真理之中,爱就是真理”[3](P228~229)。小说中的彼得发自内心地尊重每一个俄罗斯人的生命,亲自驾船营救被困在洪水中的彼得堡居民;对于在波尔塔瓦战役中出生入死的水兵,沙皇亲切地称他们为“孩子们”,并做出了庄严的宣告:“国家不能没有你们,就像身体没有灵魂一样”[2](P124)。评论家伊丘克指出,梅氏小说中的彼得“显现出对人民和对社会公正的爱……就像上帝的思想一样博大精深……围绕着美与诗的光环”[1](P303)。正如圣经神话中的耶稣背负起象征人类命运的十字架走向各各他山,彼得也甘愿默默背负俄罗斯民族命运的重担,为了人民和祖国牺牲了自己的健康,甚至“不惜自己的性命”[2](P213)。作家正是借此说明,与小说中大肆宣传自焚、滥交、大肆敛财的所谓“圣人”和“先知”相比,“彼得的事业即是真正的基督教事业”[15](P205~206),爱民如子的彼得才是基督之爱真正的践行者,沙皇彼得与“三部曲”前两部中的尤利安和达·芬奇一样,亦是背负着“叛教者”、“反基督”恶名的真“圣徒”[16](P88)。
梅氏在《反基督》中运用一以贯之的“二元对立”手法[17](P10),展现了彼得性格中的矛盾因素,并运用“诸神”和“基督”两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概念,阐明了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作为人类精神世界中“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18](P64)所具有的辩证关系。虽然梅氏提倡和弘扬“多神教中鲜活的艺术美、创造力和健康的人本精神因素”[10](P244),但作家同时说明,“并不是所有光明与快乐的东西都是属于异教的”[1](P302)。彼得亲自处决叛乱火枪兵的场景使人联想起希腊时代血腥的多神教祭典,“在一片欢呼万岁声和乐曲声中,他喝一杯酒,砍一颗头;酒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砍头声一声接着一声地响;酒和血流到一起,酒中掺合了鲜血”[2](P59);在宴会上狂饮的彼得对下属关于涅瓦河水情的汇报置若罔闻,致使洪水冲进了毫无防备的彼得堡,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梅氏在彼得的失误中看到了不加克制的自由意志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将“基督”所代表的道德与理性视为引导彼得走上正确道路的标杆。应当指出的是,小说中的“基督”并非狭隘的宗教概念,而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所主张的理性与道德“臻于至善”的象征,是引导人走向理性成熟的精神力量。恰如米尔斯基所言,“他(梅氏)的基督是一种抽象,而非一个人”[19](P10),与自由意志主导的愿望得到满足时的快乐相比,理性赋予人们的则是更为崇高的幸福感。作家通过强调彼得一世性格中的“二律背反”特征,以此说明人们固然拥有满足自身欲望的合理需求,但倘若一味放纵自由意志、任由兽性因子掌控全局,那么将会招致世界的堕落,致使“恶奴役着人”[20](P10),而在欲望与理性的博弈中,道德与理性必然会超越人类的原始天性,取得最终的胜利。尽管有学者称,在《反基督》中“梅氏依然没有超越正统基督教神学思想中耶稣基督所代表的‘上天的真理’在与多神教所代表的‘尘世的真理’搏击中,‘尘世的真理’必然要屈从于‘上天的真理’的铁律”[13](P39),但这恰恰表明,人必须通过人性因子对兽性因子的制约,以其代表的理性意志来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行为,才能成为伦理意义上的真正的“人”。因此,梅氏在“三部曲”中所提出的使“地上的真理”与“天上的真理”合而为一的“第三约”哲学思想,正是作家试图在创作中寻求一种在合理满足自我需求的同时,在理性的引导下追求道德与精神的提升,以期实现“斯芬克斯因子的理想平衡”[21](P21)的一种伦理探索。
二、伦理困境制约中的“弑子者”
《反基督》中的彼得一世形象之所以能够在浩如烟海的俄罗斯文学人物长廊中独树一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即是梅氏在创作中另辟蹊径,通过对历史人物的主观理解与艺术加工,凸显了彼得“力量和弱点结合在一起”[2](P117)的精神特质,展现了这位历史伟人“被忽略的人性及其欲望”[22](P54)。“彼得弑子”作为集中整部小说主要矛盾的关键性事件,对于把握小说主旨以及作家的伦理观念具有重要的作用。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研究者们或从道义上谴责彼得是杀害亲生儿子的刽子手,或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将其解读为大义灭亲的无奈之举。然而,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说,研究者必须“进入文学的历史现场”,对文本中人物的行为“进行客观的伦理阐释”而非以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标准对其进行“简单地进行好坏和善恶评价”[11](P15),以一种全面、客观的视角分析作家借助作品中的人物所传达出的道德理念与思想主张。
“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11](P263),每一种特定的伦理身份都同与之相称的伦理秩序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处于多重伦理身份规约下的人往往由于不同伦理规范之间的差异或冲突而面临伦理选择上的困境。《反基督》中的彼得和阿列克塞都因其所具有的多重伦理身份而处于复杂的伦理关系之中,两者各自所代表的不同伦理秩序之间的矛盾也在沙皇父子的对立中表现得尤为鲜明:一方面,彼得与阿列克塞作为父子,有着不能割断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太子阿列克塞和沙皇彼得分别作为“保守派”和“改革派”两个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在执政理念上有着根本的冲突;此外,彼得因对教会制度的改革被视为“反基督”,而阿列克塞则被拥护俄国旧有制度的教会称作“上帝的羔羊”。沙皇父子间复杂的伦理关系构成了作品伦理困境产生的先决条件,而他们对于彼此不同的伦理身份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太子阿列克塞的记忆中,“爸爸”彼得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亲人、一个可亲的伙伴、一个“手疾眼快、情绪欢畅的卷发男孩”[2](P223),而“沙皇”彼得在太子眼中却是一个冷酷无情、暴戾残酷的“变形人”。阿列克塞深爱着“爸爸”彼得,同时却不无讽刺地称沙皇为“生我者”,甚至诅咒他快些死去。对于作为执政者的彼得而言,太子生性软弱、难当大任,故而他向来对太子严加管教、怒其不争。然而,当彼得从“君主”化身为“父亲”时,却对儿子的命运产生了无以言说的自责、痛苦与悲哀。正如小说中所指出的,“他俩好像是立下了残酷的誓言:彼此相亲相爱,又相互为敌,暗自相爱,明面上彼此憎恨”[2](P238),沙皇父子无法合理地解决由多重伦理身份所造成的一系列伦理问题,致使二者间的冲突达到极致,将两人引向了父子反目的伦理困境,进而导致了沙皇“弑子”的伦理悲剧。
在《反基督》中,太子阿列克塞对父亲的改革思想感到不满,并企图在一些主张恢复旧制度的俄国宗教和政界人士的帮助下发动政变,但因篡位失败而仓皇出逃,携情妇流亡海外。太子对彼得的欧化改革持否定态度,认为如果自己能够登基,就“将要启用所有的老人,而对新人则要根据自己的意旨挑挑选选”[2](P278)。但这样一来,彼得为俄国改革所耗费的心血必将付诸东流,而沙皇本人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旦放任太子的所作所为,那么盘踞俄国多年的旧势力必将卷土重来,使初现现代文明星火的俄国重新走入愚昧和黑暗,进而“使整个国家走向彻底毁灭”[2](P346)。宽恕太子就意味着向保守势力妥协,因徇私情而置国家前途和人民安危于不顾,故而彼得宁肯冒着被百姓乃至上帝唾弃和诅咒的危险,决定处死太子。然而,阿列克塞与叛乱的火枪兵和旧派宗教分子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是和彼得拥有血缘关系的儿子,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弑子”都是一种违反家庭伦理的行为,理应受到惩戒。况且彼得通过书信与太子有约在先,只要太子按时回国,他就会宽恕儿子和有关人员的一切罪孽,而违背誓言也是普遍道德原则所不允许的。在“沙皇”和“父亲”两种身份分别代表的伦理秩序产生冲突的情况下,彼得陷入了“弑子救国”和“赦子亡国”的“伦理两难”困境:“弑子”固然是对家庭伦理的破坏,而“赦子”则是将在西欧列强的虎视眈眈下艰难图存的俄国置于亡国的危险之中。恰如作家在文中所写,“一个人尽管是为了祖国的幸福,可是犯下灭亲之罪,在上帝面前能够问心无愧吗?但怎么办呢?宽恕儿子——就要毁掉俄国,处死他——就要毁掉自己。他觉得永远也无法解决这个矛盾”[2](P347)。对于彼得来说,做出其中任何一项选择都意味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起初,他向上帝呼求,企图借助“上帝”的干预规避两种行为之间的道德悖论,但他最终发现,自己必须在这一伦理困境中做出选择。因此,沙皇痛下决心,要为了俄国的未来处死太子,并准备好承担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让这鲜血落到我的身上吧,让我一个人承担吧!把我处死吧,上帝呀,——保佑俄国平安吧!”[2](P349)。彼得这一痛苦而决然的呼告表明,在“伦理两难”的情境下,纵然每一项选择都有着道德上的正确性,但“无论选择哪一项在伦理上都会导致另一项违背伦理”[11](P263)。纵然彼得以儿子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了改革的顺利推行,但他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天才、新的俄罗斯帝国的缔造者”[23](P14)。与此同时,彼得为国家创下的丰功伟绩并不能为他的“弑子”行为进行开脱,他也必将因为自己的杀戮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24](P6)。梅氏在对“彼得弑子”悲剧的前因后果进行交代的过程中,并没有武断地定义这一行为的是非对错,而是着重描写了彼得在作出最终抉择前的内心矛盾与挣扎,表达了对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赋予了整部小说“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的感伤情调”[25](P23)。
“伦理身份是道德行为及道德规范的前提,并对道德行为主体产生约束,有时甚至是强制性约束”[11](P264),彼得正是由于其背负的多重伦理身份而陷入了伦理困境之中,这一困境迫使他必须在“赦子”和“救国”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弑子”的伦理悲剧中“彼得的错误只是混淆了自己的角色”[10](P107),由于无法合理地解决因身份问题造成的两难困境,彼得做出最终选择的一刻即昭示着其命运悲剧的必然降临。梅氏在《反基督》中通过对彼得弑子前后的内心冲突的全景式描绘,表达了对主人公人生悲剧的深切同情,体现了梅氏的人道主义伦理观。正如罗森塔尔所言,“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双方的同情态度,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他最好的小说”[3](P144),梅氏在“彼得弑子”这一作品情节的核心事件中着重表现了彼得复杂和多面的情感,将目光由“作为君王的伟人”转向了“作为常人的君王”,展现了身处历史洪流中的人物因无法摆脱伦理困境的制约而遭遇的人生悲剧,赋予作品以超越时代的悲悯情怀与人本主义精神,使这部小说在世界文学语境中拥有了独特的伦理价值。
三、冲破旧有伦理桎梏的“反基督”
“俄罗斯民族探寻千年真理王国的旧梦,是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命脉之一”[20](P24),与17世纪轰轰烈烈的彼得改革时代类似,身处“白银时代”的诗人和作家们也敏锐地感受到了一种对“具有重要综合意义的、更高级的公共制度的需求”[10](P302),他们“指望着并预感到尚未发现的感染力世界”,充满着“对尚未体验的事物的渴望”[26](P38)。在《反基督》中,梅氏通过描写主人公彼得一世精神世界中“诸神”与“基督”所表征的不同伦理准则之间的矛盾,反映出处于变革时期的俄国社会中“自然原则同道德理想同宗教道德、传统风俗和现代文明的冲突”[11](P202)的同时,也在期待着一种新的、更加完善的伦理秩序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俄罗斯民族未来精神走向的“第三约”哲学思想。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他(梅氏)总是在历史中寻找那些他所认为的、在尘世的生活中践行了他的‘第三约’理想的伟人”[27](P663),彼得一世作为“个性是17世纪末俄罗斯文化的典型产物”[28](P264),在一定程度上即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象征。彼得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对俄国旧有伦理秩序的背离与突破,也正是俄罗斯民族在永恒的精神探索中不断冲破桎梏、建立更加适应时代需求的新的伦理秩序之过程的鲜明体现。
古往今来,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彼得一世的改革成果之于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意义,但出现在文艺作品中的彼得一世形象却一直颇受争议。在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中,一场袭击了彼得堡的洪水彻底摧毁了小人物叶甫盖尼的生活,使他在希望破灭后悲惨地死去,“而这个可悲的灾难同彼得大帝当年在芬兰湾海岸建立这座临海的城市直接相关”[9](P112),而在梅氏的小说中,彼得更是被冠以了“反基督”这一颇具负面色彩的名号。作家在《反基督》的开篇经由旧信仰派教徒多库金之口,解释了彼得“反基督”之名的由来:彼得大力推行的改革措施使俄国人“丢掉了房舍和商贸、农耕和手艺以及自己从前的一切行业和古代定下的法律……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语言以及服饰,剃掉了头发和胡须”,在多库金看来,这些措施使俄国“丢掉了基督教的一切虔诚”、“走上一条奇怪的未知道路,毁灭在朦胧之乡”[2](P3)。从表面上看,彼得对东正教机构大刀阔斧的改革完全符合“反基督”的特点,他也因之成为了宗教保守派人士攻击的对象。东正教自“罗斯受洗”以来一直被俄国社会奉为“国教”,在俄罗斯民族传统的精神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以东正教教会所代表的历史基督教借用宗教教条“把人虚弱化”[10](P30),进而导致了“人的个性丧失与个体价值被藐视”[29](P77),已经成为了俄国文明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为了使俄国脱离封建和愚昧,尽快走向文明与现代,沙皇彼得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也要“用鞭子往他们(俄国民众)头脑里抽打科学”[2](P66),有时甚至使用一些强制性的措施来革除旧有思想的约束。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哲学大家别尔嘉耶夫指出,历史基督教“以法律的名义捍卫的抽象的善”,是对人的价值的盲目否定,同时也是一种“伦理的极端表现”[20](P23),而“在梅氏创作的历史哲学小说中,作家对于历史基督教始终持有怀疑态度……并感受到了它的必然消亡”[27](P664~665)。梅氏在论及《反基督》中彼得对东正教会的改革时明确提出,彼得对历史基督教的所谓“打压”与“戕害”不过是“砍伐了一棵不结果实的枯树”[10](P100),揭穿了“打着基督圣像幌子所进行的拙劣表演”[1](P314)。因此,被称作“反基督”的彼得所“反”的并非是“基督”本身,而是历史基督教所代表的“律法主义”哲学观,其行为从本质上来说,正是一种试图革除旧有伦理约束、探索现代道德秩序的“伦理的反叛”[30](P94)。
“一种哲学,如果它竭力否定人在世界上的特殊意义,否定人是对世界奥秘和意义的认识的特殊来源,就会陷入内在矛盾,身染致命顽症”[20](P7)。“白银时代”作为俄罗斯文明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思想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感性主义的人文主义道德观不谋而合。梅氏正是在“白银时代”的文化语境中抛弃了宗教律法轻视个人价值的消极情绪,在创作中突破了19世纪文学中的抽象道德与宗教维度的制约,强调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实现自主创造的权利。小说中的彼得作为俄罗斯历史上伟大的革新者,正是梅氏所主张的人应当打破宗教律法的制约、进行积极的自我价值探索的象征。彼得通过对宗教律法伦理的“反叛”证明,“上帝存在于人的自由创造之中。正是由于人的创造活动,使上帝得以诞生;而真正的人的诞生(那种摆脱的奴役状态、自由存在的人)也是上帝的手笔”[20](P12),因而梅氏所倡导的“新宗教发现”究其本质而言“只能是关于人的发现、关于作为具有神性的人的发现,是人的创造性的揭示”[31](P125)。与呼喊着“好牧羊人”的名字痛苦死去的尤里安和在精神的迷失中黯然离世的达·芬奇相比,面对风浪的彼得充满信心地宣告:“我们的新船结实:经得起暴风雨。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位掌管俄罗斯命运的舵手“坚定地操纵着战舰在铁与血的波涛中向未知的远方驶去”[2](P475)。彼得的改革举措在当时的俄国可谓是前所未有,但“更新了一切,甚至可以说,重新造就了一个俄国”[2](P132)彼得正是通过自己非凡的创造力与行动力证明,“他身为沙皇就是主手中的铁锤,在锻造俄国”[2](P475)。诚如索洛维约夫所言,“真理本身、真正的完全真理必须和幸福、美、力量联系在一起,因为真正的哲学是与真正的创造力和道德活动紧密联系的”[32](P30),梅氏在彼得身上灌注了自己的世界观及其对人类崇高道德理想终将实现的坚定信念[17](P12),从而说明人类必将脱离精神蒙昧的状态和封建道德的约束,在自主创造的过程中推动文明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不可否认,由于自身的局限,彼得在改革过程中未能完全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明与暴力”等因素中做出符合所有伦理规范的选择,致使俄国社会各阶层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也使其借由武力手段强制推行的现代文明受到了俄国人民心理上的排斥。然而,“历史进步的一个过程,也是道德和理性在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环节。进步不会一蹴而就,正是这些迂回曲折的环节,才赋予了进步以积极的意义和丰富的历史内涵”[33](P83)。梅氏在小说中通过对彼得所代表的“人神”形象的描写,宣扬人类实现自主创造、掌控自我命运的合理性,从而说明“第三约”理念的核心即是对人的自主创造力的肯定与发扬,彰显了作家在创作中始终如一的人本主义立场。
“按照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观点,彼得大帝以后的时代,是战胜了兽性、战胜了反基督的思想时代”[1](P314), 梅氏本人在对彼得改革进行评价时,认为其“不但使俄罗斯从本民族封闭的文化圈子中走出来,加速了俄罗斯世界化、历史化进程,而且使俄罗斯融入西欧、融入更大的基督教文化圈中,为最终的全人类联合与救赎作了准备”[15](P205)。虽然作家在小说结尾将完美地融合一切对立因素的“第三约”视为俄罗斯民族精神信仰的最终出路,但小说却并没有落入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的窠臼。与此相反,梅氏在创作《反基督》的过程中“没有教派立场,而是超乎其上”[10](P23),贯穿整部作品的“第三约”哲学思想实际上是梅氏对于彻底解决一切伦理问题与道德冲突、构建以理性为主导的和谐世界、追求至高精神与完美道德的伦理构想。对于“在基督和反基督这两个对立的幻影之间处于没有出路的矛盾和混合之中”[34](P346)的俄罗斯民族来说,梅氏在小说中所进行的“第三约”哲学思想的探索“不仅在进行宗教哲学的探究,道德的叩问,更是在寻找俄国,乃至人类的未来之路”[16](P95)。因此,《反基督》不仅是梅氏早期宗教哲学思想成果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俄罗斯近代精神探索道路上的里程碑,更是对积极追求崇高道德理想与理性意志的“创造的人”的颂歌。
四、结语
对于处在19—20世纪之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交汇的时代”的俄罗斯人来说,他们面对的是实证主义规约下“无以言表的晦暗和寒意”[20](P190),身处“世纪末”焦虑中的俄罗斯民族究竟该走向何方,这一问题引发了俄罗斯知识界的一场思想革命。作为“白银时代”象征派的主要旗手之一,梅氏“不仅在自己的心灵中敏锐地感觉和意识到两个世纪的‘交战’、新与旧的‘交战’,还异常准确地猜测到这一矛盾的巨大世界性特点。他把周围现实的一切方面都归结为两种绝对因素——基督和反基督”[35](P75)。梅氏在《反基督》中,通过对作为俄罗斯民族精神象征的彼得一世形象的艺术塑造,充分展现了俄罗斯民族所面临的“肉体与精神”、“诸神与基督”、“东方与西方”等充满悖论的伦理问题,借助对人物心灵世界的探索及对历史事件主观的“二分法”阐释,提出了“第三约”的道德伦理构想。作家在作品中极大地肯定了以彼得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对国家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坚信人类必将通过自主的创造活动,实现个人精神与社会伦理的完善。可以说,《反基督》既表达了梅氏对人类天性与理性归于和谐的向往,也反映了作家本人对俄罗斯民族未来精神出路的想象,无论是在俄罗斯近代文学史抑或思想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启发意义与伦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