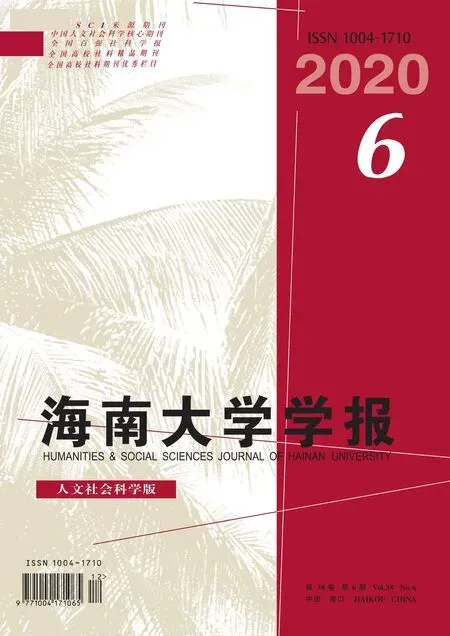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
——以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为视角
韩立新,冯思嘉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116026)
南海海洋经济活动如火如荼,海洋环境污染及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的现实状况及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但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与该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活跃的海洋经济活动却不相匹配,与其他区域海如波罗的海、地中海海域(1)波罗的海6 个沿岸国于1974 年通过了《保护波罗的海海洋环境的赫尔辛基公约》;地中海沿岸国于1976 年缔结了《保护地中海海洋环境沿岸区域公约》。乃至加勒比海域(2)加勒比地区已于1983 年通过《保护和开发泛加勒比地区海洋环境公约》(简称《卡塔赫纳公约》),以及合作应对溢油、特别保护区和野生动物、防治陆源污染三个议定书。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相比,南海海域的生态环境治理起步较晚、规模有限、深度有待加强;这种状况不利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也与实现南海人海和谐的发展模式相差甚远。目前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理念是一方面吸收之前海洋生态管理实践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发扬全球治理的智慧,对传统海洋治理相关理念进行革新,这对破解目前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现存的诸多问题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对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也会起到促进作用。
一、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起点与特征分析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应当是国际社会应对海洋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案与努力方向,但是,学界对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相关认识尚不充分,基本的看法是将它视为全球治理在海洋生态领域内的回应。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要成为力促解决海洋生态问题的一种理论与行动并存的机制,就有必要厘清它的逻辑起点,与此同时也有必要分析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一些特性,从而力求达成理论上的基本共识,寻求全球层面的协调认知,才能更好地开展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行动。
(一)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起点
1.海洋生态问题发生与应对的全球性
人类对海洋利用程度的加深以及海洋经济活动的扩展,使得海洋生物入侵、大规模海上溢油事件频发、渔业资源锐减、海洋生物多样性失衡、海水赤潮化、海洋垃圾泛滥。一方面,由于海洋本身的流动性,加之季风、洋流的影响,全球海洋是一个动态整体;另一方面,人类的全球化活动强化了海洋整体性与全球性的特质。种种海洋生态问题的发生很少仅局限于一国海域内,也很难将该责任归咎于某一国家。例如海洋生物入侵事件,“原产于美洲海域的筛贝通过船舶压载水现已入侵至我国福建海域,争夺了当地牡蛎等土著经济物种的栖息地”(3)百度百科:《海洋生物入侵》,https://baike.baidu.com/item/海洋生物入侵/22300988,2020 年3 月9 日访问。,很难指出具体的责任方。对此必须认识到:海洋生态破坏愈演愈烈根源于全球化,解决海洋生态问题必须要以全球智慧为指引、集合全球力量。
2.从管理到治理的路径转变
海洋生态问题的解决路径经历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如何解决海洋生态问题,过去乃至当前比较通行的是海洋环境管理理论及其相关实践(4)主要包括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区域管理、美国的区域海洋管理行动、联合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海岸带管理”综合政策等。,国内外对此方面的研究也较为丰富。例如,美国学者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所著的《美国海洋管理》一书对海洋生态管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5)该书主要阐述了“海洋环境管理是法律和行政的控制,包括国家对海洋水质和各种物质的入海处置、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渔业活动、某些水域中船舶运输方式、外大陆架油气生产以及其他许多事务”。,强调海洋管理的主体是国家,客体是影响海洋环境的相关活动。目前,国内有关海洋环境管理的概念多采纳学者鹿守本的观点,他认为“海洋环境管理是以海洋环境自然平衡和持续利用为宗旨,运用行政管理、法律制度、经济手段、科技政策和国际合作等方式,维持海洋环境的良好状况,防止、减轻和控制海洋环境破坏、损害或退化的行政行为”(6)鹿守本:《海洋管理通论》,北京:海洋出版社1997 年版,第106 页。。由此可见,海洋生态管理的最大特点在于主体是政府,各种管理行为属于行政行为,这种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仍然没有摆脱“管”的范畴,难以有效地解决海洋生态问题。治理与管理虽是一字之差,但治理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多向度的运行模式等。“而从海洋环境管理到海洋环境治理,体现的却是主体特征、工作方法与权力运行向度的变化”(7)全永波,尹李梅,王天鸽:《海洋环境治理中的利益逻辑与解决机制》,《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1 期,第1 页。。当今全球政治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全球市民社会的不断崛起,这也推动了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在海洋生态领域,全球市民社会的深度参与也给海洋生态问题的解决增添了许多新的动力。
3.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概念析出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根源于全球治理,它是作为全球治理的子概念而存在的,两者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全球治理并非一个新兴的概念,它形成于20 世纪90 年代初期,最早由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于1992 年提出,把它定义为对高度复杂和范围各异的行为进行管控的体系。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多种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以及合作性行动得以采取的一种持续性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8)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23 页。虽然全球治理尚没有统一的概念,但其应具有以下本质特性:第一,主体的多元化,包括主权国家、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正式的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等;第二,要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第三,价值取向应该是超越国家、种族等,聚焦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第四,全球治理的客体应该是影响全人类的、很难依靠单个国家得以解决的跨国性问题;第五,倡导治理手段的多元化,倡导全方位的协商合作。由于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对此可以参考全球治理的本质特征,结合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希冀的效果及其特殊性,对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概念进行剖析,即: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是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在海洋生态领域的具体运用,是指主权国家、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等行为主体,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建立协调规范制度,通过主体间协商合作来解决全球性的海洋生态问题,保护和促进海洋健康、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建立与维护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和谐关系的诸多方式的总称。
4.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外延
“外延”是一个逻辑学上的名词,指的是某一概念的适用范围以及所涵盖的思维对象的数量。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外延,简单来说就是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适用范围与层次。“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中不仅对“治理”一词进行界定,同时指出,迄今为止全球治理并没有一种确定的组织形态模式或制度模式,而是由全球、国家、区域不同层面上的众多的全球行为者共同协商合作而形成的一种合作关系(9)星野昭吉:《全球治理的结构与向度》,刘小林译,《,《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第3 期,第3 页。。据此,从适用范围和层次上而言,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应包括国家间合作、区域性合作以及全球多边合作,这样才构成系统、全面和完整的全球海洋治理(10)鉴于本文讨论的是南海海域生态环境治理,而南海海域属于区域海,故本文未从国内治理的角度讨论此问题。。
其中,国家间合作治理指的是国家双边合作的模式,它以两国政府合作为主,但是也包括两国国内组织及企业的合作治理机制,它具有双方参与度高、治理效率高、安排较为细致等特点。区域性合作治理立足于特定海域,以该海域生态环境改善为直接目标,它以沿岸国、本区域组织的合作参与为主,但不限于本区域内主体,一些国际组织所主导或者参与的区域性治理项目也属于该范围,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主导的“区域海行动计划”。区域性合作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方面一直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行动也要以区域性合作治理为重点,着眼于加深区域性合作的广度、深度及参与度,形成稳固统一的合作治理机制。在全球多边合作治理的层面上,由于统一开展全球范围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难度很大、各参与方利益很难协调一致,因此该层面的合作重点应着力于统一全球治理合作的认知、加强海洋环境治理的国际法基础。总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行动应是不同层面的有机统一,在各层面应该注重有的放矢、协调并进。
(二)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特征分析
1.自然与社会属性统一的治理客体
厘清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客体是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传统的海洋生态环境管理或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对海洋生态环境管理或治理的客体(海洋生态环境)的内涵把握得不够全面,更多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待海洋生态环境,涵盖海洋气候、海水状况、海洋渔业、生物多样性以及海洋突发污染事件等。这种思维模式导致海洋管理或者治理更多地停留在海洋生态事后恢复的层面,加大了海洋环境状况改善的成本与难度。海洋环境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海洋环境仅包括自然要素,依据韩德培先生的定义,“海洋环境指的是地球表面除内陆水域以外的连成一片的海和洋的总水域。包括海水水体、海洋生物,海底、海岸和海水表层上方的空间等组成的自然综合体,溶解和悬浮于海水中的物质、海底沉积物属于海洋环境的组成部分,还包括入海河口区域、滨海湿地和与海岸相连等相关活动的沿海陆地区域。”(11)韩德培:《环境保护法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250 页。广义的海洋环境还包括非自然要素,例如,国内学者鹿守本认为,“海洋环境指的是以人类生存与发展为中心,相对其存在并产生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海洋自然和非自然的全部要素的整体”(12)鹿守本:《海洋管理通论》,北京:海洋出版社1997 年版,第106 页。。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客体应当是广义上的海洋生态环境,包括海洋自然环境以及直接作用于此的海洋经济活动,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因此,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一方面要实现全球海洋生态环境的直观性改善,包括海上固体废弃物减少、海洋渔业资源及生物多样性状态改善、海水水质状况提高等;另一方面要规范各种形式的海洋经济活动,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利用,构建人海和谐的发展模式。
2.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
在2017 年12 月9 日召开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7 年会——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文明分论坛上,挪威气候与环境大臣赫尔格森指出:“海洋治理首先全球要达成共识,利用各自的资源;其次就是要有一个治理框架,要研究机构、公司、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13)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全球海洋治理与“蓝色伙伴关系”学术研讨会在青岛顺利举办》,《太平洋学报》2018 年第9 期,第2 页。。治理与管理的显著区别之一就是多元主体的参与,具体到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领域内,参与主体应该涵盖主权国家、全球性及区域性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甚至是个人。目前通行的海洋生态管理项目的主导力量为主权国家政府以及政府间组织为代表的公权力,但该体制的弊端显而易见。单纯依靠公权力去弥补损失、恢复海洋生态容易受困于污染企业与政府之间信任不强、信息不畅、协调不够的弊病,仅依靠公权力的规则约束、行政介入、职能协调等手段去规范海洋从业者行为、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毕竟有限。随着全球市民社会的不断崛起,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愈发突出,如专门保护鲸鱼、鲨鱼等海洋动物的海洋守护者协会(14)百度百科:《海洋守护者协会》,https://baike.baidu.com/item/海洋守护者协会/6435993,2020 年3 月11 日访问。。非政府环境组织超越意识形态、领土冲突等以全人类的视角为价值取向,尽管在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略显理想化,但是其价值理念值得推崇,其作用也不容忽视。当然,公民个人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也必不可少,着力点应集中在公民海洋环境权意识的崛起,规范好公民主体的海洋活动,自觉维护良好海洋环境。
3.以规则建构为核心
治理理论的创始人罗西瑙认为:“治理通行于规则空隙之间的那些制度安排,或许更重要的是当两个或更多规则出现重叠、冲突时,或者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需要调解时才发挥作用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15)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刘小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9 页。。可以看出,罗西瑙的治理理论是认可治理要以原则、规则、规范的建构为核心的。按照一些英国学者的说法,“制定和执行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的规则是全球海洋治理的要义所在”(16)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曹荣湘,龙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13 页。。规则的建构具体要以法律规范为核心,因此,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要义就在于构建与完善全球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具体涵盖全球多边、区域间与国家间三个层次。在全球多边层次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规范海洋问题的‘宪法性纲领’”(17)史晓琪,张晏瑲:《公海保护区与公海自由制度的关系及发展进路研究》,《中国海商法研究》2017 年第1 期,第79 页。,它的制定标志着国际社会达成有关海洋治理的基本共识,为海洋环境保护开启了崭新的纪元。截至目前,其缔约成员有167 个(18)包括163 个联合国会员国、1 个联合国观察员巴基斯坦、1 个国际组织欧盟、2 个非会员国库克群岛和纽埃,数据来源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parties_to_the_United_Nations_Convention_on_the_Law_of_the_Sea,2020 年8 月4 日访问.,涵盖了大部分的主权国家,但是它毕竟不是专门关于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安排,对此仅有原则性规定(19)如第九部分闭海或半闭海国家的合作涉及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第十二部分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从宏观层面规定了各国在海洋环境保护上的合作义务。,很难单独作为该层次上的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要义”;而一些涉及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约,如《1954 年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1972 年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及其议定书、《1990 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等则由于缺乏足够主权国家的协商参与及对许多国家利益表达的缺失,导致签署的成员国有限。因此,在该层面上应该制定统一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约,重点是力求在国际社会普遍达成关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基本原则、合作理念、行动共识,以提高参与的广度为直接目标。在区域性治理层面上,已经有不少海域内沿岸国也制定了统一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约(20)具体参见下文提及的“区域海公约”。。当然也有一些区域、双边国家间海洋生态保护只是停留在备忘录、合作意向等软法形式,这一特点在包括南海在内的东亚海域尤为突出(21)具体见下文第二(一)部分。。在区域性及国家间治理层面上采取软硬法并兼的规则建构是较为合理的,能够兼具灵活性与拘束力。低敏感的重点领域需要由条约加以固定,其他较多涉及利益导向的内容可以通过软法形式来达成行动共识。
4.以组织管理体制、实施机制为配套
“海洋治理框架是由管理体制、法律法规及实施机制构成的。目前,这一治理框架已广泛而明确地存在于国际、区域及国家层面的海洋治理实践之中”(22)龚虹波:《海洋环境治理研究综》,《浙江社会科学》2018 年第1 期,第104 页。。这一特点运用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上依然适用。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要以规则建构为核心,但组织管理体制、相关实施机制也必不可少。其中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下的组织管理体制区别于传统的海洋管理体制,后者主要是在国家层面上各个海洋行政机构间职能协调,从而提高海洋管理效率的一种行政机制,如美国于1970 年设立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统一行使海洋管理职能;又于2004 年设立国家海洋政策委员会,监督区域海洋委员会的工作,发布海洋政策等。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组织管理体制的革新性体现在:第一,要在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国家双边层面以及国内层面建立统一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各治理主体的相关行动,以达成各层次上的高效协调合作;第二,它的本质不是一种行政机制,而是一种议事协调机制,各主体通过统一管理机构来协商合作、共同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实施机制是指与法律体系相配套的各种具体行动安排、执法与司法的协同,它作为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行动的着力点与落脚点,包括但不限于资金及援助制度、信息共享、污染事故报告制度、应急事故处理、海洋生态恢复共同行动等。
二、当前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制的不足
目前,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治理体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联合国“区域海项目”下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二是多个全球性组织开展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三是南海域内国家、区域性组织开展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合作。目前这三个层面的南海区域性生态治理项目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不足。
(一)“区域海项目”下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不足
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一直是作为联合国“区域海治理”项目的一部分来进行。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组织推动下,“旨在通过共享海洋的方法解决世界海洋和沿海地区加速退化的问题——即通过让邻国参与全面和具体的行动来保护其共同海洋环境”的“区域海项目”(Regional Seas Program,RSP)于1974 年拉开帷幕。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区域海项目”涵盖了全球18 个海域,涉及143 个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该项目以强有力的法律框架为基础、以区域公约和相关议定书的形式解决具体的海洋问题”(23)“Why Does Working with Regional Seas Matter?”,https://www.unenvironment.org/explore-topics/oceans-seas/what-we-do/working-regionalseas/why-does-working-regional-seas-matter,2020 年3 月15 日访问。。以1976 年地中海国家通过的《保护地中海免受污染公约》为开始,在UNEP 的组织或推动下,迄今为止,已有14 个区域海公约(24)“Why Does Working with Regional Seas Matter?”,https://www.unenvironment.org/explore-topics/oceans-seas/what-we-do/working-regionalseas/why-does-working-regional-seas-matter,2020 年3 月15 日访问。通过并生效。南海海域作为由UNEP 直接管理的7 个区域海洋项目(25)这7 个区域分别为:加勒比海、东亚海、东非、地中海、西北太平洋、西非、里海。之一的“东亚海行动计划”(East Asian Seas Action Plan)的一部分,尚未形成有关区域海生态公约。尽管UNEP 认为:“在区域海洋计划中,东亚引领了一个独特的路线——即没有区域性公约;相反,该计划促进遵守现有的环境条约,并以成员国的信誉为基础”(26)“About COBSEA”,http://www.cobsea.org/aboutcobsea/background.html,2020 年3 月15 日访问。。但是,该说法更像是一种借口,东亚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不依靠区域性公约作用有限,而依靠成员国的信誉而非国际法的约束力去推动合作计划的实施也值得怀疑。除此之外,尽管在“东亚海行动计划”的基础上也成立了东亚海洋协调机构(COBSEA)(27)其成员国有10 个,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柬埔寨、韩国、越南,负责协调政府、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和捐助机构以及个人在该地区保护海洋环境方面的活动。,但是该机构毕竟不是以区域性公约为基础成立的,它仅仅是作为一个协调组织而存在,实际的功能发挥极其有限。
(二)UNEP等国际组织主导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不足
目前,关于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各类已诉诸实践的合作计划主要是由UNEP、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海事组织等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发起的,由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际海事组织共同执行的“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PEMSEA)”,以及由UNEP 和全球环境基金共同资助的“扭转南海和泰国湾环境退化趋势项目”。但这些项目到目前还未取得关键性成果。这一事实其实暴露了在南海海域生态环境治理上,以UNEP 等国际组织为主导的现行治理机制存在的问题。
第一,将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限于东亚海生态环境治理的框架内,缺乏对南海海域区域特色的足够考量,加大了合作治理的难度。东亚海域包括日本海、东海、黄海、南海等,甚至澳大利亚部分海域也被划分在东亚海海域内,而且某些海域(如南海等半闭海)实际是作为一个较为独立的海域单元存在的,具有比较鲜明的自然气候特征、生态系统状况。这些海域的沿岸国不同,面临的海洋生态环境状况不一,需要重点解决的生态问题有所差异。除此之外,订立东亚海区域海洋条约的难度与复杂程度也远远大于南海区域海洋条约,前者牵扯的国家众多、涉及利益繁杂,这也是东亚海洋计划迟迟缺乏区域性公约的诱因之一。
第二,上述国际组织的主导力与向心力不足,具体能对沿岸国施加的影响或提供的支持极其有限。UNEP 的使命是“激发、推动和促进各国及其人民在不损害子孙后代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提高自身生活质量,领导并推动各国建立保护环境的伙伴关系”(28)“About UNEP”,https://www.unenvironment.org/about-un-environment,2020 年3 月18 日访问。。由此可以看到,UNEP 更多的是一个促进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议事协调机构,而“UNEP 一直未能突破这种制度设计的局限,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缺少这种制度合法性,必然影响到其能力建设和管理范畴”(29)董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如何渐进强化》,《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7 年第1 期,第102 页。。另外,以UNEP 为代表的国际环境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会员国的捐款,而且环境基金都是专款专用,具体能给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提供的资金支持相当有限。从根本上说,UNEP 力促的海洋治理国际合作所能引发的各国参与度如何,更多地依靠的是国家的道义与责任,而非国际法上的义务,其本质仅仅是作为一种倡议而存在。如果转而采取南海海域当事国去主导、倡导的方法,途径是从单边力倡到寻求双边共识进而扩展到多边参与,依靠的是主导者的区域影响力、资金技术上的援助与互助、经济合作的助推力、合作理念与方案的共通性与现实性,这样的方法更能提高沿岸国参与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热情与深度。
(三)区域性组织开展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合作的不足
除了由全球性国际组织所主导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合作体系以外,还存在着东盟(30)即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简称,包括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十国。与非东盟成员国之间的“10+1”(31)即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10+3”(32)即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框架下的环境合作安排、亚太经合组织(APEC)在亚太地区的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安排、《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对海洋环境保护的合作倡议,甚至包括今后可能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等。这些涉及南海海域生态环境合作的内容,其深度、广度等都无法与前文提及的“东亚海行动计划”相比,它们不能被视作一种合作机制,只能被称为相关合作安排。而且这些合作安排大都是上述论坛、会议等的衍生品,并非有关南海海域生态合作的专门化安排,这也表明在上述活动或组织下,对于南海海域生态合作的重视程度还不高,更多的议题与精力放在经济合作、寻求政治共识等方面。尽管以上述活动为契机成立了一些致力于生态合作的官方组织,如在APEC 经济与技术合作委员会高级官员会议下设立“海洋和渔业工作小组”(Oceans and Fisheries Working Group,OFWG),以及为落实《中国与东盟环保合作战略》而由我国环境保护部于2010 年成立的“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前者作为保护亚太地区海洋环境与资源的官方常规活动机构,其核心目标在于“确保海洋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以支持渔业、水产业的发展需求”(33)《APEC 海洋和渔业工作小组》,https://www.apec.org/Groups/SOM-Steering-Committee-on-Economic-and-Technical-Cooperation/Working-Groups/Ocean-and-Fisheries,2020 年3 月21 日访问。,看起来更侧重于后半部分——对于经济效益的考量,而且其范围涵盖整个亚太海洋,这几乎将世界一半海洋涵盖在内。而后者的定位是:“区域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与智库平台、区域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基础性支撑力量、环保技术与产业合作与交流的平台、南南环境保护合作的技术支撑”(34)《“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简介》,http://www.chinaaseanenv.org/zxgk/zxjj/201612/U020171106402682831249.pdf,2020 年3 月21 日访问。,可见该中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生态合作的平台而存在,并非执行具体合作机制的机构。总之,这两个机构都不是专门针对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而设立,很难在南海海域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尤其是在面临突发性海洋生态事故(譬如海上溢油事故)上,发挥足够的作用。
三、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完善建议
(一)把握好中国与东盟各自的角色定位,消除治理行动上的误解
在现行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东盟凭借其构建的地区系列对话机制,始终扮演着‘驾驶员’的角色,不遗余力地掌控着议程设置、规则制定和机制建设的主导权”(35)吴士存,陈相秒:《论海洋秩序演变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太平洋学报》2018 年第4 期,第32 页。。但是,受制于大部分东盟成员自身经济实力有限、发展水平不高,经济效益考量会优先于生态环境考量,导致他们对于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意愿与参与度有限;加之资金、科技水平的制约,以东盟为“驾驶员”推动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现实性与实效性不高。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不是由单一国家或者几个国家所主导的价值模式,它倡导的是机会均等、广泛参与、平等协商,以全球思维、合作理念解决生态问题。中国在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中国所参与的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不是为了展现自己力量、扩展海权与势力范围,而是为了弥补传统国际机制“治理失衡”与“治理赤字”的问题。
东盟的宗旨在于“本着平等与合作精神,共同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36)百度百科:《东盟》,https://baike.baidu.com/item/东南亚国家联盟/1059562?fromtitle=%E4%B8%9C%E7%9B%9F&fromid =168517&fr=aladdin,2020 年3 月25 日访问。,它在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关注点不应置于对治理体系话语主导权的争夺,要杜绝成员国的恶意揣测,防止刻意制造不和谐,不能将生态环境治理视为地区政治平衡、权力对抗的工具;更多的关切点应放在东盟成员国经济发展、生态改善的切实利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惠及南海各国经济发展,亚投行与丝路基金提供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资金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中国的善意,除此之外中国也会提供技术信息等支持,积极参与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东盟应该把握此大好机会,积极主动地转变角色,运用好“东盟方式”(37)其核心是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坚持通过非正式协商来达成全体一致的原则。(The ASEAN Way),发挥好内部磋商的功能,促进东盟南海沿岸成员国内部达成共识,积极参与由中国所主导的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
(二)倡导多元主体的参与,构建人海和谐的发展模式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倡导多元主体的参与,这对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当前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参与主体限于沿岸国家甚至域外国家、国际政府间环境组织、区域性政府间组织。这并不符合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合理吸收非政府组织、企业甚至个人的参与。
第一,应把握好非政府间环境组织在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需要发挥的功能。“非政府间环境组织的出现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环境危机,这些环境危机一些是本地的,一些是区域性的,还有一些是全球性的。作为以国家为导向、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的国家体制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存在困难”(38)Grant J.Hewison,“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Ocean Governance”,Ocean Yearbook,Vol.12,1996,p39.。非政府间环境组织参与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可以从以下角度开展:(:(1)非政府组织可以参与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制定过程,通过提供数据信息、专业意见等方式进行非正式的磋商参与。例如,国际捕鲸委员会(IWC)作为观察员出席“伦敦倾废公约年度会议”并提供相关专业意见,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治理可以借鉴这种做法,吸收非政府组织的参与。(2)非政府环境组织可以向南海沿岸国政府、国际及区域性政府间组织提供相关研究报告,以弥补国际信息和数据收集方面的空白。非政府组织经常参与编写科学实地研究报告等,它们在此方面实践经验丰富。(3)非政府环境组织可以通过出版专门书籍和宣传手册、研究论文或发布宣传视频等提高民众对于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度。
第二,企业作为南海海洋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上述政府主体、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环境组织的主要干预对象,“也是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支撑力量和生产力量”(39)王琪,何广顺:《海洋环境治理的政策选择》,《海洋通报》2004 年第3 期,第75 页。,其在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合理把握企业在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需要借鉴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治理客体理念:即海洋生态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自然属性在于海洋生态环境的直观改善,表现为水质改善、海洋生物多样性提高、海洋环境优美等,对此可以有限度地借鉴环境法中的“污染者自负原则”,加大开发企业在南海海洋生态恢复中的责任,由以石油企业、船舶企业为代表的南海经济获益者设立“南海开发者生态保护基金”,用以改善与恢复南海海洋生态状况。海洋生态的社会属性在于规范以企业为主的海洋经济活动。但企业的自发行为会以利益为导向,道义与法律上的约束不如利益激励的作用明显。对此可以设立“南海企业环境友好激励制度”,给予那些注重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企业以物质奖励,如在同等条件下给予该企业以资源开发优先选择的权利。
第三,公众(如渔民、游客)一方面会参与南海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公众作为海洋环境权的享有主体,南海海洋生态环境关乎公众切实利益。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在海南省开展“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也是自贸区建设的重要内容(40)《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http://www.gov.cn/xinwen/2018-10/16/content_5331223.htm,2020 年7 月31 日访问。,公众更要主动参与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一方面民众力量分散但广泛,在海洋生态环境污染事故报告与反馈上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同时更要发挥好监督者的角色,重点监督各种海洋经济活动。另一方面更要通过宣传教育唤醒民众海洋环境权的意识,增强民众尤其是沿岸居民对南海海洋生态环境的关注度。南海海洋经济从业者在开展经济活动的同时,牢固树立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自觉维护南海生态环境,从而构建起南海人海和谐的发展模式。
(三)建立以规则制度为核心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
前文已指出,虽然“缺乏海洋保护公约是东亚海生态保护的一大特色”,但是鉴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要以规则建构为核心要义,即在全球多边层面上制定统一的海洋生态保护公约,在区域性及国家间层面上形成以公约为核心、软硬法并兼的海洋保护规则体系。对此,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也不具有特殊性。
第一,在全球多边治理层面上,南海有关各方应该积极参与全球海洋保护公约的制定过程,在此过程中积极阐述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特殊状况、对自身合法利益做合理表达,使该公约可以充分吸收考虑这些因素,方便它与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特性融洽对接。
第二,在区域性治理层面上,制定统一的南海海洋保护公约势在必行。而统一的南海海洋保护公约应坚持开放多元的态度,尊重各国基于利益考量所作的保留,因为“要协调众多国家的意愿和要求而制定出统一的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公约是有一定难度的”(41)张丽娜,王晓艳:《论南海海域环境合作保护机制》,《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6 期,第46 页。。对此可以革新传统区域性公约的协商方式,不宜采用南海域内各国多边接触、统一磋商的方式,转而通过东盟与中国双边磋商来推动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约的达成是更为明智的选择。通过区域组织的行动先行可以加速在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上持“观望者”身份的成员的步伐,推动东盟内南海成员国在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约上的步伐一致,可以有效避免公约的制定进程因陷于单个成员的行动迟疑而停滞不前。在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约的体系构建模式上,业已形成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体系(42)即“由分立到综合”的模式:从某一领域的合作实践开始逐渐推广至更大范围的合作,从1969 年为应对海上油污而订立《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最终到全面涵盖海洋生态问题的《OSPAR 公约》。、赫尔辛基公约体系(43)即“由原则到规则”的模式:波罗的海沿岸国直接于1974 年签署了《赫尔辛基公约》,规定了海洋环境保护的原则性问题,而后通过附录将具体的海洋环境保护的规则、程序加以规定,公约与附录是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沿岸国要一并签署。和巴塞罗那公约(44)即“公约-议定书”模式:地中海沿岸国直接制定了《巴塞罗那公约》以及各项议定书,前者规定海洋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般义务,后者规定了具体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措施、标准和程序,沿岸国签署公约后可以有所保留,选择至少一项议定书签署即可。体系这三种类型。南海区域性海洋保护公约可以借鉴巴塞罗那公约体系的构建模式,即采用“公约-议定书”的形式,将合作机制的框架、组织机构等原则性内容通过公约固定下来,而后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有步骤地由浅入深地签订某一议定书。其中议定书可以主要包括防治陆源污染议定书、船舶污染议定书、倾倒污染源议定书、海底开发污染议定书、渔业开发及海洋生物多样性议定书等,这样的方式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
第三,在国家间治理层面上的双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条约可以起到补充强化的作用。南海区域目前涉及双边生态环境保护合作的法律安排,如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于2007 年签署的《海洋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就涵盖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合作的内容,但这些法律安排也仅仅是停留在软法层面,容易受制于国家关系的变化而陷于停滞。双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条约不仅具有法律拘束力,而且更具针对性与可实施性。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双边条约与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区域统一公约并不冲突,两者可以相互协调、有机统一共同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具体来说,在尚未制定统一的区域海洋保护公约时,双边条约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先行作用,可以为制定统一区域公约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即使已经制定了统一的区域海洋保护公约,双边条约也可以在不违背区域性公约内容的前提下以两国间法律互信为基础,针对两国间某一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现状进行更加具体、更具针对性的法律合作安排。
除了制定相关公约外,南海现行存在的各种涉及海洋合作的软法机制:包括《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正处于磋商阶段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甚至前文提及的UNEP 的行动计划,以及国家间双边层面上的各种备忘录、合作意向等;在减少分歧、加强互信、巩固合作基础与成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以公约为核心、软硬法并兼的规则体系才是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道路选择。
(四)完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组织管理机制及相关实施机制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理念运用到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上,还要求完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组织管理机制及相关实施机制。对此,第一,要整合现存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合作机构,建立统一的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委员会,给予该组织以足够的决策权及管理权,而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议事协调机构存在,同时要利用好UNEP 所搭设的现存平台,注重与全球性环境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第二,要开展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演,增强各国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理能力,同时要加强双边及多边层面的组织机构联动合作。第三,要完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保障机制,除前文提及的以企业为主体的开发者基金外,还要形成以沿岸国家为主要捐助主体的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基金,可以由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委员主管运营该基金。基金的捐助份额可以按照所辖海域大小、各国南海经济获益状况、各国实力状况等配置捐助金额和比例。第四,要完善信息分享与事故通报制度,建立统一指令、反馈及时的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信息互联中心,可以归属于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委员会下。第五,要加强海洋生态环境领域的科技合作,不仅仅是事后污染处理技术的合作,还包括海洋监测技术的合作、海洋水质标准的统一,乃至开发企业在绿色化生产方面的合作等。上述机制与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法律体系互相配合,推动南海海洋生态环境状况的改善,构建起人海和谐的发展模式,有利于将南海打造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更是“美丽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