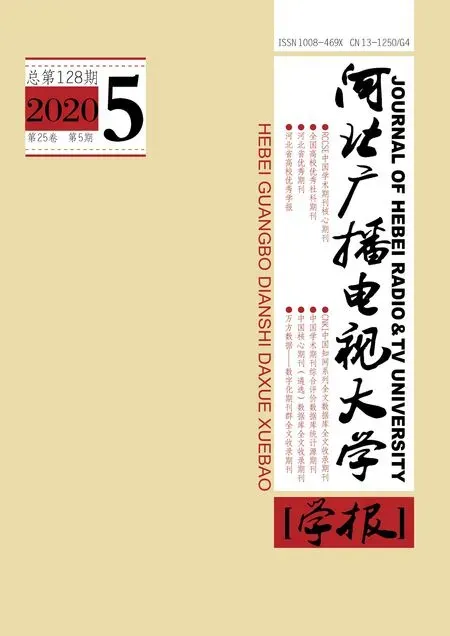工业化进程下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衍变
——以近代宝坻手织布区为例
由俊生
(天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1860 年开埠后,天津开始了近代工业化进程,受其所带来的积极影响,环津圈区域的手织业形成了两大繁荣区域:高阳手织布区和宝坻手织布区,这是城市工业化对周边区域经济积极影响的一个主要现象。当前,学术界对高阳手织布区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①相关高阳手织布区域的研究多从经济角度考察,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森时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日资纱厂与高阳织布业》,《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4 期;彭南生:《论近代中国“半工业化”——以华北乡村手工织布业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 年第5 期;顾琳:《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王玉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冯小红:《高阳模式:中国近代乡村工业化的模式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 年第4 期;孟玲洲:《城乡关系变动与乡村工业变迁——以近代天津和高阳织布业的发展为例》,《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3 期等。,而对宝坻手织布区的研究则较为薄弱,目前很少有学者从近代工业化背景下来探讨具有地缘优势的宝坻手织布区的变迁轨迹及其特征。
随着城市近代化的发展和城市工业化对周边区域的影响,手工棉织业之中心“均在通商大埠如上海、汉口、天津、广州等地附近之四乡”。②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南京:国立编译馆,1934 年版,第276 页。得益于天津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属于其“四乡”范围的宝坻、香河、三河逐渐发展成一个以宝坻为中心的新兴手织布区域。③它是一个以宝坻县的新集镇、香河县的渠口镇和三河县的皇庄镇三镇鼎足而立为中心,涵盖宝坻县城城关镇、新安镇、林亭口镇、大口屯镇、黄庄镇等,香河县的刘宋镇等和三河县的皇庄镇所辖的各个村庄在内的纺织区域。这个手织布区域经历了怎样的兴衰衍变历程?衍变中的手工业生产组织形式和制度出现了怎样的变革?它们在手织业变迁中的作用如何?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和深入研究。本文将在近代城市工业化的大背景之下,主要依靠这一时期的丰富史料,着眼于近代宝坻手织布区域的变化发展,探讨手织业从传统的独立主匠制家庭手工业向包买制家庭手工业衍变的兴衰历程,“尽量基于数据做定量分析,以探明其实际状态”④森时彦:《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袁广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版,第2 页。和特征,以求从历史角度对当前方兴未艾的乡村工业化提供一点有意义的借鉴。
清光绪末年以后到1915 年时,宝坻县的乡民织布渐渐改用铁轮机,这是宝坻手织业兴盛的开始,随后近邻的香河县与三河县开始积极效仿并共同形成了一个繁荣的手织布区域。宝坻手织布区经历了兴起、兴盛和衰落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宝坻手织布区的初步发展时期(1902—1916),独立主匠制①独立主匠制家庭手工业下的手织业只是农户的一种副业,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和交纳赋税,剩余部分才拿到市场上出售。在中国漫长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手织业在家庭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包买制家庭手工业时期,手织业成为家庭主业,产品以满足市场消费为目的,织户领取工资或代替工资的原料。家庭手工业向包买制家庭手工业演变
和华北其他农村地区一样,宝坻、香河、三河自古以来一直有纺纱织布的传统,并以传统家庭手工业为主。到19 世纪末,随着天津开埠及其近代工业化的影响,该地区手织业开始发生变化,以出售家庭剩余手织粗布②即传统土布,原料为手纺纱或来源于印度的机纺粗纱。为目的向以生产手织商品细布为目的转变,并形成了著名的手织布区。在这一“传统部门的演变时期”③森时彦:《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袁广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版,第2 页。的初期,织户使用的织布工具是效率较高的拉梭机,它在19世纪末代替了效率低下的投梭机。拉梭机虽然提高了织布的效率,但仍然属于传统的家庭手工业生产,不足以引起生产力的变革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这种变化虽然潜伏着生产扩大后既无多余的资本亦有生产过剩之忧,却为手织业从传统土布(手织粗布)纺织向改良土布(手织细布)的转变打下了基础。不久,这种潜在的不确定因素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消失了——铁轮机的引进,“庚子年间,新式日本织布机即由津运入”④殷梦霞、李强:《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2 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版,第590-591 页。,并伴随着新式织布方法的传入和机纱的广泛使用,新式织布工具很快普及开来。
随着布匹商品交易的扩大,资本雄厚的布商为了节省资金和简化收布的手续,随“由商人自行供给棉纱,交由织工纺织,然后按件予以工资,较为简单……宝坻织布工业商人雇主制度(包买制)之由来,殆由于是”。⑤方显廷、毕向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方显廷文集》(第3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第156 页。这是传统家庭手织业转型的开始,其表现特点是独立主匠制向包买制转变,包买制的初级形式换布制开始出现。到民国初年,“时城东各村屡遭水患,农产品多为淹没,农民生活生问题。城内永善堂为救济农村发展手工业起见,乃出资购机械及棉纱,散给各村农家,令其织布,限定日期交活,每匹给以一定之工资。所产之布,则销张家口、古北口、内蒙古、东三省一带,名为永机布(因工厂由永善堂所组之故),成绩优良,获利甚厚,是为土布之始。其后他人见有利可图,群起仿效,土布之贸易乃日臻活跃”。⑥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415 页。而包买制的高级形式撒机制因此开始流行。到1913 年,宝坻手织业“成熟其新型,产生出新的布商,新的手工业制度”。⑦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419 页。至此,包买制日臻完善。
由此可见,从手织业转型伊始,包买制就如影随行了,只是最初的表现形式多为散活制。⑧散活制就是换布制,也称其为制定货、换纱制、换线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宝坻手织业还有了零星的作坊手工业,据史料记载,1915 年后,“少数小康农家,自行开场织布,首置五机,以后增为十机,雇工织布,最盛之际,达十余人之多,每年生产约一千匹至三千匹,各有特殊商标,以别于邻家生产”。⑨方显廷、毕向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方显廷文集》(第3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第168 页。说明宝坻手织业不仅发展到了作坊手工业阶段,还拥有自己的品牌。这种小规模的布厂在最繁荣时期有十余家之多。当然,宝坻的手织业还没有发展到作坊手工业占主导地位的阶段。这种作坊手工业的发展是否带有包买制工场经营的特征目前还没有得到史料的佐证。但是制度的变革仍然是宝坻手织布区乃至整个近代乡村手工业的一个明显特点,它的出现对织户而言起到了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解决了织户资本匮乏的问题,促进了手织业的兴起。制度的兴衰深深地左右了手织业的变迁,二者衍变的曲线基本都是重合的。
二、宝坻手织布区的繁荣时期(1917—1929),布匹的产量花色种类销量日臻发达且能满足不同阶层的需求
“1917 年以后,手织业大兴,全县一、四、五、八、九区操是业者为数尤多。每村织布家占五分之四,务农者占五分之一,其他各区亦有之,但位数较鲜,全县合计有铁轮机六千架以上,尤以新集镇及县城四郊为最盛。”①殷梦霞、李强:《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2 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版,第591 页。此时,“宝坻县的工商情形,完全以织布业为中心,全县人民生计,亦惟此事赖。……总计全县人民,以织布为业者,约占十分之七八。”②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202 页。在香河县,“本县临近宝坻,故布业颇为发达,二三两区各村镇织户达两千五百户,……产量为两千五百万匹,共值一百五十余万元。”③殷梦霞、李强:《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1 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版,第558 页。三河县也是如此,“县东南各村,恃此为生计者,十之七八,营业日臻发达”,④殷梦霞、李强:《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1 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版,第558 页。一战给宝坻手织布区提供了大好的发展机会,使其布业走向繁荣,并在1923 年达到顶峰,“该年销棉纱五万三千包,产布四百八十万匹”⑤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年版,第243 页。,而且随着市场的不断拓展,手织布的种类也呈现多样化趋势。到1924 年,因受害于当年的直奉战争⑥直奉战争后,热河市场处于奉军控制之下,“其政治经济之状况,已极恶劣,诸如战祸遍野,纸币滥发,苛捐杂税等等,宝坻棉布之贸易,胥受影响”。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20 页。,永机布的织造开始出现衰落,年产此布五六万件,但这一时期大尺布的产量还在上升,甚至超过了永机布的产量,年产货十万件,除在本地销售外,销往东三省居多,还有北路的张家口、热河和赤峰以及西路的宁夏一代,从而维持了手织业的繁荣。到1926 年,永机布中兴,又恢复到年产十万件左右的史上最高水平,价格由原来的两元上升到两元三四角,这种繁荣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929 年。
宝坻手织布区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布匹种类和产量增加等方面,但是三县各有自己的特点:
宝坻县所产改良土布主要有永机布、本机布、大尺布和爱国布等布种。永机布是手织布改良后最早的一种仿洋布,属于窄面布,也是产量最多和产值最高的。民国初年,“有布商永善堂提倡模仿长三十三尺,宽六寸五,重二斤半之高阳布式样,向各村织布家,定织长三十二三尺宽六寸五六,重三斤之布,即谓永机布是也。永机布大别有花条布、市布、斜纹布三种”。⑦殷梦霞、李强:《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2 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版,第591 页。最早的永机布“用十六支纱织成,”后来经过改良,经线的数额、布匹的长度和宽度、重量都增加了。在这一时期,仅新集镇和县城四郊两处年产永机布约十万件,到1923 年,全县的永机布总量为2 104 344 匹,占布匹总产量的44%。本机布是由祥庆经理张文英在1910 年去热河考察市场后首先开始织造的,以供销售热河市场,其产量仅次于永机布,每匹长五十六点四尺,宽三寸三三至三寸六,重五点三四斤,用十支到十六支纱织成,年产量为1 482 606 匹,占布匹总产量的31%。占第三位的为大尺布,是“仿照由东省(东北三省)购来长三十二三尺,宽七寸四五(其成色不同,分为上中下三等)之草包四十匹布,制成同样长度宽度约重三斤半之布,即今所谓大尺布是也”。用十六支纱织成,“每年出产总量占全县布产百分之十七”。⑧方显廷、毕向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方显廷文集》(第3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第159 页。仅新集镇和县城四郊两处年产约五六万件,全县的大尺布总量为813 042匹。还有一种在一战中兴起品质较差售价较低的爱国布,多是在宝坻手织布区附近销售。除了永机布、本机布、大尺布和爱国布外,还有宽面布,主要销往河北省各县。
三河县“所产手织布种类甚多”⑨殷梦霞、李强:《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1 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版,第13 页。,窄面布有四种:大布、大尺布、永机布、定机布,均长五十九尺宽一尺三寸;宽面布有三种:布长一百三十尺宽二尺七寸重十三斤的大標;布长一百二十尺宽三尺三寸重八斤半的二標;布长一百零八尺宽二尺六寸重十三斤的大线布。香河县所产手织布有三种⑩殷梦霞、李强:《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1 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版,第562 页。:布长三十二老尺宽六寸五六分老尺(合度量尺一尺余)的干织布;刘宋镇农民多纺织的长二十八老尺宽六寸二分老尺的干线布;渠口镇附近农民多纺织的长一百三十老尺宽二尺六寸老尺洋標,这种布匹质量上乘,能与日本飞鱼牌洋標形成竞争。
总之,宝坻布匹尽管种类繁多,但是没有以染色棉纱或白色棉纱或极少量的棉纱、麻丝的花股线织成的条子布、格子布和呢布等更精致,竞争力更强的布匹种类,这也是宝坻手织布区衰落后无法复兴的一个主要原因。从整个手织布区的情况来看,无论是织机的改良、棉纱的引进还是包买制度的流行,宝坻县一直都起领先的作用,其余两县皆紧随其后仿效之。不仅如此,宝坻县的手织布匹种类较多,创新能力较强,产品总体上适合中下层老百姓的消费需求,而香河县虽然布匹种类最少,但其洋標的生产适合富裕阶层的需求,且能与洋布形成竞争。三河县的手织布生产紧紧追随宝坻市场,自身则没有比较明显的特点。在手织业不断繁荣的情况下,它在“地区经济总量及家庭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手工业依附于农业的自然经济状态,转向与工业化建立起更密切的联系”。①彭南生等:《固守与变迁——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农村手工业经济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28 页。
三、宝坻手织布区的衰落时期(1929—1935),局势危乱和经济危机导致市场萎缩,包买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宝坻手织布区的繁荣给当地带来了诸多益处,不仅有利于织户收入的提高,而且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29 年,手织业开始出现了明显衰落的迹象,其表现是织机数量下降、布匹产量减少、生产萎缩。从织机总量来看,这一年织机总数为10 158 架,比1923 年顶峰时期减少了12 000 架;布匹总产量为320 万匹,与1923 年顶峰时期的480 万匹相比下降了33%,仅占河北省“年产布2 398 万匹”②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 年版,第3 页。的13%,其中最畅销的永机布年产量则降到两三万件,为全盛时期的三分之一,其后产量有所回升但数量不大;大尺布的销量也在减少,年出货降至五千件。这是宝坻手织业的第一次衰落,但从总体上来说,手织业还是比较繁荣的,手织布的价格也没有大的变化。
到1930 年时,手织业稍有复苏但总体上仍呈下滑趋势,从这一年开始,机纱的销量也大幅度减少,“从1919 年到1928 年连续年销一万余包的机纱开始减为两三千包”。③殷梦霞、李强:《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2 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版,第589 页。机纱销量的减少意味着布匹产量的下降。此时的永机布每年产货可达五六万件,为顶峰时期的一半,价格没有大的变动,但是大尺布已经衰落了,“每年只出少数,供当地需用而已”,其他的小种类布匹产销量更是可想而知。1929 年,宝坻手织布区“总产量为301万匹布,消费棉纱为112 500 担”,④方显廷、毕向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方显廷文集》(第3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第138 页。其中,仅宝坻一县的手织布产量有“两百余万匹……值七百余万元”,⑤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二),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版,第490 页。这一年的布匹总量还不及1923 年宝坻一县在热河一省所销售的数量(330 万匹)。到1930年,手织布匹总产量降为265 万匹,价格也在下跌,布匹的销售量也在锐减,永机布销售仅一千余件,大尺布的销售情况不变。到1933 年,“销纱一万三千余包,产布一百六十余万匹”,⑥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55 年版,第243 页。机纱的销量为1923 年的五分之一,布匹产量仅为1923年的三分之一。这一年,“永机布的销量仅为58.7万匹,比1923 年减少了72%;本机布的销量仅为35 万匹,比1923 年减少了76%;大尺布的销量仅为23.4 万匹,比1923 年减少了72%;宽面布的销量仅为17.9 万匹,比1923 年减少了55%”。⑦方显廷、毕向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方显廷文集》(第3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第175 页。这种销量锐减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35 年。到1935 年,手织业“竟一落千丈,农民改业者改业,布商关门者关门,昔日群意所向之业,今渐视为畏途,生产与贸易剧减,及及乎不可终日矣”。⑧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709 页。
与此同时,织户的工资也在降低,在布业繁荣时期,如1921 年,每织一匹布散户的工资为0.362 元,到1929 年,散户的工资降为0.158 元,降低了56%,不可谓不重也。随着机纱销量和布匹产量的锐减,包买商和传统布商也在减少。在宝坻手织业鼎盛的1923 年,仅宝坻县“包买商就有67 家,传统布商有26 家。到1931 年布业衰落之际,包买商只剩下18 家,传统布商增为34 家”。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208 页。随着包买商的减少,传统布商稍有增加,只是增加的数量不如包买商减少的数量,这是因为一部分包买商转营他业。此后,随着布业的衰落,不仅包买商退出历史舞台,到手织业衰落的晚期,布商也在逐年减少了。“近年织布事业凋谢,……例如1933 年顷,上述县城新集二处,遗存布商不过三十家。”②方显廷、毕向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方显廷文集》(第3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第157 页。
宝坻手织布区的衰落原因诸多,但最直接的原因是局势危乱和经济危机导致的销售市场萎缩。东北三省是宝坻手织布区的主要市场,受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影响,其东北市场销量开始减少,1930 年西北地区水旱灾害不断,当地老百姓购买力下降,西北市场广受影响。1931 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华北局势,瞬息万变,不特如此,该年秋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中国农村开始萧条,“1929—193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及随后日本的侵华战争,是加速乡村手工业衰败的外力”。③彭南生:《欺诈行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衰变》,《江汉论坛》,2006 年第10 期。宝坻手织布的销售区域主要在东北西北华北广大农村,这给手织布的销售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市场萎缩,“至民(国)二十年,共减少百分之四十四,亦即宝坻布匹在热河之市场缩小几一半矣”。④方显廷、毕向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方显廷文集》(第3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第180 页。1932年热河市场因日本侵占而萎缩,宝坻布匹“销路日疲,较诸常年减去三分之二”⑤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二),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版,第505 页。,1933 年塘沽协定后,东北和热河市场的沦陷给宝坻手织业致命的一击,使其严重衰落;雪上加霜的是,这年春天,伪“满洲国” “对宝坻棉布征收的进口税,每包(30—40 匹)17.55 元,到宽城县后每包又加征印花税4元,合计每匹布增加费用6 角左右”⑥方显廷、毕向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方显廷文集》(第3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第181 页。,到1934 年,宝坻手织布区在东北市场布匹销量仅剩3%;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纱走私猖獗,造成纱价跌落,布匹销售又减少了75%。
市场萎缩导致布商利润降低,这种恶果最终转嫁到织户身上,织户所受剥削加重。而织户为了生存,为了弥补布商过度剥削所带来的亏损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其所织布匹的质量就会人为地被降低,“织布者浆纱之时,恒以白垩涂之,用增分量。多增白垩一两,即增棉纱一两,即可多得一两棉纱之利,因是之故,信用丧失”。⑦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三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202 页。这就会导致布商的信誉一降再降,进而导致市场进一步缩小,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此类事件屡有发生,如宝坻布匹运往山西市场,因布匹掺假,“往往未经售出,既已腐烂……买卖双方至于诉讼,而自此山西销路大减”。⑧方显廷、毕向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方显廷文集》(第3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第182 页。上述的这些不利因素直接影响了宝坻手织布区的发展,使其彻底走向衰落,“仅通县东站运输的土布在1934 年降至低点,为1 835吨”。⑨殷梦霞、李强:《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1 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版,第113 页。此时,宝坻手织布区的销路只剩下西路即西北的宁夏、绥远,北路只剩下张家口了。即使在这些销售区域,宝坻手织布也受到其他手织布区所产布匹的强有力竞争,如江苏南通、山东潍县、河北高阳与定县的手织布,它们在失去东北市场后迅速转向了西北市场,“高阳织区,既因销路狭隘,谋向此数省(晋察绥蒙)推销;南通织区,亦因东北丧失,有向此数省寻求出路之意”。⑩严中平:《手工棉纺织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严中平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 年版,第434 页。至此,华北乡村手织业的近代化进程被日寇侵华所打断了,近代城市工业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也微不可察了,宝坻手织布区丧失了一次由传统手织业区转型为区域型工业中心的机会,其农村经济也因为传统手织业的中落而一蹶不振。
四、结语
进入近代后,城乡关系明显的一大特点是城市工业化会带动周边腹地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甚至在其周围形成新的手工业经济区域,这是城乡经济关系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也是近代天津与周边腹地经济互动的主要内容。随着新的手工业经济区域的发展衍变,其自身会借助地缘经济优势获得城市提供的工业品和技术支持而形成自己的经济体系,推动原来的维系在自然经济体系内的城乡关系向商品经济体系内城乡关系转变,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破茧成蝶,向区域型工业中心转化或转型为城市次中心。
在天津开埠至1935 年间,宝坻因特殊的地缘经济优势和对传统手织业的创新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与近邻的香河、三河形成了著名的手织布区域,周边的乡村经济也在其带动下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具有原始工业化特色的经济区域,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典范。在这个过程中,借助于大城市工业发展的带动,宝坻手织布区获得了优先发展的区位优势,经历了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和制度的变革,并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销售网络,打破了华北区域“乡村社会经济自身以小农生产为依托,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作为世代相传的内陆经济结构,形成一种自给自足的简单复制与循环发展模式,无法为城市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源和保障力”①任吉东:《近代中国百年城乡关系的两极性衍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4 月18 日。的魔咒,不仅使得农村手工业依附于农业的自然经济状态发生了质的改变,使手工业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而且反过来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依靠且朝着区域型工业中心缓慢衍变。遗憾的是,宝坻手织布区尚未发展到成熟期就为外力所阻断,最终走向衰落,但这也为当前正在不断推进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一条可以借鉴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