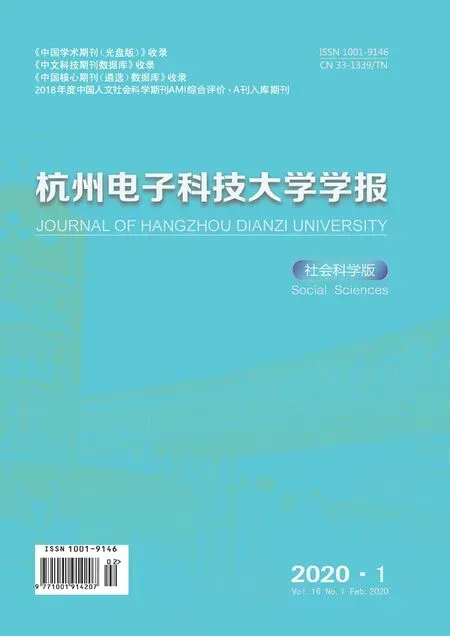葛浩文的文学翻译忠实观及其实践
黄卫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2012年,莫言成为我国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本土作家。随着莫言获得巨大成功,其背后默默耕耘的翻译家,包括葛浩文(英语翻译)、杜特莱夫妇(法语翻译)、陈安娜(瑞典语翻译)、藤井省三(日语翻译),进入普通读者视野,成为焦点人物,受到国内媒体和学界空前的关注。其中,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居功至伟,尤其引人瞩目,被媒体称为“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在国内媒体对葛译在莫言获奖中的作用推崇备至的同时,学界则对葛浩文的翻译策略存在不同声音。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葛浩文的翻译是否遵循了基本的忠实原则。批评者认为,葛译“不忠实地肆意操控、篡改,扭曲了本意,可谓罪人”[1],“葛译的改写是个人意识形态体现的典型例子”[2]。葛浩文的部分支持者同样认为,葛译的成功归因于其“删节、改译、整体编译”的翻译策略,并据此对以忠实为原则的翻译观提出质疑。
事实上,葛浩文既没有违背翻译基本的忠实原则,也没有更新“做翻译要忠实于原文”的常识;他只是翻译忠实原则的真正践行者,其译文对本质意义上的文学忠实作了最好的诠释。换言之,与其说葛浩文改变了翻译忠实的基本原则,不如说他通过自己的实践让人们真正理解了文学翻译忠实的含义。从理论意义上来说,葛浩文的翻译实践推动了文学翻译领域关于忠实问题的讨论,其强调“整体的翻译和文学意义的忠实”的观点是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翻译忠实观的颠覆[3]。
一、葛浩文的文学翻译忠实观
虽然葛浩文不是翻译理论家,但他在《亚太同济会季刊》等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探讨翻译的文章,阐述了自己对翻译的认识和看法。2002年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写作生活》一文尤其具有代表性,是葛浩文翻译思想的集中体现[4]。基于这些文章和葛浩文的翻译实践,不少学者对葛浩文的翻译观进行了分析,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葛浩文翻译观探究》,该文把葛浩文的翻译观概括为四个方面:忠实,翻译即背叛,翻译是重写,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5]。虽然论及葛浩文翻译观或翻译思想的文章对葛浩文关于翻译忠实的看法多少有所提及,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专文对葛浩文的文学翻译忠实观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
忠实不仅是翻译活动应该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翻译研究中需要不断探讨的一个根本问题,更是保证翻译自身存在的伦理要求[6]。因此,“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是所有翻译理论家和从事翻译工作实践者的基本共识。不过,译界对忠实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一种观点认为,忠实只是相对于源语文本而言的,最具代表性的说法就是我国翻译界普遍流行的“信、达、切”三原则,把忠实等同于“信”;另一种观点认为,对原文的忠实就是忠实于原文的语言文字。但葛浩文对忠实的理解不同于这两种狭义上的“忠实”,而是更接近我国著名翻译家刘重德先生的提法:“严格说来,忠实是对信、达、切三个原则的概括”[7]。换言之,忠实实际上包括了“信”“达”“切”三要素。
与大多数翻译家一样,葛浩文认为,译者的首要任务是传达作者的思想,因此应该把忠实于原文放在首位。这一观点在他谈及翻译的文章中一再被提及。在《写作生涯》(2002)中,葛浩文提出,“忠实是译者的首要任务”,翻译在内容上必须与原文保持一致[4]。在《翻译季刊》上发表的论文中,他表示,自己一直试图在语气、情感、细微差别以及其他方面保持对原文的忠实,但由于自己主要从事翻译实践,依靠的是转换直觉,而且在汉语及中国文化知识等方面都存在欠缺,因此翻译过程中损失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8]。葛浩文的这种忠实观典型体现在他关于重译《骆驼祥子》的想法中。当时,《骆驼祥子》已经有三个译本,但他认为都不好。第一个译本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把原文悲剧的结局改成了喜剧性的结尾,导致原著遭到完全歪曲。第二个译本依据老舍出于政治需要修改后的版本,而且以字面翻译为主,无法体现老舍作品风格。第三个译本虽由美国人执笔,但英文表达并不到位。在葛浩文看来,这些译本“实在对不起老舍”,因此他觉得有重译的必要[6]。由此可见,葛浩文在关于翻译的看法上并没有背弃传统意义上的忠实原则。相反,“忠实一直都是指导葛浩文翻译的第一准则”[5]。
对于葛浩文来说,忠实首先体现在文本类型和语言的选择上。他认为,译者在选择文本时不能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就他本人而言,他认为自己的汉语水平有限,只能理解中国现当代小说,因此他不会尝试翻译中国古典文学。葛浩文还强调,他选择翻译的文本不仅是自己擅长的文学领域,而且是自己感兴趣的:“我要挑一个作品,一定是比较适合我的口味,我比较喜欢的。”[9]在语言转换类型问题上,葛浩文认为,对于译者来说,最理想的翻译类型是从外语向母语的转换,即“译者应能熟练地阐释源语及其文化,并能用译入语自如地表达”,而“译入语最好是其母语”。他认为,自己虽然用中文写作不存在问题,而且已经出版两三本用中文写的书,但并不适合从事英译汉,因为自己的汉语还达不到翻译的要求,“无法即刻想出很合适、恰当、传神的汉语译文”[10]。葛浩文在翻译文本类型和语言选择上的这种慎重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不难想象,一个学哲学的人翻译历史著作,难免会犯历史常识错误。可以说,目前我国翻译著作中出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译者在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勉强为之的结果。
在表达上,葛浩文重视译文的“准确性”“可读性”“可接受性”,同时力求在不影响读者阅读效果的情况下保留原语文化的“异质性”。葛浩文认为,翻译的目的是满足读者的需求,因此译文应该流畅、地道。另一方面,与一般西方翻译家不同,葛浩文同时是一个汉学家和翻译批评家,因此他对自己作为西方人的文化身份格外敏感,在处理中国文化元素时非常慎重,竭力做到忠实,以免有“东方主义”之嫌。他认为,在处理语言问题时,应该坚持灵活处理的原则,而不是死板地固守某种翻译技巧或方法。他认为,对于作者为了表达特定意义、取得某种效果而在特定语境中使用的表达方式,译者应该尽可能找到最能保留原语文化色彩的合适表达方式,通过增加文本的“陌生感”达到“延长读者的审美体验过程”的效果[11],而对于独特的语言现象,译者可以采取变通的方式,不必拘泥于原文的表达方式,以增强译作的可读性。
葛浩文尤其重视风格方面的忠实。他认为,翻译应尽力体现原文独特的文体[9]。他对那种“矫揉作态、古古怪怪,有时甚至是佶屈聱牙的译文”非常反感。当文字忠实与风格或语气忠实发生冲突时,葛译追求的是更高层次、整体意义上的风格忠实。他表示,为了达到忠实的目的,自己会把忠实于原作者的语气放在首位,尤其是处理对话时,只有在直译不合适的情况下,他才会采取变通的方式[12]。
二、葛浩文的忠实观在翻译实践中的体现
在翻译实践方面,学界普遍关注的是葛浩文在译文中采用的“删节、改译、整体编译”翻译策略,而大多数探讨葛浩文译文忠实性的文章目的也不在于证明葛译如何忠实于原文,如在《莫言英译者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与“伪忠实”》一文中,作者通过对葛浩文的《生死疲劳》英译本的研究发现,该英译本“并非如学界和媒体所说的精确或忠实”,而是存在大量“通过删减文化负载信息来降低目标文本在目标语言文化中的受阻性”的现象,虽然他对这种“伪忠实”译法持肯定态度,认为它能“凸显中国文化和语言特质,从而传达源文本的异国风情”[13]。事实上。葛浩文不仅倡导忠实,而且在翻译实践中一以贯之。可以说,他的忠实观实际上是对自己翻译实践的概括总结。
(一)理解方面的忠实
理解是翻译过程的第一步,翻译中的许多问题源于理解错误或不到位,对此从事过翻译工作的人都深有体会。理解的过程绝不是译者单方面能够完成的,需要与原文作者不断进行沟通。葛浩文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为了力求准确把握原文意思,葛浩文遇到不懂或理解没有把握的地方时不耻下问。在翻译莫言的作品时,他经常就理解方面的问题向莫言请教。他这种严谨的态度给莫言留下了深刻印象。据莫言后来回忆,葛浩文经常就小说中的某个字或不熟悉的事物与他反复磋商,仅写信就达一百多封,电话更是多得难以统计。莫言对此深表赞赏,认为葛浩文作为一位翻译家不仅才华横溢,而且作风严谨,“能与这样的人合作,是我的幸运”。为了帮助葛浩文理解,莫言有时“不得不用我的拙劣的技术为他画图”[14]。
葛浩文认为,文学的理解不能停留在简单的词句表层,还需要深入把握构成文学要素的结构、风格和主题呈现方式等深层信息。有学者研究发现,在翻译毕飞宇的《推拿》过程中,葛浩文和林丽君在阅读原文时通过邮件向作者提出了131个问题,涉及追索词句意义、交流创作意图、求证原文矛盾等理解方面的问题[15]。
(二)表达方面的忠实
理解是否忠实,最终是通过表达体现出来的。对于文学翻译来说,表达忠实不仅体现在内容上,而且体现在文学形象和文体风格等形式上。葛浩文具有创新性的翻译方法或许可以为我国翻译工作者提供借鉴。
葛浩文非常重视表达的准确性。在翻译白先勇的《孽子》时,葛浩文为了掌握同性恋细腻隐晦的表达方式,经常光临旧金山的同性恋酒吧,请同性恋者喝啤酒,与他们聊天[3]。在翻译某些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表达方式时,葛浩文尽可能采用音译或直译的方法。在《檀香刑》中,葛浩文没有把“爹”和“公爹”采用意译的方法译为“father”和“father-in-law”,而是音译为“dieh”和“gongdieh”。这种做法不但保留了原文的语言特色,而且丰富了英语的表达法。这是中国本土译者想不到也不敢想的,因为在已有现成英文表达方式的情况下,这样做很可能被扣上“死译”或译文不地道的帽子。另一个音译的典型例子就是“娘”,葛浩文同样采用音译的方法保留了这一古时中国人对母亲的称谓。他还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称呼语“父老乡亲们”直译为all you elders, fellow townsmen。顺带一提的是,有的文章提到了“炕”的翻译问题,并把其异化翻译方式“kang”归功于葛浩文[16],这显然是有悖事实的。实际上,早在《红高粱家族》葛译本(1993年)出版之前,我国的汉英词典中就已经出现该译文(1)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英词典》(A Modern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年),第502页。该词典提供的另一个译文是a heatable brick bed。。因此,在讨论葛译翻译特色和技巧的时候,有必要区分哪些译文为葛浩文独创,哪些是现成的译文,以免张冠李戴,导致讨论失去意义和价值。
葛浩文在译文中不仅尽可能忠实于原文内容,而且尽力保留原文的意象。有学者研究发现,以葛浩文前后翻译莫言五部小说中的500个意象话语为研究对象,发现异化策略一直占主导地位[17]。在翻译《推拿》时,葛浩文对描述女主人公金嫣心理活动的词语“活络”的用意不是很明白,经过向作者毕飞宇询问,得知其目的是强调人物的心里“有了动静”,意思是“激动、快乐、庆幸”,于是创造性地译为came alive,保留了原文的动态和“活”的意象[15]。在《红高粱家族》中,葛浩文把“黄泉”直译为the Yellow Springs,而不是西方社会的Hell(地狱),或汉英词典中提供的译文the netherworld或the dwelling place of the dead。葛浩文的这种翻译方法在汉语成语翻译中更加典型。根据具体语境,在不影响读者理解的情况下,葛译尽可能采用直译方法。如:
原文:跟鬼子拼个鱼死网破吧![18]177
译文:We’ll take the Japs on until either the fish die or the net breaks.[19]204
评析:葛浩文在翻译“鱼死网破”时,不是通过意译的方式采用英文中固有的说法a life or death struggle,而是保留了汉语原文中的意象“鱼”和“网”,读起来生动形象。
葛浩文在遵循英语文本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尽力采用直译方法保留中国文化的异质性,从而“既保留文化特色又保持译文的流畅”[10]。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译文中保留汉语独特的谚语、俗语、谐音等语言表达方式。有的学者通过语料统计分析发现,葛浩文在翻译方言土语时以直译为主,从而得以保留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20]。以下这些具有中文特色的表达方式都出自葛浩文的译本:Flies can’t get into an egg that isn’t cracked.(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A fallen phoenix is not the equal of a common chicken.(落魄的凤凰不如鸡)He’s the proverbial toad wanting to taste the swan’s flesh.(癞蛤蟆想吃天鹅肉)If you marry a chicken you share the coop; marry a dog and you share the kennel.(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俗语方面,葛浩文通过“直译+意译”结合的方式保留原语的文化色彩,如:an economy lantern, someone to be taken lightly(省油的灯)。在翻译一些形象生动的骂人表达方式时,葛译有时并不借用英语中类似的说法,而是采用直译的方法,如:I’ll skin you alive and rip the tendons right out of your body.(我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No easy death for you!(你不得好死!)Stop acting like a fucking idiot.(他娘的,你装什么憨!)这类译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极大地丰富了英语的表达法。当然,葛浩文的直译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直译不同,只是保留原文的形象或文化色彩,在句子结构上依然遵循英语的表达习惯,这是非英语本族语者难以做到的。
在语言与风格发生冲突时,葛浩文更重视风格层面的忠实。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檀香刑》的翻译。他认为,《檀香刑》是一部以声音、节奏、韵律和声调为基调的作品,因此译文也应该体现出这种特点。为了找到既能保留韵脚又能传达原意的合适表达方式,葛浩文可谓“绞尽脑汁、殚精竭虑”[21]。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小说标题的翻译。汉语“檀香刑”有三个音节,其中“檀香”对应的英文单词sandalwood已经有三个音节。由于“檀香”属于专有名词,不能随意更改,因此只能在“刑”的译文上动脑筋。我们知道,“刑”一般译为penalty或punishment,但这样一来译文的音节就会大大超过原文。为了尽可能取得韵律上的平衡,葛浩文决定采用意义相近的单音节英文单词death。这就是Sandalwood Death译名的由来。该书的正文也体现出这种特色,如他在翻译猫腔戏文时力求保持原文合辙押韵、朗朗上口的韵律。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中文教授石江山(Jonathan Stalling)对葛浩文的译文推崇备至,认为葛浩文的译文不仅“再现了莫言小说中的各种声音,而且还采用了汉英两种语言非常接近的格律和尾韵”,是“用英语所能达到的翻译的极致典范”[16]121。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葛浩文在翻译小说时能够做到这点。这足以说明葛浩文翻译技巧之精湛。
(三)效果方面的忠实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在政治经济体制、某些价值观方面甚至相互冲突。因此,在翻译时如何处理这种差异,是对译者提出的挑战。葛浩文为了忠实于读者,消除译文读者的抵触心理,对于原文与译文之间存在冲突的文化或政治现象有时会采取删减或改换说法的策略。这种做法从表面上看是对原作者和原文化的背叛,但由于译文消除了文化上的障碍,有助于译文读者像原文读者那样轻松自如地欣赏作品,从而达到效果和意义忠实的目的。
例如,在中国,狗是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元素,狗肉被认为是一种非常美味的食物,但在西方文化中,狗是最受欢迎和喜爱的宠物之一。如何处理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对于译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红高粱家族》中,我们会读到关于土匪头子余占鳌吃狗头过程的细致描写:
译文:It was delicious. And he was ravenously hungry, so he dug in, eating quickly until the head and the wine were gone.[19]107
评析:作者为了说明土匪头子的豪爽,用了“吞”“吸”“嚼”“啃”等动词,活灵活现描写了余占鳌吃狗头的过程,但中国人眼中的这种粗犷,在西方人看来却是非常残忍的。可能基于这种考虑,葛浩文在译文中对描写各种吃法的动词和部位等细节进行了部分删减,只保留了原文大意。这种处理方式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忠实于原文,但却忠实于读者和译语文化。
这种改写在政治文化方面更加明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当代小说无法回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之类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此相关的描述,尤其是带有明显宣传口吻的语言,如果采用直译的方法,显然会引起生活在截然不同政治制度下的西方读者的反感。如:
原文:我们是共产党,饿死不低头,冻死不弯腰。[18]345
译文: We’re resistance fighters. We don’t bow our heads when we’re starving, and we don’t bend our knees when we’re freezing.[19]367
评析:在译文中,“共产党”的影子不见了,而是变成了“抗日战士”。可以想象,如果中国本土译者进行这种改变,不仅原文作者不会同意,而且译者可能还会承担政治风险。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改写称为外国译者的翻译“特权”?
(四)改写背后对原作者的忠实
对葛译忠实性提出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译本中的改写现象。但实际上,除非文化差异需要,葛浩文反对译者随意改变原文。当葛浩文发现原文有错误时会与原作者沟通。为了尽可能做到忠实,葛浩文在译完一部作品后会请自己的中国夫人林丽君或母语是汉语的人帮忙校对译文,“以确保不会有所失误”[10]。葛译在篇章层面饱受诟病的改写实际上往往是编辑、译者、作者三者在互动中完成的,因此这种改写本质上并没有违背忠实的原则。
老家的房屋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盖的,因为长时间没人居住,现在已经残破不堪,和左邻右舍新盖的房子一比,像是回到了旧社会,可那是母亲大半辈子生活过的地方,也有我童年和少年数不清的快乐和烦恼,正因为它没变,所以我小时候的记忆都格外清晰。当然,最熟悉的还是院里的枣树,它从我记事起就高高挺立在院子的东边,给我提供了数不清的脆甜可口大枣,它也记载着我成长的过程。但是这二十多年来,只剩它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只有母亲还记得它。
在葛译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1993年,负责《红高粱家族》英译本的编辑发现,该书第四章中某个场景描写存在衔接不当、表达重复等问题,于是询问葛浩文是否可以删除,葛浩文在征得莫言首肯后才表示同意[22]。同样,编辑认为刘震云的《手机》开篇是对中国三四十年前发生的事情进行的回忆,而美国读者感兴趣的是现在发生的故事,因此建议葛浩文在译文中对原文顺序进行调整,把第二章讲述现在故事的一小部分移至小说开头,这一建议得到了作者刘震云的认可。《天堂蒜苔之歌》的编辑认为,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充满愤怒的故事”,但其结尾过于平淡。葛浩文于是把编辑的想法反馈给莫言,莫言据此创作了一个全新的结尾,结果皆大欢喜[10]。这些典型例子说明,文学创作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改写的过程。
总之,文学翻译并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涉及到译者、作者、编辑等多种因素,摆在读者面前的译文很可能是某种妥协的结果,因此译者承受的许多责难是不公平的[10]。
三、葛译在忠实方面存在的问题
诚然,我们在肯定葛译忠实性的同时,对其存在的各种问题也不应该视而不见。葛浩文的译文并非完美无缺,无论在理解还是表达上都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误。当然,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敢说完全精通,更没必要对一个外国人过于苛求。因此,笔者在这里列举葛译中的一些问题,目的不是证明葛译的不忠实性,而是希望读者能够对葛译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首先是理解上的问题。这种问题有的表现在词语层面,如中国文化中,“嫂子”至少有两种指称意义:1.用于称呼哥哥的妻子(elder brother’s wife),是一种亲属称谓;2.用于称呼年纪与自己相仿的已婚女性(sister, a form of address for a married woman about one’s own age),是一种社交称谓。但葛浩文没有根据具体语境对这两种意义进行区分,有时把纯粹用作社交用语的“嫂子”也译为sister-in-law,容易造成混乱和误解。还有的表现在句子层面,如:
原文:“干爹!”从街上跑回来的我父亲高叫一声,把爷爷高举门闩的手固定在半空中。[18]330
译文:“Dad!” Father ran in screaming, grabbed the door bolt, and held on for dear life.[19]346
评析:原文的意思是说“我父亲的叫声阻止了爷爷殴打奶奶”,但把译文回译成中文,意思却变成了:“父亲不仅大叫了一声‘干爹’,而且抢过门闩,拼命阻止爷爷殴打奶奶”,显然这是误解原文意思造成的。试译为:“Dad!” My father ran in from the street and screamed, stopping grandpa’s hand with the door bolt from falling down from the air.
又如:
原文:他们躲在咸水口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每当太阳上来,队员们就一堆一堆地躺在断墙边上抓虱子晒太阳。白天不敢行动,夜晚寒气逼人,想出去骚扰敌人只怕不被鬼子打死也要活活冻死。[18]349
译文:After making camp in a tiny village not far from Saltwater Gap, they lay atop the battered wall when the sun came out, to pick lice off their bodies and soak up the midday heat. All day long they conserved their energy; then, at night, they nearly froze in the cold. They were afraid that if they weren’t killed by the Japs the weather would do them in.[19]366
评析:该译文存在多处问题。首先,原文是“躺在断墙边上”,在译文中却变成了“躺在断墙上”,破坏了原文的逻辑。在原文中,该句上文写道:“逐渐壮大的胶高大队被寒冷和饥饿扼住了咽喉。病号大量出现;从大队长到普通队员,都饿得面黄肌瘦,瑟缩在一两件破破烂烂的单衣里发颤。”由此看来,“躺在断墙边上”的说法有两层含义:一是战士们已经饿得没有力气,只能躺着;二是为了躲避寒风,靠墙躺着。第二,把“晒太阳”译为“soak up the midday heat”也歪曲了原意。从上下文看,队员们不是中午(midday)才出来晒太阳。第三,把“白天不敢行动”翻译成All day long they conserved their energy(白天他们保存精力)也存在逻辑问题,无法与后面形成衔接。按照正常逻辑,“保存精力”是为了采取行动,但原文意思恰恰相反。试译如下:They hid themselves in a small village near Xianshuikou. Whenever the sun came out, they lay in groups at the battered wall to warm themselves up. They did not dare to take actions in the day. And, at night, they could do nothing either, for the extremely cold weather would do them in even if they were not killed by the Japs.
作为一个英语本族语者,葛浩文按理应该不会犯语法方面的错误,所以下面例子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倾向于认为是笔误:
原文:他去公社里开会啦。[18]344
译文:He went to a meeting at the commune.[20]361
评析:这句话是村支书的老婆向耿十八刀解释支书不在家的原因时说的话。按照英语习惯,应该使用现在完成时更恰当,即改为He has gone to attend a meeting at the commune.
原文:那里盛产红薯,吃的也不成问题。[18]350
译文:And since there’s plenty of yams there, food won’t be a problem, either.[19]366
评析:这句话出自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中队长之口,用词和语法都很规范,因此从风格上来说,译文也应该规范。但译文却存在语法错误。我们知道,yam在英语中既可用作可数名词,也可用作不可数名词。这里既然用作可数名词且使用的是复数形式yams,那么谓语动词应该使用are,而不是is,即译文应改为:And since there’re plenty of yams there, food won’t be a problem, either.
另外,可能由于时间仓促的原因,葛浩文没有时间仔细推敲每一句译文,因此个别译文存在明显的文体问题。如:
原文:“我们是共产党,饿死不低头,冻死不弯腰。”[18]345
译文:We’re resistance fighters. We don’t bow our heads when we’re starving, and we don’t bend our knees when we’re freezing.[19]367
评析:从风格角度来说,译文过于啰嗦,既不符合原文简洁的文风,也不符合典型的英文表达方式。译文完全可以简化为:We’re resistance fighters, neither bowing our heads when starving, nor bending our knees when freezing.
四、结语
无论是葛浩文的翻译观还是翻译实践都表明,他“在翻译中对忠实性原则不仅没有忽略,而且还有所追求”[6]。他对保留中国文化特色方面的贡献甚至超过了某些中国本土译者。可以说,葛浩文的忠实译文为国外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如果说葛浩文的翻译对忠实原则有所冲击,那么他只是没有拘泥于传统的文字忠实,而是同时兼顾、有时优先考虑意义忠实、风格忠实、效果忠实。他在篇章层面的改写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在出版社、编辑、作者共同参与下进行的,并没有背离忠实原则。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葛浩文的翻译观和翻译实践加深了我们对文学翻译忠实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