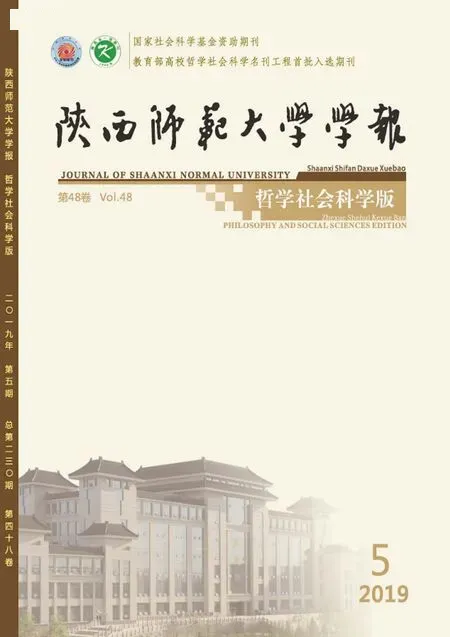清华简《治邦之道》墨家佚书说献疑
陈 民 镇
(清华大学 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北京 100084)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八)》新公布了8篇先秦佚书(1)2018年11月17日,清华大学隆重召开了“纪念清华简入藏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8辑在会议上正式发布,涉及《摄命》《心是谓中》《治邦之道》《邦家之政》《邦家处位》《天下之道》《虞夏商周之治》《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8篇。,多涉及治国理政的观念。其中《治邦之道》一篇(2)本篇原无篇题,整理者据本文所见“治邦之道”一语拟题,亦可概括全篇要旨。,整理者认为与墨家有关:
简文围绕如何治国安邦展开,其中许多论述与《墨子》一书的思想关系密切,涉及尚贤、节用、节葬、非命等内容,应该是一篇与墨学有关的佚文。众所周知,墨子是战国初年的著名思想家,墨家学说在战国时期曾为显学,但此前与墨学相关的出土材料比较少见。本篇简文的面世,对研究墨家学说及其在战国时期的传播颇有价值。[1]135
简文作者在这里所表达的思想,与墨家的尚贤、节用、节葬、非命等主张是完全相通的。相关的内容在《墨子》一书中的《尚贤》《节用》《节葬》《非命》等各篇中有系统的阐述。……从清华简《治邦之道》的这些内容来看,这篇文献应是一篇与墨学有关的佚文。[2]
《治邦之道》果若是墨家佚书,其价值自然非比寻常。该篇的论述 ,确乎多与墨家相合。但篇中所谓墨家思想,有的亦见于其他学派,非墨家独有;有些倾向又与墨家截然对立,不可不察。整理者注意到该篇与墨家思想的相合之处,但篇中与墨家相冲突或见于其他学派的观念,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试对《治邦之道》的主旨及思想倾向作全面考察,探讨该篇所谓“尚贤”“节用”“兼爱”“节葬”“非命”的观念,以期重新审视该篇的性质以及战国时期不同学派之间的交互关系。
一、 “尚贤”“节用”:非墨家独有的观念
贤能政治的思想贯彻于《治邦之道》全篇。虽然目前简文的编联尚有疑义,但内容大致可读。该篇现存27支简,其中简2至简5的内容为:

这段话奠定了本篇的主调,具体表现为3个层次:
其一,“祸福不远,尽自身出”,即祸福都是由自身的作为所决定的。“明者”知道尽人事以避祸,“愚者”反之。作者指出“兴不可以幸”,强调不可寄望于听天由命的侥幸。在下文中,作者进一步指出尽人事较之天命更为重要。
其二,尽人事的关键在于用贤。无论君主还是臣子,都要用贤,即简20所谓“其政使贤用能”。一方面,要任用“仁者”“圣人”,期待“明王圣君之立”;另一方面,还要选拔贤臣辅佐圣君。
其三,贤能的才能与出身贵贱无直接关联,关键是否有“道”,故称“不辨贵贱,唯道之所在”。“道”者谓何?本篇所见“治邦之道”可为注脚。作者认为即便出身贫贱,如若秉持治邦之道,亦可“御众、治政、临事、长官”。
以上3个层次,构成了典型的贤能政治学说。整理者认为本篇体现了墨家的“尚贤”思想,但众所周知的是,战国诸子多主张任贤使能,是为当时士人阶层崛起的反映。如《孟子·公孙丑上》云“尊贤使能”,《荀子》中《王制》《富国》《君道》《强国》《君子》诸篇一再强调“尚贤使能”,便与《墨子》同调。即便是将“道”或“法”凌驾于贤能之上的黄老道家与法家,同样重视贤能的重要性,如马王堆帛书黄帝书《经法·六分》云“轻县国而重士”,《十大经·前道》云“壹言而利国者,国士也”;《管子·权修》云“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使民之机也”,《版法》篇云“修长在乎任贤”;《吕氏春秋·先己》云“尊贤使能”,《不屈》篇云“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求人》篇云“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韩非子·八奸》云“明主之为官职爵禄也,所以进贤材劝有功也”。只不过在黄老道家或法家看来,“道”或“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国家应按照法度所设定的轨道运行,君佚臣劳,君主的才能并不具有决定性,人才的选拔应该遵照法度而非君主的主观取择,故《荀子·解蔽》称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总之,“尚贤”的观念绝非墨家所独有,不能以此作为判定《治邦之道》性质的依据。

在用人方面,简文还希望破除唯出身论,即一反过去的世卿世禄制度,唯才是举,即前文所言“不辨贵贱,唯道之所在”“何宠于贵?何羞于贱?虽贫以贱,而信有道,可以御众、治政、临事、长官”。这近似于整理者所引《墨子·尚贤中》:“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然墨子尚天志,故认为不避贵贱是“天”的意志,这在《治邦之道》中并无体现。且战国之世,不避贵贱的选人方式实际上是诸子的普遍主张,亦非墨家所独有。与本篇同时公布的《邦家处位》,便反对“子立代父,自定于后事,皆嫡长”(5)参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八)》,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128页。“皆”,整理者读作“阶”,笔者改读。的世袭制度,而是主张君主择贤任之。整理者引《墨子·尚贤上》“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之语,墨子紧接着便说到尧举舜、禹举益、汤举伊尹、文王举闳夭等,近似于《孟子·告子下》所云“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再如儒(尤其儒家后学)、墨两家均称道尧舜禅让,亦肯定人才能够跨越阶层升迁。荀子虽希望维护“尊贱有等”(《荀子·礼论》)“等贵贱,分亲疏”(《荀子·君子》)的礼制,但亦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荀子·王霸》)“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之类的论述,认为若有才能德行,虽出身低微仍可得到重用,而王公士大夫子弟若不遵礼义,同样有可能沦为庶人。这正是战国之世士人崛起、阶层升替的写照。
从简9开始,简文论述了君主具体的为君为政之道:

作者强调君主务必“事必自知之”,这是典型的贤能政治思想,与黄老君佚臣劳的主张截然不同。具体如何成为“明王圣君”呢?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君主所应遵循的准则:不可贪图安逸而无忧患意识,要有长远考虑,即与本篇同时公布的《心是谓中》所谓“知事之卒”;不可被巧言令色所疑惑,任用臣子时要考量其德行;不可放纵欲望而背离治邦之道;不可诈伪;不可喜听恭维之言而无明察之心,任用贤人而远离佞臣;不可厌恶谏言,而是要据以改正过失;不可听信一面之词,而要善于察证;不可骄恣放纵,而应善待百姓,百姓便不会背弃而去;贫病之民,甚至是不遵循教化的无业之民,也不应放弃,而是要坚持感化,他们则无怨言;臣子无论出身贵贱,均应一视同仁。这实际上是典型的“仁政”主张了,可呼应开篇所呼吁的“仁者”以及下文的“仁圣”。从这一点看,本篇的思想与儒家的为政之道更为接近。
本篇的“仁政”还体现于节用裕民,整理者认为这是墨家“节用”的体现。其文曰:

简文谓君主应揆度民力,奉行俭约,宽政爱民,从而节用裕民,“敷均于百姓之兼利而爱者”。这里的“敷均”与“兼利而爱”,与墨家思想亦相呼应。
所谓“敷均”,又见于下文简25“此毋乃吾敷均,是其不均”,这在《墨子》中也有体现,如《尚同中》篇云:“分财不敢不均。”不过在儒家那里,也有类似的均平观念,如《论语·季氏》云:“不患寡而患不均……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另可参见《荀子·王霸》:“天下莫不平均。”《韩非子·六反》:“论其税赋以均贫富。”《晏子春秋·景公问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对以问道者更正》:“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

节用裕民的观念多见于诸子的学说,如《论语·学而》载孔子语“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尽心上》云“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管子·牧民》云“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荀子·富国》云“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在《富国》篇中,荀子批判当时“厚刀布之敛”“重田野之赋”“苛关市之征”的苛政,呼应《治邦之道》的“薄关市”等内容。类似的主张,荀子在《王制》篇中有更充分的讨论。《富国》篇批判墨子“私忧过计”,认为墨子极端的“节用”最终会导致“使天下贫”,故主张“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即通过开源节流,最终做到节用裕民。相比之下,墨子的“节用”更为消极,即通过极端的节俭来积累财富。荀子的主张则是更为积极的富民之道,《治邦之道》似与《荀子》更为接近。
《治邦之道》的理想是从君主到贩夫走卒都各安其位,从而令“天下无有闲民”(简18)。简文指出:“君守器,卿大夫守政,士守教,工守巧,贾守贾鬻聚货,农守稼穑,此之曰修。今夫逾人于其胜,不可不慎,非一人是为,万人是为。”(简15、16)认为君主、卿大夫、士、工、贾、农各有其职分,便是“攸(修)”。如果我们联系到《荀子·正论》的“圣王在上,决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载其事而各得其宜”,以及《王制》篇的“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便不难理解《治邦之道》全篇的为政之道了。
综上,本篇所出现的“尚贤”“节用”甚至疑似“兼爱”的观念,并非墨家所独有,不能简单将其作为判定本篇性质的依据。即便是这些所谓的“尚贤”“节用”“兼爱”,细究起来,其倾向与《墨子》并不完全一致,而更接近《荀子》诸书的旨趣。
二、 “节葬”与“礼”的冲突
本篇简21的一句话被整理者视作墨家“节葬”说的注脚,其文曰:“不厚葬,祭以礼,则民厚。”其说看似有理,但“不厚葬”并不意味着一定等同于“节葬”,而“祭以礼”显然更接近儒家,有必要结合儒、墨诸家的丧葬观念予以讨论。
墨家当然是反对厚葬的。在《墨子·节葬下》中,墨子反复申论“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的道理。在《公孟》篇中,墨子指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其中一条便是“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可见墨家“节葬”说的靶子是儒家,“厚葬久丧”被视作儒家的一大标签。《淮南子·要略》亦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即墨家以儒家之“礼”为烦扰,认为“厚葬靡财”可使百姓贫敝。
但儒家是否果真主张“厚葬”呢?在《论语·先进》中,记录了这么两个故事: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后,不可徒行也。”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孔子虽很赏识颜渊,但门人欲为颜渊厚葬时,孔子却是极力反对的。他说即便是自己的儿子孔鲤死了,也只有内棺而无外椁,拒绝了颜渊之父颜路要求置办外椁的请求。而在门人厚葬颜渊之后,孔子仍十分抵触,称自己并未参与此事。在这里,孔子并非不近人情,也不是简单的反对厚葬,而是为了遵循礼制,即其所言“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正呼应《治邦之道》的“祭以礼”。这也透露出儒家丧葬观的基本宗旨,即并非一味主张节葬抑或厚葬,而是倡导合礼为宜。
在儒家后学的追述中,孔子对丧葬之礼多有阐论。据《孝经·丧亲章》,孔子认为“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即丧葬出自人伦之常与自然流露的“哀戚之情”,并不强调厚薄,亦即《论语·八佾》所谓“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甚至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礼记·檀弓上》),哀戚之情甚至比“礼”更为重要。墨子也认为“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墨子·修身》),这一点是与儒家共通的。但相比之下,墨家的“节葬”观显然苛刻得多,甚至试图完全摒弃丧葬之礼。儒家的“哀”在墨家那里,也便成了“久丧伪哀”(《墨子·非儒下》)。
在《礼记·檀弓下》中,子路感叹过去因家贫而“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为父母死后能尽礼而愧疚,孔子则说“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在自身的家庭经济条件之下满足基本的丧葬要求便是合礼了。在子游请教葬具时,孔子有类似的回答:“有,毋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县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礼记·檀弓上》)即家庭富裕的话“毋过礼”,否则满足基本的丧葬要求即可。针对桓司马为石椁三年不成之举,孔子说“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礼记·檀弓上》),可以看出他是明确反对丧葬之奢靡的。丧葬的厚薄本是相对的,在墨家看来,儒家的葬礼显然属于厚葬之列。但儒家主张在“礼”的框架下灵活变通,又以人伦为皈依,与无节制的奢靡厚葬不可同日而语。从某种程度上讲,儒家也是反对厚葬的。
据《孟子·梁惠王下》,鲁平公之嬖人臧仓称孟子“后丧逾前丧”,即孟子为母亲办丧事的规格超过父亲,而“礼义由贤者出”,可见孟子很难说是贤者。鲁平公听信了臧仓的话,便拒绝去拜访孟子。乐正子知道此事后,便问平公:“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平公回答:“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乐正子便说:“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在乐正子看来,孟子为母亲办丧事并未越礼,只是在棺椁衣衾的精美程度上有所差异,而未违反礼制的规定。棺椁衣衾精美程度的差异,充其量只是贫富的差别罢了。在《公孙丑下》中,当有人质疑孟子为母亲准备的棺椁是否选料过于精美时,孟子回答道:
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孟子认为,棺椁礼制的确立,并非仅仅是为了外表的美观,更重要的是尽孝子之心。如果合乎相应的礼制,又有相应的财力,那么何不选择更好的材料呢?最后孟子称“不以天下俭其亲”,主张在合礼的前提下绝不节俭。在这里,孟子也不是简单的主张厚葬,仍希望遵循礼制,同时又突出了人伦的温情,可与《孝经·丧亲章》相呼应。《滕文公上》所记孟子对墨家夷子“葬其亲厚”的回应,也同样强调了这一点。
荀子对墨家的“节葬”说有进一步的回应。在荀子眼中,墨家“大俭约,而僈差等”(《荀子·非十二子》),“差等”是“礼”的核心,葬礼要适用于相应的阶层,以“隆礼”著称的荀子便以此批判“节葬”之说。针对“太古薄背,棺厚三寸,衣衾三领,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乱今厚葬饰棺,故抇也”的“世俗”之说,荀子指出若是圣王当政,则国富民安,即便墓葬再奢华,也无人盗掘;反之,若法度不行,贤人不得进用,那么就会世道大乱,不只是盗墓这么简单了。可见,因“厚葬”导致盗墓的说法不过是“奸人之误于乱说,以欺愚者而淖陷之,以偷取利焉”(《荀子·正论》)。荀子认为“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事死如事生”,如若“厚其生而薄其死”,则“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荀子·礼论》)。基于“隆礼”的立场,荀子则是明确反对“节葬”的。
可见,儒家内部的丧葬观念虽亦有别,但其总体倾向是一致的,即遵循礼制,反对极端的节葬或厚葬。除了《墨子》将儒家视作厚葬的典型,据《晏子春秋·仲尼见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为不可》,晏子亦称孔子的学说导致“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晏子还曾劝谏齐景公“废厚葬之命”(《晏子春秋·景公欲厚葬梁丘据晏子谏》)。但将“厚葬久丧”作为儒家的标签[4],又不免过于绝对,故有学者指出先秦儒家无“厚葬久丧”观念[5]。据《论衡·薄葬》,“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只不过“儒家论不明”,儒家因没有明确论述,从而导致世人有儒家鼓励厚葬的误解。但此前的儒家文献除了反对越礼的行为,的确也不曾像《治邦之道》那样明确否定“厚葬”。我们不妨说,《治邦之道》“不厚葬”的说法与墨家相合,与儒家的宗旨亦不相悖。至于其“祭以礼”的表述,则与《论语·为政》一致,而墨家恰恰是不强调“礼”的。
丧葬之礼,在于“饬丧纪,辨衣裳,审棺椁之薄厚,茔丘垄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礼记·月令》)。在《庄子·天下》中,作者便强调“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6)《荀子·礼论》所记相同。,而墨家背离古已有之的丧葬之礼,“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这一倾向“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并不合时宜(7)《庄子·列御寇》载:“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在这则故事中,庄子反对厚葬,则出于道家因任自然的观念。。马王堆帛书黄帝书《称》谓“减衣衾,薄棺椁,禁也”,也不主张极端的“节葬”。在《韩非子·显学》中,韩非子对儒墨两家皆有讥评,将“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与“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相对立。据《韩非子·内储说上》,“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衾,材木尽于棺椁”,齐桓公遂下令:“棺椁过度者戮其尸,罪夫当丧者。”这一故事则是反对厚葬的。《吕氏春秋》一方面承认丧葬是“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批判当时“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的现象(《节丧》);“世之厚葬”者容易被盗掘,而“先王之葬,必俭、必合、必同”(《安死》),可与《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所记孔子“送而以宝玉,是犹曝尸于中原也”之语相参看。从战国时代的诸子看,包括儒家在内,当时知识分子大多反对无节制的厚葬,《治邦之道》“不厚葬”之说也是合乎当时主流思潮的;同时,又多对墨家极端的“节葬”不以为然。《治邦之道》“不厚葬,祭以礼”的主张,实际上与墨家不完全同调,而与儒家等学派的论调更为契合。
三、 “命”与《治邦之道》的主旨
从简22起至文末,简文通过“愚者”与“智者”(即前文所谓“明者”)的对话展开关于“命”的讨论:
此治邦之道,智者知之,愚者曰:“在命。”曰:“夫邦之弱张【简22】,落有常,譬之日月之叙,一阴一阳。”曰:“彼岂其然哉?彼上有所可慼,有所可喜,可慼弗慼,可喜弗喜,故坠失社稷,子孙不属。【简23】可慼乃慼,可喜乃喜,故常政无忒。彼上之所慼,邦有疠疫,水旱不时,兵甲骤起,盗贼不弭,仁圣不出,谗人在侧弗知,邦狱众多,妇子赘假,【简24】市多台,五种贵,上乃忧戚,靖殛以知于百姓,乃恤其政,以遇其故,曰:‘吾焉失此?毋乃吾敷均,是其不均?繄吾作事,是其不时乎?繄【简25】吾租税,是其疾重乎?繄吾为人罪戾,已孚不称乎?’故万民慊病,其粟米、六扰败竭,则鬻贾其臣仆,赘位其子弟,以量其师尹之征,而【简26】上弗知乎?此物也,每一之发也,足以败于邦。故妨夺君目,以事之于邦,及其野里四边,则无命大于此。”【简27】
愚者认为治国纯粹在于听天命,国家的盛衰正如日月升降,按照既定的轨道运行,即所谓“在命”。而智者则反对这一论调,认为君主当有所为,不可听天由命。君主应忧其所忧,乐其所乐。所忧者,在于疠疫、水旱、兵甲、盗贼、谗人、邦狱等,君主当时刻考虑百姓的疾患,从而恤政爱民。君主应时刻反省自己是否不分均,是否不以时行事,是否赋税过重,是否德不配位。如若放任百姓贫病,庄稼、牲畜败坏,买卖奴仆,抵押子女,诸如此类的负面现象足以令邦家倾颓,君主需要有所“知”,即前文所言“事必自知之”。如若君主被蒙蔽,这些生民之弊便会扩大到全国,邦家便毁。智者最终称“无命大于此”,即如若君主不作为,便不能奉行治邦之道,对于治国而言,君主尽人事与否较之“命”更为关键。
傅斯年先生曾将东周的命论分为5种,分别是命定论、命正论、俟命论、命运论与非命论[6]136。愚者的主张,无疑是属于命定论的。而智者的主张,同时也是作者的主张,则认为尽人事比听天命更为重要。整理者认为简文体现的是墨家的“非命”观念,作者对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有“命”之论持否定的态度[2]。我们知道,先秦时期除了墨家、法家倾向于非命论之外[7]313,其他诸子都是承认“命”的存在的。但细究之下,《治邦之道》并不否定天命的存在,只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为政中更为关键。这一观念,实际上是与《荀子》“天人之分”的观念相契合的,以下试作讨论。
前面已经论及,本篇开篇指出“祸福不远,尽自身出”“兴不可以幸”,即祸福并非天定,而由己出。《孟子·公孙丑上》云:“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褔无不自己求之者。”所论近同。将国家兴衰系于人事,是西周以来伴随人文理性觉醒而逐步强化的观念。《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谓“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僖公十六年谓“吉凶由人”,均强调国家兴亡在人事而不在鬼神。
而《墨子》的祸福观却与此不同。《墨子·法仪》云:“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公孟》篇云:“古圣王皆以鬼神为神明,而为祸福,执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国安也。”谓祸福由上天与鬼神所降。《非命下》篇云:“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这一说法与《治邦之道》已经极为接近了,整理者将《治邦之道》归入非命论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尚同中》篇中,墨子谓“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亦即《治邦之道》中不理国政的恶劣后果,墨子将其归结为“此天之降罚也”,认为是上天带来的惩罚。至于挽救措施,《尚同中》篇固然也强调“听狱不敢不中,分财不敢不均,居处不敢怠慢”,但更为注重的是对天志鬼神的敬奉,即“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洁,牺牲不敢不腯肥,圭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时几”,这在《治邦之道》中是得不到体现的。
在简5至简7中,简文论及“圣士”的“由(用)”与“不由”:

简文认为,贤人不得进用,正如气候异常,水旱无度,草木、百谷便会遭殃。如果四季正常更替,那么草木、百谷便会繁盛。简文进而将人比拟为草木百谷,人是否进用,正在于“时”。我们不难想到《荀子·宥坐》的记载:
孔子南适楚,厄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弟子皆有饥色。子路进而问之曰:“由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孔子曰:“由不识,吾语女。女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吴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

我们知道,《荀子》便主张“天人之分”。如《天论》篇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指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即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同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再如《正名》篇谓“节遇谓之命”,“节遇”指偶然的遭遇,是命所决定的。《尧问》亦云“天下不治,孙卿不遇时也”,也涉及“遇”与“时”的问题。正如池田知久先生所论,在《穷达以时》中,“遇”与“天”的意思大致相同,或者说“遇”是“天”下面的子概念[9]90。故承认“遇”的存在,便是承认“命”的存在,所以《治邦之道》所反映的显然不是所谓的非命论。而无论是《治邦之道》,还是《荀子》《穷达以时》,一方面强调谋事在人,另一方面又承认成事在天;在试图割裂天、人的同时,也在努力弥合二者。因此,在这些文献的论述中,我们常常可以体会到来自天人两端的拉锯与冲突。
《治邦之道》谓“兴不可以幸”“上之情之不可以幸”,“幸”的观念亦见于《荀子》。《仲尼》篇云:
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仇,遂立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贵贱长少,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贵敬之,是天下之大节也。诸侯有一节如是,则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数节者而尽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数也。
此即《王制》篇所谓“朝无幸位,民无幸生”。齐桓公之霸,并非“幸”,而是其为政之道的必然。亦可参见《孟子·离娄上》“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若不行仁政,国家还能存在只能是“幸”,可以说是“兴不可以幸”的注脚了。《礼记·中庸》记孔子语:“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大戴礼记·曾子本孝》亦云:“故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俟命”并非认命,而“幸”则将命运推向不可知或不可抗的境地。
以上观念,在与《治邦之道》同辑公布的《心是谓中》中有系统的阐论[10]。《心是谓中》认为,“幸,天;知事之卒,心。必心与天两”,“幸”出于天,而能否预知事情的走向,则是心所决定的,必须兼顾心与天,不可“谋而不度”,即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正是《治邦之道》所强调的“两于图”“必虑前后,则患不至”。简文还提出了“身命”的概念,认为“断命在天,苛疾在鬼,取命在人。人有天命,其亦有身命,心厥为死,心厥为生。死生在天,其亦失在心”,这一先秦心论与命论的新线索,正可帮助我们理解《治邦之道》的天命观。
可见,《治邦之道》虽然称“无命大于此”,但从文本的内证和其他相关文献看,其前提正是承认有“命”的存在。墨家与天志说、明鬼说相结合的非命说,与此不可同日而语。
四、 结 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知道,将《治邦之道》定位为墨家佚书实际上似是而非。该篇的思想倾向,确有不少与墨家相近,不容忽视。但其与墨家的交集,如所谓的“尚贤”“节用”“兼爱”“节葬”等观念,亦多见于其他学派的论著,很大程度上属于“公言”,并不能成为判定该篇性质的依据。而且,该篇的一些观念,如对“礼”与“命”的认识,又明显与墨家不合。相较于其他诸子,墨家独树一帜的实际上是“明鬼”“天志”“非命”诸说,但它们并未在《治邦之道》中得到体现。因此,将其简单定位为墨家佚书并不适宜。
李锐先生强调,以后世的学派观念来套用出土文献是不适宜的,由于当前的知识极为有限,尚不能清楚判断这些文献的思想来源与师承渊源[11]。《治邦之道》便是一种溢出我们现有认识的文献。但将出土文献与同时代的文献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它与哪些文献的思想体系兼容,又与哪些文献明显冲突,哪些属于公共思想资源,从而确认其思想倾向,仍是可行的。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治邦之道》有接近墨家的思想,也有其他学派的因素,但总体来说更兼容于儒家的思想体系。
这也启示我们重新反思儒墨关系。儒、墨同源而异流,故思想多有交集[12],亦多有针锋相对之处,乃至于相互攻讦非难,此即所谓“儒墨相非”。在看待儒、墨两家的关系时,我们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因为无论是儒家还是墨家,都经历思想上的嬗变。孔子、孟子、荀子之间,便有不少差异。与孔子相比,儒家后学的一些观念与墨家之间的差距已经逐渐缩小。其中有时代背景的变化,也有相互渗透与影响。
尽管《治邦之道》更接近儒家的旨趣,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便是儒家著作。如果置诸战国中晚期思想交融的大背景[13]79-81,明乎“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汉书·艺文志》)的现实需求,我们也便不必急于给这篇新见文献定性了。战国中晚期的齐地之学是百家争鸣的缩影,出自齐地的《管子》《晏子春秋》《荀子》有不少与《治邦之道》相吻合的思想,可作为《治邦之道》的重要参照。至于同见于清华简的《心是谓中》等文献,多与《治邦之道》呼应,它们之间的关系颇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