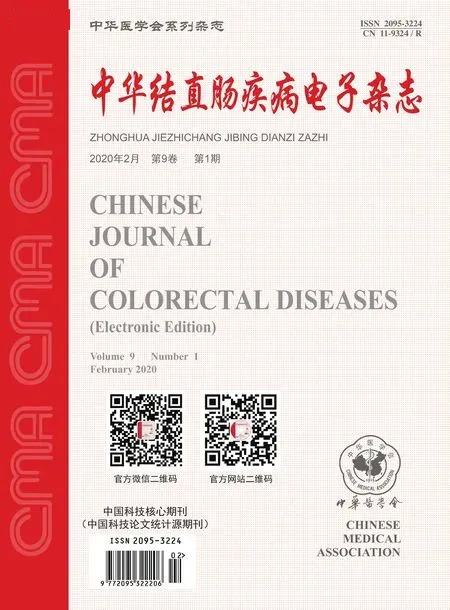2019年结直肠癌领域治疗进展
王正航 李彦豪 陈米芬 王晰程 沈琳 李健
2019年,虽然结直肠癌在治疗领域并没有太多的突破,但是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基于临床问题的不断探索。这些探索和成果主要集中于围手术期的治疗模式以及姑息治疗的方案研究。本文根据各大国际会议的报道和高质量文献的检索,对2019年结直肠癌治疗领域的临床进展进行梳理,希望能够为中国结直肠癌医生带来简明扼要的年度总结与展望。
一、围手术期
1. 新辅助治疗
对于无梗阻的局部晚期结肠癌(cT3-4N0-2M0)患者,FOxTROT研究将患者按照1:2随机分为辅助治疗组(n=364,术后氟尿嘧啶联合奥沙利铂[OxFP]共24周)和新辅助治疗组(n=698,术前根据KRAS状态予以OxFP±帕尼单抗共6周,术后OxFP共18周),主要研究终点2年复发率在新辅助治疗组和辅助治疗组分别为17.2%和13.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新辅助治疗显著降低了非R0切除率(4.8%vs.11.1%,P=0.001),其围手术期并发症反而有减少的趋势。有趣的是,在新辅助治疗组,针对肿瘤退缩分级(tumor regression grade,TRG)的分析提示,错配修复功能正常(pro ficiency of mismatch repair,pMMR)的患者TRG2-TRG4的比例为22.6%,远高于错配修复功能缺失(de ficiency of mismatch repair,dMMR)的患者(4.7%)。
FOxTROT研究在主要研究终点方面没有得到统计学差异,因此目前局部晚期结肠癌的标准治疗仍为术后辅助化疗,新辅助治疗可以作为一种治疗选择及今后的探索方向。dMMR患者对于联合化疗的反应较差,这似乎提示dMMR患者(无论Ⅱ期还是Ⅲ期)无法从联合化疗中获益,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似乎对这一人群是可行的。
2. 辅助治疗
对于高危的II期结直肠癌,IDEA研究共纳入了3 273例患者,1:1随机分组至3月化疗组(n=1 639)和6月化疗组(n=1 634)[2]。主要研究终点5年无病生存(disease free survival,DFS)在3月组和6月组分别为80.7%和83.9%,没有得出非劣效性的结论。对于使用CAPOX方案(卡培他滨+奥沙利铂)的患者(n=2 019),3月组和6月组的5年DFS分别为81.7%和82.0%(得出非劣效结论);对于使用FOLFOX方案(5-FU/亚叶酸钙+奥沙利铂)的患者(n=1 254),3月组和6月组的5年DFS分别为79.2%和86.5%(没有得出非劣效结论)。
对于IDEA研究中的子研究——来自日本的ACHIEVE2研究,却未能得到上述结论。该研究发现,3月组(n=255)和6月组(n=259)分别有84%和84%的患者接受CAPOX,两组的3年DFS分别为88.2%和87.9%,未得到非劣效性的结论;无论是CAPOX还是FOLFOX方案,均未得到3月组的非劣效结论[3]。
总体而言,对于高危Ⅱ期的结直肠癌,考虑到其良好的预后,故可以推荐3个月的CAPOX或6个月的FOLFOX。但是,传统的危险因素在决定辅助治疗方面是否具有相同的权重?不同的基因状态(如微卫星状态是否稳定)是否对于治疗具有影响?液体活检对于辅助治疗决策的影响如何?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分析。
事实上,对于辅助治疗而言,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已经逐渐成为了一项重要的考量因素。2019年,JAMA Oncology发表的三篇研究,证实ctDNA为根治术后患者的一项重要预后指标[4-6],但是其能否作为一项决定辅助治疗的指标尚缺乏足够的证据。
IDEA-FRANCE研究前瞻性地留取了法国参与IDEA研究的患者的血液标本,探索了ctDNA对于辅助治疗时长的预测作用。该研究共有805位患者进行了ctDNA检测(另有1 205位未检测)。结果发现,对于高危III期(T4或N2)而言(n=333),无论ctDNA状态如何,似乎使用3个月的治疗效果均不如6个月的辅助化疗。而对于低危III期(T3N1)的患者(n=472),若ctDNA为阳性,6个月的辅助治疗(n=29)数值上优于3个月(n=30);而对于ctDNA为阴性者,6个月(n=191)和3个月(n=222)的辅助治疗效果相似[7]。但该结果仅仅为ESMO 2019会议报道,缺乏更加详实的数据,以及无法明确ctDNA的作用在不同治疗方案中是否一样。因而,后续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于ctDNA状态对于临床辅助治疗的指导作用,而非预后作用。
二、姑息治疗
(一)免疫治疗
1. MSI人群
KEYNOTE-164研究探索了pembrolizumab在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dMMR患者中的疗效。根据既往治疗线数纳入两个队列:A队列为既往接受≥2线治疗的患者(n=61),B队列为既往接受≥1线治疗的患者(n=63)。主要研究终点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在A队列和B队列分别为33%和33%,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分别为2.3个月和4.1个月,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分别为31.4个月和未达到。治疗相关的3~4级不良反应分别为16%和13%。本研究对于目前的临床实践改变较小;但有趣的是,既往接受过≥2线治疗的患者比例在A队列和B队列分别为90%和62%,似乎PFS在B组中更优[8]。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中疾病进展(progressive disease,PD)者在A队列和B队列中分别达到了46%和40%。这充分提示了在MSI-H/dMMR人群中进一步筛选获益人群的必要性。
一项小样本研究共收集了使用PD-1/L1抑制剂治疗的22位MSI-H/dMMR患者的资料,发现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 burden,TMB)较高者ORR、PFS和OS均明显优于TMB低者[9]:使用log-rank检验,TMB的最佳阈值为37~41突变/百万个碱基(Mb)。13例高TMB的患者均对治疗有反应,而9例低TMB患者中,6例患者出现疾病进展。高TMB患者的中位PFS尚未达到(中位随访时间超过18个月),而低TMB患者的中位PFS仅为2个月。最佳的TMB阈值为37.4个突变/Mb,对应于MSI-H的mCRC患者数据库(821/18 140;4.5%)TMB的第35百分位数。除此之外,目前并未发现其他特定的基因状态与MSI-H人群的免疫治疗效果存在相关性[10]。
2. 微卫星稳定(microsatellite stable,MSS)人群
IMPALA研究在一线治疗达到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或部分 患者(partial response,PR)后将患者随机分组为Le fitolimod维持组(TLR9激动剂,可激动先天免疫系统和适应性免疫系统)和标准治疗组(原方案维持、减药维持或不维持),主要研究终点OS和次要研究终点PFS在Le fitolimod维持组和标准治疗组中分别为22.0个月vs.21.9个月和11.5个月vs.14.6个月,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11]。
REGONIVO研究在标准治疗失败的人群中使用瑞戈非尼+nivolumab(n=25),其中1例MSI-H,24例MSS。总人群的PFS达6.3个月、ORR达36%,MSS人群的ORR达33%。这可能和瑞戈非尼的靶向CSF-1R作用有关[12]。但是,自从研究结果公布至今,小范围的临床实践似乎并未取得相似的疗效。
CCTG CO.26研究发现,对于标准治疗失败的MSS人群,在血液TMB≥28突变/Mb的患者中,末线使用双药免疫治疗(抗PD-1和抗CTLA4)较安慰剂存在明显的OS优势,而在TMB<28突变/Mb的患者中不存在优势[13]。
(二)一线三药化疗+BEV
一项随机III期对照研究VISNU1在基线≥3个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中,对比了一线使用FOLFOXIRI(5-FU/亚叶酸钙+奥沙利铂+伊立替康)+BEV(贝伐珠单抗)和FOLFOX+BEV的疗效[14]。基线≥3个CTC的人群占总筛选人群的40.5%(487/1 202)。主要研究终点为PFS,三药+BEV组(n=172)的显著优于两药+BEV组(n=177):12.4个月vs.9.3个月,次要终点OS在三药+BEV组中有延长趋势:22.3个月vs.17.6个月(P=0.1407),次要终点ORR在可评估人群中三药+BEV组显著较高:69%vs.57%(P=0.0381)。PFS的亚组分析显示,左半及RAS/BRAF野生的患者更能从三药+BEV中获益,而右半或RAS/BRAF/PI3K突变患者无法获益。
既往的TRIBE和TRIBE2研究均对比FOLFOXIRI+ BEV 与 FOLFIRI(5-FU/亚 叶 酸钙+伊立替康)+BEV的疗效差异,本研究首次证实了在预后较差人群(CTC≥3个)中FOLFOXIRI+BEV同样优于FOLFOX+BEV。但令人困惑的是,TRIBE2研究显示,右半和/或RAS/RAF突变以及ECOG 0级的患者亚组(n=470)似乎更能从一线FOLFOXIRI+BEV治疗中获益(1st-PFS和PFS2的HR分别为0.69和0.68),而对于左半且RAS/BRAF野生型和/或ECOG 1-2级的患者(n=186),其获益较小(1st-PFS和PFS2的HR分别为0.90和0.87)[15]。这一结果与VISNU1研究结论存在矛盾。
(三)BRAF V600E人群
BEACON CRC研究是一项随机、三臂、Ⅲ期临床研究,在665例BRAF V600E突变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中评估了三靶向(BRAF抑制剂-Encorafenib,MEK抑制剂-Binimetinib,抗EGFR单抗-西妥昔单抗;n=224)或双靶向(Encorafenib联合西妥昔单抗;n=220)对比研究者选择的伊立替康或FOLFIRI+西妥昔单抗(对照组;n=221)的疗效[16-17]。中期分析显示,三靶向和双靶向组的OS和PFS分别为9.0个月和8.4个月、4.3个月和4.2个月,均显著优于对照组的5.4个月和1.5个月;三靶向和双靶向组的ORR分别为26%和20%,均显著优于对照组的2%。三靶向和双靶向组的≥3级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58%和50%;因AE停药的概率两组类似,分别为7%和8%。
有趣的是,此次中期分析的结果提示,三靶向和的OS、PFS和ORR和双靶向组差异并不显著,且与SWOG 1406的VIC方案(BRAF抑制剂-威罗菲尼,西妥昔单抗,伊立替康)的数据相似(PFS 4.3个月,ORR 16%)。三靶向对比双靶向的数据尚不成熟,今后临床上应首选三靶向治疗还是双靶向±化疗,仍是需要探索的方向。
(四)抗EGFR治疗的超选择
对于抗EGFR合适人群的选择始终都在探索之中。随着肿瘤异质性的出现以及检测手段的多样化,我们产生了新的困惑。既往研究提示当RAS突变的界值应选为1%[18],然而今年的研究却对这一结论提出的质疑。
在传统手段检出的72名KRAS和NRAS野生型患者中,Santos等[19]使用数字PCR法可以筛出23位(32%)患者存在RAS突变、25位(35%)患者存在RAS/BRAF突变,并探索了究竟该选取何种界值(0%、0.1%、1%、2%、3%、4%和5%)才能够真正筛选出从抗EGFR单抗获益的人群。结果发现5%的界值区分效果最佳,RAS/BRAF野生患者和突变患者的ORR、PFS和OS分别为51.7%vs.14.3% (P=0.076)、8.8个月vs.4.0个月(P<0.001)和16.2个月vs.7.4个月(P=0.012),RAS的分析结果也提示5%的界值最为合适。Vidal等[20]也发现使用二代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方法检测出的1%并未能在5%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获益人群。
对于组织RAS野生型者,当使用ctDNA检测RAS时,无论选取的界值为1%、0.1%还是0.02%,突变型和野生型患者中帕尼单抗的疗效均类似[21]。
除了以上单独对RAS突变丰度与抗EGFR疗效之间的探讨外,也有研究探讨了包括低丰度RAS突变在内的多平台panel检测(包括免疫组化、原位杂交、RNA测序、NGS测序以及多重PCR)与抗EGFR疗效的关系(基于帕尼单抗维持治疗-Valentino研究的探索性分析)[22],但该panel距离临床实践还有很大的距离。
(五)RAS突变人群
一项单中心随机对照研究BECOME纳入RAS突变的仅有同时性肝转移的结直肠癌患者,1:1随机分组至FOLFOX+BEV组(n=121)和FOLFOX组(n=120),主要研究终点肝转移灶的转化切除率[23]。在意向治疗人群中,经多学科综合评估的理论R0切除率在BEV组和对照组分别为23.1%和6.7%(P<0.001),实际R0切除率分别为22.3%和5.8%(P<0.001)。两组的ORR、PFS和 OS分 别 为 54.5%vs.36.7%(P< 0.001)、9.5 mvs.5.6 m(P< 0.001)和 25.7 mvs.20.5 m(P=0.031)。无论原发灶位于左半还是右半,均存在上述差异。
本研究为BEV在转化治疗中增添了证据。但是,考虑到初始不可切除的RAS突变患者的最佳治疗选择为双药化疗+BEV,因此本研究并不能改变当前的临床实践。既往的OLIVA研究、TRIBE研究和TRIBE2研究虽然对比了三药化疗+BEV和两药化疗+BEV的疗效,但纳入的人群还包括RAS/BRAF野生患者,因而对于RAS/BRAF突变的患者,三药+BEV是否在转化治疗方面优于两药+BEV,仍需更多的临床数据。
KRAS突变既往被认为是不可被靶向的靶点,在今年我们却看到了一些突破。AMG510及MRTX849都是针对KRAS G12C突变的药物。在12例接受AMG510 960 mg qd剂量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中,1例疗效为PD,1例PR,10例疾病稳定(stable disease,SD),ORR 为 8%(1/12),疾病控制率为 92%(10/12)[24]。MRTX849的Ⅰ期试验纳入了4例结直肠癌患者,1例达到了PR,肿瘤退缩达47%,3例为SD[25]。
一系列喜人的数据让我们看到了RAS突变患者治疗的曙光。但是目前仅有KRAS G12C位点研制出了相应的药物,该位点突变仅占所有KRAS突变的约5%[26],且不同KRAS突变的生物学行为也不尽相同[27],因而针对RAS突变的治疗仍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实践。
(六)肠道菌群
除了肿瘤部位、分子分型对于结直肠癌的治疗的影响,肠道菌群也逐渐被学者重视。研究显示右半结肠癌中梭杆菌(Fusobacterium)和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的丰度高于左侧肿瘤,而微单胞菌(Parvimonas micra)的丰度则低于左半肿瘤[28]。
另有研究报道使用抗生素后,结直肠癌小鼠模型的菌群多样性和组成均受影响,5-FU的作用也会相应渐弱[29]。但目前,关于结直肠癌和肠道菌群的研究距离临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0]。
对于围手术期治疗而言,结肠癌的新辅助化疗并未能在生存获益方面优于辅助治疗,术后辅助治疗仍然为标准治疗模式。对于高危Ⅱ期的结肠癌患者,可以考虑使用3个月的CAPOX或6个月的FOLFOX(类似于Ⅲ期);ctDNA已经成为根治术后患者的预后因素,但是未来能否根据其状态决定辅助化疗时长仍需要更多的探索。
对于姑息治疗而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对于MSI-H/dMMR结直肠癌的疗效已经确定,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原发性耐药,除了TMB显示出与疗效一定的关联外,目前尚无筛选有效人群的可靠标志。MSS/pMMR人群的免疫治疗仍无明显突破,高TMB人群也许能够获益于抗PD1单抗联合抗CTLA4单抗。三药联合靶向治疗逐渐崭露头角,但鉴于其不良反应较大,故亟需明确最可能获益的人群,但VISNU1研究与TRIBE2研究的亚组分析结果却未能找到一致的最大获益人群。对于BRAF V600突变的患者,后线使用抗EGFR+抗BRAF±抗MEK治疗效果显著,但仍需探讨双靶向与三靶向之间在生存、不良反应、生活质量、经济效应成本等方面的优劣。对于RAS野生患者,基于数字PCR、NGS也许能够进一步筛选抗EGFR的有效人群。对于KRAS突变患者,靶向G12C取得了良好的安全性与疗效,我们期待Ⅱ期和Ⅲ期临床试验的进行。肠道菌群对于结直肠癌发生与发展乃至治疗的影响才刚刚起步。
2019年结直肠癌治疗领域虽然没有重大突破,但也在围手术期治疗和姑息治疗方面有所进步。除了治疗模式和方案的创新外,在精准治疗的背景下,更加精确地筛选有效人群是也是今后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