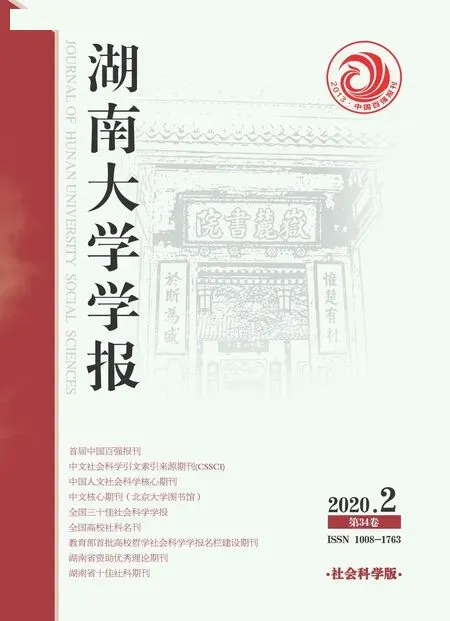宋代随州大洪山的佛教变迁:以碑刻为中心的考察①**
陈 曦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随州,位于今湖北省北部,地处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交汇地带,北通南阳盆地,南连江汉平原,西邻荆襄道,境内多山,大洪山和桐柏山呈西北—东南向分布,地当要冲,史称“ 随地有括囊之势”。(1)(宋)王象之 :《舆地纪胜》卷八三,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1992年版,第2700页。其地晋属义阳郡,后分置随郡,其后屡有废置;唐武德三年(620)置随州,领随县、光化、安贵、平林、顺义五县,贞观十年(636)割唐州枣阳来属;宋初为防御州,属山南东道,乾德四年(966)升为崇义军节度,复改崇信军,领随县、枣阳、唐城、光化四县;后属京西南路,元丰(1078-1085)时领随县、唐城、枣阳三县;南宋初陷于伪齐,岳飞收复后复置随州,升枣阳为军,割德安府应山县来属,领随县与应山二县,治随县。(2)(宋)乐史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四,中华书局点校本2007年版,第2795-2796页;(宋)王存 :《元丰九域志》卷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版,第25-26页;(宋)王象之 :《舆地纪胜》卷八三,第2696-2698页。
关于宋代以前随州地区的佛教,传世文献留下的记载很少。两宋之际,随州所在的京西南路虽然地处宋金交战的前线,南宗禅之一的曹洞宗却在该地区成长、壮大,位于州西南隅的大洪山则成为南宋曹洞宗中兴之地,这与唐五代以来佛教尤其是禅宗的演变有关,宗教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已有揭示。(3)成果如(日)石井修道 :《宋代禅宗史の研究:中国曹洞宗と道元禅》,大东出版社1987年版;(日)阿部肇一著,关世谦译 :《中国禅宗史——南宗禅成立以后的政治社会史的考证》,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顾吉辰 :《宋代佛教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杨曾文 :《宋元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毛忠贤 :《中国曹洞宗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闫孟祥 :《宋代佛教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吴仕钊主编 :《慈悲大洪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齐子通 :《湖北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等等。然而,佛教何以选择来到随州这个至宋代仍然“ 庳贫薄陋”(4)(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 :《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一四,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33页。之地、尤其在两宋之际战乱之时依然坚守大洪山?仅仅因为大洪山山势“ 斗绝 ”,避寇之人可“ 立寨栅自保”吗?(5)宋)王象之 :《舆地纪胜》卷八三《京西南路·随州》,第2705页。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如何与当地信仰交汇、又如何与地方社会和国家政权互动?同时,曹洞宗如何借助大洪山摆脱困境、走向复兴并影响两宋佛教的发展?《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佛祖统纪》等宋代佛教文献保存了唐宋时期随州及大洪山佛教的一些记载,若要进一步探讨其具体情况,《湖北金石录》收录的七方宋代大洪山保寿禅院碑石无疑是一组宝贵资料。七方碑石即《大宋随州大洪山灵峰禅寺记》(以下简称《灵峰禅寺记》)、《宋故随州大洪山十方崇宁保寿禅院第一代住持恩禅师塔铭》(以下简称《恩禅师塔铭》)、《随州大洪山崇宁保寿禅院十方第二代楷禅师塔铭》(以下简称《楷禅师塔铭》)、《随州大洪山十方崇宁保寿禅院第四代住持淳禅师塔铭》(以下简称《淳禅师塔铭》)、《随州大洪山第六代住持慧照禅师塔铭》(以下简称《慧照禅师塔铭》)、《净严大师塔铭》和《大洪山崇宁保寿禅院第十一代住持传法觉照惠空佛智明悟大师塔铭》(以下简称《明悟大师塔铭》)。(6)本文所引这七方碑石,均出自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之(清)张仲炘《湖北金石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356页。虽然宗教学领域在利用这些资料研究隋唐以来随州佛教的发展时,对大洪山佛教也有所涉及,但要回答上述问题,仍须围绕并仔细解读这组碑刻材料,以进一步探讨唐宋时期大洪山及相关地区佛教与政治权力、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考察宋代长江中游的信仰与社会变迁。
一 从襄阳到随州
东晋南朝时期,襄阳与江陵先后成为荆襄地区佛教传播的中心。晋哀帝兴宁三年(365),释道安率众南奔,两度分张徒众,抵达襄阳后,道安先居白马寺,后立檀溪寺,传法十五年,开启荆襄地区佛教之盛;道安弟子昙翼、法遇、竺僧辅、昙徽、慧远、慧持等先后在荆州长沙寺和上明寺讲经著书,(7)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八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3-148页;(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 :《高僧传》卷五、卷六,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5-203、212、229页。道安与弟子弘法之“ 流泽广且久也 ”,(8)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八章,第147页。如唐释道宣所言,东晋南朝荆州僧徒常有数百人,陈末隋初时达到“ 有名者三千五百人,净人数千 ”,殿宇数量多、规模大,且“ 至今三百余年,无有损败”。(9)(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 :《法苑珠林校注》卷三九,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57页。
南朝至隋,襄阳与江陵之间的佛教沟通,仍以道安为主线。道宣曾记载,释罗云兄道颙在江陵上明东寺起重阁,“ 在安公驴庙北。传云安公乘赤驴从上明往襄州檀溪,一夕返覆,检校两寺,并四层三所,人今重之,名为驴庙”。(10)(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 :《续高僧传》卷九,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01页。关于驴庙的传说,《道宣律师感应记》中却有如下对答:
又问:弥天释氏,宇内式瞻,云乘赤驴,荆襄朝夕而见,未审如何?答曰:虚也。又曰:若尔虚传,何为东寺上有驴台,岘南有中驴村。据此行由,则乘驴之有地也。答曰:非也。后人筑台于寺,植树供养。焉有佛殿之侧,顿置驴耶?又中驴之名,本是闾国、郄国之故地也。后人不练,遂妄拟之。(11)(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 :《法苑珠林校注》卷三九,第1258页。
两处说法都出于道宣,但两说相悖,一“ 实”一“ 虚 ”,暗示了道安之后荆襄地区佛教中心从襄阳转移至江陵。今人研究亦显示,六朝前期江陵成为荆襄地域佛教学术中心,宋齐之际衰落。(12)陈志远 :《六朝前期荆襄地域的佛教》,《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08-123页。
隋唐时期,佛教宗派大兴,荆襄地区亦是盛行之地,(13)汤用彤 :《隋唐佛教史稿》第四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6页;(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 :《续高僧传》卷九《释罗云传》、《释法安传》、《释慧哲传》,第299-304页。这一时期,檀溪寺与上明寺已少见于记载,位于襄阳与江陵之间的当阳逐渐成为本区的传法中心。隋释智顗即智者禅师在当阳弘教一事常为后人提及。智顗与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过往甚密,隋开皇十二年(592)十二月,智顗在当阳玉泉山创立精舍,重修十住寺,“ 道俗禀戒听讲者,至五千余人”;次年七月,杨广为智顗所创之寺奏请赐名“ 玉泉”;智顗一生造寺三十六所,仅仅将玉泉和栖霞、灵岩、天台三寺称为“ 天下四绝 ”,(14)(宋)志磐撰,释道法校注 :《佛祖统纪校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180、184页。按,(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 :《续高僧传》卷十七记智顗所立精舍得敕额“ 一音 ”,未提及“ 玉泉”敕额一事;另记智顗造寺总数为35所,第631、635页。可见玉泉寺地位之重,“ 天下四绝”的说法影响颇深。唐代,当阳地位仍然隆盛,如玉泉寺释恒景,武则天和唐中宗时三次被诏入宫为受戒师,“ 帝亲赋诗”时,恒景等人则“ 捧诗振锡而行,天下荣之”。(15)(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 :《宋高僧传》卷五,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0页。
虽然蕲州东山寺因禅宗四祖道信与五祖弘忍俱住其中,成为当时影响区域佛教发展的新的出发点,但弘忍弟子神秀在上元二年(675)去往荆州当阳山,推动了当阳佛教的隆兴,一时间,“ 四海缁徒,向风而靡,道誉馨香,普蒙熏灼。则天太后闻之,召赴都,肩舆上殿,亲加跪礼 ”,并“ 敕于昔住山置度门寺,以旌其德。时王公已下,京邑士庶竞至礼谒,望尘拜伏,日有万计。洎中宗孝和帝即位,尤加宠重 ”, 其后“ 天下散传其道 ”,誉其宗为“ 秀宗 ”,与同为弘忍弟子慧能之“ 能宗”并称“ 南北二宗 ”,且“ 名从此起”。(16)(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 :《宋高僧传》卷八,第177-178页。
随着神秀门人普寂与慧能弟子神会各立其师为禅宗六祖,北南二宗争端随之而起(17)汤用彤 :《隋唐佛教史稿》第四章,第189页。,加上双方卷入朝政,天宝(742-756)中,偏向于普寂的御史卢弈诬奏神会“ 聚徒疑萌不利 ”,玄宗敕徙神会于徙荆州开元寺般若院居住。(18)(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 :《宋高僧传》卷八,第180页。神会此次徙居荆州开元寺,从侧面反映出此时江陵的宗教地位已远不如东晋南朝时期。其后荆州天皇寺的兴起也可看出这一变化。据《宋高僧传》记载,释道悟在参谒径山法钦、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三位“ 哲匠”后,为玉泉山所吸引,选择栖止于玉泉寺附近的柴紫山(19)按,柴紫山在当阳县南八十里,与紫盖山相连,紫盖山有南北二峰,南者与覆船山相接,覆船山又名玉泉山,即智顗玉泉寺所在,见(宋)乐史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第2848页;(宋)王象之 :《舆地纪胜》卷七八,第2560页;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版,第500页。,致荆州“ 亿万计”都人士女“ 莫不擎跪稽首,向风作焉”;时荆州天皇寺“ 据郡之左,标异他刹,号为名蓝 ”,因“ 困于人火,荡为煨烬 ”, 僧坊主灵鉴认为,道悟才是复兴天皇寺之主,“ 乃中宵默往,肩轝而至”;其后江陵尹右仆射裴公“ 驱车盛礼,问法勤至……自是禅宗之盛,无如此者!”(20)(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 :《宋高僧传》卷十,第231-233页。道悟入灭后至唐末,似未有可称“ 名蓝”的江陵寺宇见于记载。
八世纪后期之后,慧能南宗迅速发展,慧能的两位弟子南岳怀让与青原行思法嗣广布,南岳怀让与弟子马祖道一禅系、青原行思与弟子石头希迁禅系分别从湘、赣流域崛起,迅速传播到各地,禅宗五宗出其门下:马祖道一在洪州形成洪州宗,至唐末分为临济、沩仰二宗;石头希迁以下,在唐宋之际逐渐形成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全国有多个传法中心。(21)杨曾文 :《唐五代禅宗史》第七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
曹洞宗始自洞山良价,洞山在高安县,唐属洪州,宋属筠州;(22)(唐)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版,第670页;(宋)乐史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第2117页。良价上承石头希迁——药山惟俨——云岩昙晟法系,从良价主要弟子青林师虔与曹山本寂、疏山匡仁(亦称光仁)法嗣的传法地点可以看到宋代以前曹洞宗在汉水中游地区的扩展:青林师虔复称后洞山师虔,因其先住随州青林山,后回洞山得名;(23)(宋)道原 :《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四部丛刊三编本。曹山法嗣处真禅师在襄州鹿门山华严院;青林师虔法嗣献蕴禅师在襄州凤凰山石门寺,广德和尚在襄州万铜山广德寺、芭蕉和尚在郢州芭蕉山;疏山匡仁法嗣守澄禅师在随州随城山护国院、省禅师在安州大安山、后洞山和尚在襄州。(24)(宋)道原 :《景德传灯录》卷二十。襄州鹿门山、凤凰山和广德山,随州青林山和随城山,郢州大阳山和芭蕉山,安州大安山,形成曹洞宗六世以前的传法中心。随着唐代佛教宗派大兴与禅宗五家的变化,随州佛教逐渐兴起,加之北宋中期曹洞宗开始走向繁荣,(25)相关成果如顾吉辰 :《宋代佛教史稿》第四章,第182页;毛忠贤 :《中国曹洞宗通史》第八章,第322-336页。皆为随州大洪山成为宋代曹洞宗的重要基地奠定了基础。大洪山佛教受人关注,或可上溯至唐释善信之驻锡。
二 从幽济禅院到保寿禅院
佛教进入大洪山的具体时间不详。道宣称自己曾在随州“ 兴唐伽蓝 ”,却未言何时;(26)(唐)释道宣 :《净心戒观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五册,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本2008年版,第819页。《景德传灯录》在弘忍大师第一世法嗣下录有随州禅慥禅师,在怀让禅师法嗣二世下记有随州洪山大师,二僧皆因无机缘语句,未载其传。(27)(宋)道原 :《景德传灯录》卷四、卷八。后世多以北宋张商英的《灵峰禅寺记》为据,认为随州洪山大师即宝历二年(826)来到大洪山的洪州开元寺僧善信。记文称:
元祐二年秋九月,诏随州大洪山灵峰寺革律为禅。绍圣元年,外台始请移洛阳少林寺长老报恩住持。崇宁元年正月,使来求《十方禅寺记》……
唐元和中,洪州开元寺僧善信,即山之慈忍灵济大师也,师从马祖密传心要,北游五台山,礼文殊师利,瞻睹殊胜,自庆于菩萨有缘,发愿为众僧执炊爨三季。寺僧却之,师流涕嗟戚。有老父曰 :“ 子缘不在此,往矣行焉,逢‘随’即止,遇‘湖’即往 。”师即南迈,以宝历二年秋七月抵随州。远望高峰,问乡人曰 :“ 何山也?”乡人曰 :“ 大湖山也 。”师默契前语,寻山转麓,至于湖侧。属岁亢旱,乡民张武陵具羊豕,将用之以祈于湖龙。师见而悲之,谓武陵曰 :“ 雨旸不时,本因人心口业所感,害命济命,重增乃罪,可且勿杀,少须三日,吾为尔祈 。”武陵亦异人也,闻师之言,敬信之。师即披榛扪石,乃得山北之岩穴,泊然宴坐,运诚冥祷,雷雨大作。霁后数日,武陵迹而求之。师方在定,蛛丝幂面,号耳挃体,久之乃觉。武陵即施此山为师兴建精舍,以二子给侍左右,学徒依向,遂成法席。太和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师密语龙神曰 :“ 吾前以身代牲,辍汝血食。今舍身偿汝,汝可享吾肉 。”即引利刀截右膝,复左膝,门人奔持其刃,膝不克断,白液流岀,俨然入灭,张氏二子立观而化。山南东道奏上其状,文宗嘉之,赐所居额为“ 幽济禅院”。晋天福中改为“ 奇峰寺 ”,本朝元丰元年又改为“ 灵峰寺 ”,皆以祷祈获应也。(28)(宋)张商英 :《灵峰禅寺记》,《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第322页。
《灵峰禅寺记》撰写并立石于崇宁元年(1102)正月,此时张商英降知随州。张商英述及善信来自洪州开元寺,并于元和(806-820)中师从马祖,此说素为后人所引用。但据《景德传灯录》,马祖道一在贞元四年(788)入灭,“ 元和中”为追谥道一为大寂禅师的时间;(29)(宋)道原 :《景德传灯录》卷六。《宋高僧传》亦载道一“ 至戊辰岁,举措如常,而请沐浴讫,俨然加趺归寂,享年八十 ”,(30)(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 :《宋高僧传》卷十,第222页。“ 戊辰岁”即贞元四年,因此,善信无法在元和中师从道一,也无法认为善信即《景德传灯录》之“ 随州洪山大师 ”,善信师从马祖道一之说恐误。后人提及善信师承及其传说时,颇与《灵峰禅寺记》相合,唯元人黄溍称善信生于广德二年(764),未知其说来源。(31)(元)黄溍著,王珽点校 :《黄溍集》卷十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80页。关于善信较为完整的信息,或载于杨傑《大洪山慈忍灵济大师碑》,然而此碑已亡佚,内容无从知晓。(32)(宋)王象之 :《舆地纪胜》卷八三,第2717页。杨傑卒于元祐(1086-1094)中,(33)(元)脱脱等 :《宋史》卷四四三《杨傑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第13103页。张商英卒于宣和三年(1121),(34)(元)脱脱等 :《宋史》卷三五一《张商英传》,第11098页。据此推测,张商英或得见杨傑之碑文,但以张商英的学识和对佛教的熟知程度,何以忽略善信“ 师从”马祖时间上的断裂?
善信来到大洪山即逢亢旱,遇到当地“ 异人”张武陵祭龙祈雨,于是,善信沟通龙神、劝诫与感化张武陵,以身代牲,祈雨成功。善信超然舍身,使佛教进入大洪山,这类征服本地神灵与“ 异人”、从而主导当地民间信仰的“ 进入模式 ”,颇具代表性。隋释智顗初至当阳时,亦有令本地神灵关羽父子臣服的一幕。其时智顗苦于道场寻址,在一番风雨阴魔之后,他见到威仪如王者二人,有了一场精彩的人“ 神”相遇:
长者美髯而丰厚,少者冠帽而秀发,前致敬曰 :“ 予即关羽,汉末纷乱,九州瓜裂,曹操不仁,孙权自保。予义臣蜀汉,期复帝室,时事相违,有志不遂,死有余烈,故王此山。大德圣师,何枉神足?”师曰 :“ 欲于此地建立道场,以报生身之德耳 。”神曰 :“ 愿哀闵我愚,特垂摄受。此去一舍,山如覆船,其土深厚,弟子当与子平建寺化供,护持佛法,愿师安禅七日,以须其成 。”师既出定,见湫潭千丈化为平阯,栋宇焕丽,巧夺人目,神运鬼工,其速若是。师领众入居,昼夜演法。一日,神白师曰 :“ 弟子今日获闻出世间法,愿洗心易念,求受戒品,永为菩提之本 。”师即秉炉授以五戒,于是神之威德昭布千里,远近瞻祷,莫不肃敬。(35)(宋)志磐撰,释道法校注 :《佛祖统纪校注》卷六,第178-179页。
引文所涉关羽信仰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冻国栋先生已有讨论。冻先生认为,宋人昙照《智者大师别传注》与志磐《佛祖统纪》关于智顗在玉泉山与“ 神”相遇的说法,很可能来自唐人董侹的《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以下简称《庙记》);将智顗立玉泉寺与关羽的灵异传说相关联,亦始于董侹,而昙照与志磐则进一步引申和渲染,“ 将关羽这一历史人物正式援入佛教‘护法’者之行列 ”,这说明德宗朝以来佛教在民间快速发展,不仅深入地方社会,还在与民间信仰的角逐中处于优势,既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又体现了当地官府和民众的需求。(36)冻国栋 :《略论唐宋间关羽信仰的初步形成及其特点——以董侹所撰〈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为例》(以下简称《略论唐宋间关羽信仰的初步形成及其特点》),杜文玉主编 :《唐史论丛》,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258-271页。董侹赞许关羽为地方保护神 :“ 所寄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 ”,(37)(唐)董侹 :《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清)董诰等编 :《全唐文》卷六八四,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第7002页。与此相比,志磐则将关羽置于“ 弟子”之位,让关羽敬称智顗为“ 大德圣师 ”,主动表达其“ 护持佛法”的心愿,关羽地方保护神的威力在智顗授以五戒后才昭布千里。从“ 出于入佛道之间”的董侹(38)冻国栋 :《略论唐宋间关羽信仰的初步形成及其特点》,杜文玉主编 :《唐史论丛》,第259页。到佛道兼修的张商英,在刻画智顗创立玉泉寺和善信进入大洪山的路径上有相似之处,当佛教与民间信仰交汇时,他们皆将佛教置于民间信仰之上,当然,他们还要借助一个重要推力,即国家祀典。
张商英称善信所居禅院因其舍身祈雨得到唐文宗赐额,后晋与神宗元丰元年(1078)再分获赐额“ 奇峰寺”和“ 灵峰寺 ”,皆因“ 祷祈获应”。而善信的“ 慈忍灵济大师”封号,则因庆历七年(1047)春旱,朝廷遣使前往大洪山祈雨,神灵迅速响应,“ 翌日大雨”。(39)(宋)志磐撰,释道法校注 :《佛祖统纪校注》卷四六,第1077页。奇峰寺改灵峰寺一事未见于正史,巧合的是,元丰元年朝廷赐封大洪山神宣泽灵骏公祠庙额“ 镇安侯 ”,(40)(清)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礼二0之九二,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810页。虽然张商英未言此事,但已显示出民间信仰和佛教同步发展,又暗示了二者之间的竞争。张商英通过塑造一个师承马祖道一、舍身降服龙神、令张武陵父子敬信的高僧,并得到皇帝赐封,进入国家礼典,从而使佛教扎根当地,征服地方社会。此时,来自洪州开元寺的善信,是否真正师从过马祖已远不重要。
《灵峰禅寺记》还记录了革律为禅后,张商英调解禅、律双方纠纷一事。(41)(宋)张商英 :《灵峰禅寺记》,《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第322页。关于灵峰寺是否曾归属律宗,学界有不同看法。(42)刘长东 :《论宋代的甲乙制与十方寺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80页;罗凌 :《无尽居士张商英研究》第四章,第120页;(日)石井修道 :《宋代禅宗史の研究:中国曹洞宗と道元禅》第三章,第234页等。不过,《恩禅师塔铭》称 :“ 绍圣元年,诏改随州大洪山律寺为禅院 ”,(43)《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第326页。按,此处所记灵峰寺革律为禅的时间与《灵峰禅寺记》不同。明确将灵峰寺称为律寺。如果绍圣以前灵峰寺为律寺,则意味着从幽济禅院至灵峰寺,大洪山佛教经历过宗派之间起伏消长的某些变化。(44)葛洲子关于唐末至宋初赣、湘与荆襄地区曹洞宗兴衰原因的探讨,可为理解这一变化提供线索,参见氏撰《政局·法席·法脉——唐末至宋初曹洞宗的兴衰》,《早期中国史研究》第八卷第二期,2016年,第31-47页。
北宋前期,因禅学体系难度较大,修习不易,导致曹洞宗面临困境,直至郢州大阳警玄禅师托临济宗浮山法远代立法嗣,得弟子投子义青,在警玄和义青的努力下,曹洞宗逐渐摆脱危机。(45)相关研究参见杨曾文 :《宋元禅宗史》第六章,第467-479页;毛忠贤 :《中国曹洞宗通史》第七章,第273-300页。对此,报恩当有所感受,他师从投子义青后,虽为士大夫所器重,如韩缜曾延请他住持少林寺,但他仍奉诏来到大洪山灵峰寺,开始了艰难的重建,如塔铭所云 :“ 部使者奏请师住持,已而丞相范公守随,复左右之。师普施法雨,远迩悦服。于是富贵者荐货,贫者献力,辟荆蓁蓬藋之场为像设堂皇,化豺狼狐狸之区为钟鱼梵呗……更定禅仪,大新轨范。由是,大洪精舍壮观天下禅林矣 。”(46)(宋)范域 :《恩禅师塔铭》,《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第326页。从“ 辟荆蓁蓬藋之场”“ 化豺狼狐狸之区”等描述来看,报恩当择新址增修禅寺,并得到前相、时任知随州范纯仁的支持和民间多方力量的相助,建立起一套规仪,令禅寺享有盛誉。报恩重建灵峰寺与曹洞宗走出低谷的进程大体相符。
灵峰禅寺或于崇宁元年(1102)更名“ 保寿禅院 ”,(47)报恩于崇宁二年(1103)离开灵峰寺,结合报恩为保寿禅院第一任住持,灵峰寺或于崇宁元年更名“ 保寿禅院”。报恩成为禅院第一任住持。次年,报恩奉诏离开保寿禅院赴东京法云禅寺,但他并不安于京城,而是“ 恳还林泽 ”,后在嵩山、郢州大阳山驻锡数年,于崇宁五年(1106)经知随州奏请复归保寿禅院;回到大洪山,报恩 “ 勤于诲励,晨夕不倦,缁徒辐辏 ”,从学者近三百人,宗风“ 遐振 ”,故《恩禅师塔铭》赞曰 :“ 祖提心印,惠于后昆。曹洞承之,与祖同源。源深流远,亹亹诸孙。惟大洪老,为世导师。蝉蜕冠绶,毗尼焉依……”(48)《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第326页。颂辞强调自报恩开始,大洪山传承禅宗,开启保寿禅院与曹洞宗新的一页;而“ 毗尼焉依 ”,恐与前述灵峰寺由律寺改为禅寺的背景相关。
三 佛氏内外
如所周知,北宋中叶后,投子义青的弟子芙蓉道楷推动了曹洞宗走向兴盛。道楷法嗣中,以丹霞德淳(即丹霞子淳)、净因自觉影响最大;德淳门下,真歇清了、天童正觉(即宏智正觉)、慧照庆预以提倡默照禅闻名,南宋曹洞宗南方各系的发展都与他们的后嗣有关。(49)关于芙蓉道楷及其法嗣与曹洞宗中兴的研究,参见杨曾文 :《宋元禅宗史》第六章,第480-516页;毛忠贤 :《中国曹洞宗通史》第八章,第322-336页。道楷、德淳、庆预和大洪守遂都曾住持保寿禅院,下面逐一述之。
道楷,保寿禅院第二任住持。自元丰五年(1082)出世,道楷先后住持郢州大阳山和大洪山保寿禅院等七座寺院,“ 皆当世元老名公卿以礼延请 ”,后来,道楷“ 被诏住东京十方净因,又徙往天宁万寿,皆中使奉命恩礼兼隆,诸方荣之”;《楷禅师塔铭》称 :“ 盖天下三大禅刹、曹洞之宗,至是大振矣 ”,将道楷所住持禅院视为三大禅刹之一,皆因道楷从大阳山和大洪山走出,将曹洞宗传播至东京及其他地区,其法“ 盛行于时 ”,对曹洞中兴影响尤大;道楷居大洪山五年间,“ 天下衲子辐辏云萃,不远千里而来 ”,弟子散布四方,广为弘法;政和八年(1118),道楷归寂于故乡芙蓉湖,七年后,保寿禅院第六代住持庆预禅师认为应酬其大恩,“ 示不忘本 ”,于是在大洪山为道楷建浮图,迁其灵骨回归大洪山。(50)(宋)王彬 :《楷禅师塔铭》,《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第331页。
德淳,保寿禅院第四任住持。德淳曾参谒大洪报恩禅师,复至郢州大阳山礼道楷为师,再住持大洪山,史载其“ 学识威仪,为众标表,峥嵘道望,推重一方”;保寿禅院经过报恩和道楷的建设,已颇具声望和规模,崇宁三年(1104),京西南路提点刑狱公事王信玉邀请德淳前往南阳丹霞山天然道场;其后保寿禅院经历一场大火,化为荒墟,政和五年(1115),知随州向公复请德淳住持大洪山,以重振保寿禅院;德淳到来后,“ 悉力营缮,增壮于前,逾年之间,复就者十七八,衲子依投,众几五百,方缘盛道广”。(51)(宋)韩韶 :《淳禅师塔铭》,《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第328页。德淳两度住持保寿禅院,进一步弘扬曹洞宗风,巩固了大洪山传法中心的地位。
庆预,郢州京山人,十四岁依道楷居于大阳,道楷“ 三贤孙”之一,宣和三年(1121)至绍兴三年(1133)住持保寿禅院,为第六代住持。当真歇清了、天童正觉尚在游方之时,庆预“ 已坐汉东两大刹 ”,“ 既而鼎立东南,问望迭胜”。庆预为道楷所器重,曾被派去辅佐德淳,与德淳同居大洪山。政和七年(1117),知州令庆预住持随州水南兴国禅院,并奏请朝廷颁赐“ 慧照大师”封号。庆预住持保寿禅院期间,正值两宋之际,时局动荡,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慧照禅师塔铭》记载 :“ 当群盗扰攘间,群盗环山如林,预恬不为意,日据绳床,颐指闲暇,外饬其役之强毅者固守圉以折豺虎之冲,内帅其徒之静专者谨禅诵以觊国威之立。若是者凡几年,卒与山岿然不拔,所活何翅万人,士大夫之家赖以生者,犹七八百数 。”(52)本段引文俱见(宋)荣嶷 :《慧照禅师塔铭》,《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第339页。塔铭盛赞庆预利用众僧特长,坚持抗敌数年,使大洪山过万人幸免于难,士大夫尤受其惠。庆预的成功,与当地易守难攻的地理条件有关:大洪山“ 崛起一方,巉然云间,四面斗险,山绝顶峰……靖康避寇之人立寨栅自保,贼竟不能破,以斗绝不可跻攀也 。”(53)(宋)王象之 :《舆地纪胜》卷八三,第2705页。庆预在大洪山曾聚积二千禅子,称“ 丹霞淳公,其后尤大 ”,(54)(宋)王彬 :《楷禅师塔铭》,《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第331页。说明在群盗四起之时,大洪山的佛教仍在发展。
关于庆预坚守大洪山,李心传云,绍兴元年(1131)三月,“ 时随州阙守,通判州事王彦威与州县官寓洪山僧寺,主僧庆预给其资粮,守洪山以拒贼……汪藻外制有《大洪山守珍补承信郎制》云,汝营壁坞,辑乡闾。恐与庆预事相关 。”(55)(宋)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85页。赵彦卫亦称 :“ 建炎、绍兴初,随陷于贼,而山中能自保,有带甲僧千数,事定皆命以官 。”(56)(宋)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 :《云麓漫钞》卷十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20页。据此,庆预不仅组织地方武装,筑堡自卫,守山拒敌,还保护通判州事与其他官员,为地方官府提供粮草,保全了大洪山,流盗平定后,僧人皆补以官。与逃窜的官兵相比,僧人的表现可用“ 忠”来概括,令朝廷满意,僧守珍的补官制书足以说明此点 :“ 既卫善良,亦除凶慝。其忠可录,何惜一官!”(57)(宋)汪藻 :《浮溪集》卷八《大洪山僧守珍补承节郎制》,《四部丛刊》初编本。知襄阳军府荣嶷亦感慨道 :“ 虽艰难中,所设施举中礼法往往,迄今颇能道之者,然则预岂惟有补于佛氏者邪?!”(58)(宋)荣嶷 :《慧照禅师塔铭》,《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第339页。
宗邃,或称大洪守遂,(59)(宋)冯檝 :《净严大师塔铭》称其为“ 宗邃 ”,《五灯会元》则记为“ 大洪守遂禅师 ”,后人多以后者称之,参见《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第341页;(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 :《五灯会元》卷十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97页。另,《慈悲大洪山》将其列为保寿禅院第三代住持,当误,参见该书第八章,第181页。曾在大洪山师从报恩。政和八年(1118),应知随州袁灼请求,住持随州东双泉禅院,袁灼还为其奏赐“ 净严”师号,后改住水南禅院,声望日隆。靖康二年(1127)局势恶化,净严退居德安府,住持延福禅院,不久,兵戈蜂起,郡守命净严率众僧移居德安府城内的化城庵,共同抗敌。绍兴五年(1135),净严移住保寿禅院。虽然净严来到大洪山距庆预离开不久,但兵燹已使大洪山满目疮痍,净严开始了艰苦的复兴之路。很快,“ 四方禅衲,骈肩而来,檀越社供,如赴约束。逾年,僧及半千,次满七百,复修院宇,追述先范,大阐纲宗。自此,灵济道场废而复兴。师住持十有三年,丛林再盛,不减畴昔 。”知泸州冯檝称,作为报恩嫡嗣、曹溪十四世孙,净严曾结十万人念阿弥陀佛,刊《华严经》《遗教经》诸经,注解《四十二章经》《佛遗教经》《沩山警策》,并有语录、偈颂并行于世,可谓今世高僧。冯檝特别提到,能称为当世“ 高僧”的,不外乎具备以下品质之一 :“ 阐扬教典,传授祖灯,护戒精严,存心慈忍,禅定不乱,精勤匪懈,身不衣帛,囊无积财,力兴丛林,善荷徒众,长斋不昧,坐脱立亡,有一于此,号曰名德 ”,更为重要的是,当面对祸患忧危时,净严仍能“ 心不摇夺 ”,“ 又能为高尚者之所难能 ”,可谓“ 追述先范,大阐纲宗 ”, 令“ 名蓝废而复旧 ”,故冯檝有“ 大洪之巅,灵济开山。始自恩公,更律为禅。嗣法净严,继踵而住”之语,实为褒奖净严之功业上接善信,堪比报恩。(60)本段引文均参见(宋)冯檝 :《净严大师塔铭》,《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第341-343页。那么,“ 能为高尚者之所难能”者,所指何事?
建炎年间,李横围攻德安府城,时任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率军民艰难守城七十日,粮尽之时,陈规出家财犒劳将士,士气益振,击溃李横;陈规镇守德安府期间,积极开展屯田和营田,于守城贡献尤大,《宋史》称“ 自绍兴以来,文臣镇抚使有威声者,惟规而已”;乾道八年(1172),孝宗诏刻陈规《德安守城录》,颁天下为诸守将法,并为陈规立庙于德安府,赐额“ 贤守 ”,追封忠利侯,后加封智敏。(61)(元)脱脱等 :《宋史》卷三七七《陈规传》,第11643-11645页。
坚守德安府城一事,冯檝提供了另一个版本 :“ 贼围城久,米升四十金。时众尚广,日惟一粥,师独请半。士大夫分惠粮储之类,即均赡大众。晨夕提振祖命,愈懃不辍。贼势甚紧,高声唱言:‘城破,但存延福长老。’攻既不利,而曰:‘城中果有异士。’遂引去。镇抚陈公规闻而谓众曰:‘异士,乃吾净严也!’”冯檝笔下可见德安官民与僧同仇敌忾、共同保卫家园之豪情,但将守城之功归于净严一人,仰赖其与城同在,此说大概与保寿禅院小师宗善有关。因冯檝与净严同乡,宗善“ 不远数千里”来到泸州,求铭于冯檝。与庆预率众僧坚守大洪山得到朝廷嘉奖不同,净严“ 以道德保护一方 ”,但未能进入朝廷视野,这使得净严无法与生前、身后皆获褒奖和封赐的陈规并提。另一方面,宣抚司对于净严舍身护城、忠于朝廷颇为赞赏,称其“ 于传道修行之外,又为人之所难能有如此者 ”,故兵燹之后,宣抚司奏请净严住持大洪山,复兴保寿禅院。宣抚司对净严的选择,体现了地方政府对佛教的需要与支持,这对于南宋初年身处战乱、陷于困境的曹洞宗而言,相当宝贵。而净严身后,宗善试图通过冯檝这位地方官员之手,“ 神化”净严的守城之功,使其超越陈规,恐怕是希望能够将净严事迹传至朝廷,提升本宗之影响,从而谋求自身发展。或许这是宗善“ 千里求铭”的一个重要原因。(62)本段引文均参见(宋)冯檝 :《净严大师塔铭》,《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第341-342页。
庆显,净严弟子,得到京西帅漕、汉东守倅的共同论荐,成为保寿禅院第十一代住持。庆显住持禅院引人注目,因“ 朝廷下省帖照应举请,盖自师始也”。庆显与士大夫来往密切,“ 缙绅名流,参叩以求 ”,如“ 丞相虞公、郎中陶公、殿撰陈公、左司丁公,皆当路主司者,一见而忘势交之,出口荐之”。此外,庆显道号“ 牧蛇 ”,因孝宗在东宫时,“ 为之亲洒翰墨,作‘牧蛇庵’三大字以标榜丛林 ”,还赐其“ 觉照慧空佛智明悟”大师法号,令“ 牧蛇”之声遍满江湖。此时,曹洞宗经历了北宋以来大阳警玄、投子义青的重振和报恩、道楷等人的中兴,(63)本段引文均参见(宋)张渊 :《明悟大师塔铭》,《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第354-355页。达到高峰期。曹洞理论与法门融合多家,更加丰富,而宏智正觉继承以往曹洞宗的“ 休歇”禅法,形成“ 默照禅 ”,使曹洞宗成为宋代禅宗内部与临济宗“ 看话禅”相对应的两大禅法之一;正觉的著名弟子中,包括大洪山法为法师、襄州凤凰山石门寺法真法师等,显示了该时期大洪山及附近地区曹洞宗之活跃。(64)杨曾文 :《宋元禅宗史》第六章,第467-516页;并见毛忠贤 :《中国曹洞宗通史》第七章至第九章。
从灵峰寺至庆显住持时的保寿禅院,禅院逐渐发展为名蓝,这个过程与曹洞宗的中兴和兴盛大体同步。令人困惑的是,绍兴三年(1133)慈忍灵济大师获赐“ 圆通应感慈忍灵济大师 ”,如此重要的赐封,上述七方碑石竟未尝提及,是因为知随州李道奏言灵济大师的灵迹如同民间的大洪山神镇安侯吗?(65)(清)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道释一之二,第7869页。除了同时奏请加封大洪山神与慈忍灵济大师外,李道还请朝廷赐封大洪山另外六位山神,因“ 金人侵犯本州,虏骑至山下,神变灵异,贼寇潜遁。收复之初久旱,祈祷降雨,民获秋稔”;诸山神还在绍兴十三年(1143)和乾道六年(1170)两度得到加封,封号均加至八字。(66)(清)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礼二0之九二、九三,第810-811页。民间诸神因与佛教具备同样的灵迹而得到朝廷的高度赞赏,这恐怕是佛教在与民间信仰的碰撞中希望回避的。进入皇权视野、纳入国家礼典无疑是佛教与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发展的共同出路之一,不过,佛教似乎对于如何得到赐额更为在意,或许它更希望通过高僧名德的弘法得到皇权认可,不断推进佛教向上层社会与地方社会的双向发展;而从朝廷与地方政府的立场出发,即使是不同的信仰,若在地方治理上能为政权提供“ 灵异”功能,朝廷危难之时能帮助官府组织各方力量共同抗敌,大加封赐并非难事。
四 结 语
与宋代保寿禅院有关的一组碑刻,记录了宋代随州大洪山佛教的兴衰,其变化与曹洞宗由低谷走向繁荣复渐衰落的过程基本同步,从中可以看到宗教与政治权力、地方社会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
张商英应报恩请求写下的《灵峰禅寺记》为后世提供了大洪山佛教发展的重要线索,报恩则为记文亲建碑石,使之成为大洪山的开山之典。其后碑石两次重立,一次在宣和六年(1124)由住持庆预重立,另一次在庆元元年(1195),由功德主覃道钟、监院僧宗邃再立。
宣和三年(1121)庆预前往保寿禅院时,面临北宋末年的动荡局势,如何求得生存和发展,恐怕是庆预需要思考的问题。庆预住持大洪山十二年,其间重立《灵峰禅寺记》碑以正本清源、传续大洪基业,或许可以看作是他的回应。一个祥瑞征兆透露出他的些许想法 :“ 凡两告去,皆弗克;及归,则一再有圆光之瑞,咸疑慈忍所忻相云,而师未始异也”。(67)《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第339页。举出慈忍祥瑞,颇具象征意义。
前述宏智正觉创立默照禅迎来曹洞宗的发展高峰,但绍兴二十七年(1157)正觉入灭后,(68)(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 :《五灯会元》卷十四,第902页。曹洞宗渐趋衰落,换言之,庆元元年前宗邃等人当已感受到曹洞宗的变化,故其对于大洪山的丛林地位尤为在意。《明悟大师塔铭》刻意强调三事,一是庆显住持保寿禅院由“ 京西帅漕、汉东守倅共论荐之 ”,而且“ 朝廷下省帖照应举请”始于庆显;二是庆显得赐“ 觉照慧空佛智明悟”法号,以“ 八字”凸显法号尊崇;三是以孝宗亲作“ 牧蛇庵”三字来标榜丛林,“ 此盖前辈衲僧遭逢当世得未曾有也”。(69)《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第355页。面对曹洞宗的危机,宗邃再立《灵峰禅寺记》碑,由报恩上溯义青乃至善信和马祖,伴以皇帝封赐、朝廷举请和地方官员论荐之说,试图强化大洪山的传法中心及曹洞宗的地位,具有现实意义。
如果说各级官员支持僧人出任住持与他们的个人信仰或是私人情谊有关,那么,朝廷危难之时僧人主动投身保护地方社会,则不仅与自身利益有关,也符合朝廷与地方社会的需要。前引汪藻所谓“ 其忠可录,何惜一官 ”,深刻表达了朝廷对“ 忠”的呼吁。而一个“ 忠”字,涵盖了政权对宗教、国家对地方、官员对僧人的规范要求。
七通碑石有一共同之处,即强调寺宇和住持们所获得的赐封。这本属常情,与皇权互动当然是声满江湖的“ 捷径 ”,而背靠地方官员的支持、借助与朝廷高官的私交,对于住持们走出大洪山、保持大洪山的传法地位以及曹洞宗走向繁荣十分有利。住持们还以另一种形式“ 走出”丛林,即辅佐朝廷和地方政府,这种方式看似“ 入世 ”,实则以“ 入世求出世 ”,在宋代佛教与儒学不断交融与相互影响的背景下,尤其在两宋之际的特殊时期,于佛氏内外皆有补益。这或许并非是走出丛林的藉口,恐怕也难以“ 僧俗界限模糊”简单论之。(70)毛忠贤在《中国曹洞宗通史》中提出,佛教由早期的“ 出世”变为后期的“ 以入世求出世 ”,虽冠之以“ 入世劝化”的名义,但成为许多僧众走出丛林的藉口;唐代禅宗尚能保持丛林的独立性,宋代的僧俗界限日渐模糊,第374-375页。另一方面,与唐代普寂、神会卷入朝廷斗争不同,报恩、道楷等人选择远离政治权力,在走出大洪山后又以不同形式“ 回归 ”,或复归大洪山,或由后人建浮图迎回灵骨。(71)(宋)荣嶷 :《慧照禅师塔铭》,《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第339页。这与曹洞宗谋求修正宋代禅宗“ 不安丛林”的“ 避世型”禅风有关,(72)毛忠贤 :《中国曹洞宗通史》第八章、第九章,第331、375页。《明悟大师塔铭》亦道出了众僧选择大洪山的原因 :“ 夫野人之居于深山,所与游啸而燕息者,草木之臭味、麋鹿之资性,适其所自适而已。其于身后荣名,与王公大人借势以为光宠,不惟地偏事左,非其所便利,而其世故缘法,不相关涉,莫或梦想及之也 。”(73)《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第354页。伴随着曹洞宗内部不同传法中心的发展态势,原本并不是曹洞宗发源地与大本营的大洪山,丛林地位日渐下降,在正觉引领曹洞宗走向高峰的时候,宗邃等人却希望借助孝宗御笔“ 牧蛇庵”来标榜丛林,宣扬“ 牧蛇”之声遍满江湖,实则反映出他们的隐忧与焦虑。
这些忧虑在元代得到了证实。据元人记载,宋末京湖制置史孟珙遣人自随州“ 捧佛足及累朝所被告勅 ”,徙寺额于鄂州侨置,奏请赐额“ 崇宁万寿 ”,称其为“ 鄂之洪山”(74)(元)黄溍著,王珽点校 :《黄溍集》卷十五,第581页。,此事虽未见于宋代文献,但已可看到宋末大洪山曹洞宗传法中心的衰落,此时道楷南宗已然趋弱,而道楷北宗迎来曹洞宗的第二次中兴则是元代的事了。(75)毛忠贤 :《中国曹洞宗通史》第十章,第386-3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