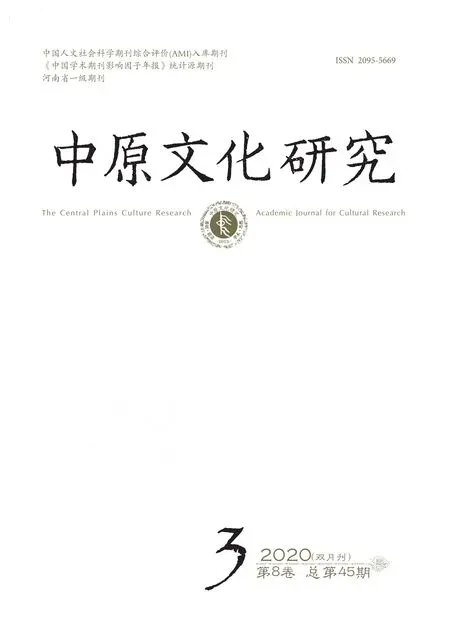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发展规律初探*
李建华 牛 磊
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历史错综复杂,但纵观数千年来政治伦理思想的萌芽、发展与变迁,不难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并非孤立存在、更非杂乱无章,而是呈现出一定的发展规律。当然对这种规律性的把握难免会有“以偏概全”和“先入为主”之嫌,但从中国政治伦理思想发展中找到规律,并汲取有益于国家治理的思想资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与社会历史同步发展
自先秦以来,我国伦理学家进行理论研究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追求书斋式的学问,而是寄希望在国家和政治的层面施展抱负,这才有了子夏“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名言[1]458。这也决定了我国的政治伦理思想往往服务于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其表现出与社会历史基本同步的发展特征。这一点在汉代政治体制的变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垓下之战击败项羽,建立了汉王朝。传统史学观点往往认为汉承秦制,但事实上,汉初的很多政治制度安排与秦朝相比差别甚大。如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秦始皇认为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分封和世袭制度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失去了拱卫中央的作用。基于此秦朝废除了三代以来的分封制,全面推行由君主任免和中央直接控制的郡县制。然而,刘邦统一天下之后却没有沿袭秦朝的郡县制,而是采取了郡国并行的混合体制。这里面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形势所迫。刘邦为了击败实力强大的项羽,不得不联合其他诸侯王,甚至不惜用列土封疆的手段来牵制项羽。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六大诸侯王的拥戴下登基为帝。这些诸侯王不但占据了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土地,而且拥有对属地的行政管理权、金属开采权、赋税征收权和军事指挥权,享有高度自治权。此时汉帝国的体制更像一个松散的邦联。这些都给帝国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隐患。尽管在后来的平叛战争中,所有异性诸侯王均被消灭或者撤销。然而,接下来刘邦并没有把王国的土地变成郡县,而是将自己的兄弟和子侄派往各地为王,先后分封了九位同姓诸侯王,用以拱卫中央政权。为了保障这一体制的长期运行,刘邦与大臣杀白马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但好景不长,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和六年(公元前174年)分别发生了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的谋反事件,汉文帝面对的严峻形势与当初的刘邦颇为类似。为了缓解和消除帝国面临的巨大危机,梁怀王太傅贾谊呈上了自己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见解,这便是著名的《治安策》。透过歌舞升平的表象,贾谊看到了帝国潜藏的三类巨大危机:“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其中首当其冲“可为痛哭者”指的就是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贾谊认为强大的诸侯王的存在从根本上破坏了君尊臣卑的伦理纲常,无疑会造成国家的混乱。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要削弱诸侯王的实力,即通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式,削弱诸侯王的实力,才能够明确君臣之礼[2]123。遗憾的是,当时汉朝中央政权所直接管辖的区域,不管是土地、人口还是财富,都无法与众诸侯王相提并论,为了尽快恢复国家元气,同时也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叛乱,汉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在国力逐渐恢复的基础上,汉文帝借助齐王刘则死后无子的有利时机,重封齐王和淮南王,将齐国一分为六、淮南一分为三,正式拉开了削藩大幕。
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官拜中大夫的主父偃沿着贾谊和晁错的削藩路线,第三次提出了削藩建议。在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基础上主父偃提出了“推恩令”,即诸侯王除了由嫡长子继承王位之外,可以推“私恩”,将封国的土地分给其他的子弟为列侯。按照汉制,列侯的封国隶属于郡,与县相当。与晁错强硬的削藩主张相比,主父偃的主张实现了王国小宗成员的利益均沾,诸侯国将会从削藩的阻力变成有效的推动力。果然诏令一下,诸侯王纷纷奏请分国封子弟。这一政策不仅使诸侯国的土地和实力大大缩小,国力大减,而且获得了诸侯王的普遍拥护。至此,困扰汉王朝一百余年的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被彻底根除。从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到晁错的“削亦反、不削亦反”,再到主父偃的“推恩令”,终于使得汉朝的政治管理体制从汉初弱中央、强地方的郡国并行体制,一步步回到了秦始皇时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得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重新得以整理,以君主为根本与核心的伦理纲常重新得到确认。在此之前,尤其是刘邦时期的汉初政治体制,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夏商西周时期,天子只是天下诸侯承认的共主,本身直接统治的土地是很有限的,并不具有管理诸侯国的权力,仅仅是在诸侯王国世代继承的时候给予合法性的确认。随着推恩令的实施,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主张终于经由主父偃的建议变成现实,并成为历朝历代秉承的基本原则,影响深远。司马迁在著述《史记》的时候就受到了大一统观念的影响,其撰写五帝本纪的时候,在确切史料缺乏而导致五帝之间血缘关系存疑的情况下,将颛顼、帝喾、尧、舜描写成了黄帝的后裔,进而将汉武帝之前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变成了统一的黄帝世系,也是对华夏文明正统性地位的佐证。不管后现代史学的“史为文也”的主张,还是观念史研究的“可超越”意识,都无法否定思想研究的基本规律和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即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发展。
二、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在思想文化演进中优势发展
如果说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伦理主义,而政治的伦理化与伦理的政治化又使伦理与政治始终纠缠在一起,那么政治伦理思想在中国思想的演进过程的优势发展就成为一种必然。早在上古时期,具有人格化的“天”成了人类社会一切道德的最终来源。“天子”是上天派来管理人间的统治者。因此天子统治民众的合法性来源不在于民众,而在于上天的意志。正因如此,面对“天子”的统治,民众便只有同意的权力,而没有反对的权力。人的命运都是上天提前安排好的,诚如子夏在《论语》所指出的那样,“死生有命,富贵在天”[1]286。尽管孟子在民众权利方面进了一大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重要民本思想[3]288。但不论是孔子倡导的“仁”还是孟子的民本思想,本质上依然是利用神秘主义中人格化的“天”来服务于君主的统治需要。然而,作为先秦儒家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的荀子,却在当时科技水平与人类认知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公然指出所谓天道不过是统治者的“文饰”而已。在《荀子·天论》篇中,荀子将观察的对象从道德个体、国家政权上升到了抽象的天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4]109。无情地戳穿了统治者利用民众迷信上天来编造自身统治合法性的谎言。作为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对那个时代诸侯利用自然现象装神弄鬼的事情进行了批判,揭露了政治虚伪的一面:“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4]268-269因此,君主要保有天下就必须让国家安定而非动乱,要实现国家安定就必须要有真正的功绩,真正的功绩就要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制天命而用之”。尽管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改造传统儒学思想的时候为了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而摒弃了荀子的重要思想。不过,作为先秦时期唯物主义思想的首倡者,荀子的政治伦理观直接影响了汉代王充等人的天命观,开启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先河。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制定了一整套的礼仪规章制度来确定朝廷君臣之间的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这一全新的政治伦理规范完全不同于上古三代以分封制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而是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布衣出身的刘邦由于认知水平的原因,对秦以来的伦理规范并不认同。《史记》记载,早在刘邦南征北战时期,身边的儒士陆贾常常在其面前引述《论语》《尚书》等古代典籍来说明治国之道。刘邦呵斥他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唇相讥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5]114于是,刘邦让他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和历史上治乱的缘故。他便写下了《新语》十二篇,讨论“行仁义、法先圣”的道理,使得刘邦不得不称善。汉朝建立后,由于刘邦和身边的谋士、将军等人大多出身微末小吏乃至屠狗之辈,所以对朝廷礼仪几乎一无所知。据《资治通鉴》的记载,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帝益厌之[6]94。秦代建立的君臣之礼荡然无存。
面对君不君臣不臣的乱象,汉初著名的儒士叔孙通向刘邦建议,必须要通过儒家的礼仪规范重新确立朝堂的行为规范,避免乱象继续下去。他认为:“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面对刘邦的疑虑,叔孙通指出:“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6]98-99从中不难看出叔孙通观点的可贵之处。一方面,每一个时代的伦理规范随着时代的变迁是不同的;另一方面,礼仪规范是为了时代和人情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而非本末倒置,为了礼而礼。因此,汉朝的礼仪规范要从自身的需要入手,并非单纯的恢复上古时期的礼制,而是采取博采众长的方针,将上古时期与秦代的礼仪规范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于是刘邦命叔孙通征召了山东地区的诸生三十余人开始起草朝廷礼仪。在叔孙通的努力下,只见朝堂肃穆,群臣俯首。刘邦看到此景,不由得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6]101自此之后,秦汉奠定的礼制规范成为之后两千多年中国历朝历代奉行的基本行为规范。因此,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之所以获得优势发展的地位,一方面源于政治伦理的“实用理性”,另一方面得益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哪怕是带有欺骗性的。
三、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在官方与民间中协同发展
不同于西方国家以性恶论和原罪论为基础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起源则是基于性善论的儒家思想。早在上古时期,以德配天、敬天保民便成为中国政治伦理的根本原则,上至天子、下至微末小吏无不遵循。《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有云:“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7]78这是当时讽刺夏启之子太康不务朝政而被放逐,但正是这样的政治事件更能充分体现出传统政治伦理的取向,就是说当时已经形成民众百姓是国家之基、社稷之本的政治伦理理念。可见,早在上古的理念中,用来协调君臣之间、官吏与民众之间的政治伦理规范就已经显现出了官方与民间协同发展的特点。虽然天是一切道德的来源,天道是统治者要遵循的根本原则。但是人道是实现和遵循天道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到了春秋时期,人道隶属于天道的认知和顺序发生了重大变化。诚如《左传》所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天道尽管是根本原则,但是却远离人间甚至缥缈不可捉摸;人道却存在于身边的社会人事之中,可以就近掌握。而对于人所难及的事物,又如何能知道呢?因此,在春秋之后,人道便成为了印证统治者是否遵循天道的重要证据。换言之,人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天道的决定因素,由此伦理道德更加使民众受益。先秦时期,尽管法家依靠着相关思想短时期内便可实现富国强兵,其代表人物管仲、李悝、商鞅等人纷纷在列国出将入相,大获成功。不过,在战国晚期荀子的著作中,处处碰壁、周游列国几乎一无所获的儒家却被其列入了“显学”的范畴。这充分说明,先秦各诸侯国的君主尽管大多信奉法家思想,但都意识到儒家倡导的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性。只有民众和统治者上下一心,才能够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粮食、布帛以及其他财富,才能够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军队。
儒家思想由民间思想成为官方思想,进而成为两千多年政治伦理的主导思想,也印证了官方与民间协同发展的思想轨迹。儒家创始人孔子将我国政治伦理的最终目标憧憬为一个理想境界:天下大同。其将这一理想境界描述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8]142。而实现天下大同的关键,在于统治者要能够“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在孔子看来,统治者能否取信于民,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所在。在孔子“仁”的基础上,孟子明确提出了统治者应当推行“仁政”的观点,从而提高了民众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进一步提高了统治者的道德义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3]288刘邦立国之后,尽管主要采纳了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但其目的依然是为了休养生息,尽量减少人民的各项负担,进而逐步恢复国力、巩固统治。在这点上,道家与儒家思想的目标是一致的。汉文帝时期,倡导统治者通过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来实现以德治国的儒家思想逐步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根据一些学者的考据[9]173,官拜长沙王太傅、多次被汉文帝召见的贾谊,从官方的角度率先阐述了官吏为民服务的利害关系,“故夫民者,虽愚也,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民苦之,则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新书·大政下》)。这是贾谊的一个创举,也是传统政治伦理的一个进步,用十分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深刻阐述了“官”与“民”之间的辩证关系,把“王”对于民众的依赖扩展到国、君、吏对民的思想依赖。到了汉武帝时期,尽管出于实现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在对先秦传统儒家思想的改造中更多强调三纲五常、借以推崇汉武帝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依然保留了孔孟倡导的关于统治者进行道德修养的很多内容。
贞观后期面对四海升平的局面,唐太宗开始大兴土木,名臣魏征上疏劝谏其要居安思危,这就是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文中指出:“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10]魏征认为,统治者对民众实施的仁政,和树木的根本以及泉水的源头一样重要。北宋中期大儒张载,在汉唐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对统治者的道德义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被近代哲学家冯友兰总结为“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儒学所代表的官方伦理思想而言,宋代包括二程和张载在内的北宋五子,以及南宋朱熹,则把汉唐以来的儒学拓展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张载所谓的“为万世开太平”,所表达的是先儒也是宋儒的永恒政治理想,民胞物与,全体归仁,让困惑无明的现代人重新回归率性诚明的人类精神家园。横渠四句也成为宋元以来历代士人不论为官还是为学所遵循的重要政治伦理价值观。所以,中国政治伦理思想总是在“官人”与“仕人”之间互动中得以发展。
四、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在思想争鸣中创新发展
思想只有在争鸣中创新,也只有在创新中才能发展。纵观我国数千年的发展史,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政治伦理思想最集中、最丰富、论战最激烈的时期,同时这个时期也是我国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发生巨变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各家各派的政治伦理理念并非一味的“法先王”或厚古薄今,而是能依据时代变化和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进行有针对性的扬弃,使得固有的政治伦理思想在争鸣中被有效继承的同时实现了创新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政治体制第一次面临巨大变化。通过两次东征,周公旦基本消除了原殷商属地和部分诸侯的反叛势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夏商时期类似邦联的政治组织形式,从而真正将天下诸侯的任免权与合法性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在此基础上,根据西周甲骨文、铭文和现有文献的记载,为了维系宗法制度,商朝时期并不常见的“德”字已经司空见惯。周人不仅在德字的构成上增加了“心”,而且将德与正、明、敬等一起使用,将德上升到了关系国运的高度。这便是西周王朝封建宗法制度的根基。以德治为核心的封建政治伦理成为封建宗法制度的指导理念。然而,随着周平王东迁洛阳,天子式微,已经逐渐沦落为天下名义上的共主。原有封建宗法制度对各诸侯国权利义务的约束基本消失,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礼制逐渐解体。道德成为苍白无力的说教,诸侯国之间频繁的征战成为常态。
当此同时,各派学者秉承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带着如何实现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重新建立起对各诸侯国行之有效的约束体系的思考,进入了百家争鸣的阶段。各学派之中,又以儒墨道法四家最令人称道。不过,四家学派之中,道家希望通过统治者的清心寡欲来实现无为而治,显得最为消极。诚如萧公权先生所言,老子近乎放任,庄子又接近无政府主义,既不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也不符合当时的客观发展趋势[11]7。因此道家思想并没有在各诸侯国引起重视。墨家尽管能够通过守城的技术来帮助一些弱小的诸侯国,然而其倡导的类似基督教无差别的爱的主张,在中国自古以血缘关系来确定远近亲疏的历史背景下注定不可能得到统治者甚至老百姓的认同,影响力同样有限。四派之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最为正统。孔孟为了宣扬儒家主张,皆周游列国,认为统治者应当意识到与土地和军队相比,人心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而要争取人心,依靠严刑峻法显然不如依靠恢复西周的德治主义传统,从而让整个社会和国家,实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的理想境界。不过,儒家主张看似合理,却没有为统治者解决最根本的难题,即面对敌国重兵压境,弱小国家的统治者如何通过仁政和德治来化解城破国灭的危机。由于无法实现道德的有效性,孔孟尽管周游列国时都受到了礼遇,却始终没有真正获得各诸侯国的重用,到处碰壁。
相对于道家的消极和儒家的说教,法家的先驱者管仲则对整个天下秩序如何重新恢复,以及诸侯国如何保境安民、尤其是保住宗庙和祠堂,给出了一个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的全新政治伦理思想。首先,管仲并没有否定西周以来的德治主义传统,而是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2]。其次,要实现物质的富足,在当时生产力颇为落后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农业显然是不够的,因此他倡导士农工商四民各安其处、各司其事,世代相承,避免发生混乱。最后,在诸侯国实力增长的同时,以“尊王攘夷”为口号,通过打着尊崇周天子的名义协调各诸侯国的矛盾,打击周边的异族部落,来实现中原秩序的稳定,从而以实力彰显德行,获得各诸侯国的服从。不难发现,管仲的法家思想并非是摒弃儒道,单纯主张严刑峻法,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吸取了儒家仁政与德治主义的伦理观念,以及墨家主张的兼爱、非攻的思想,既恢复了西周时期的安定秩序,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夏商时期的霸主格局。正因如此,管仲富国强兵的伦理思想引领了整个春秋时期两百多年的争霸格局与各国的改革道路。战国初期,管仲富国强兵的法家思想经李悝著述的《法经》而发扬光大,直接导致了战国时期各国期盼通过变法实现富强的改革思路。尤其是卫国人公孙鞅携《法经》西入秦国,历经十九年让秦国从西部边陲的弱小国家一跃成为战国时期的西方强国。
以商鞅变法为基础,秦国始终坚持法家富国强兵理念,先后历经七代君主,至秦王嬴政最终灭掉山东六国,一统华夏。尽管秦国十五年之后灭亡,但刘邦在建立西汉政治体制的时候亦部分承袭了秦朝体制。西汉武帝时期通过儒士董仲舒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彻底改造,杂糅并吸取了阴阳五行和法家等各派思想,使得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到汉武帝时期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百家合一的效果。这种由董仲舒首倡,汉武帝认可的全新的以外儒内法为核心、并吸取一定阴阳五行学说的儒家思想,影响了接下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进程。董仲舒等两汉大儒虽然奠定了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框架,但在往后的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无数次的理论挑战,特别是佛教的传入,以及明清之际西方文化开始的冲击,都显示出其在争鸣中求创新的发展轨迹。当然,这种争鸣往往是“内部性”的反思,抑或是同质异体之间的碰撞,缺少外部性参照,但也不失为一种思想发展的模式。
五、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在文化变革中开放发展
中国政治伦理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并非是完全的封闭的,而是随着整个文化的变更在开放发展。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文明未曾中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拥有强大的兼容并蓄的能力。在几千年的文化演进中,黄河流域的中原先民和周边部族不断的聚居和融合,逐渐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譬如在音乐领域,笛子、琵琶、箜篌、胡琴、羯鼓、腰鼓就是先后从少数民族地区引入的。尽管早在春秋时期,中原各诸侯国由于文明程度较为先进,为显示自身的正统地位,各国史书习惯于将周边的少数民族部落称之为夷狄。不过,中原文化并未采取对立或者隔绝的态度,而是主张开放包容。孔子就认为,只要进行了道德教化,“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世界观与国家治理就已经蕴含了宝贵的平等主义价值观念。春秋早期,身处南方荆楚之地的楚国,一向被视为蛮夷之国。不过,随着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推行,以周礼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认同感不断加强,中原文化也不断向四周传播。到了楚庄王时期,楚国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了华夏文化的一部分。楚人也已经完全接受了中原的文化观念,与中原人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邲之战,晋军大败,楚庄王与鲁、秦、宋、陈、卫、郑、齐、曹等中原各路诸侯在今山东泰安西侧的蜀举行会盟。通过此次会盟,楚庄王紧随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霸主地位被正式确认。自此,西周、春秋以来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地的楚国终于成为中原承认的霸主。之后历朝历代的史书在记载春秋五霸时,一直将楚庄王与齐桓公和晋文公一道位列其中。这也显示了中原文化对楚国的接纳,认为其通过学习和接受中原文化,实现了从蛮夷向华夏的转变。
到了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力图重新建立统一国家的格局愈加明显。为了增强本国实力并且在国际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各国君主对游走于列国的客卿所提出的诸如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理念大都采取了开放的态度。于是,平民出身的苏秦能够身佩六国相印,联合各路诸侯共同对抗秦国;主张连横的张仪能够在一河之隔,数百年争战不休的秦国与魏国均出任相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华夏,中原文化向南延伸到了南海之滨,向北则延伸到了阴山脚下。自此之后,正史的记载中均不再将边疆地区称呼为蛮荒之地,而是按照地理分布称之为岭南、云贵、陇西等,同样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开放式发展。
两汉之际,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传入我国。由于佛教倡导的出家修行与四大皆空等理念从根本上断绝了与家人、君主、朋友以及社会的基本伦理关系,与秦汉以来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严重对立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难以实现的。不过,由于东汉的灭亡,中国进入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和大动荡时期,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和挑战。佛教与当时流行的方术以及魏晋玄学一道,逐渐获得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欢迎,从宫廷传播至民间。在传播佛学思想的同时,佛教也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尤其是魏晋时期玄学在统治者和士人阶层中广为流行,佛经译家即用老庄学说中的概念、词语来比喻佛教经典中的名词,僧肇的般若理论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也是对魏经玄学的深化总结。同时佛教宣扬的因果循环报应说与儒家的善恶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通的。
自晋元帝司马睿东渡建康至宋齐梁陈,由于常年战乱,民众客观上需要精神层面的寄托和慰藉,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与统治地位,同样需要类似玄学的伦理思想出现。佛教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在民间日益深入。在一段时期,佛教的发展势头甚至超过了本土的道教以及儒家思想。其中最著名的事例当属南朝梁武帝萧衍。萧衍建立南梁后,定佛教为国教。为了推动佛教的兴盛,萧衍一生花费大量的金钱在全国各地修造了几千所顶级的寺庙,同时供养了十多万名僧人,用来供奉神明,并让众人们每逢节日时都前去朝拜。萧衍一生数次舍身出家,并把大量的宫人和土地贡献给寺庙,朝中大臣们前前后后筹集了四万万钱财为其赎身。佛教在中国经过四五个世纪的传播,到隋唐后,达到了鼎盛,这时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发达,文化交流融合,佛教也随着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涌现出诸多中国化佛教,如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并传播到日本、朝鲜,在那里又产生了新的流派。至此,佛教的中国化正式完成。
不过,随着佛教的日益兴盛,中国原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亦发生过矛盾与冲突,究其原因,有政治、经济利益,有哲学和宗教伦理方面的问题,以南北朝时为最激烈。当时思想门派众多,互相争鸣,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东晋末年,佛家经典越来越多,讲经论经兴起,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论战。与此同时,随着寺庙和出家僧人越来越多,能够从事农业生产、手工业和军事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少;同时很多寺庙在朝廷的支持下占有大量耕地,僧人本身不但不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历代寺庙都能够免除朝廷的劳役和徭役,更对人民群众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很多统治者认为佛教的发展威胁到了国家的农业、财政、经济乃至政权稳定。为了消除佛教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著名的“三武灭佛”。三武灭佛对当时蓬勃发展的佛教产生了沉重打击。北宋之后佛教主要流传的是禅宗,这一时期随着北宋五子对儒学思想的倡导,儒释道三教在对立、论战了数个世纪之后,不仅中国佛教各宗派已走向融通,佛、儒、道之间也日益相互调和,形成了宋明理学为主体的政治伦理思想,虽然儒学为主流,同时也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学说、理事理论。此后,无论心学还是理学,均在政治道德与政治伦理两个层面形成了修身养性与规章治理的独特思想传统。直至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中国人开始接受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政治伦理理念,中国政治伦理思想进行现代转型,表现出一股强劲的发展动力。
结 语
政治伦理思想是对政治伦理现象的观念性把握而形成的系统、稳定的认识,可以是专门化的,也可以是分散在其他思想文献当中。中国政治伦理思想史是一门专门化通史,如果说一切通史的总问题都在于通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或某一考察对象的“古今之变”,那么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的总问题则在于通古今政治伦理思想之变,即澄明中国自古及今的所有政治伦理思想所形成的谱系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变化规律。对于思想发展规律可以做两种理解:一种历史学的理解,认为思想发展本身存在一种客观的规律;另一种是解释学的理解,即如果说思想发展存在某种规律,那也是思想被解释的结果,或者说是被认识规律所赋予的。我们主张第一种理解。尽管如今观念史研究与新史学研究方法方兴未艾,但我们还是认为思想与社会的互动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遵循,离开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谈思想的发展,总有被“悬空”的感觉。上述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发展的几个基本规律或规律性特征,既反映了人类思想发展的一般性,也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独特性。一般性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立场与方法;独特性就是社会文化发展的民族差异性的客观事实。认识和把握规律是为更好地利用规律,服务于现实与当下。这就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并揭示其规律,为国家治理提供史鉴;就是通过呈现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脉络,厘清中国政治伦理思想之间的内在关系与历史进路,提炼中国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从思想史维度揭示我国政治伦理思想引领政治生活的机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