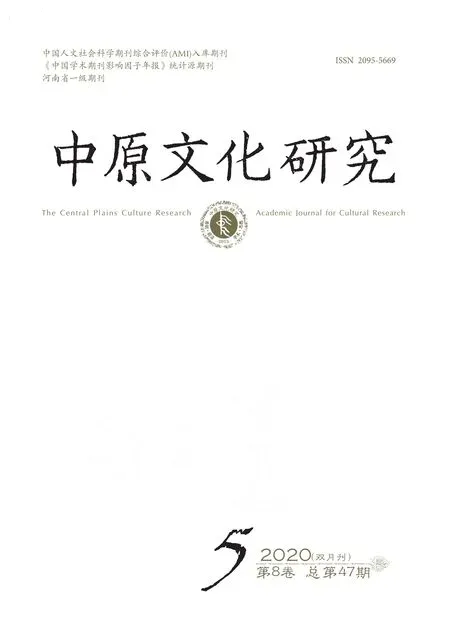五帝时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及人类学解读
沈长云
五帝时代是夏代以前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进入文明以前的一个时期。当前,我国学界正在进行中国古代文明探源的工作,有必要对五帝时代有一个比较全面清晰的认识。首先要认清历史上是否确实有过一个五帝时代?五帝时代的基本状况和社会性质如何?它的时间范围如何?所谓“五帝”是哪五帝?他们的身份与来历又是如何?考古发掘能够找到五帝的线索吗?这些问题历来引起不少争议,在当今学者中也存在着不少分歧。鉴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将个人的一些浅见和大家交流。请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一、五帝来历与五帝时代的确认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五帝时代,这是不容置疑的。《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即是讲五帝时代的历史。司马迁在该篇后面的“太史公曰”下谈到此篇的史料来源,称《五帝本纪》不仅依据了孔子所传《五帝德》和《帝系姓》(载今《大戴礼记》),更直接依据了《春秋》(《春秋左传》)和《国语》,是司马迁所言五帝的史事皆出自先秦时期更早的文献记录。尤其《左传》与《国语》,据称出自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之手,可以说是我国最早成书的两部历史著作,其史料价值绝非一般战国时期史著及诸子著作可比。今查《左传》《国语》两书,上面确实记有五帝及其他一些古帝的名称或名号,其时代在禹建立的夏王朝之前,是知太史公所述并非虚言。要之,五帝及五帝时代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不是人为编造的历史,这应当是讨论五帝时代的一个前提。
但是,仅仅从文献上找出五帝时代在历史上的存在还是不够的,强调《史记》《大戴礼记》《左传》《国语》记有五帝或五帝名号也还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人们会说这些书籍文献都是晚出的文字材料。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即“五帝”的来历,“五帝”的名号是否可信的问题。这个问题首先是顾颉刚先生提出来的。顾先生根据自己的“层累说”,提出“五帝”的名号产生皆晚。他说,周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神化人物),到孔子时才有尧、舜,到战国时又有了神农、黄帝。此说明显包含着“五帝”皆属后人层累地添加进中国古史的意味,也就是说他们都不那么可信。
顾先生的这个说法虽有依据,却有那么一点片面性。应当说,“五帝”的名号产生虽晚,却是其来有自的。它们并非出自后人的凭空想象,而应是出自后世一些著名氏族(或姓氏集团)对自己祖先的一种追忆。“五帝”之“帝”,按训诂说,实在是指自己祖先的牌位。《礼记·曲礼》说:“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帝”就是后人所立祖宗的牌位。对于自己祖先的牌位名号,想必人们(主要是主持祭祀的各姓氏集团的贵族)是不可以随便加以想象或随意杜撰出来的,那样的话,就是对祖先的不尊了。尽管祖先都生活在距离自己很久远的年代,但我们知道古人对于自己祖先的记忆同样也会保持得相当久远的。这在古代、近现代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那里都可以找到佐证。例如彝族某些家支通过父子连名的方式,可以将自己的祖先上溯到五六十代甚至上百代以前。所以“五帝”的名号产生虽晚,但亦可以相信是出自古代真实的历史。
当然,承认五帝名号及五帝时代历史的真实性,并不意味着对文献所记五帝时代的所有文字内容一概毫无保留地照章接纳。相反,我们主张要对这些文字加以检视,要通过科学史观,从各个角度加以识别,不仅鉴别它们的时代真伪,还要对它们的内涵意蕴进行研究考察。
二、五帝时代的历史学解读
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所谓五帝时代就是我国第一个早期国家——夏之前的一个历史时期。这对于每一位研究者来说,应当是很清楚的。而今要对五帝时代展开讨论,我以为主要是我们对五帝时代的内涵还有一些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对五帝概念的不同认识。这里面包含有以下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五帝”到底是哪几位古帝?按照通常的说法,即上述《大戴礼记》和《五帝本纪》的记述,“五帝”指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五位古帝。但是这里面却没有炎帝。其他一些文献对五帝有不同记载,如《礼记·月令》中的五帝便是指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这五位,可是却不包括帝喾、帝尧和帝舜。也有说“五帝”是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的。还有所谓“五方帝”的说法。这些“五帝”说,无非都是前人从不同角度对上古历史的一种总结,各有道理,无所谓对错,我们也不好去辨别它们的是非曲直。我们只需认识到这些古帝都是远古时期我们民族的一些著名祖先,是那个时代同样具有祖先性质的一些历史人物即可。
第二,这些古帝到底是一些什么性质的历史人物呢?此即是我们要给予回答的有关五帝概念的第二个问题。过去,不少人们都认为“五帝”是五位前后相继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君主或帝王,《史记·五帝本纪》即是这样一种认识。但这个认识显然是不对的。顾颉刚主张,要打破我国古代向来一统的观念,其实那时我国黄淮江汉广大地区连真正的国家都尚未出现,更不存在有什么一统国家的君主或帝王。按照文献记载,那一时期人群主要聚居的地区尚处在一个“天下万邦”的状态,帝尧、帝舜之治理天下,称“协合万邦”;禹会诸侯于涂山,称“执玉帛者万国”,万国即万邦,邦方同谓,万非实指,极言邦国数量之多耳。这众多的邦国都互不统属,各个邦国实际都是一些各自独立的氏族部落团体,它们上面并没有一个凌驾在所有氏族部落之上的权力机构。所谓五帝(包括其他古帝)不过就是这样一些邦国亦即不同氏族部落的首领,或者是其中一些比较强大的氏族部落集团的首领而已。我们看我国较早时期的历史文献如《左传》便称黄帝、帝颛顼为“黄帝氏”“颛顼氏”①,又称帝颛顼为高阳氏,称帝喾为高辛氏,称他们的十六位后人(所谓“才子”)为“十六族”②,说明“五帝”(包括其他古帝)原本确属我国上古时期一些氏族部落首领的性质。彼时这些氏族部落的势力都很有限。《国语》曾谈到黄帝、炎帝两个氏族部落的情况,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③可见黄帝和炎帝那时都只据有一条小的河流,地盘并不广大。其中黄帝所居姬水不可确指;炎帝所居姜水,据徐旭生研究,仅是宝鸡附近渭水的一条支流。是故,黄帝、炎帝部落都局限在今陕西中西部,远没有达到凌驾于整个中原地区之上的势力,更不用说是什么一统国家的君主了。下面我们还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所谓邦国的性质作进一步的分析。
第三,是包括五帝在内的各个古帝之间是否具有血缘亲属关系?过去《尧典》《五帝德》《世本》及《史记》所记录的“帝系”说,自颛顼以下的各位古帝均是一统天下的黄帝的子孙后代,甚至以后夏、商、周三代国家的君主也都是黄帝的后代。今天看来,这个所谓的“帝系”是十分不近情理的。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过去顾颉刚先生的说法,他在所发出的推翻非信史工作的几项倡议中,一开始就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④,就是针对这个以黄帝为首的“帝系”而言的。他认为这个所谓的“帝系”,实只是自春秋以来各民族融合而导致产生的一统观念的产物。实际上早期各族,“原是各有各的始祖,何尝要求统一?”这里提出中华民族非出于一元,各氏族部落皆有其各自奉祀的祖先,所谓“帝系”或者五帝的谱系乃后世民族融合的产物,是很有见地的。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古史专家徐旭生先生,尽管他在“信古”还是“疑古”的许多问题上抱有与顾颉刚不同的立场,但在对于五帝时代即传说初期历史性质的问题上,却持有与顾颉刚相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我国近二十余年史学界中所公信一点观念:我国有纪录历史开始的时候也同其他民族相类,就是说它是复杂的、合成的、非单一的”,“我国历史开始的时候,种族是复杂的,非单纯的”[1]3,28。可见徐先生对于五帝具有同一个血缘谱系的说法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遗憾的是,当今学者中却有人反其道而行之,仍旧将“五帝”的谱系奉为信条。例如许顺湛先生的《五帝时代研究》就坚持认为,“尧舜及夏商周三代的鼻祖都是黄帝的后裔”,“颛顼、帝喾、尧舜、夏商周都是黄帝的后裔”⑤。对于许先生的这个坚持,我想最好用考古发掘的事实来加以回答。设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及以后的夏商周各族都出自一个共同的谱系,那就要求它们各自的祖先都具有一个共同的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然而这与我们观察到的这个时期考古文化的多元性质和区系划分的格局却是不相符合的。考古文化的多元性质与古代民族的多元性、非单一血统的性质是正相吻合的。
顺便指出,现在许多人最常提起的包括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在内的五位古帝,实只是战国时人的一种归纳,即只将其时政治舞台上占统治地位的几支姓族的祖先加以归纳而得出来的。其中黄帝应是姬姓族的祖先,颛顼是包括妫姓、嬴姓暨芈姓族的祖先,帝喾是子姓商族人的祖先,尧是唐人暨祁姓族的祖先,舜亦是妫姓族的祖先。“五帝”不包括姜姓族的祖先炎帝,也不包括东夷族的祖先太昊和少昊,更不包括苗蛮族的祖先伏羲氏,为什么?因为其时这几个姓族在中原的政治舞台上已被排挤出去了(炎帝本是齐、许、吕、申等姜姓国族的祖先,但这几个国家到战国时都一个个“坠姓亡氏”了)。也正因为如此,后人才又有不同的“五帝”的组合。因此,我们今天所说的“五帝时代”,实是指先秦时期众多姓族的祖先在更早的文明时代以前生活繁衍的这样一个时期。
第四,是“五帝”的排列顺序问题。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五帝”并不是一个纵向的排利,它们之间应主要是一种并列的关系。即这些古帝(不止是“五帝”)大致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相差的时间不会太久。他们之间的先后关系也不一定如过去人们理解的那种顺序。过去徐旭生就曾辨析过帝喾与帝尧的关系,说《山海经》中帝尧总是摆在帝喾之前,这显示帝尧决不会是帝喾的儿子[1]91。所可论定者,是颛顼一定在帝舜之前,因为《左传》记载他们都是有虞氏的祖先,而颛顼的辈分要高于舜好几辈。至于黄帝、颛顼、帝喾这几位,因为并非出自同一个氏族,实在是不好比较他们的时间先后的。
第五,是各位古帝所在的地域问题。联系上面的内容,我们可推知各位古帝所在的地域实际也就是上古各姓氏集团分布的地域。那时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按血缘亲属关系居住在一起的,不若以后各姓族之人已是插花般地错居杂处在一起。根据文献,那时以黄帝为首的姬姓部族,即后世所称之白狄族者,应当居住在今陕西省和山西省的北部,兼跨今内蒙古阴山山脉以南的一些地方,因为文献记载春秋时代的白狄就居住在这一带,并所谓黄帝的陵墓亦在这一地区(所谓桥山黄帝陵,在今陕西子长县,非今日之黄陵县)。炎帝姜姓部族,包括后世所称之西戎或姜氏之戎者,居住在今甘、青一带,以及今陕西关中地区。他们应是渭水流域的土著。作为黄帝后裔的周人只是在后来才移徙到渭水流域与姜姓族人结为婚姻的(《诗经》称古公亶父“爰及姜女”)。颛顼所率领的有虞氏,应主要生活在豫东及鲁西一带,这两省交界的濮阳号称“颛顼之虚”,古今无异辞。它的一个支系,即祝融氏,生活在豫鲁苏皖交界一带,后来他们迁到今河南省的中部,故新郑有“祝融之虚”的称号,但这已是商代中晚期了。帝喾氏作为子姓商人的祖先,原居住地应在今山西省的中南部,他的两个儿子即两个支系,一个叫实沈,迁居至晋南大夏;一个叫阏伯,迁居至商丘,即商人最早的老家。帝尧陶唐氏乃祁姓之祖,据载曾有过多次迁徙,大概他们最初兴起在鲁西南的定陶一带,后迁至今河北省的唐县(或隆尧),再迁至晋南实沈居住过的大夏,也就是今临汾地区(《左传》昭公元年称“唐人是因”)。帝舜为颛顼氏之后,不必再述。少昊为东夷嬴姓族祖先,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太昊为东夷风姓集团的首领,居住在今河南周口淮阳一带,那里有所谓“太昊之虚”。最后,伏羲实是苗蛮族祖先“不疑”的音变,虞夏时期的苗蛮族实分布在今湖南洞庭湖至江西鄱阳湖之间,或稍北面的地区⑥。
关于五帝时代的年代,其下限应是没有争议的,关键是其起始的年代,也就是黄帝所在的年代。窃以为黄帝所在的年代不一定像现时一般人说的那么靠前。大家习惯了“黄帝五千年”这句口号,所谓五千年,其实只是一个约数。真要谈到黄帝的具体年代,恐怕没几个人这么说的。因为五千年前的中国社会还处在仰韶文化时代,怎么也不会出现如文献所述黄帝时代才具有的那些特殊的社会现象,如大规模的战争、符契、官署、城邑之类。这些东西是文明社会前夜才应具有的。因而谨慎的学者总是将黄帝的时代说得离文明社会更近一些。过去孙中山建立民国,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这是以当时一些学者的考订为基础算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制定的中外历史年表,则是以黄帝在公元前2550年。最近的一个说法是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的李伯谦老师提出来的,他说黄帝应当是在公元前2500年或公元前2300年[2]。我比较赞同李先生这个说法。大家知道,我主张陕北神木石峁古城就是黄帝部族的居邑,石峁古城的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这应当是五帝所在年代的一个标尺。当然,五帝中的尧、舜的时代不会有这么早,而应接近于夏初的年代,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五帝时代的考古学与人类学解读
尽管我不是学考古学的,但上面既然列出了我所认可的黄帝活动的上限年代,即公元前2500年或公元前2300年,所以整个五帝时期当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70年,或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070年左右。这个年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所以我判断五帝时代就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
如果再细致一些,要划分出各位古帝即各部族集团与龙山文化时期各考古文化的对应关系,那么可以大致认为,与黄帝部族相对应的是分布在今内蒙古中南部与陕西、山西交界一带的老虎山文化与朱开沟文化;与炎帝部族相对应的主要是分布于陕西渭水流域的客省庄文化,以及西部甘青一带的马家窑文化晚期类型(马厂类型);与颛顼氏相对应的应是分布在今豫北、冀南一带的后岗二期文化;与帝喾集团相对应的可能是分布于晋南一带的陶寺文化的早期,它的后嗣阏伯即子姓商族的祖先后来迁到河南商丘,则当属于王油坊类型文化的范畴了;与帝尧集团有关的也是陶寺文化,不过应是它的晚期。与东方少昊集团相对应的自然是山东龙山文化;与太昊集团相对应的则是分布在豫东、鲁西南一带的王油坊类型文化;与南方苗蛮族相对应的是湖北石家河文化。
从这些考古文化的性质、特征看,上述古族皆已进入农业定居的阶段,即使是地处今内蒙古中南部与陕西、山西一带的作为白狄祖先的黄帝部族,也基本是以农业为主[3]261-263,300-301,兼营畜牧业。其粮食作物主要是粟,黄河中游一些地方已种植有小麦,其下游及江淮流域则已有了稻的种植。他们的聚落形态也较过去先进,出现了较大型的聚落。一个较大型的聚落下面更有一些中型和小型的聚落,形成了一些学者所称的“都、邑、聚”这种聚落群结构。其中一些大型聚落上面还建起了城址,以维护住在里面的族邦领袖和贵族。这种情况也意味着各族邦内部的等级分化和财富的不均(这在各地的墓葬中亦多有发现),意味着社会正处在文明的前夜。
五帝时代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根据当代西方文化人类学四阶段进化的理论,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应当属于酋邦阶段。也就是说,上面我们说的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所谓邦、国,其实都应是酋邦组织,或复杂酋邦组织。
当代西方文化人类学有关人类社会早期发展的理论,一般国人喜欢称为“酋邦理论”。这个理论主要是在过去人们理解的氏族部落社会与国家之间加进了酋邦这样一个阶段,因而使得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更加合理,也更符合实际。从理论上说,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并不冲突,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起源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因此十分有利于我们的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研究,也有利于相应的考古学文化的研究。
上面谈到,我国五帝时代乃是一个“天下万邦”的局面⑦,这一个个的“邦”,实在就是酋邦。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所谓的“邦”,在我国古代文献或古文字中又往往称作“方”,或称作“国”,“天下万国”也就是“天下万邦”。今学者或笼统地称它们为方国,或邦国,也就是现在一些考古学者所说的“古国”。这些“古国”的性质并不是真正的国家,而只是酋邦。今从事聚落考古的学者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也是这样一种状况,如上所述,其时社会由许多的“聚落群”所构成,每个“聚落群”实际便是一个个的酋邦。聚落群的这种“金字塔结构”(或者“都、邑、聚”结构),实际正是酋邦社会的典型特征。这些酋邦有大有小,其中一些较大型的酋邦可称之为复杂酋邦,但其性质仍然是一种单纯的氏族结构。酋邦并不是某些人理解的那样,由不同血缘亲属关系的人群组成的社会组织。
当龙山文化时期,我国的酋邦社会已存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一些地区的酋邦组织或可上溯到仰韶文化中晚期。再进一步,便要进入国家社会了。文献表明,我国的早期国家即是在一个地域内由一个较大的酋邦联合若干个势力较小的酋邦组成的。例如夏代国家,即是由夏后氏在古河济之间通过联合该地区众多本姓族及他姓族的族氏治理本地区发生的洪水,通过集中使用众氏族部落的人力物力,从而树立起自己凌驾于各族氏之上的威权,才建立起来的。由五帝时代的酋邦社会转化为国家社会这一历史进程,是可以从这一过程中看得很清楚的。
结 语
综上,五帝时代作为中国夏代之前的一个历史时期,其存在是客观事实乃是讨论五帝时代相关问题的基本前提。“五帝”的名号产生虽晚但并非后人层累地添加进中国古史,其来源大致可信,多出自后世一些著名氏族对祖先的追忆。因此,五帝有不同说法和不同排列顺序也是与古代民族的多元性、非单一血统的性质正相吻合的。五帝时期尚处在一个“天下万邦”的状态,一统观念尚未出现,因此“五帝”不可能是前后相继的五位大一统君主,只是不同氏族部落的首领。“五帝”为代表的古帝是大致处于同一时代的人物,后世所谓“五帝谱系”实乃后世民族融合的产物。“五千年”只是理解五帝时代的约数,五帝起始年代的上限应在公元前2500年或公元前2300年。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应大致对应五帝时代,不仅出现了明显的农业定居特征,而且其社会发展也更接近于“文明前夜”的特点。根据当代西方文化人类学四阶段进化的理论和具体实际,五帝时代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应属于酋邦阶段,也是国家社会形成之前的一个重要时期。
注释
①参见《左传》昭公十七年和昭公七年。②参见《左传》文公十八年。③参见《国语·晋语》。④参见《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⑤相关论点见许顺湛先生的《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⑥参见《战国策·魏策》吴起之语。⑦参见《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等相关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