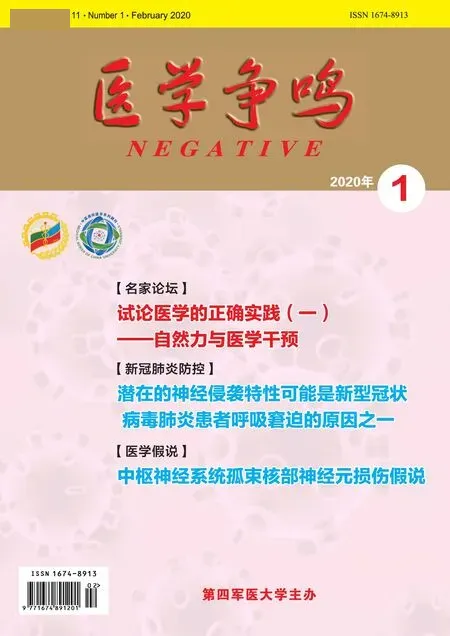收缩功能不全性心力衰竭心肌逆向重构: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
李海嵘,陈关良,方小丽,蔡兴赳,许荣丽,林慕如
(海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海南省临床医学研究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海南 海口 570311)
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病最严重的表现之一或晚期阶段的一组临床综合征,死亡率和再住院率居高不下。一项对国内10 714例心力衰竭患者住院期间调查显示,心力衰竭的主要死亡原因为左心收缩功能不全性心力衰竭(59%)[1-2]。以往认为心力衰竭是一种不断发展的疾病,一旦发生心力衰竭即便没有发生新的心脏损害,在各种已经激活的病理生理变化作用下,心功能不全将不断恶化进展[3]。但近些年来,随着左西孟旦等新型心力衰竭治疗药物的出现,以及心脏再同步化治疗、左室辅助装置(left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LVAD)等新型器械治疗的应用,研究发现治疗后患者心室容积和质量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降低,部分心室甚至恢复到正常形态大小。这种改变反映了心肌大小和功能的生物学好转以及心室结构和组织的修复,伴随左心室舒张末期压力与容积的关系向正常化方向转变,称为“逆向重构”[4-5]。这一发现迅速成为心力衰竭研究领域新的焦点,虽然目前已经仔细研究和认识逆向重构的各种可能病理生理机制,但仍不清楚这些机制在整体上如何推动心脏结构和功能恢复,现有的研究和认识之间也存在一些争议和矛盾之处,下面就一些关键性争议进行探讨。
1 心力衰竭逆向重构存在差异性生物学特征
临床研究表明,已发生心力衰竭逆向重构患者预后存在明显差异。部分患者发生逆向重构后心脏结构和功能恢复正常或趋近于正常,在此后的随访中,无需任何治疗情况下没有再次出现心力衰竭事件,而部分患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复发性心力衰竭事件可能性增加[4]。基于逆向重构的不同临床结果,有学者提出将逆向重构划分为心肌复原和心肌缓解两种情况。心肌复原应用于描述与之相关的分子、细胞、心肌和心室几何变化的正常化,这部分患者预后不发生心力衰竭事件。而心肌缓解应该用于指分子、细胞、心肌和心室几何变化的近正常化,这些变化能够引起心脏逆向重构,但不足以阻止今后在正常和/或异常的血流动力学负荷时心力衰竭的再次发生。这种基于生物学特征划分方法虽然可以将逆向重构不同预后区分开,但仍没有回答和解决二者间的关联,是同一种生物学现象的不同阶段,还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物学现象?目前仍不得而知。且这种通过患者结局预后判断的分类方法严重滞后于临床治疗,有 “事后诸葛亮”之嫌。但从中可以得出一些启示,在心力衰竭逆向重构期间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正常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心脏内在的生物学机制实际上变得正常,只有研究真正确切认识清楚心肌复原和心肌缓解之间潜在的生物学差异和联系,寻找新的治疗策略在这些患者中启动和加速逆向重构,才能对临床实践有真正的指导意义。
2 心力衰竭逆向重构临床评价尚无统一判断标准
心力衰竭逆向重构受血流动力学、神经—体液因素、表观遗传因素和遗传因素影响,心肌主要在肌细胞、心肌间质、微血管密度等方面发生了修复性改变,其外在表现形式是心室的缩小、室壁结构的恢复以及收缩和舒张功能的正常化。目前心脏逆向重构的临床评价方法也主要集中在心脏的结构和功能方面,主要的评价方法有超声心动图、心脏磁共振成像(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CMR)、生物标志物。经胸超声心动图临床应用广泛,使用简便,可动态观察心脏的结构、收缩和舒张功能,是临床评价心脏结构和功能最常用的方法,但目前尚无统一心力衰竭逆向重构超声观察指标。最早有学者应用左心室舒张末期压力与容积的关系评价心力衰竭逆向重构[6-7],也有学者认为,左心室容积和左室射血分数是临床更为实用的左心室逆向重构评估指标[8]。还有一项荟萃分析表明[9],左心室射血分数升高,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和容积、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和容积,以及左心室质量的降低是反映逆向重构的可靠证据,且与临床预后存在显著相关性。目前CMR技术是测量心室容积、室壁厚度、左心室质量和左室射血分数等心脏结构和功能指标的“金标准”,其准确度明显优于超声心动图。此外,部分CMR成像技术能观察心肌间质和微循环的病变,并据此判断逆向重构的发生[10-11]。逆向重构是一系列心肌生物学表现变化的结果,故生物标志物应是最佳评价标准。但现有的各种生物标志物均不能直接评估心脏逆向重构,部分生物标志物如N末端B型利钠肽原和可溶性生长刺激表达基因2蛋白临床证实可用于预测逆向重构的发生。其他还有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下心肌灌注成像和心内膜心肌活检等。综上所述,虽然逆向重构临床评价方式很多,但多是间接指标,尚无能够反映和衡量心肌逆向重构基本生物学“始动因素”直接指标。没有统一判断标准,就容易造成不同研究间对逆向重构评价体系不同,研究结论可信度良莠不齐,不利于对逆向重构病理生理机制的研究。
3 心力衰竭逆向重构有效治疗方案莫衷一是
对于左室收缩功能不全性心力衰竭患者而言,左心室逆向重构无疑是一个预后改善的积极表现。左心室逆向重构一般定义为在收缩功能不全性心力衰竭患者中,左室射血分数随着时间变化逐渐增加,同时伴有左室舒张末容积缩小。尽管在最佳药物治疗下,可能自发的出现左心室逆向重构,但更多数情况下左心室逆向重构发生在这些条件下:间接获益于心脏负荷的减轻,如主动脉瓣关闭不全治疗术后;直接获益于某些侵入性的治疗方法例如LVAD、心脏再同步治疗。而对于某些特定病因引起的心力衰竭(急性心肌炎、围产期心肌病等),高达40%~50%心力衰竭患者发生临床症状恢复以及左心室结构和功能正常化[12-13]。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左心室逆向重构不会导致“正常”心脏,基因表达谱分析研究表明,尽管对LVAD支持有典型的逆向重构形态学和功能反应,但只有大约5%在衰竭心脏中失调的基因经LVAD支持后恢复正常[14]。心力衰竭逆向重构有效治疗方式众多,这就给临床带来困惑,心力衰竭的逆向重构究竟是获益于心脏负荷减轻,受益自药物使用后神经—体液因素的变化,还是得利于心肌收缩协调性的改善,亦或是上述治疗方案间相互协调作用的结果?事实上真正与逆向重构生物学机制对应且有效的治疗方案目前仍不清楚,有待于对这些研究进行有效的荟萃分析,甚至选择适当的患者进行临床试验后得出。
4 结语
综上所述,心脏为适应心力衰竭时许多不良改变,经历结构和功能上诸多变化(心室重构),最终导致心力衰竭疾病进展。许多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还表明,心力衰竭具有潜在的可逆性,并且心脏能够有利地逆转心室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变化究竟如何推动心室结构和功能恢复正常,也就是说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我们根本不明白心肌逆向重构的基本生物学“始动因素”是什么,我们也不了解它们是如何相互协调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有时逆向重构发生后未再出现心力衰竭事件,以及为什么有时逆向重构发生后出现心力衰竭事件复发,甚至是哪种治疗方式更有利于逆向重构发生。但毋庸置疑的是客观上确实存在逆向重构这一现象,并且研究这一现象后面的病理生理机制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可以将目前减弱重构的“消极”治疗方式,变革为寻找新的“积极”治疗策略,在这些患者中启动和加速逆向重构,让心脏趋近正常甚至恢复正常。鉴于我们目前对逆转左室重构的生物学机制缺乏了解以及逆向重构存在不同的临床结果,实谓之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