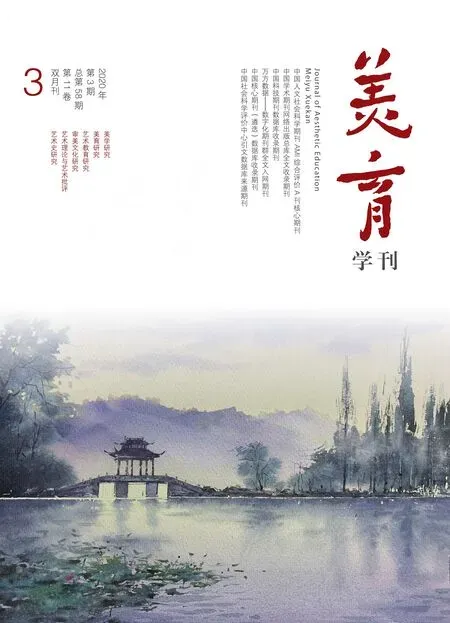新实用主义的美育观
——舒斯特曼与罗蒂比较论
王 伟
(福建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福建 福州 350001)
与传统美学范式相比,西方后现代哲学、美学最为突出的特征莫过于反形而上学,或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形而上学可谓一把“双刃剑”,它既开启了美学生态的崭新空间,也引发了热衷解构、不事建构以及流于相对主义等诸多担忧。正因如此,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严词批评柏林(Isaiah Berlin)在坚决反形而上学时,往往流连于多元主义与反极权主义之类的主题,而对正义、同情或者团结等问题则漠然相向。[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反形而上学之后做什么这一方面,新实用主义阵营的罗蒂(Richard Rorty)与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二位学者的表现可圈可点。罗蒂以其《哲学和自然之镜》(PhilosophyandtheMirrorofNature,1979)解构了传统哲学的基础主义,并在《哲学与社会希望》(PhilosophyandSocialHope,1999)一书中明确提出“泛关系主义”(panrelationalism)[2]的主张——一切均需在关系网络中进行定位——取而代之,有效地堵住了相对主义的可怕漏洞。而其《偶然、反讽与团结》(Contingency,Irony,andSolidarity,1989)虽然从偶然的哲学立场起航,但落锚之处却是经由美育去创造出共同体的团结。同样,舒斯特曼现在也持这种偶然的观点,也特别强调美育对促进共同体团结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舒斯特曼每每极力论证自己与罗蒂的不同,甚至不惜付出对罗蒂著作断章取义的代价。因此,全面考察罗蒂与舒斯特曼的美学、美育思想,厘清两者的差异与共同点所在,并进一步辨别其中的洞见与不见,显得颇为必要。
一、舒斯特曼对罗蒂的误读举隅
虽然罗蒂与舒斯特曼通常都被视为新实用主义的健将,但有意思的是,舒斯特曼不太乐意别人把他与罗蒂相提并论,尤其反感别人将他们的观点混为一谈。在回应马格利斯(Joseph Margolis)“太深地落入罗蒂的咒语”的攻击时,舒斯特曼一方面表示这可以理解,因为毕竟罗蒂强烈影响了他在实用主义中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他又认为这种理解令人吃惊且具有误导性,因为他与罗蒂的观点有太多的冲突。通读舒斯特曼的多本著作,不难发现,他时常批评罗蒂,并在与罗蒂进行论辩的过程中来彰显、界定自己的观点。遗憾的是,很多批评常常经不起推敲,有的批评甚至被舒斯特曼本人后来的著作所否定。
首先,关于形而上学或本质问题,舒斯特曼在《实用主义美学》(PragmatistAesthetics:LivingBeauty,RethinkingArt,1992)中明确表示,实用主义“必须反对不可改变的本质的基础主义观念,这种本质永久地定义我们的对象和概念的不同的同一性”。然而,紧接着他就开始指责罗蒂的反本质主义过于激进,甚至因强调个性和偶然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而成了“倒转的反本质主义的本质主义”。(1)这种论断未能明了罗蒂“偶然”范畴的内涵,难以成立。详见王伟《罗蒂是倒转的本质主义者吗?——与舒斯特曼先生商榷》一文(载《华中学术》2018年第3期)。他主张,“后罗蒂的实用主义”既能与基础主义认识论断绝关系,又可以重新启用本质的观念。[3]119-119显然,这是一种较为温和、两面讨好的折中之举,这一本质属于历史化的本质。耐人寻味的是,约莫十年之后,舒斯特曼的《表面与深度》(SurfaceandDepth,2002)继续批评罗蒂“夸大了实用主义的偶然性观念,赋予它一种独特的任意性或随机意外的意义”[4]255,却对所谓历史化的本质绝口不提。而在其最新著作《情感与行动:实用主义之道》(ActandAffect:PathsofPragmatism,2018)(2)该书源于舒斯特曼2017年在复旦大学的系列讲座。中,开篇第一章“实用主义十原则”的首条即是“实在的性质是变动的、开放的、偶然的”。舒斯特曼指出,“生活和社会世界中的事物或事件是偶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完全偶然、任意的,并因此不受任何可测、可知、可用的规律的支配。这即是为何尽管所有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都强调偶然性(皮尔斯[C. S. Peirce]称之为‘偶成论’[tychism]),却都怀有对科学和科学方式的积极信仰。当代哲学家中的后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包括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也时而吸收这种‘偶然性’,但并未导致怀疑主义或相对论立场,而是不时地推进了新实用主义视角”。[5]3-4时隔多年,舒斯特曼终于在哲学立场上向罗蒂致敬,就此与罗蒂“握手言和”。他现今对偶然的上述认识与阐述,恰恰正是罗蒂一直以来申述再三的观念。不妨说,历经长期的误读,舒斯特曼最后还是选择站在罗蒂身边,选择维护新实用主义出发点的一致。因此,他在这个问题上才对罗蒂做出了完全正面的评价,当然也是客观的评价。
舒斯特曼坦承,“我的立场有时候等同于罗蒂的立场,因为我们都清晰地表达了实用主义的杜威版,这种实用主义强调审美的维度”。[4]255虽然他们都从杜威的理论遗产中不断汲取营养,但在具体取向上有时却分道扬镳。譬如,舒斯特曼对罗蒂拒斥杜威的经验概念就非常不满,他大张旗鼓地呼吁应予重振并付诸实施。准确地说,舒斯特曼抨击的是罗蒂对经验的语言化、阐释化,因而,他针锋相对地张扬非话语性的身体经验。诚如马莱茨基(Wojciech Malecki)所言,“罗蒂并不否认非话语性经验的存在。事实上,他只是主张,我们在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时,不能将非话语性经验视为一种哲学上的工具”。[6]如果回到历史的系谱,可以发现,舒斯特曼与罗蒂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可谓实用主义“语言”与“经验”百年纠葛的重演——从皮尔斯的语言开始,经詹姆斯(William James)、杜威(John Dewey)的经验,到罗蒂的语言,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经验,再到布兰顿(R. Brandom)的语言,实用主义在语言与经验之间往复式拉锯。需要说明的是,杜威的“经验”概念涵义复杂,“既有真实的生物学所描述的特征,又有精神文化渗入其中,即便是最基本的感觉,也超越了纯粹生物的特性而有思想和观念的介入”。[7]换句话说,它包容了相互角力的两个向度,而罗蒂与舒斯特曼则分别执其一端。正是针对罗蒂过于强调人类的语言活动与动物的非语言活动之间的差异,舒斯特曼起而推崇男男女女非语言经验的重要性。基于此,舒斯特曼还批评罗蒂“忽视了愉快和美的美学,从而把艺术简化成制造道德工具的诗学”。[4]257然而,与此显然互相矛盾的是,当谈到审美教化的社会效应时,舒斯特曼却又武断地断言:“这就是我的新实用主义立场区别于杜威最有影响力的当代拥护者罗蒂的一个要点。罗蒂(虽然不同于本雅明)认为,美学理应限定在私人领域。”[5]213我们知道,罗蒂反基础主义的结果包括两个板块,其中,存在主义与实用主义部分各自构成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领域,两者都深度关涉美学问题。实际上,舒斯特曼的两次批评都遮蔽了另一部分,应该合而观之方可看清全貌。不过,从这种无的放矢般的苛责中,倒是能够一窥美学、美育被舒斯特曼及其批评对象罗蒂所赋予的力量,形塑社会共同体的巨大力量。
二、舒斯特曼与罗蒂美育观的异同
舒斯特曼与罗蒂对审美教育的重视都受到杜威美育思想的影响,同时两人又都有各自的发展与新创。杜威晚年著作《作为经验的艺术》(ArtasExperience,1934)对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把诗人称作“文明社会的缔造者”赞赏有加,他强调美学的伦理效用,认为艺术比道德规范更加道德。因为后者“往往会变成现状的供奉、习俗的反映、既定秩序的加强”,而艺术对现实可能性的洞察不仅可以转换成新的生活图景,指引着人们去不懈地追寻。设若风云际会,它们的想象性呈现甚至能够成为政策规则,积极介入并重新塑造红尘俗世。“艺术成了使得对某些目的和意义的感觉保持活力的手段,这些目的超过了证据,而这些意义越过了僵硬的习惯”。[8]425-426在援引杜威的这一论述之后,舒斯特曼《哲学实践》(PracticingPhilosophy,1997)指出,既然美学拥有丰富个体经验、造就公共世界的效力,那么,就可以在此基础上推演出“民主的美学观”,或者说,从实用主义美学的角度论证民主。它包括三个相关的层面,其一,个体与社会息息相关,相互作用。个体对民主生活的积极参与可以使其经验与自身更为丰富,而民主制度则可为其提供更多的机会,为其审美生活提供可靠的保证。其二,民主实践既是实践手段,亦是目的本身,共享经验堪称最大的人类之善。其三,民主制度尊重差异性,鼓励个体自由平等地参与制定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从而丰富个体的生命经验。[9]109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内容几乎原封不动地在舒斯特曼的新著《情感与行动》中再次重现,用以证明实用主义如何青睐美学构筑伦理与政治的伟力。不难看到,这些还被概括提炼成实用主义十大原则的第五条“共同体”,更鲜明地突出了美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对舒斯特曼而言,“共同体不仅是认识的主题,也是审美、伦理与政治的主题。它促进实用主义最根本的民主倾向。如此,实用主义哲学家为民主制提供了认知的、伦理的和审美的论证”。[5]7让人不禁莞尔的是,考虑到实用主义的这种美学观念不免使其与审美主义的主流哲学背道而驰,舒斯特曼特地简要回溯美学史并申辩,对美育工具性力量的看重是世界美学源远流长的传统,而非美国审美贫乏和文化庸俗主义的结果。
与舒斯特曼一样,罗蒂对审美与伦理的融会也来自杜威对艺术的理解——艺术不只是男男女女闲暇时的消遣,而是“人类交往中一种公认的力量”,“解放和统一的力量”。[8]426众所周知,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描绘了一幅自由主义乌托邦的蓝图,其中,杜威与马克思(Karl Marx)、穆勒(J. S. Mill)、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罗尔斯(John Rawls)等人一道,担当着社会公民的示范。“他们共同参与一项社会任务,努力使我们的制度和实务更加公正无私,并减少暴虐残酷”。[10]4罗蒂对团结的重视还淋漓尽致地体现在《筑就我们的国家》(AchievingOurCountry:LeftistThoughtinTwentieth-CenturyAmerica,1999)一书中。他激烈批评其时一些小说中四处弥漫的“民族自嘲和自憎”情绪,高度赞扬之前小说中展现的“民族希望和理想”思想。他认为,杜威与惠特曼(Walt Whitman)对民族希望与理想的形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他们眼里,讲述国家、民族的故事绝不应停留于准确再现现实的水平,而更应该经由故事的重新描述努力培养一种精神认同,激发人们的参与感与自豪感。正因如此,虽然他并未采纳布鲁姆(Bloom. H)饱含激愤的“怨恨学派”一语,但依然完全赞同他对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人文化研究路数的批判,依然完全赞同他对文学经典启迪价值的竭力捍卫。
在汲取杜威美育思想,共同奔向团结的漫漫征途中,舒斯特曼与罗蒂所走的道路并不完全一致。舒斯特曼最引人瞩目的是从经验出发,举起了身体美学、身体美育的旗帜。经历过语言论转向的罗蒂,自然批评杜威将经验作为其哲学之中心难逃基础主义的嫌疑。与之相反的是,舒斯特曼在承认杜威的经验基础主义的前提下,仍为杜威经验概念的价值尽力辩护。他认为,“杜威的错误不在于强调经验的统一性质,而刚好在于把这种性质视为一种在先的基础,而不是一种重构的目的和手段”。[9]194舒斯特曼强调,经验不仅在实用主义中仍然至关重要,而且,许多实用主义的价值恰恰在于那种直接的、非推论的经验之上——它足以与被罗蒂指控的经验区分开来。而这种经验最显著的构成是身体感觉,因此,身体经验顺理成章地成为问题的焦点。舒斯特曼直言,虽然自己赏识语言学转向,但还是对其无所不在的笼罩趋向担忧不已。所以,他坚持回到实用主义对身体和非推论经验的传统关注轨道。舒斯特曼大声疾呼:“哲学需要给身体实践的多样性以更重要的关注,通过这种实践我们可以从事对自我知识和自我创造的追求,从事对美貌、力量和欢乐的追求,从事将直接经验重构为改善生命的追求。处理这种具体追求的哲学学科可以称作‘身体美学’。在这种身体的意义上,经验应该属于哲学实践。”[9]203若是在罗蒂的理论脉络里,这种私人的完善与公共的目的断然不必也不应统合起来,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两者完全可以各行其道、是其所是。但对舒斯特曼来说,自我完善则是通向、达到公共目的的重要工具。只要我们心仪那些目标并为之奋斗不息,那么,我们就理应尊重实现目标的工具。舒斯特曼之所以力倡身体美育,还与身体意识在传统人文主义教育中所处的边缘位置紧密相关。他认为,长期以来的一个偏见是把人文主义教育与自然主义相互对立,前者偏于精神方面而后者偏于生理方面,身体美育则致力于弥合这种分裂,将两者融为一体。出于对经验的重视,舒斯特曼还批判传统的艺术概念与艺术制度狭隘地把通俗艺术视为美学上的非法存在物,有意远离喧嚣的生活实践与活泼的日常经验。他建议开放与扩大精英式的艺术概念,更多地关注社会与伦理的维度以持续推进它们的进步。明乎此,我们才能更深刻理解舒斯特曼为何乐此不疲地聚焦娱乐、拉普、爵士乐、乡村音乐等话题,为众多遭受贬低的通俗艺术家族发声,不遗余力地展示它们被忽略的审美价值,以及它们对维护和充实生命的意义,论证它们的审美合法性与潜在的美育价值。
罗蒂的团结思想既闪烁着反本质主义的耀眼光芒,又携带着反讽主义的呼啸激情——“反讽主义者是一位唯名论者(nominalisist),也是一位历史主义者(historicist)。她认为任何东西都没有内在的本性或真实的本质”。[10]107因此,讨论罗蒂的团结思想,必须与偶然、反讽紧密结合。具体而言,罗蒂认为,“西方世俗民主社会中典型的道德和政治语汇,就是从这些历史的偶然所发展出来的。随着这些语汇被逐渐地非神学化和非哲学化,‘人类的团结’遂浮现出来,成为雷霆万钧般的有力修辞。我无意削减它的力量,只是企图使它摆脱过去常被视为它‘哲学预设’的那些东西”。罗蒂“相信有所谓的‘道德进步’,而且这进步也确实朝着更广大的人类团结的方向发展”,但他不认为“那种团结乃是对于所有人类共有的核心自我或人性本质的承认”。[10]273换言之,团结不再是对某一先在本质的朝圣与体认,而是一种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动态创造与建构。而且,罗蒂构想的团结颇具开放性,从理论上说其边界有着不断拓展的希望。这也暗示,与其沿着普遍主义的进路证明团结的必要性,不如从地方性视角来得更接地气。不应误解的是,放弃了内在本质的追求并不意味着放弃人类救赎的需要或美好生活的冀望,只是两者要区分开来而非杂糅一处。否弃了不变的本质基点之后,反讽主义将团结感引至人类对危险共有的感受上。有意思的是,被舒斯特曼屡屡批评否定了经验范畴的罗蒂,在这里恰恰主张正是这种人人皆有的非语言性的痛感,将芸芸众生相互连成一体。问题在于,如何提高个体的敏感度,实现对陌生人的接纳与认同呢?罗蒂十分赞同杜威想象力是善的主要工具的看法,在此基础上,他更是提出整个文化应该诗化,从理论转向叙述、从理性转向想象、从知识转向情感、从灌输转向感染。“逐渐把别人视为‘我们之一’,而不是‘他们’,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详细描述陌生人和重新描述我们自己的过程。承担这项任务的,不是理论,而是民俗学、记者的报导、漫画书、纪录片,尤其是小说”。[10]7不言而喻,以小说为代表文类的诗化文化或文学文化针对的是先前的宗教文化与哲学文化。于是,它不再把精神教育的重任赋予学习宗教传统或道德哲学等本质性的真理性知识,而是将虚构作品尤其是小说置于德育、美育的核心;它不再满足于对神圣的服从,不再孜孜不倦地试图发现真正的实在,而是尽力扩展人类的想象力、情感容纳范围的界限。罗蒂乐观地展望说:“文学文化可以像哲学文化一样成为民主政治忠诚的同盟军。它不能被看作是反启蒙运动的胜利,而应当被看作是用另一种更好的方式继续启蒙运动。”[11]
三、舒斯特曼与罗蒂美育观的缺陷
舒斯特曼满怀信心地宣称:“比起其他大多数西方哲学家,我的实用主义哲学更加强调作为生活实践的哲学的一个方面:培育有感知的身体,把其当作自我完善的核心手段,改善知觉、行动、德行和幸福的钥匙。”[5]222这种对身体维度的极度凸显,成就了舒斯特曼驰名中外的身体美学。比较起来,它在国内学术圈收获了不少学者的热捧,而在西方哲学界则遇到一些批评与质疑之声。从学术的脉络来看,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主张通过身体训练培养身体意识,打破了身体与意识截然二分的传统窠臼,这无疑是其历史意义所在,也是其受到肯定、追随的重要原因。但在其身体美育的框架中,身体的训练目前还滞留于自娱自乐的技术层面,与实用主义美学珍视的共同体原则仍然距离遥遥。或者说,我们尚未看到两者接续的迹象。揆其根源,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身体“只是生活中的中性因素,本身并不能决定生活品质的高低”,舒斯特曼只触及“活着”的层面,而搁置了“如何活”的价值选择问题。[12]这种对身体价值维度的忽视,在舒斯特曼与张再林的一次对话中也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谈及身体意识的培养,舒斯特曼认为,中国古老的气功、武术与印度的瑜伽等都是良好方式。值得留意的是,张教授马上接过话头,委婉地说:“您独特的身体美育方面的思想与实践,对于纠正我们当前对身体美育的片面理解很有意义。但我要补充说明的是,中国古人的身体美育不仅注重气功、武术等身体训练方式,而且特别注重通过‘修身’的方式来达到身体美育的结果。这种修身思想既强调对身体‘率性自然’的回归,又不忽视对身体欲望‘发而中节’‘欲而不贪’的人文教化。如果说道家更多钟情前者的话,那么儒家则更多地推崇后者。”[13]不难看出,张教授补充的恰恰是舒斯特曼遗漏的关于身体美育的价值问题。舒斯特曼对中国古代身体美学的误读或者仅仅表面相似性的勾连,由此亦可见一斑。所以,不必惊诧的是,当舒斯特曼被指责身体美学带有挥之难去的自恋与享乐倾向时,儒家的“乐”“悦”之论才会让他备受鼓舞。殊不知,儒家哲学固然将愉悦与认知紧密关联,但儒家的“乐”是视野宏阔、治国理政的“乐教”,而非单纯的感官快乐。《礼记·乐记》有言:“生民之道,乐为大焉”,“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14]254换句话说,这里的“乐”的主体绝非普通男女,而是圣人。“乐”的客体同样也有限制,是为圣人所乐。因为乐乃人之常情,众声喧哗不免趋于混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导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14]257两相对照可知,舒斯特曼注意到了儒家善政离不开身体的一面,但并未明了儒家乐教对身体的询唤及塑型、规训与惩罚。儒家乐论与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的共同体旨规在精神上的确有些合拍,但与后者正面联系快感与理解、欲望和身体实则又南辕北辙。
罗蒂敦促人们抛弃那种道德义务源于人性本质的理性教导,倡导通过文化的诗化进行美育,从而在想象与情感的扩容中建立鲜活可感的共同体或政治秩序。完成这一任务,小说确实拥有抽象说教难以比拟的优势。正如德国思想家利希滕贝格(G. Ghr. Lichtenberg)所言:“我读《一千零一夜》《鲁滨逊漂流记》《吉尔·布拉斯》《弃婴》要比读《救世主》乐意一千倍;我愿花两本《救世主》的钱去买一本篇幅不长的《鲁滨逊漂流记》。”[15]尽管如此,理性认识仍有不可抹杀的必要作用,罗蒂实际上也未能将其彻底丢弃,它仍可作为一种有益的手段:“‘我们对于任何的人都有义务,只因其为人’的口号,正确的解释方式乃是把它当作一种手段,来提醒我们随时尽量扩充我们的‘我们’感。”[10]277进一步的问题是,罗蒂以广义的小说来促进团结的大道,必须面对如下事实:文学既是巩固意识形态的工具,同时亦是解构意识形态的利器。也就是说,小说美育正向的团结作用不容忽视,但它也有可能带来分歧、对抗或分裂等负向的恶果。因此,关键还是怎样的思想观念在支撑、支配着美育的目标。毋庸置疑,它不可能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牵绊。形成较大反差的是,罗蒂在小说美育正向的坦途上高视阔步,而对负向的沟坎、泥潭与陷阱并未提及。在这方面,舒斯特曼的考虑显得较为周全。他提醒人们,“或许我们不应止步于杜威关于艺术与社会之和谐有机的观点。其实,艺术既带来统一也带来分离。比如,不同趣味群体之间的冲突是对创造力的有力刺激。除了统一的愉悦,在极度分离、不协调的和摧毁性的艺术体验中也有审美、教育甚至社会价值”,“审美欣赏社会和谐也应警觉于不和谐之音,即遭掩盖或驱逐的部分”。[5]212舒斯特曼还认为,艺术发展人的感性,提高道德感受与同情的能力,从而促进团结,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观念。它需要直面如下两种指控:一是热衷美育可能产生颓废的审美主义,它不再有效刺激人们的道德感觉,反而助长了他们从恶劣现实中逃避;二是不应太相信艺术普遍的与民主的魅力,因为“美的艺术,通过其享有特权地区分于手艺、娱乐和通俗艺术,与其说是清楚明白地团结社会,不如说是将社会分隔开来并传播那种分隔”。[3]208有鉴于此,对于从美育到团结的进发,还是保持低调的乐观为宜。
结 语
尽管舒斯特曼对罗蒂多有一些不实之指责,譬如,将美学限定于私人领域、把艺术简化为制造道德工具的诗学,等等,但作为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实两人都在反对形而上学之后致力于建构,都特别强调美育对促进社会团结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所不同者,是由美育通向共同体团结的路径:舒斯特曼强调非语言的经验,高度凸显了大众审美与身体美育的功用;罗蒂则看重语言,诉诸诗化的文化。问题在于,舒斯特曼的构想囿于技术层面,缺少价值维度的引导;罗蒂则过于张扬想象在美育过程中的作用,对其负面效果未有顾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