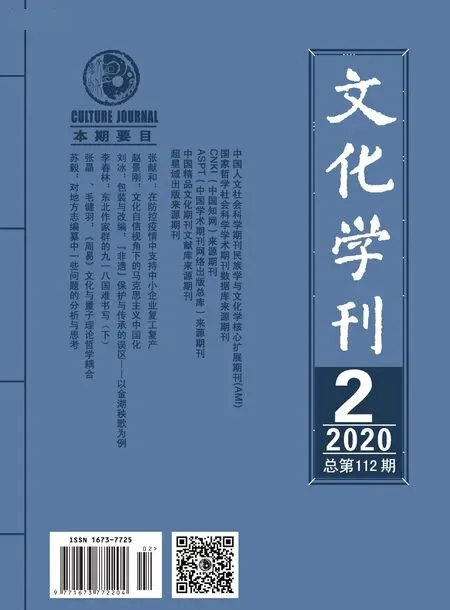名实观视域下对《三国演义》劝说言语行为的语用分析
郭勤勤
《三国演义》是中华文学宝库的瑰宝,相关文献汗牛充栋,如对小说内蕴、人物形象、叙事艺术的研究、与区域文化、电子数字化新方法及新观念引进的结合研究,以及对其英译的研究等[1]。《三国演义》的语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其中的说客贯穿整部小说,他们通过辩论、劝说等言语行为说服他人改变态度或者立场,如诸葛亮“以三寸不烂之舌,退却百万之师”。其中的劝说言语行为具有典型性,对其进行研究能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新方向[2]。本文将以名实观为切入点,对《三国演义》中劝说言语行为进行语用分析。
一、中西方名实观研究概述
在语言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中国的先秦诸子还是古希腊的先贤哲人,都不乏对“名”与“实”这一问题的思考及讨论[3]。名实观的研究有其历史渊源,要真正理解它,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
(一)中国名实观的发展
在中国,儒、道、墨、名各家都对“名”与“实”的关系、指称等进行了讨论,即所谓的“名实之辩”。其中,儒家主要关注“正名”,讲究“入世”,旨在“治世”,即孔子所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4],意在强调名正言顺、言行合一。目前,学界对孔子“正名”中的“名”的理解,尚未统一。孔子这一思想是在礼乐崩坏的战国时期提出,因此便有传统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名分”一解,亦有后来汉代儒学家提出“名-物-事”的哲学认知一解,甚至还有“正书字”一解[5]。既有哲学关怀,又有政治关怀。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出发,孔子的“正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入世的哲学思想,强调名实统一、名实相符。他指出了“名”与“实”的非对称性,呼吁人们“循名责实”,既要考察事物之“名”,又要考察事物之“体”[6]。
除此之外,道家也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7]。总之,道是客观的,但“道”是不能命名的(1)另外一种解释认为:“非常名”是说最高的“名”是无形的、含混的;相反,普通的“名”是“高世之名”,是“自然常在”的。,是无法用语言去表达的,即“名”不能用来解释“道”,这也是其与儒家名实观的不同之处。墨家研究“名”的“定义”“本质”“分类”,即墨家逻辑学的概念论部分[8]。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墨家强调“名实藕”“取实予名”,属于经验主义流派,其整体上坚持语言可以反映客观实在的语言哲学观。名家尤以惠施为代表。名家虽诡辩,但他们也对“名”与“实”的关系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尤以“循(控)名责实”为著。《史记》中也如是记载:“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9]司马迁在批评名家苛察的同时,肯定了其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的主张。同时,公孙龙提出了“物莫非指,而指非指”[10]的论断,意即物均可以被指称,但用于指物的指和符号指称之物并不等同。在笔者看来,公孙龙的“名实观”即是“物”是可以被“名”指称的,物不是不可名的;而符号之指和概念之指又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是不对等的。因此,“物”虽被“名”指称,但是用来指称“物”的“名”(符号之指)不代表“物”(概念之指)本身,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
需要注意的是,《三国演义》成书的年代是宋明理学思想盛行的时代,而理学沿袭孔孟之道,因此,当时盛行的名实观与孔子的名实观一脉相承,但不同之处是,与政治结合的程度更高,“将正名完全与政治勾连起来”[11]。
(二)西方名实观的发展
西方语言哲学的三大支柱理论是指称论、阐释论和意义论。这里提到的意义论和中国的“名实观”高度契合。西方早期对意义的哲学解释有两种。一是理想化解释,认为语词是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心智图像或者是来源于外在世界的内在印象[12]。二是直接指称,认为一个语词意义是它运用到的所有个体的集合。这两种解释都有开创意义,但都有各自的局限[13-14]。语词的意义在西方是一个传统的议题,关注较多,理性主义阵营如柏拉图和莱布尼茨,经验主义阵营如亚里士多德和洛克,都对语词的意义做了相关论述。后来的西方哲人又对意义理论做了改进与发展。穆勒对于名称采取了大一统的办法,将名称分为类名和私名、区分了内涵和非内涵名称。弗雷格采取了数理逻辑的办法,将逻辑观念和技巧运用到自然语言的语义结构的分析上,努力实现莱布尼茨的规划,将推理和计算运用到语言的分析中。罗素采取了数学方法,提出摹状词、有定摹状词和逻辑专名的概念,指出有定摹状词是不完整的符号。克里普克则采取社会化的方法,提出可能世界和名称的因果论。
(三)中西方在名实观上的异同
就相似性而言,中西方对于“名”的本质和名实关系的探讨的认识一致,但侧重点不同。中国的“名实观”是与政治、道德等结合起来的,是“入世”的;西方的“名实观”的探讨是限于哲学范围内,“就事论事”,是“出世”的。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名实观”不如西方的纯粹,哲学意蕴也不如西方的浓厚,没有上升到科学、数理逻辑层面。究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国“名实观”相关问题的探讨开始于礼乐崩坏的先秦时代,当时急需规章制度以及思想上的引导,且文人提出的思想服务于封建统治是由来已久的传统,探讨多是经验主义方面的。而西方对名实的探讨相对较晚,当时的生产力已经得到了长足发展,有足够的后备力量让哲学家在自己的象牙塔里潜心研究哲学问题,因此,西方的名实观发展得更为完善。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语言特点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也是中西方“名实观”不同的原因[15]。
二、名实观视域下的劝说话语分析
下面将从名实观出发,对《三国演义》的语料进行语用分析,主要涉及奥斯汀的言语三分行为。
(一)劝说话语
张红娇[16]将劝说定义为“劝说者采用非强制性手段影响被劝说者对事物的态度、评价等”。结合奥斯汀提出的言语三分行为,劝说言语行为是在共知的语境下,采用非强制的态度影响或者改变被劝说者的态度、立场或者评价等。劝说言语行为有三个层次:劝说者所说的话语,即以言指事;劝说者劝服对方的意愿,即以言行事;劝说者说完劝说语之后所达到的效果,指是否影响或者改变被劝说者的态度、立场等,即以言成事。本文将重点关注“以言成事”层次。
(二)名实观视域下的劝说话语分析
《三国演义》历史背景特殊。战事纷繁,诸侯并起,最终三分天下,因此,战与不战、与谁战、为何而战、为何不战、拥戴谁、支持谁,谏客谋臣(劝说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笔者看来,谋士劝谏战与不战,拥戴讨伐主要受三大因素影响,即天时、地利、人和。
因“天时”而劝不战的如第三十一回。曹操在仓亭破了袁绍之后,欲进荆州伐刘备,却因当时正值寒冬腊月,有违行军作战者的“天时”。“程昱曰:‘……不如还兵许都,养军蓄锐,待来年春暖,然后引兵先破袁绍,后取荆襄:南北之利,一举可收也。’操然其言,遂提兵回许都。”[17]此番劝谏,程昱以“顺天时”为劝谏理由,曹操“然其说”,听从劝告。
因“地利”这一因素而劝说的言语行为的如第四十三回。曹操、刘备、孙权三足鼎立之势尚未形成之时,刘备式微,曹操于是写信托于孙权,意在使孙权纳降共同拒刘备,不参与到曹与刘的战争中去。是战是和,孙权犹疑不决。其中张昭是主和派,就以长江这一“地利”已和“曹共有之”为不战的理由。张昭曰:“……且主公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既得荆州,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势不可敌。以愚之计,不如纳降,为万安之策。”[18]虽然孙权心中不愿纳降,但张昭的这一番话很有说服力,因此孙权沉吟不语,这是“地利”这一因素在劝说话语中的体现。
“人和”在《三国演义》中劝说语言的体现如四十三回张昭进谏的前半段。张昭曰:“曹操拥百万之众,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顺。”[19]这里主要体现了“正名”的重要性。曹操虽是借天子的名号,但也有一定的正当性,出于“人和”而不战。
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的“人和”主要体现在“正名”上,尤以“刘备乃汉室宗亲,名正而言顺;而曹操假天子之令以命诸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最为常见。刘备占得“人和”这一优势,即得民心,常常成为各诸侯伐与不伐的决定性原因。
“正名”思想,即名实观的体现。那他们持有何种名实观呢?名实观在劝说话语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下面将以几则语料为例进行简单分析。
谦曰:“今天下扰乱,王纲不振;公乃汉室宗亲,正宜力扶社稷。老夫年迈无能,情愿将徐州相让。公勿推辞。谦当自写表文,申奏朝廷。”
玄德离席再拜曰:“刘备虽汉朝苗裔,功微德薄,为平原相犹恐不称职。今为大义,故来相助。公出此言,莫非疑刘备有吞并之心耶?若举此念,皇天不佑!”
谦曰:“此老夫之实情也。”再三相让,玄德那里肯受。[20]
这一劝说言语行为的背景是,曹操欲领兵攻打徐州,刘备出兵救陶谦,陶谦自觉刘备大义凛然,便说出了让出徐州的打算,体现了以言指事;言语间表达了自己让出徐州的意图,这便是以言行事;但是被劝说者没有改变立场,这是以言成事的结果。第一个话轮中,陶谦出让徐州的理由是:自己年迈,而刘备是“汉室宗亲”。从名实观的角度来看,刘备有汉室宗亲之“名”,让接管徐州也是情理之中,可见,他把“名”放在第一位,“实”放在第二位,但也要求名实相符,而后又提到,会“自写表文,申奏朝廷”。第二个话轮中,刘备严词拒绝,理由是“虽是汉朝后裔,但是‘功微德薄’,遂不能接受”,这体现了刘备把“实”放在第一位,要求循名责实,自己“功微德薄”就不能去领下徐州牧这一名号。若领下了,便是名实相异,不可取。在名实观的主张上,二者都要求名实相符,但顺序有别。劝说者陶谦所持是“名在实前”的名实观,而被劝说者刘备所持的是“实在名前”的名实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这一劝说言语行为没有取效。
座上又一人应声问曰:“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犹是相国曹参之后。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屦之夫耳,何足与曹操抗衡哉!”
孔明视之,乃陆绩也。孔明笑曰:“公非袁术座间怀桔之陆郎乎?请安坐,听吾一言:曹操既为曹相国之后,则世为汉臣矣;今乃专权肆横,欺凌君父,是不惟无君,亦且蔑祖,不惟汉室之乱臣,亦曹氏之贼子也。刘豫州堂堂帝胄,当今皇帝,按谱赐爵,何云无可稽考?且高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织席贩屦,又何足为辱乎?公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陆绩语塞。[21]
以上是孔明与陆绩的辩论,仍可以理解为二者之间的一种动态的劝说言语行为。总体来看,双方所持的名实观都是正名思想的一种体现,要求名实相符,且都体现了“名在实前”,强调循名责实,结果是陆绩“语塞”,即劝说行为取效的间接体现。
分析劝说言语行为的两个例子后分析,双方持相同名实观且时序相同时,劝说言语行为取效,否则将无法达到劝说的目的。《三国演义》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因篇幅有限,在此仅以两则语料为例。
三、结语
综上,中西方名实观各有独特的发展脉络,西方“出世”,东方“入世”,主要受历史背景、语言特点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从政治角度出发,所选语料体现了孔子所提倡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正名思想观;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出发,体现了朴素的名实观,要求“名”与“实”一一对应,名实相合。差别在于名实的重要性问题,即文中提到的“名在实前”还是“实在名前”的问题。如果劝说者与被劝说者在名与实的重要性问题上达成一致,则会达到劝说的目的;反之,劝说言语行为不能取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