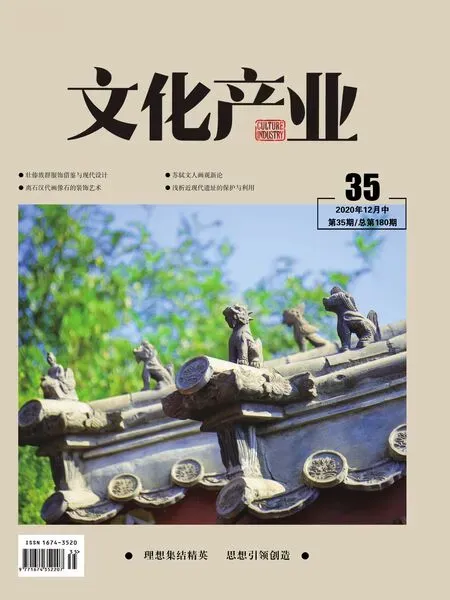浅论中国音乐审美中的“和而不同”与“尽善尽美”
◎郭俊婷
(天津音乐学院 天津 300171)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的境界,追求一种天人之间、人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在音乐创作中同样也追求尽善尽美、和而不同。音乐中的“和”主要体现在其包容性,在音乐创作过程中不断融合世界各地的音乐文化,吸收和借鉴西方的优秀文化。中国的音乐作品中既有传统的音乐元素,也巧妙地运用了西方音乐元素;其中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体现了“和而不同”。“和合”的目的就是“尽善尽美”,两者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和合精神强调协调把握整体中各要素的动态关系,中国艺术的和合精神推动着人们对整体中各要素关系的动态把握,渗透于价值论、主体论、结构论以及审美表述等诸多方面。
一、何为“和而不同”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对“和”有自己十分睿智的见解。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很显然,孔子认为实现“和”的前提是“不同”的存在,也就是“和”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相互协调。这种说法涉及到辩证法的思考。
在中国器乐合奏中,有弹拨组、弓弦组、打击组、吹奏组等等,在各有特色的基础之上进行合奏,使乐曲的寓意表达更为准确、情感更为丰富、层次感更加鲜明。这也是一种“和而不同”的表现。在合唱中也分着声部,有女声部、男生部、童声部。在这些声部中又细分为低音声部、中音声部、高音声部。正是在这些不同的基础之上才能对“同”的表达更为贴切。
在西洋器乐合奏中,有提琴声部、管乐声部、打击声部等等;在弦乐四重奏中分得更为细致,有四把小提琴,分别是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在音色不同的基础之上演奏同一首乐曲,分别演奏不同的声部、不同的旋律、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分工合作。这也尽显了“和而不同”的精神。
“和合”是具有整体性和对待性、结构性和层次性、流传性和模糊性,这些在《乐记》中都有所体现。乐为天地之和,也充分体现着“和而不同”的特征。
二、何为“尽善尽美”
“仁”是孔子思想主张的核心之一,而他“尽善尽美”的观点则充分体现了“仁”这一思想主张。“尽善”,表达的是人性的仁德之美;“尽美”,表达的是音乐的形式之美。两者交融,才是孔子所推崇的“仁乐”。更通俗易懂的表达是:音乐的内容与形式要相互匹配。“尽善”表达的是人性的仁德之美,在音乐中也非常适用。音乐创作就是为人类服务、陶冶情操,在学习和工作疲惫时可以听一听音乐来缓解压力。比如中国琴曲《高山》《流水》《阳光三叠》等,音乐中的旋律起伏不大,且音色较为柔和、节奏也较为规整。音乐整体的感觉很放松,人的情感很容易能够被带进去。再听一下音乐的名字,《高山》《流水》这一类型的音乐作品,一般都以大自然的名称命名。
在孔子“尽善尽美”的音乐美学观点中,“善”表达的是孔子政治上的态度,而“美”则表达的是孔子音乐审美的态度。在孔子政治标准的思想主张上,“仁”与“礼”的思想贯穿始终,他所向往的天下是君行仁政、民行仁礼。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始终与社会生活相联系;在音乐创作中,歌词的编写与一定阶段的社会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在西方音乐中,从开始宫廷音乐、宗教音乐、进而有世俗音乐的产生,一直到20世纪的偶然音乐、序列主义音乐等,也都与当时西方社会生活以及公民思想的开放程度有关。
音乐来源于社会生活,音乐又服务于社会生活。“尽善尽美”既表明了音乐创作的出发点,又体现了音乐的创作目的。
三、音乐创作所追求的美学境界
在音乐创作中,同样也追求尽善尽美、和而不同的美学境界。音乐中的“和”主要体现在它的包容性,尤其是中国音乐。以琵琶为例,琵琶有四条弦,在演奏琵琶时用左手按弦、右手弹弦;音与音的区分在于品,既能拉弦也能揉弦,还可以吟弦,根据乐曲所要求的情感来运用不同程度的揉弦力度。琵琶独特的构造,可以发出各种不同的音色来模仿其他的乐器,音色的可塑性极强。因为四条弦,从一弦到四弦、从细到粗,音色也是由清脆到浑厚,所以琵琶的音色可以模仿很多乐器,在这方面体现出了和而不同。在这方面有所建树的方锦龙先生在一档演奏节目中有展示过用琵琶演奏众多乐器的音色,并且音乐美妙动听。比如用琵琶模仿电吉他的声音,用琵琶模仿打击乐的声音等等,都体现着“和而不同”。“和”体现在音色的共通性,运用两种不同的乐器演奏相同或者相似的音色,表达的情感是一样的;但“不同”体现在表达情感或者传递思想的形式不同。
“和而不同”的目的,就是“尽善尽美”,不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都有体现。进入新时代新时期,经济和文化得到迅猛发展,音乐更是得到空前的发展和融合。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种外国音乐涌入中国,与中国音乐相互融合。比如中国著名的音乐家谭盾创作的音乐,吸收了西方偶然音乐的创作元素在里面,也包含着对各国优秀文化艺术的融合。当代音乐重视“美”的感染力及其本质内涵所带来的社会功能,希望用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从而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提高国民整体文化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