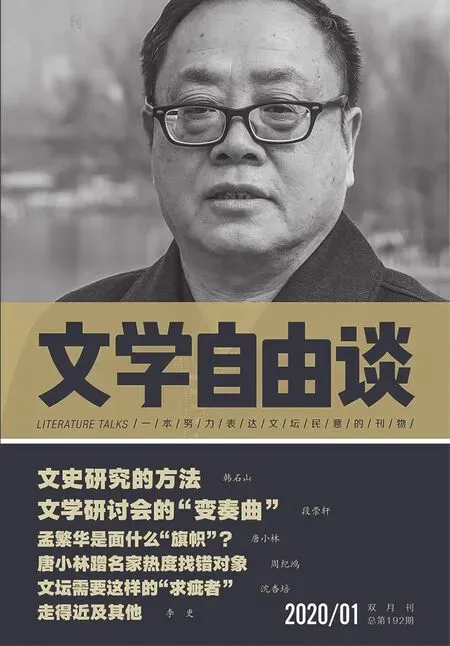“后喻文化时代”的儿童话本
□蒋 蓓
美国人类学家M. 米德提出,农业社会是“前喻文化时代”,网络社会则是“后喻文化时代”。这一“前”一“后”间的差别在于:过去,主要是子女向父母学习;现今,父母向子女学习的“文化反哺”现象变得常见。不同于传统亲子关系里父母对子女绝对的耳提面命,“后喻文化时代”的亲子关系建立在倡导民主平等的基础上,鼓励子女在尊重父母知识、经验的前提下,拥有自己的认识、见解,亲子交往谋求的是家长和子女共同发展。新近面世,由文学批评家冉隆中创作的“那年我×岁”系列诸册,正呈现了一种“后喻文化时代”的亲子关系面貌。
“那年我×岁”的故事,始于冉潇然小朋友三岁半时——冉潇然正是“那年我×岁”系列图书唯一的主人公。现实生活中,这个大字还识不得几个的小男孩,其言行间的活泼、伶俐、天真、淘气,甚至个性,激起了潇然爸爸——也就是本书作者冉隆中的“晒娃”之心。另外,当时的潇然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陪读儿童,离开昆明的家,给求学天津、上海等地的妈妈“陪读”。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的改变,让这小子得以在小小年纪便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一有机会,他开口噼里啪啦讲给爸妈的也更多了。
不同于网络上常见的秀图片、发视频之类的“晒娃”手段,潇然爸爸的“晒娃”方式比较特别。这位素以文艺批评、文学创作见长,且文字“狰狞”、语言尖刻的“大书”作者,俯下身子,转型童书创作,并且甘为代书人,持续“誊抄”潇然一路自道的那些发生在家庭、幼儿园和学校的小事情,推出了一套“小书”——《那年我×岁》,让人不由一惊,继而一喜。
以图片、影像“晒娃”,直观、即时,重在形之展示,却多缺乏语境。而文字“晒娃”,一旦成了文,就有前因后果,有上下文。于是,书中那名从三岁到六岁的男孩的滔滔不绝或喃喃自语,悄然间触动读者。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折射出当下中国家庭面临的某些焦虑与纠结,折射出现今家庭与学校教育里的那些探索、欣喜与无奈。诚如儿童文学名家吴然在《序》里所言:“我更愿意欣赏书中充溢的神奇和有趣,以及尊重孩子天性、塑造美好人性的智慧。孩子成长过程歪歪扭扭的脚印,妈妈一切为了孩子投入的全部的爱,以及幕后英雄爸爸的许多努力……我都在书中真切地体会到了。很多故事,让我微笑、大笑;一些段落,让我泪目、沉思。”
《那年我×岁》保留了很多“糗闻”。也是因为它们,以及其他不少细节,整套书童趣盎然。比如,崇尚英雄的男孩到了津门大侠霍元甲纪念馆,敬佩归敬佩,却自知“肯定还不能拜他当师父,学功夫”,因为“我拉完臭臭还不会擦屁股!我这个寒碜样子……”比如,有恻隐之心的男孩,会把爸爸口中顺流而下自投罗网的“笨笨鱼”,给“正名”作“活蹦乱跳的小鱼”,更慷慨地取出自己攒下的零花钱交给爸爸,“布置”他买下小鱼放归河中,尽管也留意到了“我爸有点不情愿”。再比如,因老师表扬而自得的男孩,终归还是诚实地向读者“交代”了自己诗歌习作的灵感来源,和那首《约定》里最最关键的一句“风和蒲公英有个约定”,是从动漫《熊出没》里借来的……
判断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的价值如何,故事性、趣味性、审美性、想象力、哲思性等要素,都是重要指标。此外,我们还会特别留意,留意这部作品是不是带着那么些混沌。因为嘛,小孩子每做一件事,动机往往幼稚、朴拙,成人世界里复杂的明暗规则,同他们隔着千山万水。而正是这份无来由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沌,透露出单纯的心性和天然的趣味。“那年我×岁”系列里,不乏混沌无解的地方。过生日时,收到上海师大幼儿园同学们送的“炫酷”礼物的潇然,心底生出一丢丢惆怅——刚满五岁的小朋友,词汇仓库里自然还没有贮存下“惆怅”,是我这个成人读者代他归纳、提炼的——炫酷的礼物,源自同学们的教授爷爷、教授奶奶,或者博士爸爸、博士妈妈们教导自家孩子的社交规矩“不要太拿得出手”,而我们的潇然,却怀念起了更早时候自己在天津姚村的同学,那些同学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有不少曾是或仍是农人,置办东西,他们喜欢自己动手。有一回,大鹏的奶奶做了一筐煎饼,让孙子送给潇然当生日礼物。那筐煎饼味道如何,潇然并没有说,可后来我一回忆,又告诉自己:不对!书里头明明“记录”啦。《那年我六岁》里的原话是这么写的:“(大鹏的奶奶)还带话说,这东西瓷实,潇潇吃了长劲。也不知道我现在力气大,是不是与那筐煎饼有关。”
《那年我五岁》里的潇然,曾因动漫中的一句旁白,举一反三出了一首小诗,就是前面提到的那首《约定》。在诗的最后一节,他没忘记“我和妈妈有个约定 / 我说,请妈妈不要吼叫 / 就算我做错了事情 / 妈妈说,谢谢你的提醒,我保证!”整套“那年我×岁”系列书中,“批评家暨作家”“作家暨博士研究生”是潇然爸爸、潇然妈妈各自的标签,不过呢,最重要的是,他和她的交集还包括“凡人”:他是潇然的“凡人爸爸”,她是潇然的“凡人妈妈”。书里头,当然也是生活里头,他们总有“莫名其妙”、不够淡定、无法完美的时刻。当那些时刻被老老实实讲述出来,我们这些同样是凡人的读者不难明白:这世界总归有缺憾,能够稀释、弥补或这或那的缺憾的,只有爱。
因为给先后在津、沪两地深造的妈妈陪读,潇然的童年故事,更多是同妈妈联系在一起。这位妈妈,勇于承认错误,乐于跟儿子一同成长。她用自己要么温柔、要么浅显、要么不动声色的方式,给予孩子认知引领。“那年我×岁”里第一次出现“性”的内容,是在潇然五岁时,他和幼儿园的一位小女孩相约要在操场上举办婚礼。妈妈阻断这桩浪漫的理由是:人都是要结婚的,结了婚,就要生活在一起!五岁的小朋友固然不能理解“生活在一起”所意味的责任、担当,但妈妈的严词,多少会让他意识到些什么吧?
一直记得德国儿童文学作家米切尔·恩德的中篇《去圣库鲁次的遥远之路》。故事里,八岁的男孩赫尔曼,因为厌倦了学校和老师、爸妈和妹妹,一心渴望成为英雄,某天,他决定逃学,东游西逛了一整天。他幻想着城市起火自己就可以去扑灭,幻想着马戏团里的蟒蛇一旦叼走了谁家的婴儿自己就可以去拯救,幻想着有哪个间谍栽在自己手里……通过一连串幻想,赫尔曼不断“证明”着自己,借以逃离日常的庸碌和不断的否定。最后,被人骗了钱的他惊觉,假如自己再一直这么空想、晃荡下去,也会像那骗子一样,沦为一个把一生都晃荡掉的酒鬼。于是,被豪雨淋成落汤鸡的赫尔曼,悻悻然回到家里,做好了挨一顿猛训的准备。
当赫尔曼坦白自己没去学校,先前总对儿子百般挑剔的妈妈,听了不过是点点头,说了一句“我猜也是这么回事”。至于爸爸,则在赫尔曼睡前取来一本书,在儿子床头念了一个故事《去圣库鲁次的遥远之路》。圣库鲁次是书中主人公的目的地,他历经重重困难抵达后,却发现,那曾令人无比向往的地方,其实什么也没有。
听完故事的赫尔曼低声表示,自己当天的遭遇就和这个故事一模一样。爸爸严肃地点了点头:“我知道,儿子。”面对儿子惊讶的目光,爸爸解释道:“我也去过‘圣库鲁次’呀。”
原来我们所有人都有过“去圣库鲁次”的经历!潇然小朋友的妈妈和爸爸,也一定记得自己年幼时曾去过“圣库鲁次”,所以,在“一地鸡毛”的“那年我×岁”里,他们一方面参与并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同时,也不耻以孩子为“师”。
“一心不能二用”这个道理,本是家长教会孩子的,但,边烧菜边看书而烧糊了一锅红烧肉的潇然妈妈,面对儿子的诙谐批评,再也做不出“分秒必争是因为课业紧张”之类的自我辩解,她伸出手,允许儿子打自己掌心以为惩戒。
潇然好奇家中的山茶瓶插为何每天总有骨朵冒出,好像永远花开不败——
我问妈妈,花朵吃了什么呀?妈妈说,花朵吃了清水。
我说,清水里面难道有很多营养吗?
妈妈告诉我,花不需要很多营养,它知道我们爱它,就使劲开给我们看。
我接过妈妈手里的小喷壶,每天给山茶花喷一点儿水。有时候我看见爸爸想把喝剩下的凉茶往花上浇,被我一把夺下茶杯,我很严肃地告诉爸爸:妈妈说了,爱干净的花,只喝干净的水!
鲜活一幕!当然啦,书里的鲜活,远不止这一幕。
大概两年前吧,我见过冉潇然小朋友一面。当时,他正对身旁的一位叔叔讲着什么,津津有味。当“巴雷特”“勃朗宁”“甘地”“福笛”一类的词语飘过来,我禁不住伸长脖子问:“小弟弟,你这都打哪儿知道的啊?”小朋友扬起他的圆脑袋——嗯,就是这套书的插画作者书路路勾勒的那颗圆脑袋——一字一顿地回答:“喜马拉雅。”瞧,作为网络原住民的“10后”,人家早早就懂得通过音频信息平台学习感兴趣的内容了。最近,我积累了一些热兵器方面的知识,下次再见,难说不可以就此跟潇然切磋切磋。那样的话,潇然爸爸、跨界儿童文学作家冉隆中先生,也许又能记下一节故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