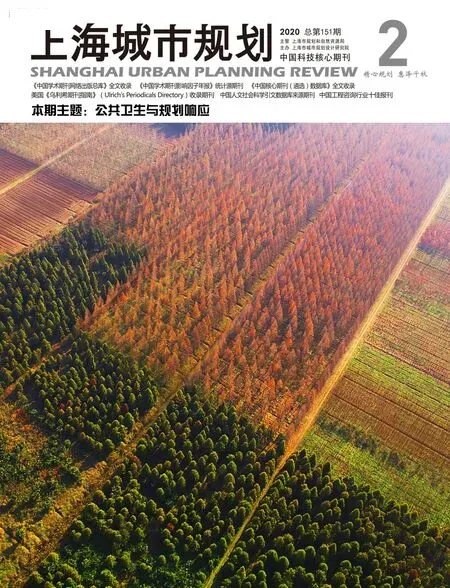浅议新基建背景下城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趋势
赵丽虹 王 鹏 ZHAO Lihong, WANG Peng
一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让公共卫生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2003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疫情后,国家发改委联合相关部委,组织全国“加大投入、加快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中,亚投行表示将对中国提供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协助加强中国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并认为此举将对全球公共卫生发展带来长远影响。可以预见,城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将再次进入一个全面快速的建设时期。
202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由此释放出强烈信号,新基建将成为下一个建设工作重点,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新基建的本质强调以科技端为发力点,这也为新时期更为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指明了重点与方向。新基建时代,城市公共卫生建设将面临怎样的转变,又将以何为建设重点,本文试图结合城市需求与新技术支撑,以及近年已经发生的案例,对此进行分析阐述。
1 城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范畴
19世纪中叶的英国公共卫生运动与《公共卫生法》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城市规划的起源。公共卫生运动通过清理城市垃圾、改善下水道,消除在城市中蔓延的传染病。《公共卫生法》规定政府卫生委员会的职责包括城市的给排水与垃圾清运,以及提供公园、公共浴室等公共设施。可以说,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是提高城市公共卫生水平的主要手段。
通常讲的城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更多指的是各级医院与疾病控制中心等医疗设施,而非环卫、给排水等市政基础设施。这一方面与公共卫生领域的不断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部门的事权划分有关。在卫健系统职权范围内,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多限于医疗设施。然而无论是公共卫生本身的职能要求,还是国际惯例,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含义都更为广泛,涵盖与公共卫生相关的各类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的职能除了对重大疾病尤其是传染病进行预防、监控和救治之外,还包括对公共环境卫生的监督与管制,如向公众提供安全卫生的饮水等。
因此,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至少包含以下3类传统设施:一是通常所指的医疗卫生设施;二是与环境卫生相关的基础设施,如公共厕所、垃圾收集与转运设施等;三是市政设施中的给排水设施。此外,信息时代催生的全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如远程医疗、人工智能诊疗、在线卫生服务等也在公共卫生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新型数字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2 新时期城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转变
2.1 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到“新型化”升级改造
随着城市发展模式从增量转向存量,增量时代作为土地开发配套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将越来越少。随着城市人口的进一步聚集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将从基本供应的达标转向对于安全性、可靠性、保障性的提升上,这里的安全包括公共卫生安全。
在多年行业规范约束下,城市的环卫系统和给排水系统基础设施看似能够满足城市公共卫生的基本需求,但实则相当脆弱。2003年在香港淘大花园暴发SARS超级传播事件,在事后调查中认为很可能是由于没有及时维修排水管,导致U型隔水阀干枯所致①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Department of communicable disease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consensus document on the epidemiology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In Geneva: WHO/CDS/CSR/GAR/.2003:1-44。。作为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风暴眼——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目前普遍认为其并不是病毒的产生地,而只是一个“超级传播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集中发生了超级传播的空间场所。疫情的暴发与市场及周边的环境卫生情况有多少关系?市场及周边的环卫收运系统、污水收排系统在其间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它们是否有可能成为疫情发现、监测甚至阻断的一个窗口?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因为目前的城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水平还远不足以支撑。
相比电力系统、通信系统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中完成了代际的技术升级,城市环卫系统和给排水系统的技术水平依旧停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但这一现状并非无法突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规划系实验室,就有利用污水获取信息、分析传染病和人群健康情况的研究项目②http://underworlds.mit.edu/。。项目通过使用远程自动采样器和生化测量技术,提高污水采样和分析的时空分辨率,利用数据可视化以及下游计算工具,开展人类健康普查和传染病防治[1]。该研究一方面为公共卫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数据,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群健康与公共卫生情况;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对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控制。一旦发现病毒便可对所有排水分区实施医学封锁。通过精准的监测与控制,大大降低行政部门应对潜在风险的成本,缩短观测和评估危险等级的时间。这一项目的关键技术包括低成本的采样器和生化测量传感器,利用工业物联网技术,构建传统基础设施融合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以下简称“ICT”)的新型基础设施,实现对全网运行情况、水质情况等的实时监控,并准确及时地进行调节与干预。
新基建的本质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利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5G、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提高其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通过计算与连接更精确匹配基础设施的供需矛盾,及时发现并解决运行中存在的效率与安全问题,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自然延伸,也是提高城市公共卫生治理水平的重要手段。近年,我国已广泛开展智慧水务、智慧环卫等建设,在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慧化升级方面进行了一定探索。新基建时代,随着传感器、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升级与广泛应用,这一升级过程将整合更为丰富的信息收集、更加高频的信息汇聚以及更为复杂的信息处理,使基础设施和城市服务得以不断优化。
以笔者参与的国内某大型ICT企业的智能市政管道研发项目为例,该项目在地埋管道中缠绕分布式光纤传感器、埋入MEMS传感器,并引入无线供电和传输等技术,通过对传统地下管道的低成本适度改造,实现对整个地下管网全覆盖式的水质、水量、液位、气体(有毒有害)等状态的监测,以及温压流泄露等故障感知。这种方式相当于在地下再造一个通讯网和传感网,大大扩展了人们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把控能力[2]。
2.2 从硬件设施建设到服务与管理能力提升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口聚集到城市。加之交通运输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城市中与城市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流动强度与频率都比从前有了指数级增长。越来越庞大的城市规模与越来越高频的要素流动使得城市问题的复杂度大幅提升。这对城市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城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同样面临服务与管理能力升级的需求。
传统基础设施的新型化改造,通过测控终端、数据采集传输、数据接收分析、智能化操控、信息服务一体化的系统建设,为服务与管理能力升级提供硬件基础与技术支撑。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城市服务与管理模式,具体表现为实时化、全链条、智能化,以及效率与可靠性的全面提升。与此同时,识别城市痛点问题,采用适宜的技术集成方案,充分发挥新型设施的作用,也需要更高维度的思考与创新。
以浙江省正在推广的针对医疗废物处理的监管系统为例,为了解决医疗垃圾收运处理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污染扩散、手动称重误差、转运过程难以校准、遗失不可追踪、人工交接不易监管等问题,项目综合利用信息化技术,通过系统搭建和源头信息采集终端、溯源校准仪、闭环监管平台等软硬件设备的研发,实现“物联网+”模式在医疗废物收集、中转、存储、运输的全过程监管。通过精确到单袋垃圾的全程无缝监管机制,实现了少人化、精细化、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查处的高水平管理。随着物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成本下降,该方式可应用于更广泛的垃圾收运处理与监管,全面提高城市公共环境卫生管理水平。
清扫不及时的城市公共厕所会为疾病传播埋下隐患。2017年美国加州暴发甲肝疫情后,疾控部门与城市市政部门联合开展大规模的公厕改造行动,提供更卫生、更充足的公共厕所,以减少甲肝等通过粪口传染的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有专家提示新冠病毒粪口传播的可能性,公共厕所可能成为潜在的传播场所。在我国,维护成本高、公厕清扫人员数量有限是公厕管理的痛点。目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公厕控制系统已比较成熟,并在多个城市建设使用。通过前端采集装置、控制模块、通讯模块、云服务器的集成,智能公厕逐步实现了无人值守、自动维护、自动清洁、自动粪便处理等功能。通过提高卫生水平、无触碰控制等方式在减少疾病传播的同时,大大节约了人力维护成本,以及能源和水资源。
2.3 从单一系统建设到复合功能协同
城市管理是分部门运行的,但城市作为复杂系统,很多城市问题的解决需要多部门协作,越复杂的问题越是如此。事实上,提高公共卫生水平、优化水资源利用、垃圾资源化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都不是单一系统、单一部门可以完成的工作,需要多个系统的协同联动。而应对突发事件,更是需要多部门多系统协同。
在新技术驱动下,城市管理中的条块分工将被进一步整合。近年来,跨行业、跨部门的综合性协同机构已经出现。众多城市组建融合规划、城管、环卫、环保、市政市容等传统部门业务的大城管部门;各种城市生命线的应急能力被抽离整合成为专门的应急管理部门;大数据局等数据主管部门开始自上而下统筹智慧城市建设的设施和数据。这些管理职能整合的基础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新基建将进一步促进这一趋势的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可以看到众多以数据协同为基础的综合管理应用。如各城市推出的健康码、疫情决策指挥系统等信息化平台,打通了各部门商业数据和公共数据,为社会正常运行和管理者高效决策提供前所未有的智能工具。在流行病学调查与科学防疫过程中,运营商数据、出行数据与公安数据的整合为识别感染者出行轨迹和密切接触人群提供了高效工具。再如电子病历是一种典型的数字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除了解决传统病历的记录和存档功能之外,在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的支持下,通过共享相关医疗部门的数据,可以实现上下级医院、医院与疾控中心之间的高效协作。可以预见,随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提速,通过对分散于各部门、各机构单一系统数据的汇集和综合分析,能够实现更多复合功能的协同。这也将成为提高公共卫生水平的重要手段。
2.4 从一次性建设到动态建设与弹性布局
包括传染病医院在内的各种医疗机构是城市最重要的社会性基础设施。在城市规划体系中,医疗设施数量、规模、用地要与其服务范围和人口相适应,建立形成内容和形式相统一、适应于分级诊疗的医疗设施布局体系。而面对SARS、H1N1、新冠肺炎等大规模传染病疫情,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在大城市暴发的风险,临时医疗设施和应急临时设施的空间布局,除了预留弹性用地以外,动态弹性的规划建设技术手段也日渐成熟。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武汉火神山医院从决定建设、选址、设计施工到交付使用,只用了不到10天。而其后又以更快的速度将多个体育场馆、会展中心等大型建筑改造为收治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传染病医院有着很高的技术要求,这种建造效率在传统的城市规划建设中是无法想象的。其过程中使用的基于BIM技术的大规模协同工作、模块化预制建造,以及尚未使用的3D打印和机器人等技术,都是未来弹性化、共享化城市空间营造的技术前提。同时,在选址过程中也出现了功能兼容、水源地保护等问题,如果在未来的城市规划中对这些予以更多考虑,提前预留相关用地,并对相关的用地和建筑做出兼容性的功能预设,提供灵活转化的可能性,相信可以进一步提升应急卫生设施建设的效率。
可以预见,未来的快速建造技术将会依赖更少的人力,以更高的集成度和自动化能力实施,提升城市应急、野战、弹性空间营造等场景的空间建设和转化效率,并提供更高的舒适性和安全性。而对共享空间、弹性用地、战略预留地、可转化功能用地的考虑,将会成为城市应对新的空间需求和不确定风险的基本要求。
3 新时期城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的转变
3.1 建设与运营主体多元化
传统设施“+新型设施”的升级方式,意味着建设主体需要“+科技公司”。新基建所涉及的科技企业,如通信设备制造商、互联网公司、智能化集成商等都可能加入建设过程,或是成为主角。建设主体多元化带来技术升级的同时,也对规划设计与建设统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建设成本的提高将促进更广泛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合作。传统基础设施由于服务对象的非特定性和服务的难以计量性,其建设成本在一般情况下很难直接回收[3]。这是开展PPP合作的主要制约。而新型化升级改造后的基础设施,以数字化、智能化为基础建立新的低成本、可量化的运营方式,将深刻改变传统设施的运营逻辑与营利模式,大大推动社会资本的进入。
3.2 规划设计建设运营一体化
传统的“规划—设计—施工—交付使用”项目建设模式在新趋势下将被打破并更新整合。目前,出于控制成本、拓展融资等目的,EPC(设计—采购—施工)、BOT(建造—运营—移交)等工程建设模式已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在新基建背景下,规划设计建设运营一体化更是实现应用技术创新升级所必需的新模式。
从对城市需求的梳理,到复合功能设计、产品研发,再到设备部署和系统搭建、优化,这一系列过程需要从需求到技术,再从技术到需求的反复考量,需要对城市问题、传统设施、新技术有全面的理解,需要多专业、多环节的配合。这是由传统设施“+新技术”的创新性所决定,也是新基建时代传统行业升级的通用模式。
3.3 标准规范的升级与地方性探索
笔者所指的标准规范包含两个方面。
首先是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传统规范标准。随着公共卫生标准、应急响应等城市治理需求的不断提升,加之近年来不断发生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警示,针对这方面的法规与规划设计标准需要进一步完善[4]。事实上,我国对于这方面规范标准的制定一直相对滞后。比如,在城市给排水规划规范中,直到最近才有相关规范增加了应对防灾减灾或公共卫生事件的条款。而2019年以前,我国没有一部针对城市综合防灾的规范。因此,不断完善相关法规,提高规划设计标准是顶层设计层面的重要工作。
其次是新技术对应的技术标准。新技术集成应用中不同领域的协议、组网、数据模型、安全等标准,均需要在地方实践中完成对接、整合和统一。同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标准,还应考虑与城市其他系统领域数据标准的对接和融合,以利于数据增值应用以及城市整体的智慧化升级。
4 结语
通过不断建设和持续完善现代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是城市规划的起源,也是城市规划与管理最重要的职能之一。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以及社会运行节奏的加快,传统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面临升级需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集中暴露出公共卫生服务的诸多问题,也呈现了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的若干趋势。新基建时代,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将推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在信息化、智能化方面的升级,促进公共卫生管理与服务水平提升。与此同时,整个城市规划和治理模式,也应该顺应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建设更加韧性和健康的未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