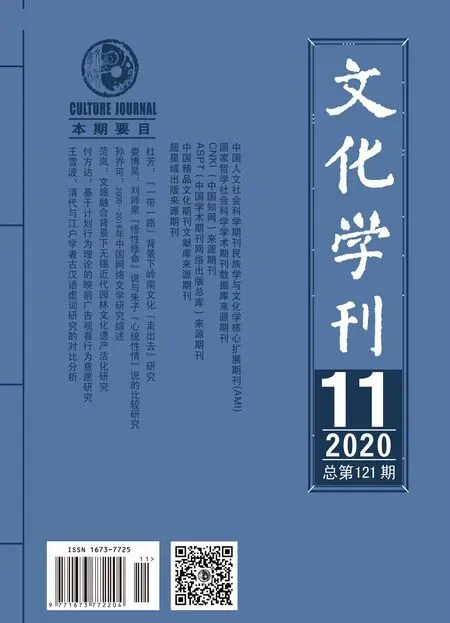论梅娘《鱼》中的女性孤独者
李德慧
梅娘是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文坛才女,与张爱玲并称为“南玲北梅”。如果说张爱玲穷尽一生展现上海洋场的繁华与苍凉,并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梅娘及其作品则遇到了相对尴尬的处境,作为文坛上近半个世纪的“失踪者”,梅娘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得以“解冻”的沦陷区文学研究活动被重新发现。在《鱼》中,梅娘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并以“孤独”这一关键词为切入点,探索这一庞大的孤独者系列。这些女主人公大多是出身闺阁的知识分子,却无法获得自由轻盈的灵魂,只能在狭的天窄的路中生存,如《鱼》中的芬、《雨夜》中的李玲、《一个蚌》中的梅丽。无论是青春年少的女孩子还是已为人妻的少妇,孤独和寂寞是她们在不同时空下共同的情感体验。
一、原生家庭的破碎
梅娘无处不在的孤独意识最早源于原生家庭的破碎。父亲孙志远是吉林长春有名望的大实业家,生母被驱逐,作为外室之女的梅娘被养母收养。虽自幼生活在优渥的家庭环境中,但那份温暖的母爱对于她来说始终犹如镜花水月,望而不得。当她16岁中学毕业后,父亲也去世了。这样一段“大宅门”内的童年经历使梅娘过早地感知人世的无奈和心酸,从而形成敏感细腻的性格,并在其作品人物身上展现出相似的生命痕迹。
父母不幸的婚姻给梅娘留下不可磨灭的创伤。尽管父亲与梅娘的关系十分和睦,但是父亲的过早离世,让梅娘彻底失去了精神寄托,或许对于父亲的依赖导致她始终无法正面面对这一事实。父爱失而不得的情绪映射在作品中,使梅娘对于父亲角色产生一种不和谐的隔膜感和疏离情绪。在《蟹》中,王福只把自己的女儿翠当作换取安乐生活的工具,喝醉酒后拿一家人泄愤,无情踢打翠的母亲,更不顾女儿的意愿,暗自将其许配给三爷做姨太太。王福从头到尾想的都是自己,女儿、妻子只是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棋子而已,父亲身份本该承担的教养职责和父爱更是无从谈起。王福和张爱玲《花凋》中川嫦的父亲十分相像,在女儿和金钱之间,他们毫无悬念地选择了金钱。梅娘笔下相似的角色还有很多,诸如《一个蚌》中梅丽的父亲、《小广告里面的故事》中的姨爹等。从现实中唯一的依靠到父爱一去不复返的巨大落差,可以看到梅娘对于父亲的复杂心理。
如果说父亲角色只在梅娘的生命中留下短暂的记忆,让她饱尝孤独的滋味,那么母爱的缺席则是这种孤独之感产生的源头。梅娘的生母遭到养母驱逐,下落不明,梅娘的笔名则是取自“没娘”的谐音。一方面,梅娘小说中的女性无法忍受继母的种种丑恶嘴脸;另一方面,她们无法撼动继母作为家长的稳固地位。梅娘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继母的复杂心理,投射到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是主人公与继母无法逾越的隔膜。在《侏儒》中,作为后母的房东太太惨无人道地虐待私生子,言语上的刺激如家常便饭,随口称呼孩子“王傻子”“王野种”“傻王八蛋”。行为上的虐待更加令人发指,冬天三两天不给饭,“那孩子全是叫她打傻的,她那样的打法,铁人也打扁了”。[1]8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神圣的母亲形象早已解构,私生子成为房东太太报复丈夫外遇的工具,房东太太已经变成了一个清醒的疯女人,母爱被她的残忍冷酷吞噬于无。《一个蚌》中,后母一心想的只是自己的利益,竭力促成梅丽嫁给一身脏病的朱家少爷,由此梅丽发出心底的呐喊:“娘做的才是应当的,该死的娘!该诅咒的社会。”[1]110母亲身份的存在名存实亡,只能进一步加剧梅丽的孤独。这是梅娘笔下的继母,没有给予孩子过多的宠爱,却一步步将他们推向孤独的深渊。
很难看到梅娘笔下的女性有对家庭的眷恋,她们坚定并且义无反顾地出走,然而这些女性很快从大家庭的桎梏下钻进了小家庭的囚笼中[2],如《鱼》中的芬、《夜合花开》中的黛黛。而在现实中,当梅娘与柳龙光组建自己的家庭后,依旧没有摆脱这种孤单的处境。幼年失母,少年丧父,青年亡夫,中年再失子女,无论是原生家庭抑或是新生家庭,始终无法让梅娘获得圆满。
二、同性间的集体孤独
在一些女作家的小说叙述中,若其笔下的女性与家庭的交流受到阻碍,或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感情而身心俱疲,往往倾向于将孤苦无助的内心世界分享给同性。如《一个蚌》中的雯姐、梅丽、秀文、倩、贞、兰之间的真挚友情,《春到人间》中的王玫和申若兰,《蟹》中的玲和翠等。然而,梅娘并不仅仅在执意描写这些女性之间纯真的友谊,而是用她女性特有的情感敏锐感受到女性在友谊包裹之下个体孤独的内心世界,以此构建一个庞大的孤独者集体。
《一个蚌》中,梅娘看似展现了一幅女性群像图,梅丽与雯、秀文、倩、贞、兰之间彼此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然而深析文本就会发现,其实她们每个人都有各自无法言说的忧愁。雯姐因为偏大的年纪和不出众的外表,迫切寻求结婚的异性伴侣,心情时常苦闷;秀文在拮据的现实生活和传统的婚姻观之间思考自己的出路,得出“到哪里都是受欺负的角色”[1]49的结论,压抑的内心世界一览无余;梅丽与琦两情相悦,却在家长的阻挠和双方的怀疑下支离破碎,琦远走他乡,梅丽只能饱受孤独之苦。倩、贞、兰没有正面出场,却也纷纷被情感琐事缠绕,无法享受真正的爱与自由。尽管梅丽和秀文、雯姐在外部空间有自己的挚友,然而每个人都生活在孤寂苦闷的状态中,她们的故事聚集在一起,更让这种孤苦氛围肆意扩张。同样在《蟹》中,玲和翠也是如此。玲生活在衣食无忧的大家族中,然而家族间的尔虞我诈让她幼小的心灵时时孤单,继母总是待她如外人,叔叔婶婶只在吃饭时招呼她,她只能在日记中记录生活的悲哀,恰好温柔的翠给了玲姐姐般的关心。翠的父亲是玲家的有功之臣,把自己的女儿当作摇钱树,以此换得晚年的悠闲生活。最终在三爷和父亲的合谋下,翠成为三爷的姨奶奶。玲的孤寂来源于精神上的无依,她并不需要时刻担忧物质的匮乏,翠的孤苦则来自生存的艰难,清贫的生活、势力的父亲、软弱的母亲,人生的任何风浪都由自己承担。这对惺惺相惜的伙伴在短暂的相伴之后,依旧走向各自孤单的空间,一个守着旧生活,一个投入新牢笼,只能独自舔舐伤口。
梅娘让笔下这些孤独的女性周围形成各自的同性朋友圈,她们以孤独症患者的姿态集体亮相,每个人苦苦挣扎在不得理解的孤岛里。梅娘旨在进一步说明,当女性个体在人生自由的道路中奋力前行时,她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父权社会的挤压,而且无法在同性朋友中获得心灵的解脱,甚至缺乏反抗的行动力。玲在尔虞我诈的大家庭中烦闷压抑,却始终没有勇气与之彻底决裂,翠更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梅娘在这里对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的出路问题进行了前溯,即这些孤寂的女性第一步如何成为勇敢的娜拉,继而一起反抗,因为“只有女人联合起来才能自救”。[3]
三、两性关系的失衡
正如马克思所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4]如果说原生家庭的破碎和同性之间共同的苦闷滋养了梅娘的孤独意识,那么两性关系的失衡则让她的人生底色变得更为苍白和黯淡。
《鱼》中的芬学生时期暗恋国文先生,暗恋受挫后又将丰富的感情转移到林省民身上,最后决定离家出走和林结合。她生下儿子,舍弃看书的时间,整天在厨房和卧室之间徘徊,丈夫隐瞒早已娶妻的事实,要把她带回家做姨奶奶。芬对爱的勇敢追逐,换来的只是丈夫的日益冷淡、责骂和剧烈的踢打。从家的围城奋力逃脱,转身又进入爱的牢笼,由此芬发出悲切的呐喊:“我感到过分的孤独,多么空旷的世界呀!”[1]32对丈夫的失望又使得芬转向丈夫的表弟琳寻求安慰。在两性亲密关系中,芬始终义无反顾的付出,强烈的渴望爱让她的姿态低到尘埃中,男性却以爱的恩赐者角色存在,平等的夫妻关系无从谈起。爱,让人沉迷,也让人失去完整的自我。
《动手术之前》少妇的丈夫长时间忽略她的存在,对她的喜怒哀乐也漠不关心,并拿着她的钱肆意挥霍,使得她在一个个孤寂的夜晚备受煎熬。直至遇到丈夫的朋友,在他的诱惑下,她释放压抑已久的性,结果不幸染上花柳病。不管是丈夫还是丈夫的朋友,他们都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随意享受“本我”带来的欢乐,以异常强势的姿态将苦难留给少妇一个人。弗洛伊德在《性爱三论》中曾提到过力比多理论,并把力比多广泛定义为身体上一切器官的快感。少妇是因强烈抑制性欲而力比多失衡的人,最后引发恶果。弗洛伊德“一切皆性”的理论与梅娘以性爱为健全女子生活的内容不谋而合。在同样关注两性关系的女性作家张爱玲那里,不同于梅娘作品中的女性对于精神之恋的极度渴望,她们则把物质生活放在第一位,如《金锁记》中的七巧为获得财富不惜嫁给患痨病的少爷,又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对范柳原讨好奉承以换得婚姻保障。梅娘《鱼》中的女性大部分出身闺阁,受过一定教育,她们在外在环境中也并不是茕茕孑立,她们有家庭、有父母,她们想要的只是纯粹的精神之爱。如梅娘自己所说,她的“女人画廊只不过是几个想获得幸福爱情的小女人”[5],可是在爱的国度苦苦挣扎,依旧得不到契合的伴侣。这些在两性亲密关系中失衡的女人,以第一人称独语的方式,竭力控诉周遭的男性和社会,对异性陷入深深的失望,因此也愈加迷茫和孤寂。
四、结语
在梅娘的小说《鱼》中,生存着一群庞大的孤独症患者,“孤独”已经成为弥漫在文字间一种无处不在的生命氛围。这些女性有着相同的哀怨,却又有个体独特的体验,在与传统对抗中追寻自我的生命之地,憧憬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尽管“孤独”成为梅娘和笔下女性共同的生命体验,但她并不排斥孤独,反而大胆展现孤独、分享孤独,进一步说明孤独的本身是对生活怀有热情,麻木才是黑暗,才是悲哀,才是日趋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