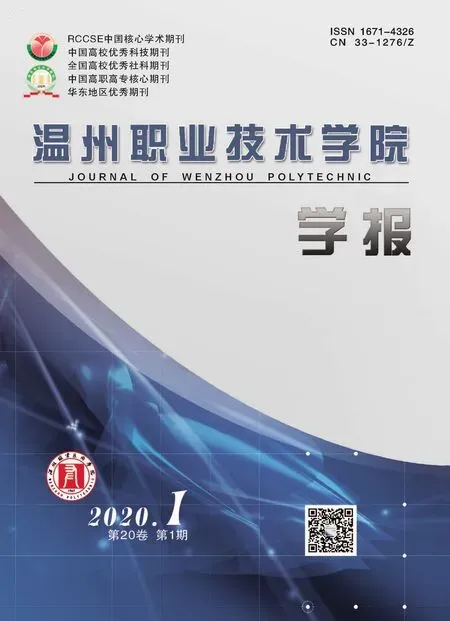清代温州瘟疫与社会应对
何伟,何泽
(1.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浙江 温州 325000;2.温州市图书馆 读者服务部,浙江 温州 325000)
跟一般的疾病基本只与病人及其亲属直接相关不同,瘟疫一旦发生,就关乎整个社会[1]。医疗水平虽已今非昔比,但肺结核、疟疾、肝炎等传统传染病仍在肆虐,又不断有艾滋病、非典型性肺炎、甲型H1N1流感等新型传染病对人类造成巨大威胁,抗击传染病威胁仍是人类重要的研究课题[2]。清代是我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历史阶段,温州是清代中国疫病常发地区之一,回顾和研究清代温州瘟疫的特点、原因及处置方略和措施,弄清其发展的历史规律及对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影响,或有重要意义。
一、清代温州瘟疫的特点及后果
由于史料的缺失,无法完全统计有清一代温州瘟疫发生的具体时间和次数。依据现有资料所揭示的数据,清代温州瘟疫的发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特征。
首先,清代温州瘟疫在全域范围内都有发生,并且有些时候呈现连续性暴发状态。如道光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年,光绪八、九、十年,光绪二十四、二十五年间温州均连续发生了较大的疫情。且在同一个年份中,疫情亦有可能多次连续暴发。如光绪二十八(1902)年温州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疫情在7月底达到了高峰,8月至9月上半月疫情已渐趋平息。……但自9月15日夜天降大雨,与之巧合的是,霍乱死亡人数亦随之陡升,出现了第二个高峰,并表现出了另一种流行方式,死亡人数也大大多于第一个流行高峰”[3]116。瘟疫的连续暴发相对于散发性疫情更为严重,它往往给民众带来极大的恐惧,连发性的瘟疫也使得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更为困难。各地暴发的瘟疫中往往彼此之间有所联系,传染性比较强。“霍乱疫情初自海关附近沿东及西各城乡,次则辗入城内各处,传染甚速,死亡相继。郡之四乡外县平阳等处流行殆遍。”[4]571有时候还会有多种瘟疫同时发生。同样是在光绪二十八年,霍乱第一波疫情高峰平息后,温州又出现严重的疟疾流行,几乎遍布整个城市[3]117。
其次,清代温州瘟疫发生的频率高,种类多。从现存资料可见,自顺治初年到宣统三年,温州地区每隔几年就要暴发一次大的疫情。瓯海关代理税务司包来翎在《瓯海关十年报告(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中说“(温州)每年秋季都会流行痢疾,有两三个年头的疫情如此严重,以致一些村庄的人全部死亡。……天花、麻疹、百日咳和流行性腮腺炎时有发生……疟疾常年都有发病,有些年份里到秋季会严重流行。伤寒和类伤寒相当常见。霍乱经常会在夏季光临这座城市。”[4]266清末居于温州的苏路熙曾想通过统计温州人群中的麻子脸的数量,来估算温州天花和麻疹的发病情况,“统计到几十个的时候就放弃了,多得实在数不清啊!”[5]
清代温州的瘟疫,除了各地普遍存在、早已成为地方病的天花、麻疹外,以霍乱、伤寒、细菌性痢疾等肠道传染病为主,从清中期开始,白喉等喉科传染病渐趋增多,疟疾在夏秋也会不时出现。瓯海关《医报》所载温州瘟疫[3]13主要有8种,具体为:霍乱(Cholera)、疟疾(Ague/Malaria)、梅毒(Syphilis)、淋巴腺肿(Bubo)、天花(Smail-pox)、痘疮(Variola)、水痘(Chicken-pox)、白喉(Diphtheria)。
清代尤其是清中期以后,霍乱成为威胁温州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罪魁祸首。小儿中以痘疹为最,另外白喉、间歇热亦颇为严重。现代研究一般认为,近代医学所指的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即Cholera,系嘉庆二十五年(1820)时从印度由海路传入[6]。霍乱传入中国的当年,温州就暴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该年八月乐清大疫,“患霍乱转筋之病,犯者顷刻死,哭泣之声几遍里巷。”[7]咸丰四年(1854),平阳暴发霍乱,“疫气到处传染……死丧累累饿殍处处有之,日日有之。”[8]159光绪二十八年的霍乱疫情尤为严重,据估计,死于本次霍乱疫情的全城人口大约在5 000~6 000,全府大约有至少30 000人罹难[3]116。
天花,俗称痘疹,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传入我国。清代温州小儿患痘疹的记载比比皆是。“嘉庆十年,永嘉痘疫。”[9]1649“咸丰七年五月间,瑞安有痧症及疫痘,甚险。”[8]171“光绪十年,温郡近日天花盛行。”[10]1894年12月到1895年3月间,温州暴发了一场天花,死亡率非常高,开始主要在儿童中流行,后来成年人开始受到感染[3]98。
同霍乱一样,白喉也是清代出现的一种新的瘟疫。其英文名为Diphtheria,系由白喉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传播,亦可通过接触传播,秋冬季多见[11]。据余新忠等学者研究,1790年以后,白喉逐渐在中国流行,首先在江浙地区,然后不断扩展,到光绪年间,已经流行于全国各地。光绪十九年,瑞安白喉盛行。瑞安人陈虬一家患白喉者就有四人[12]。清代温州名医陈葆善论述此次疫情时说:“壬辰秋冬之交,天久不雨,燥气盛行,……是症(白喉)辄大发。”[13]
再次,清代后期温州疫情呈现出明显的域外传入特征。明清以来温州商品经济活跃,鸦片战争后又开放通商,使得温州与其他地区的人口交流更加密切,特别是与一些正在暴发瘟疫疫区的人员流动,导致疫情的传入和流行。清代晚期,温州瘟疫与此相关者不在少数。以1902 年爆发的霍乱疫情为例,1902 年最早的霍乱病例是在广州发现的,随即开始从广州向周边地区扩散,不晚于5月下旬传入福建漳泉至厦门一带,很快又传入温州,是年温州霍乱大行。同年,包理茂在提及一例疟疾患者时亦称,该病例并非本地感染,而是来自广东[14]。1903年温州出现了感染登革热的病人,而这些病人都是从宁波来温的[3]117。
最后,与清代前期发生的历次瘟疫相比,清后期的瘟疫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道光十四年(1834),温州发生大疫,死于饥疫者日以十百计,棺木来不及准备,就用稻秆野草等裹尸。永嘉县二十三都某村,同族十七家只剩下一家,双门一个村落本来有三十二家,只剩下三家[8]123。可见清代晚期温州瘟疫有传染性强、社会危害严重的突出特点。
疫情严重影响社会生产的正常秩序。道光年间,温州瘟疫盛行,永嘉上河乡、永嘉场两处尤甚。农民十室九病,劳动力的丧失,使得人们连用桔橰取水灌漑以缓解旱情都无法做到。疫情的蔓延还会造成物价上涨,加重普通百姓的负担。道光十四年,永嘉春夏大疫大饥,一石米涨价高达八千文,米珠薪桂。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8]123。
二、清代温州瘟疫发生的原因
清代温州瘟疫之所以如此多发,与温州自然因素密切相关,同时还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现择其主要方面述之。
1.环境气候
对环境与疾疫间的关系,中医早有认识,且已形成了专门的“五方致病论”和“五运六气”致病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温气候的变化对人体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现代科学已经证明,生态环境影响疫病流行的因素很多,但以气候和地理因素的作用最为突出[15]。温州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区,气候卑湿、地气燠热,生物资源丰富、树种繁多。茂密的丛林,加上湿热的气候,使得温州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多瘴气之地,易于各种致病微生物的繁殖和生长。温州又濒海,每年夏秋因遭台风袭击,造成的人畜大量死亡,也会加剧瘟疫的发生。
气候的反常也是瘟疫流行的重要原因。温州地气燠热,大多数年份冬无严寒,不见霜雪,但如遇到强劲的寒潮,偶有奇寒,或夏季燥热少雨,就有可能会导致疫情的发生。《永嘉县志》载温州“晴雨无常,冷暖难测,人多时症”[16]。瓯海关税务司李明良分析光绪二十八年霍乱大暴发原因,认为“本年温州天时不正,非亢燥逼人即潮湿过度。……自六月起,暑湿交蒸,水汽污秽,以致酿成霍乱吐泻之症”[4]571。
劳里医生记载1883 温州瘟疫情况时说:“本年温州干旱,降水稀少,从9 月开始瘟疫多发,平时水量充沛的稻田如今已经干涸,水渠水量(不再流动,出现停滞)急剧下降,结果造成水渠充斥更多排泄物。”[3]75劳里医生亲眼目睹了“温州贫困阶层是如何绝望地尽一切可能获取水源,他们喝的水只比粪坑里的污水强一点[3]95。瓯海关《医报》分析1895 年温州瘟疫时认为,夏天干旱少雨,以致水井干涸,居民不得不去河里取水,但由于河水不洁,病菌丛生,这为传染病的传播提供了机会,以致霍乱流行[3]101。如果昼夜的温差突然变大,也会使得人们抵抗力下降,易被瘟疫感染。1897年的秋天,温州气候异常,昼夜温差一度超过了10 摄氏度,痢疾就开始在居民尤其是儿童中间流行[3]107。
温州多水的地形,决定了它成为间歇热等疫病的多发地。清代温州水系发达,密布而四通八达的水网既给予了人们出行的便利,但也为疫病传播提供了方便。其一,肠道传染疫病的致病细菌一般都在水中易于存活,丰富的水源自然就为病菌提供了优越生存环境。其二,相互流通的水流也为病菌的四处传播提供了可能。“每年春季,很多时候一直到秋季,间歇热就会在当地肆虐,有的村子甚至有一半人染病”[3]28。
2.社会发展
清代温州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员和物资的频繁流动,对外贸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大,国际交流不断增强,也是温州瘟疫盛行的因素之一。嘉庆二十四年(1819)暴发的霍乱就是从泰国曼谷和印度经海路传入广州、汕头、温州、宁波等口岸的,致使嘉庆二十四年到道光二年(1822),霍乱在温州流行,持续达4年之久。方志上有“夥疫流染、朝发夕死”“遭此厄者,十室八空,得生者十之一二”[17]的记载。
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也给社会生态环境带来较大的破坏,促进疫病在温州的蔓延。现有研究表明,明代中后期,特别是18 世纪以来,温州地区的人口大幅增长,在持续的人口压力之下,为扩大耕地总面积,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垦殖活动,掠夺性开发,给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破坏[18]。特别是,温州在通商以后,出现了一定的传统工业乃至近代机器工业造成的工业污染,同时由于城市卫生清除机制跟不上人口发展的要求,致使生活垃圾不能得到及时的自然消化,城市污染日趋严重。主要表现在水质变差、环境卫生状况不良。这些,都大大增加了疫病暴发的机会。苏路熙就说:“据说温州是中国最干净的城市,我会怀疑这个说法的真实性。街道上很多厕所,空气很臭,而且没有净化环境的设施。一个来拜访我的女士无法忍受,对我这个比她更难受的女人说:“亲爱的,我什么时候能把脸上的手帕拿下。”[19]
另外,清代温州随着农业垦殖活动的不断扩展,粪便这一农业生产重要的肥料也随之急剧增长,在城中建造厕所,收集粪便成了一个专门的营生。“温州城到处弥漫着厕所的气味,因此发生疾病毫不奇怪。每条街道上都有无数的茅房和公厕,当然我明白这些厕所都相当有利可图。大量增加的人口是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3]87在(温州)狭窄拥挤的街道,粪池随处可见,空气中弥漫着臭味。在城区中大量建设的厕所,如果不注重清洁,极易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诱发瘟疫的流行。因此,“像霍乱和痢疾等流行疾病在温州肆虐,几乎每年都会死很多人”[3]87。
3.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也是引起清代温州瘟疫暴发流行的重要因素,所谓“大灾之后有大疫”,自然灾害的爆发会破坏生态平衡,水源、食品受到污染,媒介昆虫迁移与孳生,灾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卫生设施被严重破坏,身体免疫力下降等,为传染病发生与流行提供了条件。综观清代温州爆发的瘟疫,往往紧随在自然灾害尤其是水旱灾害之后发生。如嘉庆二十五年温州先是发生了旱灾,七月又爆发了大风潮溢,八月出现了“大疫”[20]。水旱灾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农业收成严重下降,造成灾荒,大量人口无从就食,身体素质下降,易引起瘟疫的暴发和蔓延。道光间温州大疫,“村落有死及半者,其村五里外,有一村落,同族十七家只留一家,其十六家田产俱归此一家所有”[8]118。更为严重的是,各种自然灾害,如水旱灾、风灾等有可能前后相继或者同时发生。如道光十一年(1831)永嘉“五月不雨,至六月旱甚,十九日风雷,二十至二十三连日大风雨,天气暴沴,致成疠疫”[9]1650。各种灾害造成的重叠效应,更会加重瘟疫的暴发和流行。
4.民风民俗
瘟疫的普遍发生还与习俗有关。现代的医学和传染病学著作,一般都把社会习俗视为某地疾疫分布的因素之一。以清代温州广为流行的停丧不葬为例,清代温州“丧家惧于风水,或惧葬时化费,因此停棺不葬。富者其柩多停室内,贫者则置棺于村落树丛或祠堂中……在瑞安,则将柩藏于空室,或做一个锦屏式的朽柜围起来。在永嘉楠溪,丧仪结束后,将丧柩迁置别所或藏于楼阁上面,甚至经过二三代还不安葬。”[21]一直到民国初年,“本城(温州)小山之麓每有停柩多具,积年不葬”[4]610,以现代传染病学的观点分析,尸体的腐烂变质极容易导致瘟疫的传播和流行。常年停丧于地表,尸棺必然会孳生大量的致病微生物,所谓“露厝棺骸,雨淋日晒,腐汁入水,毒气熏蒸”[21],这些病原体一旦为人畜所感染,就极有可能产生瘟疫。特别是春夏之季,温州往往霖雨绵绵,那些裸露尸棺中的病原体就很容易通过雨水而四处流布。若再遇洪灾或潮灾,尸棺漂流,其危害自然也就更显著了。
同时还应当注意到,民众对于瘟疫的认识不足和传统防疫知识的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瘟疫的传播。“温州人相信疾病是因为鬼神,他们有一套理论,霍乱和伤寒是由最恶劣的瘟神引起……人们相信霍乱是因为瘟神进了城市。”[22]而在瘟疫流行时,举办祭祀活动所造成的的人员聚集,无疑会加大瘟疫传播的风险。另外,人们为了避疫可能还会采取某些自残行为,以此来达到驱逐瘟神的效果。“在温州城,当地百姓为了除疫,甘愿忍受巨大痛苦,以证明他们的赤诚。他们会手持高温的花瓶,走上很长的道路,并用钩子挂在自己手臂的肉上,枝条从臀部一直斜插到手上,手臂借此被固定在平举的姿势。”[3]38这种对肉体的伤害,恰恰会导致自身抵抗力的降低,使得致病菌趁虚而入。
三、清代温州地方社会对瘟疫的救助
当瘟疫来临的时候,各级政府官员履行职责,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尽可能挽救民众生命,制止疫情的蔓延,以维护社会治安。普通民众自不甘心坐以待毙,想方设法以求生存,或求医治病,或求神拜佛,尽力与瘟疫抗争。又有各种社会力量的出现,比如民间医生的治病救人,或者慈善机构与个人积极开展各种施治和善后处置工作,对制止疫情的蔓延产生了积极作用。虽然传统的医疗条件有限,政府或个人的一些应对措施并非得心应手,但在严重的疫情面前,各界力量的共同努力无疑是积极的,并产生了相当的效果。
1.官府的救疗措施
(1)设局延医诊治。这是温州官府实施疫病救疗最主要的手段,贯穿于有清一代。清代温州开设有惠民药局,凡有疫情发生,即“令医生开局,于城隍庙施药”[23]600。光绪二年(1876),温州时疫盛行,浙江提督奏巡抚设浙江官医局,并聘请温州名医赵玉兰为主任[23]57。光绪三年(1877)温州府候补同知郭钟岳倡议温州府属各级官员“月捐若干俸金”,于城内府城隍庙、三港庙、大南门天后宫,设惠民药局三所。每年三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五日,各延医生一人,到局施诊。如系赤贫患者,方上盖以戳字,持方取药,以济民病[23]14。自此,惠民药局从大疫之年收治病人的临时性机构变为常设施药慈善机构。为遏制温州频繁发生的天花疫情,同治十一年(1872)玉环同知黄维诰在节孝祠内创设了官办的洋痘局,每年三、四、五及八、九、十月开局,引种洋痘[24]。光绪二十八年,温州霍乱流行时,温处兵备道童兆蓉积极筹款,并温州名医杨逢春负责办理防疫局,以对抗疫情。[23]227
(2)刊刻医书。在大疫流行之年,刊刻切中病情的医书,以使更多的人得救也是当时常见的救疗手段,这主要由社会力量施行,但也为一些地方官员不时采用。光绪二十八年,温处兵备道童兆蓉印刷陈虬所订白头翁汤方,佐以杀虫败毒之品,檄属张贴,以遏制霍乱疫情,“救活数万人”[23]16。
(3)隔离检疫。隔离和检疫无疑是当代面对瘟疫首先需要采取的措施,但在清代早期,地方政府并不会特意采取隔离检疫的措施。晚清以后,随着西方现代防疫观念的传播,为防止疫情的扩散,地方政府开始采取检疫或隔离措施,大大减缓并阻止了疫情的扩散。咸丰十一年(1861),浙海关建立关医处,聘有专职医师,负责海关职员的医疗保健、入关体格检查,兼负责港口检疫任务。光绪二十年(1894),瓯海关医官霍厚福医生在一艘从厦门驶来的船上发现了一名腺鼠疫病例,为防止瘟疫传入,这名患者被拒绝在温州登陆[25]。光绪二十八年,温州霍乱疫情大暴发时,瓯海关税务司李明良对港口采取了各种检疫措施,以预防霍乱病毒感染,并得到了官府的支持[26]。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于发现温沪线客班轮“广济”载有一患霍乱病的旅客进港,瓯海关首次对进港船舶实施卫生检疫。
(4)建醮祈祷。由于鬼神司疫仍是当时普遍的一种认识,所以建醮祈祷以驱瘟神的方法也常常为地方官所使用。如光绪九年(1883)秋,平阳瘟疫爆发“十室九染,甚至道途之中,死者相继”。该县缙绅联名禀请县令汤肇熙迎请泰山神温元帅,以驱逐瘟疫。汤肇熙同意并主持了温元帅、城隍地主等五神巡行街道的祭祀活动[27]。不论这能否起到实际的效用,至少仪式本身能够为民众提供一定的对抗疫情的信心。
此外,在出现疫灾时,开仓救济、免钱粮税等也都是官府救疗行为的一部分。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疫情面前的作为相当积极,包括施药救治、修建惠民药局,并采取措施避行隔离措施,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社会职能,在保全民众生命、抑制或延缓疫情的进一步扩散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2.社会力量和民众的救疗措施
瘟疫发生,在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社会力量和民众自身也会开展一些救疗活动,而且形式相对更为丰富。
在救治瘟疫方面,许多民间医生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如平阳名医包焕琳,熟谙《伤寒》 《内经》 《瘟疫论》 《瘟病条辨》等,尤以善治瘟疫最著名,在瘟疫流行之时,他“不避臭秽,料险诊治,活人无数”;泰顺名医徐志仁,擅眼科兼治儿科,当景宁天花流行时,凡有所邀,莫不不辞辛劳,徒步前往诊治[28]。
此外,还有人积极撰写医书宣传医学技术,或通过传单的形式宣传相关瘟疫的救疗之方。在霍乱的宣传和防治方面,陈虬功劳为最。光绪二十八年夏季霍乱盛行,陈虬以白头翁汤加减等方治疗,颇有效验,遂编此书,他辨析瘟疫霍乱,对其病因、治法等多所答辨。并于书后附方18 首用以治疗霍乱[29]65。陈虬对治疗霍乱的药物及煎药水的灵活运用,为后世防治霍乱等传染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霍乱的预防,陈虬虽然并未明确提出阻断传播途径这一说法,但其提出“切不可使病人之气,顺风吹入吾口,又须闭口不言”,足以表明陈虬已经认识到疫病可通过空气传播。他还提出预防空气传播的方法,可见其对阻断疫病的空气传播亦有一定的认识[30]。另外,平阳金乡徐淞生所著《霍乱主治述略》一书亦为清代温州霍乱疫情的疗治做出了贡献[29]572。
清代温州医学界在救治天花方面最大的突破是种痘术的推广,孙锵鸣于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关于种牛痘,孙锵鸣自述同治乙丑(1865)“习知西洋牛痘法良,外国盛行,而我温鲜有信者,习其术者尤少”,便邀请习知此术的永嘉名医谢文波为其家人试种牛痘,成功后又在温州推广,三年后,“牛痘法畅行”。宋恕也说:“初,温人未信种痘西法之善,莫敢先试,儿多荡焉。先生(孙锵鸣)独早深信,先试于家以劝州人,由是盛行,活儿甚众。”[31]白喉的预防与治疗,以陈葆善贡献最大。他编著《白喉条辨》并广为刊布,用于治疗温州地区严重的白喉疫情,效果非常明显[32]。《白喉条辨》汇集了先贤论治白喉的主要精华,正如陈葆善在自叙中说:“深悉张氏、郑氏,明修氏三先生之书,虽各有心得,实未能穷极源流也、于是潜心探索,汇集众长,证以经谊,参以阅历,迟之数年,作《白喉订正论》一卷。”[13]陈葆善首次明确提出了白喉证属燥火:“病属燥火无疑,唯间挟少用相火,少阴君火而发,不得不兼治耳。”[13]正如陈虬在此书序言中说:“秋燥之论,至本朝而始有定说,白喉之源,至吾院而始有专书。”[13]后人认为其创制三炁降龙丹,为论治白喉开辟一条新途径[33]。
鸦片战争后,英国内地会与偕我公会传教士相继来温州传教,开创了基督教新教在温州的理事,为了扩大教会影响,更有效开展传教工作,他们兴办新式医院,收治感染瘟疫的病人,一定程度上为温州瘟疫的缓解起了助力作用。在瓯海关《医报》中,经常能看到外国医生医治疫病病人的记录。如1894 年上半年霍厚福医生在偕我公会诊所里诊治了3 424个内科与外科病例,这些病例中的大多数都是腹泻、霍乱性腹泻、痢疾及疟疾等传染病患者[3]96。
此外,一些地方士绅也积极投入到防疫活动中,他们或响应政府号召,或枳极捐献财富,组织救治,是清代温州一股活跃的防疫、抗疫力量。乾隆三年(1738),温州暴发瘟疫,温州郡城人张瑞煌施粥赈济,有死於道者,施棺木以葬之,又买集云山暨沙奧旷地,以置义冢[34]761。道光十四年,温州大疫,孟澜清捐置义冢,掩埋尸骸千余具[34]745。这些士绅积极捐资助疫,在疫病善后处置工作中做出了积极贡献,有利于抑制疫情的蔓延。
在传统封建时代,医疗条件有限,绝大多数民众对瘟疫的认识和自我处置能力极其有限,很多时候几乎无能为力,在强烈的恐惧气氛下,祈求于神灵成为人们必然的选择。永嘉县瘟疫流行时,民间互相募捐钱财“建道场,作佛事一或三日,或七日”,以送瘟鬼[16]。这或许反映了民众无可奈何的期许,更是一种心理的安慰或治疗。瑞安人赵钧说,一有富室遭疫,则“每夜笙歌达旦,为鬼侑食,别治一室,罗列珍奇,极其雅洁。设一几于中,赌具都备,四面各堆白金数块,与鬼作由吾戏”。即使是贫困之家,“一祭亦需数金,每含泪典贷成其事”[35]。
另外,清代温州,民间已部分认识到隔离病患及消灭传染源的重要性,当疫情发生时,“感染瘟疫的人会被自己的近亲送到废弃的庙宇里隔离,只给他们提供一些简单的残羹冷炙”“人们开始尝试做一些诸如清扫房间、焚烧床和死人衣服等消毒措施。尸体被迅速掩埋或运到城墙以外很远的地方进行处理”[3]28。
由于地理环境、自然灾害及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原因,清代温州瘟疫呈多发性的特点,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虽然民间的有些防疫认识和做法在今天看来未免荒唐,但认识能力基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它存在于当时的社会自有其合理性,须客观看待。总体上看,在地方政府、民间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清代温州采取了积极的瘟疫救治措施,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疫病的发展和蔓延,其中不少措施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