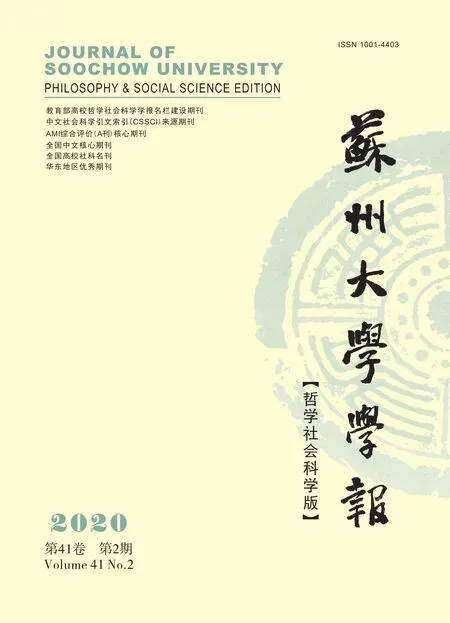水患与良田:嘉道间系列盗决黄河堤防案的考察
李德楠
(淮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黄河以善淤、善徙、善决著称,决徙地点集中于下游河段,故下游是堤防修守的重点。清道光二年(1822)两湖地区发生的谢同敖盗决州堤案中,湖广总督特别指出当地民间私堤,“非山东、河南临河大堤可比”[1]473,足见黄河下游堤防的重要地位。事实便是如此,清代重视黄河堤防的修治与管理,提出“防水之功,莫大于堤”[2]671,设有专门的河夫、河兵驻堤防守,规定每二三里设夫堡一座,派夫2名,每六七里或八九里设兵堡一座,派兵2名。[3]25册,1013还制定了严厉的防盗决的法律条文,“盗决河防,罪名綦重”[1]472。尽管如此,清代盗决黄河堤防的案件仍多有发生。[1]470-473那么,在“盗决河防罪的立法更为完善,而且得到了认真执行”[4]153的清代,沿黄百姓何以前赴后继冒死盗挖黄河堤防?决堤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历史上的黄河决堤案,引起了社会史、法律史、制度史等研究者的关注,尤其集中于影响最大的道光十二年(1832)江苏桃源陈端决堤案。陈锋关于漕运对中国古代社会消极影响的研究中,列举了桃源县决堤案的例子[5];张崇旺专门就桃源决堤案的发生,以及政府在案发后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做了全景式地扫描[6][7]631;饶明奇关于清代黄河流域水利法制的研究中,列举了盗决堤防的案例。[8]155不难发现,相比以往基于典型个案的社会史、制度史等研究而言,环境史视野下黄河系列决堤案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环境史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侧重探讨系统内人类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变化,是关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在黄河长期夺淮的影响下,下游地区灾患频发,“倒了高家堰,淮扬二府不见面”“一夜飞符开五坝,朝来屋顶已行舟”,是对这一地区最生动的描述。尤其乾隆二十年(1755)以后,整个河道进入了一个河床淤高产生决溢,决溢又进一步加重河道淤积,使之决溢频繁,尾闾问题更加严重的阶段。[9]285从嘉庆元年至咸丰初年开始时,决口地点都集中在曹、丰、沛一带,以后又向上游河南境内移动。[10]113鉴于此,本文以嘉道间系列盗挖堤防案件为研究对象,从环境史视角对其加以整体审视,希望有助于加深对黄河下游地区以水资源管理为中心的人地关系问题的认识。
一、系列决堤案的时空特征及根本原因
上文提到的桃源县陈端决堤案,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次盗决案件。该年八月二十一日夜,桃源县龙窝汛十三堡监生陈端、陈光南、刘开成及生员陈堂等湖内百姓,明目张胆驾船并携带鸟枪等器械,拦截行人,捆绑河堤巡兵,强行挖开了桃南厅于家湾黄河大堤。[3]36册,255清政府大为震惊,急派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江南河道总督等前往处置,对挖堤嫌犯从快从严惩治。首犯陈端于河堤被挖处斩首示众,从犯陈堂、张开泰、赵步堂判处绞刑,秋后处决。[1]473
除上述道光十二年(1832)桃源县决堤案外,此前自嘉庆九年至道光二年(1804—1822)的不足20年时间内,黄河下游还发生了其他四起盗挖黄河堤防的案件,决堤地点分别是河南考城和江苏安东、阜宁、睢宁。嘉庆九年(1804)八月,安东县百姓李元礼、郭林高及僧人木堂等,因黄水漫滩,田庐受淹,遂纠集众人盗决大堤,以图“进水肥田”,好在发现及时并很快堵口,才未酿成大祸。两江总督陈大文痛斥该行为是以邻为壑、损人利己,拟将首犯发往近边充军。案件上报朝廷后,嘉庆帝认为处理太轻,下旨将犯人李元礼、郭林枷号两个月,发配极边烟瘴之地充军。[3]36册,388
道光二年(1822)更是多事之秋,一年内发生了三次决堤案。该年五月,阜宁县监生高恒信、贡生张廷梓等,纠众30余人两次挖堤,强行将 陈家浦四坝堤工挖通过水,还持铁鞭围攻巡防官兵。百总杨荣趁机跳入水中脱身,呼喊河员兵役前来捉拿,事后将案犯充军发配。时隔不久,睢宁县百姓沈华锡等强抢河工物料,偷挖堤工,意图 阻挠开坝放水。事后,除勒令缉拿案犯外,还下旨将睢宁、阜宁两案合并办理,摘去睢宁知县冯立嵘、阜宁知县贺云举的顶带。[3]33册,651八月十二日夜,河南考城县百姓张孚等偷挖考城汛十三堡大堤泄水,兵夫拦阻不及,所挖之堤塌宽十余丈,堤北积水南流入河,幸亏大堤距河十余里,滩水才未漫抵堤根,形成缺口。后经守堤官夫连夜抢堵,三天后堵合断流。东河总督严烺严厉指出,黄 河以大堤为保障,万分紧要,岂能容大汛水长之 时妄行偷挖。并派知县庆熙将张孚等三人捉拿归案。[11]118
上述5次盗决黄河堤防的案件,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时间上呈不断增加的趋势,由嘉庆间1次增至道光间4次。这种现象绝非偶然,此前康雍乾三朝,“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前,对于黄河的治理还是比较重视的”[12]307。其间在靳辅、张鹏翮、齐苏勒、嵇曾筠等河臣的努力下,黄河下游堤防修守严密,未发生大的决堤水患。乾隆朝以后,国势日渐衰落,内忧外患不断,河政腐败严重,河官贪污成风,史称“嘉道中衰”。《水窗春呓》《栖霞阁野乘》等清人笔记中,均记载嘉道间河患最盛,亦最糜费。针对河务积弊,皇帝多次下旨,要求“严行惩办,以除积蠹而重河防”[3]28册,868。
空间上,决堤案件呈愈往下游愈多的特征,尤其集中于淮安地区。这与当时的河防形势是一致的,清代“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勤,糜帑之巨,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13]3770。靳辅《治河奏绩书》记载,河南开封、归德以下,“土地宽广,堤多者至四五重,无甚险”;而江苏徐州、邳州以下至云梯关,“险工栉比,几及五十”[2]772。河水携带大量泥沙,往往抬高河床,倒灌清口,梗阻漕运,淤积海口。又据铁保《筹全河治清口疏》记载,仅嘉庆七、八、九等年份,河底就淤高八九尺至一丈不等,清水不能畅出,黄河通塞靡常,变化不定。[14]2459
在清王朝严刑峻法的高压统治下,上述五次决堤案集中发生的原因有哪些?无疑与当时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因素分不开。
一是嘉道间堤防管理松弛、执法不严。堤防管理方面,虽然配备了大批夫役人员,但在岗守望者“仅止寥寥数人”[3]36册,258。平时大堤上常发生“拦截行人、捆缚堡兵”等违法行为,但守堤兵夫置若罔闻,“附近民夫并不齐集,邻堡兵丁并不趋护”[3]36册,338。道光皇帝大为恼火,指出“奸民盗决大堤,即系地方废弛之故”[3]36册,322,认为黄河大堤管理不善,原因在于“疏于防范”[3]36册,324。堤防立法方面,《大清会典事例·盗决河防》中明文规定盗决罪,不可谓不严:
凡盗决官河防者,杖二百,盗决民间之圩岸陂塘者,杖八十。若因盗决而致水势涨漫,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淹没田禾,计物价重于杖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徒三年。因而杀伤人者,各减斗杀伤罪一等……故决河防者,杖二百,徒三年。故决圩岸陂塘,减二等。
然而管理人员并未认真执行法律,松松垮垮的处罚手段,不足以阻止百姓的冒险行动,因此 盗决案件发生后,朝廷特别强调“秉公严讯,按 律问拟,毋稍宽纵”[11]118。甚至不得不临时加重处罚力度,例如桃源县决堤案中,朝廷要求“迥非盗决河防可比,必应严拿重办”[3]36册,303。自此至咸丰五年(1855)黄河北徙的30余年间,史籍中未见盗决黄河堤防的案件,究其原因,除相隔时间短暂外,也当与陈端决堤案执法力度加大的震慑力有关。
二是该地区水患多发,民风彪悍。嘉道时期,在自然和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出现了明显的生存环境全面恶化的趋势。[15]武同举《江苏淮北水道变迁史》中指出,嘉道50余年中,治河成绩远不及乾隆朝,其间黄河迭为祸患。邹逸麟关于黄淮海平原的研究中也指出,黄河下游河道淤废不堪,河槽与滩地高差极小,一般洪水年普遍漫滩,防御不慎,即行决堤。[14]102黄河决堤案多发的夏秋季节,正值黄河伏秋大汛,“河湖并涨”[11]119,动辄 影响数十州县。以淮扬地区为例,每当大水盛涨,民生不胜其累,张鹏翮《治河全书·请开支河》有载:
淮扬水患关系运道民生,淮安以南则山阳、盐城、高邮、宝应、兴化、泰州、江都七邑受害,淮安以北则清河、桃源、宿迁、邳州、睢宁、沭阳、安东、海州八邑受害。[16]660
水患长年不消,不仅眼前颗粒无收,还会影响来年的收成,对沿线百姓心理造成打击,“隐射生奸,偏重受累”[17]147,往往引发反抗情绪。该地区历来民风彪悍,“淮、扬、清江等处,向为盐枭出没之所”[3]38册,800。尤其地处黄淮运交汇的淮安府,是历史上水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社会基层民风剽悍,盗匪出没无常。[18]514上述桃源决堤案便是因为湖水大涨,“各村图宛在水中”,故陈端等百姓奋起求生,“起意挖堤”。[19]499
除以上诸条原因外,决堤的最根本原因当是为了放水淤地,改善土壤条件。一般而言,决堤泄水无非以下五种情况:一是泄私愤;二是排涝水;三是淤田地;四是利行舟;五是掩责任。第一种情况,一般是与“近堤之人有讐,而盗决以淹之”[20]476,但其做法损人不利己,故在官堤上较少发生;第四种情况主要发生在盐徒或商人身上,盗决阻碍通航的堤坝,“以图行舟私贩”[21]602;第五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官员身上,旨在掩盖低劣的工程或争取更多的经费,但操作难度及风险较大。按照《大清律例·盗决河防》的规定,河员如故意将完固堤工毁坏,希图借兴修侵蚀钱粮者,凌迟处死。
比较而言,第二、三种情况发生较多,且与普通百姓有关,“或因己田干旱,而盗泄以溉之”[20]476。嘉道间五次决堤案,均可归为这两种情况。嘉庆九年(1804)的安东李元礼案,乃因黄水漫滩,淹浸田庐,李元礼为避免河滩内“自有之田亩被淹,辄敢决堤进水”[3]36册,338。道光二年(1822)的张孚决堤案,是堤北百姓因夏秋久雨积水,“苦于田庐淹久,计图宣泄”[11]118。高恒信案是因“田被水淹”[19]663。道光十二年(1832)的陈端决堤案,是因黄水漫滩,淹浸田庐,希望“放淤肥田”[13]3739。可见,嘉道间堤防盗决案频发的根本原因,是事关百姓生计的田地问题,民众希望通过阻止开坝放水来保护耕地,或通过排涝水、淤田地来改良土壤。
二、良田变瘠土:河湖堤防与土壤环境
前已述及,嘉道间决堤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用黄河水改良土壤,这就涉及了土壤环境的问题。所谓土壤环境,是指地球表面能够为绿色植物提供肥力的表层。[22]3已有研究表明,自然水患往往造成土壤环境变化。黄河水患导致豫东地区土壤沙碱化严重,黄淮水患造成淮河流域排水不畅,土壤次生盐碱化严重。[23-26]除自然因素外,人为河工建设也影响土壤环境。“黄河以堤束水,土工乃其根本”[11]769,挖土筑堤、堵口压埽等需动用大量土方,往往对土壤环境带来影响。
其一,黄河筑堤压埽等工程建设,常占压或挖废大片耕地。黄河堤防建设用土量极大,例如修筑清河县至云梯关间95 400丈的堤坝工程,每丈用土60方,共计5 724 000方。高良涧大堤垫高3尺的工程中,用土量142 500方。[2]691即便堵口压埽这样的工作,也需要大量土方,谚曰“下埽无法,全凭土压”。而且,工程建设对土质有较高要求,多需采用老淤土,即多年淤积的胶土,由于它经过风化,质地柔软,使用起来很方便。[27]18为满足工程对土质的要求,大量随耕地田亩被挖废。乾隆《重修桃源县志》卷3记载,康熙三十九至四十年(1700—1701),桃源县筑堤挖废田地177顷48亩。又据《阿文成公年谱》卷27,乾隆间大学士阿桂奏称,兰阳、仪封、睢州、宁陵、考城、商丘六州县被占压挑废地亩共计572顷49亩。
河工取土地点,多为堤旁数丈外百姓耕种的熟地,而耕地乃沿黄百姓身家性命所系,故“每逢取土,遭多方挠阻”[28]15冊,755。为减少引发官民冲突,朝廷决定兴建工程时,往往以是否损坏淹没民田作为开工条件[16]640,要求限定取土地点,毋掘房基、毋掘古塜、毋刬膏腴。还采取措施蠲免被挖废田亩的赋税,雍正《河南通志》卷21记载,雍正初年豁除仪封县临河被挖伤的地亩20余顷。雍正七年(1729)免除虞城县开河占地6顷73亩,考城县开河占地260顷96亩;乾隆《淮安府志》卷12亦载,雍正八年(1730)蠲免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五年间山阳、清河等八州县挖废田地的地丁银米,又蠲免大河卫、桃源县挖废屯田及栽柳废田银两。又据乾隆《江南通志》卷66,雍正十二年(1734)江苏巡抚高其倬奏请将山阳、阜宁、清河、桃源、宿迁、安东、高邮、宝应八州县挖废田地428顷61亩,自雍正六年起至十年止,悉数蠲免。
其二,许多涝洼地的形成与堤防建设有关。堤防工程完成后,或由于土地挖废而形成洼地,或由于河床抬高导致水位上升,一些田地沦为涝洼之地。例如,江苏桃源县陆、吴两乡,坐落于洪泽湖北岸,有粮田2 700余顷,因沿堤加高一丈,致岁岁淹没,最终沉入水底。[29]554因此,为确保河工不出问题,黄河滩地堤堰不许自行培筑。取土地点须于数十步外,筑堤取土时要求取外滩,河水涨淤后,可填平土塘。如果背河取土,则积水成塘,易伤堤身,甚至堤坝冲决,祸害农田。
其三,背河洼地长期排水不畅,易造成土壤肥力退化。低洼的堤外滩地,因排水不畅而潴水,往往形成背河洼地。背河洼地因长期受黄河侧渗的影响,以及洼地两侧地下水汇集,往往形成涝灾和不同程度的盐碱[30],其土壤特点是瘦、盐、冷、板、浸。[31]洼地常年积水或季节性积水,是盐碱地、沼泽地集中发生的地区,长时间无法耕种,仅能生长一些盐蒿、碱蒿和芦苇等耐碱植物。豫东中牟、阳武、封丘等县白气茫茫,远望如沙漠,“有水去沙停变为沙滩者,有地土变为盐碱者”[3]7册,451。苏北安东县“田滨河海,岁罹水患”,淮徐一带低洼地亩多被迫“改种芦苇”。[3]17册,195直到今天,黄河故道滩区河槽及大堤内外,多为故黄河所遗留的沙土、两合土、淤土、盐碱土,土壤肥力相对较差。[9]10
三、水资源处置:泄水涸地与放淤肥田
黄河堤防建设对土壤环境有多重影响,或造成水患,或带来良田。筑堤挡水可使昔日湖荡涸为良田,增加土地面积;加高堤堰容易形成背河洼地,导致堤外耕地涝洼;筑堤取土可造成耕地被挖废或占压,良田变为沮洳之区;堤坝还可用于控制水流,用以泄水涸地或放淤肥田。
其一,泄水涸地有助于及时排泄低洼涝水,改善土壤环境和保证生产生活。明万历年间,徐州至淮安间堤工完成后,黄河畅流入海,“沮洳淹没之处遂多为野,而称可耕可获之田”[32]453。康熙九年(1670)御史徐越奏称,归仁堤小河疏通后,灵璧、睢宁、宿迁积水得以宣泄,“沮洳渐成沃壤”。康熙间靳辅建议多开闸坝涵洞,希望“洼下之地藉减水而得以淤高,久之而硗瘠沮洳,且悉变而为沃壤”[2]731。康熙二十六年(1687)秋,桃源县徐升滚坝关闭后,萧渡、杨庄、七里沟、新庄洼地“变沮洳为沃壤”[28]29冊,267。康熙四十二年(1703)皇帝南巡,命张鹏翮坚闭六坝,广辟清口,于是“堰以东之沮洳之地,复为膏壤”[16]590。
其二,利用黄河泥沙淤地肥田,是泥沙处理和利用的有效途径。黄河泥沙来自黄土高原的肥沃表土,被地表径流侵蚀而带入河水中,含有一定的养分,可溶盐含量低,泥沙沉积后即可耕种,对治碱改土和增产效果显著。[33]169利用黄河放淤,能将河湖低洼沮洳之所,淤成膏腴熟地。郭起元《介石堂水鉴》卷3《放淤说》中介绍了具体做法:
仍酌量遥越远近,地势宽窄,并测地面与水面之高下,择其背溜、拖溜处所,将缕堤开挖倒勾沟漕,或二三道,或四五道,俾黄水灌入,令其停淤,清水流出,仍归大河。
黄河堤防有淹浸良田和放淤肥田的双重作用,但清代河臣对后者持谨慎态度,不敢轻易决堤放淤。仅利用涵洞泄黄放淤,放淤时多选无溜地点,从上口灌入,下口放出,每年可淤高三四尺。[34]634例如,张伯行建议黄河南岸多开减水坝,泄黄水入洪泽湖,可淤平湖地。[21]595刘成忠《河防刍议》中建议于圈堰之地内外设涵洞,从闸洞放水至平地,数年之后,斥卤可变为膏腴。
很显然,清代官员以治河保运为首要任务,不敢轻易破堤引黄放淤,即使放淤,也是为了加固堤防,不是肥田种地。这种情况下,以食为天的百姓只能通过“盗决”来实现引水放淤。道光十二年(1832)的桃源县盗挖黄河堤防案,便是百姓引黄“放淤肥田”,“希图地亩受淤”的冒险行动。据事后勘察,桃源县境内有48图分隶黄河南北两岸,南岸堤内20图均系民田庐舍,本来距骆马湖边尚远,只因连年湖水涨漫,多被淹没,水退时始得重新安居,百姓深以为苦。[19]663桃源县监生陈端等湖内百姓,因各家有多顷地亩濒临湖边,土地夹在黄河与骆马湖之间,湖河环绕,地势低洼。此前这一片滩地为粮田,岁有收成,后因修筑湖堤,低田被淹浸。尤其道光十一二年间(1831—1832),河湖水面涨至2丈1尺以上,“滩上田地,遂成巨浸”,面对前所未见之黄水大灾,陈端等挖开了黄河大堤,结果确实达到了放淤肥田的目的。据林则徐《将挖堤案犯解交穆彰阿陶澍审理折》记载,该处三四十里以内,滩田均已受淤,较未淤以前高出五六尺至丈余不等,地亩受淤之处已成膏腴之地。但由于引发黄水倒灌洪泽湖,危及运河水柜,决堤者付出了惨痛代价。
四、结语
综上所述,嘉道间发生的系列盗决黄河堤防案,是民众私自改良土壤环境的灾难性事件。案件的发生固然与堤防管理松弛、执法不严、民风彪悍等有一定关系,但根本原因在于生存环境的恶化。水患与良田之间隔着一道黄河大堤,堤防建设对土壤环境具有双重影响,既易造成土壤环境恶化,又具有淤地肥田的作用,故百姓不惜冒险决堤,希图通过排涝水、淤田地来达到改善土壤的目的。
治黄保运的水资源管理手段,贯穿决堤案发生和处理的全过程,反映了以堤防为中心的人地冲突以及民众生计与国家水利的矛盾。乾隆以前,该地区人地关系相对缓和,盗决案虽有发生,但影响有限。嘉庆以后,河工废弛,腐败严重,人地关系日趋紧张。至咸丰五年黄河北徙山东以后,漕运废止,河工治理减少。此时距陈端决堤案时间不远,震慑力仍在,故未见决堤案的记载,但并不能说明人地关系得到改善,后来1931年的江淮大洪水,再次表明该地区在大灾面前不堪一击。
决堤案的解决是以牺牲地方和个人利益为代价,服从于国家水资源管理的需要。虽然清政府河工治理中常提及民生,称“运道民生,惟堤是赖”,要求“捍御泛滥黄流,保护运道民生”,但实际上是重运道,轻民生。[35]273陈端决堤案的处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洪泽湖是实施蓄清刷黄的关键,清水不足会阻碍漕运,故清政府认为陈端决堤是“希图不可必得之微利”[3]36册,337,强调造成“全黄入湖”[1]473的严重后果。相反,如盗决黄河以外的堤防,惩罚力度则要小得多。例如道光七年(1827)沧州高三洛盗决减河堤防案,同样是灌水淤地,虽然导致十余村庄田禾被淹,但事后首犯仅杖一百,徒三年。[1]470可见国家利益是水利建设活动的出发点,民众处于被动地位,所谓“运道民生”更多时候是官方的一种姿态。以史为鉴,水利工程建设中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尽可能减少给环境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事关百姓生计的土壤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