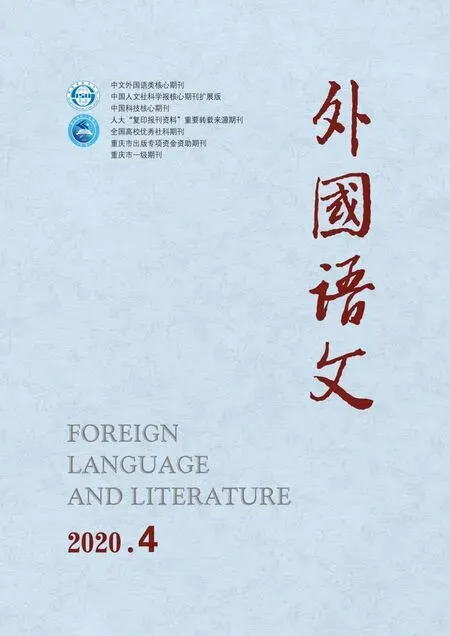《爵士乐》中的非自然叙述者及其非自然叙述行为
赵莉华
(西华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2019)《爵士乐》(Jazz)的叙述者神秘、矛盾、变化多端,令人捉摸不透。自1992年该小说发表以来,其叙述者就一直让学界困惑。菲利普·佩奇(Philip Page)认为其既无所不知,又限知,既可靠,又不可靠(1995:61-62)。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认为叙述者轻松而坦率地从无所不知的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滑动“重新定义了叙事视角可能性” (1993:54-55)。宝拉·格兰特·艾卡德(Paula Gallant Eckard)从《爵士乐》与爵士乐的个体与集体融合共性中推断叙述者是一种爵士乐叙述者,代表爵士乐,为爵士乐代言(1994:13)。梅兰妮·安德森(Melanie R.Anderson)在其《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幽灵》(Spectrality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中把《爵士乐》中身份流动而不确定且具有创造性的声音确定为幽灵。艾伦·芒顿(Alan Munton)认为《爵士乐》幽灵一般的叙述者讲述了被忽略的故事,让读者听到了遗失了的黑人声音(1997:250)。莎伦·杰西(Sharon Jessee)强调叙述者的无所不知、无处不在,认为叙述者是女神(2006:143)。卡罗琳·罗迪(Caroline Rody)也讨论叙述者鬼魅一般在场却又不在场,似人而非人,亲密而又陌生的矛盾特点,她认为“通过人格化全知叙述,《爵士乐》把叙述重塑为人的渴求场域” (2000:625)。在罗迪那里,叙述者是一种渴求主体,他/她渴求关系,渴求社区,呈现与人交流的女性主义式渴求以及回归族群集体讲述的渴求。有些学者从小说开篇的八卦风格推测叙述者是女性(Lesoinne,1997:152)。麦克·伍德(Michael Wood)注意到叙述声音的滑动,认为其人格有几次变化,故事开头喋喋不休的叙述者逐渐变成了理论家(Lesoinne,1997:152-3)。上述论者大都只抓住问题的某一侧面,没有对叙述者的神秘、矛盾及变化等特征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其判断也就流于印象。那么,《爵士乐》叙述者到底有些什么特征让评论界如此困惑?他/她到底又是谁呢?莫里森如此设计又有什么目的?下文即拟以非自然叙事理论框架,分析《爵士乐》中恼人的叙述者,回答上述三个问题。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本文认为,以非自然叙事理论框架来看,叙述者的神秘莫测源于其既在又不在、既全知又限知、既权威又不可靠、过去时和现在时随意滑动以及同一事件的多种叙述等非自然特征及非自然叙述行为。传统叙事学以模仿理念为基石,认为叙事模仿现实,虚构人物类似现实世界中的人,具有现实世界中人的各种局限,虚构叙事讲述类似现实世界中的故事讲述,属交流行为,具有现实交流行为的各种局限。从叙事实践来看,无论是传统叙事,还是后现代叙事,都充斥以模仿逻辑来看不可能的叙事现象。经典叙事学没能将这类违背模仿逻辑的不可能叙事现象纳入阐释范围,而后经典叙事学对边缘叙事现象的重视以及后现代叙事文本中大量出现的不可能叙事则催生了阐释这类现象的叙事学分支——非自然叙事学。以阿尔贝(Jan Alber)为首的论者从读者认知角度出发,认为“非自然”是指在物理法则、公认逻辑及人类属性上不可能的事件、场景、特征等(2009:80)。非自然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新的研究热点,自21世纪初诞生以来,其理论建构成果已经比较丰富,但国内外相关批评实践还严重不足。运用非自然叙事理论框架分析莫里森的《爵士乐》,从新的角度尝试揭开其叙述者神秘面纱,一方面丰富莫里森小说研究,促进文学批评多元视角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抛砖引玉,促进非自然叙事批评实践发展,同时以批评实践佐证、补充非自然叙事理论框架,推动其发展。
《爵士乐》叙述者违背现实物理法则的空间位置及存在状态是其第一个非自然特征。从叙述者与小说人物及场景的关系来看,叙述者仿佛身处故事世界,但对故事世界的人物来讲,他/她又隐身不见。“嘘,我认识那个女人……我也认识她丈夫……”(莫里森,2006:2)“嘘”和指示代词“那个”所传递的亲密语气给人以圈内人八卦的感觉,从修辞效果来讲,让读者感觉叙述者身处该社区,是该社区的一员。而叙述者对大都市的描绘也让读者感觉叙述者身处故事空间:
我为这大都会发狂。日光斜射,像刀片一样将楼群劈为两半。在上半块,我看见一张张面孔,很难说清楚哪些是真人,哪些是石匠的手艺……当我沿着河岸的一块块青草地望过去,看见教堂的尖塔,看见公寓楼奶油色和紫铜色的大厅,我才觉得踏实。(原文为“strong”,笔者认为译为“强大”更合适)是的,很孤单,但高高在上,牢不可破。(原文为“indestructible”笔者认为译为“不可摧毁”)(莫里森,2006:5)
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叙述者不仅身处作为故事世界的大都市纽约,而且好像漂浮在大都市上空,至少位于能俯瞰全市的最高点。此外,叙述者的行动也显示其在故事世界的物理存在事实:他/她“透过门窗观察他们,抓住每一个机会跟踪他们”(莫里森,2006:234)。
问题在于,虽然叙述者身处故事世界,“仔细观察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赶在其他人之前猜出他们的打算,他们的动机”(莫里森,2006:6)。他/她却未跟任何人物有过交流,也没有任何人物见到过叙述者,提到过叙述者。当叙述者不指称自己的时候,叙事跟故事外叙事没有任何区别。不仅如此,叙述者虽然跟踪观察每一个人物,在大都市徜徉,但却好像没有实体存在。“我没有肌肉块,所以我不能当真指望自己保护自己。可我知道怎样多加小心。主要一点就是保证不让任何人完全了解我。”(莫里森,2006:6)“我在自己的头脑中生活了好久,也许太久了。人们说我应该多跳出来一些,调剂调剂。我承认我跟外界挺隔绝的。” (莫里森,2006:7)正是这种在又不在的非自然状态导致了论者们把叙述者解读为幽灵或者神。
《爵士乐》叙述者第二个非自然特征是其不可能而又矛盾的能力。第一人称叙述者有时候无所不知、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有时候又怀疑、否定自己的无所不知,甚至质疑自己的不可靠,以模仿逻辑来看,既超越了人的认知和能力局限,违背了时空物理法则,也违背了公认逻辑。叙述者了解乔、维奥莱特、多卡丝等主要人物的内心活动,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能力,是已经常规化的非自然叙述——全知。叙述者不通过任何旅行,不通过任何转述,就能观察人物在大都市各个地方(包括私密室内)、弗吉尼亚乡下以及巴尔的摩的活动,叙述者能直接观察和讲述乔和维奥莱特小时候的生活,直接观察和讲述几十年前乔的母亲黑女人的活动,直接观察和讲述维奥莱特的祖母与戈尔登·格雷的渊源,直接观察和讲述黑女人与戈尔登的相遇等等。即便有时候这些活动时间重叠,也不影响叙述者的直接观察和讲述。叙述者的信息全知和时空全能违背了人类所具有的认知局限和时空局限,以阿尔贝的非自然定义来看,属于非自然现象。由于全知叙述者普遍运用于小说创作实践,读者已经习惯这种非自然现象,就阅读体验来讲,这种非自然已经显得自然,用阿尔贝的话来说,这是已经规约化了的非自然现象。
关于叙述者的能力,读者体验仍然非自然的情况是,貌似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又多次否定自己的全知能力,叙述者多次表示“我不敢说”,“我不知道”,“我纳闷”,“也许”,“我怀疑”,“我猜”,“我也不知道”。他/她甚至直接坦白自己不可靠:“我真是又粗心又愚蠢,等我(再一次)发现自己有多么不可靠,我简直是怒不可遏。”(莫里森,2006:169)“他们知道我有多么靠不住;知道我那全知全能的自我是多么可怜、可悲地掩盖着自己的软弱无能。知道我编造着有关他们的故事的时候——自以为干得漂亮极了——完完全全被他们攥在了手心里,无情地操纵来操纵去……”(莫里森,2006:234)“我把事情完全搞错了。”(莫里森,2006:234)从小说实践来看,全知叙述者可以选择全知视角,也可以选择有限视角,也即透过特定人物视角看故事世界,但其全知能力不受影响,而《爵士乐》叙述者上述这些对自己认知能力的怀疑和否定指向的不是其所选择的有限视角,而是其限知能力,限知能力与前述全知能力相互矛盾,属逻辑上不可能现象,体现叙述者又一个非自然特性。
《爵士乐》叙述者讲述时态在现在时和过去时之间自由、任意滑动,违背了一致性逻辑和时间物理法则,是其非自然叙述行为。叙事规约一般假定叙述者所讲故事已经发生,保罗·利柯(Paul Ricoeu)在《时间与叙事》中就强调 “叙述者讲述的事件已经发生”(Harvey,2006:73),费伦(James Phelan)从修辞叙事角度定义的叙事同样肯定了这一观点:“叙事是指某人在特定场合出于特定目的向某人讲述所发生的某事。”(詹姆斯·费伦,2002:172)因此,以叙事交流理论来看,作为报道的小说叙述的自然时态应该是过去时。凯特·汉伯格(Käte Hamburger)断言“过去时是虚构叙事的时态”(Harvey,2006:73),弗莱西曼 (Suzanne Fleischman)也认为“作为信息报道模式的叙事,其典型的时态就是过去时”(刘江,2011:52)。而现在时叙述则暗含事件的发生和讲述同时进行,按照时间物理法则属不可能现象。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在时小说越来越常见,读者对现在时小说也逐渐习以为常。尼尔森讨论非自然常规化叙事形式时就列举了第一人称现在时这种现象,他认为现在时小说越来越多,读者因此越来越熟悉第一人称现在时形式,在某些程度上甚至注意不到时态的特别之处(Nielsen,2011:85)。哈维也提到现在时小说的普遍性问题:“现在时运用已经相当广泛,不再具有实验性了。”(Harvey,2006:74)或许正因为这一原因,还没有学者深入讨论《爵士乐》第一人称现在时叙述。
虽然《爵士乐》的现在时态讲述不会引起读者过多注意,但其现在时与过去时之间自由、任意的转换则令读者迷惑,是叙述者的非自然叙述行为。根据弗莱西曼的现在时理论,《爵士乐》有两大现在时时间框架,一类是“故事现在”(story-now),也即事件发生的当下,一类是说者现在”(the speaker’s present)(刘江,2011:52),即叙述当下。当叙述者自我指涉,表述一般情况或者叙述当下时,一般使用现在时,比如在《爵士乐》中,叙述者常常说“I know””I see”“I wonder”等。这种策略给读者以讲述者直接面对读者,进行讲述的感觉,这种现在时强调叙述动作的即时感,显得更加生动、亲近,就叙述动作来讲,模仿的是现实世界的讲述行为,属于自然叙述。《爵士乐》叙述者后期指涉前期叙述时间时,使用了过去时,以表示叙述者观点、看法和行为的前后变化,也是自然讲述行为。
非自然的情况主要体现在故事时间,如前所述,按照叙事规约,叙事所讲述的故事已经发生,其时态一般应为过去时。而《爵士乐》有时使用现在时,有时使用过去时,而且没有规律可循。从时间上来看,现在时并非出现在故事时间的某一特定点或者某一段特定时间,几十年前的事件叙述有时运用现在时,有时运用过去时;近期事件讲述有时是过去时,有时是现在时,讲述多次重复事件或者人物习惯的情形时也是既有现在时,也有过去时。此外,时态的转换好像也跟讲述者身份关联没有任何关联,不管叙述者是否自我指涉,都有过去时和现在时情况。一句话,小说故事讲述的时态选择和变化毫无规律,无章可循。
而最令读者抓狂的时态转换发生在同一事件,甚至同一句子,从语法角度来说没有任何转换理由。例如:“He minds her death,is so sorry about it,but minded more the possibility of his memory failing to conjure up the dearness.” (Morrison,1992:28)这里 “mind” 和”minded”都是同一语境中乔发出的动作,从上下文无法看出两个动作的过去和现在时间差,至于为何一个使用现在时形式,另一个使用过去时形式,很难解释。另一个例子:“As though there never was a time when they didn’t love it.The minute they arrive at the train station or get off the ferry and glimpse the wide streets and the wasteful lamps lighting them,they know they are born for it.”(Morrison,1992:33) 这段话讲述乔和维奥莱特多年前从乡下迁徙到大都市的情况,他们到达、下车和瞥见的动作发生在几十年前,叙述者本来运用很自然的过去时讲述,但突然毫无理由转换成现在时,而且“arrive”“get off”和 “glimpse”三个瞬间动词不能表示习惯或者一般状态,没有理由使用现在时。再看下一句:“ Lying next to her,his head turned toward the window,he sees through the glass darkness taking the shape of a shoulder with a thin line of blood.Slowly,slowly it forms itself into a bird.” (Morrison,1992:224)动词“turned”和“sees”是乔在同一语境的两个连续动作,没有理由使用不同时态,但是叙述者却进行了时态转换。这些无法解释的时态转换违背了语法一致性原则和时间法则,也是一种非自然现象,是叙述者的非自然叙述行为。
另外,叙述者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相互矛盾,违背了故事线性发展的公认逻辑,其叙述行为属于非自然。戈尔登与黑女人的相遇事件有三个不同版本,按照现实故事发展逻辑来看,属于不可能现象。三个版本分别以“我看见”和“我喜欢把他想成那样”和“我知道”引导。梅兰妮·安德森提到过这一现象,不过她认为只有两个版本,而且认为同一事件两个讲述版本是叙述者是幽灵的又一证据(Anderson,2013:106)。薇罗尼卡·勒桑尼的讨论稍微详细一点,她认为第一个版本的声音赤裸、实事求是,听上去冷漠、客观、男性化,第二个版本开场的“喜欢”二字会引起读者对叙述者的可靠性的警觉,“我们会因此衡量这个版本与第一个版本相比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抑或叙述者是否在刻画一幅他/她想要在想象中保留的画面”(Lesoinne,1997:153)。勒桑尼认为莫里森引入这一疑惑,目的是让读者思考叙述者这一角色以及反过来读者怎样回应人物及其背后的动机。
勒桑尼准确抓住了两个版本中讲述声音的主客观立场,也关注了这种策略与叙述者角色之关联。遗憾的是她没能分析两个版本在内容上和叙述策略上的本质差异,并透过差异挖掘其背后的原因。我们认为,第一个版本重点集中在戈尔登的种族主义意识。戈尔登的一言一行、所思所想都表现出对黑女人身体的恶心感觉。“她的脚碰到了他的一只非常漂亮、只不过沾满了泥巴的靴子。他希望她歪着的方向不会变,尽管他对那只碰到他靴子的脏兮兮的光脚丫子无可奈何,他要是再挪动她,她可能会突然倒向他这一边……他赶着马,动作很轻,生怕车辙和泥泞的路会搞得她向前倒去或是稍微蹭到他一点。”(莫里森,2006:153)由于种族主义偏见,白皮肤的戈尔登无法忍受自己的身体被黑女人触碰,连脏靴子被黑女人碰到也让他烦心,遮盖过黑女人的衣服“算是永远毁了”(莫里森,2006:155)。此外,戈尔登眼里的黑女人远远没有他的马(动物)重要,到达猎人小屋之后,戈尔登首先照顾他的马,仔细给它擦洗,花了很长时间,四处找水和饲料。然后安置行李,最后才不得不把受伤、昏迷不醒、快要临产的黑女人搬进小屋。
第二个版本重点在戈尔登的外在行为。他“笔直地坐在马车里”(莫里森,2006:158),叙述者没有交代这种坐姿跟黑女人有何关系,没有提到黑女人的脚,只提到戈尔登两只靴子之间的水洼,没有提到戈尔登驾车的小心翼翼及其背后的动机,没有提到前一版本中戈尔登眼里那(因身边坐了黑女人而显得)特别漫长的一小时路程。这一版本重点在自然描写,树叶、松鸡、松鼠、马、蚊子,仿佛戈尔登在聆听自然,观察自然,享受自然,身边的黑女人没有给他造成任何困扰。戈尔登对自然的着迷甚至让他一时忘记了自己的目的。“他听得太仔细了,都没看见石头上竖直刻着维也纳字样的一英里标记,他走过了它。” (莫里森,2006:158)第一个版本中戈尔登的父亲被称为“那个黑鬼”“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莫里森,2006:156),第二个版本称“父亲”……所有这些,都表明叙述者所“喜欢”或者所偏爱的这场相遇应该是一场没有种族偏见的相遇。问题在于,这只是叙述者的主观愿望,并非真实情况,戈尔登的种族主义内心世界可以隐藏,但他的行动却无法隐藏,到最后叙述者不得不跳出来:“就是那个让我为他着急。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衣服,而不是那个女人。他检查了行李绳,而不是她的呼吸。这简直太过分了。” (莫里森,2006:159)
实际上,除了勒桑尼注意到的两个版本之外,论界普遍没有注意到的是,莫里森还偷偷安排了第三个版本。这一版本中,叙述者用自由直接引语记录了戈尔登的内心独白,用戈尔登自己的语言讲述了这次相遇:“没有恶心。我没觉得恶心。看哪,这儿,这事是如何毁了我的外套,弄脏了一件你再也找不出第二件的衬衫,而且没法再洗了。我有一双小牛皮做的手套,可我没有戴上它们来扯起她,抬动她。我是用我自己光着的双手做的……我一进屋就把她放在木头帆布床上,因为她比看上去要重……” (莫里森,2006:162)但是,叙述者“知道”这并不可能,因而直接出面,对戈尔登的种族主义意识和虚伪进行了评价和批判。“我知道他是个伪君子……他在撒谎,他这个伪君子……他在撒谎,这个伪君子。他满可以打开他那胖胖大大的行李箱,从两条手工刺绣的床单中拿出一条,哪怕是用他的更衣袍给那姑娘盖上。他还嫩着呢。太嫩了。他以为他的故事很棒,如果讲得恰如其分,他的诚心诚意、他的光明磊落会给他父亲留下深刻印象。可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想为这次巧遇吹牛,像一个游侠骑士那样吹嘘自己是多么冷静……”(莫里森,2006:163)
需要强调的是,三个版本最终传递的种族立场完全一致,都力图告诉读者戈尔登有种族主义偏见,区别在于策略不同。第一个版本的策略是完全隐去叙述者“我”的主观判断,“我”不做任何评价,只是透过内聚焦刻画戈尔登的内在情绪和情感,其中所暗含的种族主义意识需要读者自己分析判断。第二个版本使用了外聚焦,读者只能看到戈尔登的行动,无法了解其内心,也就无法透析戈尔登的种族主义意识,因此,“我”不得不跳出来进行直接评价,告诉读者戈尔登先照顾马而不是人背后的种族主义动机,直接向读者传递其看法。第三个版本没有聚焦戈尔登的内心世界或者外在行动,而是以内心独白的形式赋予戈尔登声音,让他讲述该事件,当然这种讲述不一定反映了他的真实情绪、情感,只是他对该事件的呈现,同时与之对立的是叙述者“我”的声音,两个声音都带有主观色彩,读者就面临哪一个更可信的选择。不难看出,第一个版本中隐含作者隐藏于人物内心活动的看法等同于第二、三个版本中“我”直接表达出来的看法。也就是说,这里的“我”的立场等同于隐含作者的立场。
那么“我”是不是隐含作者呢?“我”是不是处于创作状态的作者——文本的创作者呢?实际上,莫里森多处提到了“我”的创作者身份。“我”坦言:“他(戈尔登·格雷)这个人我琢磨了很多。琢磨特鲁·贝尔和维奥莱特爱的是否是他,还是他那虚荣、神气活现在意自己外套和背心上的象牙扣子的窄鼻子。跑那么远的路去侮辱他的父亲和他的种族。”(莫里森,2006:142) “我”对人物的琢磨其实质就是创作状态的作者的构思过程,三个版本呈现的就是这一过程。“我”也自称“好奇、有创造力而又消息灵通”(莫里森,2006:145)。再者,小说的第一句话(“I know that woman”)实际上是顺着作者在伴随文本《序言》中的创作状态中作者的声音“我了解这个女人(‘I know that woman’)……”写下来的,“我了解这个女人,我知道她裙子的尺码……’于是我写了这些,毫不费力,从未间断,玩味,只是玩味者那个声音,甚至不考虑‘我’是谁,直到叙述者看起来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能够——愿意——与创造、即兴创作、变化的过程并行和开始介入。发表意见、评判、冒险和学习。”(莫里森,2006:ⅣⅤ)《序言》中的“我”和正文中的“我”一脉相承。种种证据表明,“我”就是隐含作者。那么,如果我们把“我”阐释为隐含作者,其在故事世界的物理存在是否能够合理阐释呢?是否能合理阐释前述“我”的非自然特征及非自然叙述行为呢?莫里森这种安排又有何种含义呢?
如果说“我”是隐含作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她实实在在出现在故事世界的问题。隐含作者是韦恩·布思(Wayne Booth)提出的概念,是指处于创作状态的作者,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作者。处于创作状态的作者,其实体存在于现实世界,不可能实实在在出现在虚构世界。但叙事实践尤其是后现代叙事实践中却有很多这类现象,热耐特对此的解释是跨层(metalepsis也译为转叙、错层),热耐特从修辞学发掘出metalepsis的虚构内涵,用作者跨层(author’s metalepsis)来解释狄德罗(Diderrot)著名的“谁能阻止我让主人结婚并给他戴上绿帽子呢?”从作者跨层,热耐特发展出叙事跨层(narrative metalepsis),用以解释“虚构世界或者叙事层的边界逾越”(Kukkonen et al.,2011:2)。叙事作品中,作者(准确地说是隐含作者)和人物的边界逾越都可以称为跨层。科恩(Cohn)区分了故事层的跨层和话语层的跨层,后一分类只在文字媒介叙事中适用。瑞恩(Marie-Laure Ryan)根据边界逾越的程度,区分了本体跨层和修辞跨层,但瑞恩的定义不太严谨,她分别以两个隐喻“通道(passage)”和“小窗(small window)” (Ryan,2006:207)来定义本体跨层和修辞跨层,以强调两种跨层的区别在于本体层面的异质世界的侵入程度,而程度和隐喻作为区分标准在实践上很难操作。根据边界逾越的方向,可以分为向上跨层、向下跨层和水平跨层。(Pier,2005:304)。跨层概念虽然产生于几十年前,但其影响力一直不大,直到21世纪初非自然叙事学兴起,其非自然特性才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逐渐增多。根据瑞恩的定义,《爵士乐》中的隐含作者跨层是本体跨层。跨层的隐含作者本体上不属于故事世界,她的任务就只是创造和观察该世界,可以解释她在故事世界既在又不在的状态。
叙述者的其他几种非自然特征和叙述行为也能够以跨层的隐含作者进行合理阐释。全知和限知能力矛盾,全知是指作为作品的创造者,她对作品中的人和事有绝对权威,而限知则一方面是隐含作者承认自己作为作家的局限,另一方面展现作家创作过程的探索。可靠与不可靠的非自然特征展现的则是隐含作者凭经验对人物和事件的预测和判断与人物、事件自主发展之间的不完全对等情况,也体现作家对刻板思维、成见和套路的警醒。莫里森透过这种安排,表达了她的人物塑造观:创作需要建立在作家的经验之上,同时也需要让人物自主,这样才不会落入俗套。故事时间的时态转换可以解释为全知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之间的转换。故事现在时讲述与动作的即时感关联将动作与作家的创作自我关联,突出隐含作者的即兴创作,这正是莫里森在《序言》中强调的创作目的之一,其即兴创作特征更通过书名直接点名。尼尔森也谈到过第一人称现在时叙述的功能是强化该叙述不是报道,虽然其目的是佐证其非人格声音概念。但他也肯定现在时指向的创造功能,只不过他认为是话语创造了故事世界,不是隐含作者跨层进入故事世界进行即兴创作。考虑到跨层概念的生僻及尼尔森反对叙述者概念的立场,这种阐释还是可以理解。当作家的创作自我把声音交还给全知叙述者时,时态又转回过去时。通过时态的任意转换,莫里森向创作者和读者展现创作过程中隐含作者与全知叙述者之间的随意滑动,提醒创作者和读者区分两种声音和视角。而通过同一事件多个版本叙事,莫里森讨论的是隐含作者对聚焦策略和叙述声音策略的选择。是外聚集还是内聚焦?声音赋予叙述者还是人物?隐含作者隐身?还是侵入故事世界?不同的策略,同一个目的,哪一种更能有效传递隐含作者的立场,让读者信服,相信读者通过比较上述三个版本就会有明确答案。
正如麦克·伍德注意到的那样,《爵士乐》的叙述者“我”确实是理论家,她是小说创作理论家。以创作实例,莫里森传达了她的小说创作理念。“我写过的几部小说,其结构是为了增强意义而设计的;而这回,结构就是意义。这样做的挑战是揭穿和埋葬技巧,超越规则。”(莫里森,2006:序Ⅳ-Ⅴ)埋藏的技巧和超越的规则就是跨层隐含作者、时态的任意转换以及多版本叙述等非自然叙述行为,莫里森以实例形式给读者上了一堂生动小说创作理论课。作家需要平衡经验与人物自主性之间的关系,选择合适的声音、聚焦和时态,以产生期待的交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