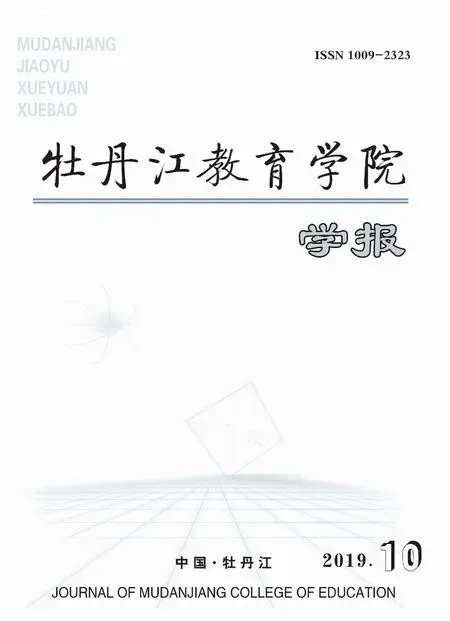论高校文学史课堂叙事化教学中的教师个人叙事
刘 郁 琪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在教学论维度的教育叙事学视野中,任何课堂教学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叙事的过程。对充满文学思潮故事、文学作家故事、文学文本故事的高校文学史课堂教学来说,自然更是如此。一定程度上,文学史的课堂教学,就是一个这三种类型的故事互相激荡、碰撞、融合的叙事场域,完全可以采取“叙事化教学的理念和模式”,从而“将过往那种概念和理论充斥的文学史课堂变成各种形象性故事的组合体,将枯燥抽象的知识讲听过程变成生动有趣的叙述之旅”[1]。但在叙事化教学的视域中,文学史课堂的叙事内容,除了文学思潮故事、文学作家故事、文学文本故事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故事的可能?答案是肯定的。笔者以为,至少还存在另外两种故事,那就是作为课堂叙述者的教师之个人故事,以及作为受述者的学生之个人故事。如果说,文学思潮故事、文学作家故事、文学文本故事,这三个同心圆式的故事构成了文学史课堂的“显性故事”,那教师个人故事和学生个人故事则构成了“隐性故事”。对这些“隐性故事”尤其是作为课堂叙述者的教师之个人故事的存在状态、出场方式、调度法则等进行探究,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文学史课堂的教学格局,提升文学史课堂的教学效果。
一、破除教师个人叙事的认识迷思
传统教学理论认为,教学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知识传授活动。知识的客观性、准确性,是必须严格要求的。它就像现代物流领域中的包裹一样,必须要能完好无损地从教师/发货者准确递送到收货者/学生那里。也因此,任何可能影响知识准确性、客观性的东西,都必须被排斥在教学活动之外。就文学史课堂来说,除了文学文本的准确分析、作家个人经历的客观描述、文学史脉络和规律的科学梳理之外,不应带入任何与此无关的东西。这种观念,把握到了教学在根本上是一项客观的知识传授活动的本质,但忽视了教学尤其是文学史课堂教学也是一项主体性、情感性交流活动的特点。“一直以来,我国传统的师生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功能性的关系’,即为了满足某种外在的个体或社会的功能性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教师和学生不是以完整的人的存在方式出现的,而是以扮演的‘教师’和‘学生’的角色面貌出现的,教师和学生真实的我深深地掩藏在这种角色互动的表面之下,彼此之间缺乏一种本源性的真诚和信任,也根本不把对方作为存在意义上的‘人’来看待。”[2]换言之,传统教学观念仅注意到教师在课堂这个特定场域的功能化“角色”,而忽视了他还是一段历史、一个故事、一个存在意义上的“人”。
作为存在意义上的个人,教师是带着他的个人历史、个人故事走进教学课堂的。而课堂知识传授的生动性和随机性,教学流程设计的主观性和个人性,都会受到这种个人故事的影响。有学者引用古德森的话说,“教师的行动与个人过去的生活历史密不可分。教师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生活历史内容,都会慢慢发展成为足以支配教师日后思考与行动的‘影响史’,对教师后续的经验选择与重组具有无所不在的影响作用”[3]16。也就是说,在课堂知识的传授过程中,教师的个人生活史、个人故事起着潜在的制约作用。如果说课堂上明确讲出来的“知识”“内容”,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那这些起着潜在制约作用的个人故事则是水面下的冰山底座。潜隐的冰山底座的状态,决定着水面上冰山的形态与高度。事实上,这也是教师教学风格多样化的重要原因。美国学者彼得·法林说:“教学活动体现教师个人的特征和价值取向,这些特征和价值取向高度个体化,甚至独一无二。”[4]而这种“高度个体化”甚至“独一无二”的个人特征和价值取向,来源于“教师的个人生活史”。同样的文学史内容,不同的教师会教出不尽相同甚至迥然相异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各自的人生故事不同。他之所以是他,不单是因为此刻的教师“角色”,更因为他还是一段独特的历史、一个独特的故事。也因此,有论者指出,“教师教学行为、处理问题的方式更多受到个人过去生活史的影响……教师在教室内使用的许多策略,都与个人的倾向及先前的经验有直接关系”[5],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风格、教学经验和技巧等无不渗透着教师个体‘个人化的东西’,凝聚着教师‘个体经验的印迹’……具有高度的个人生活史特性”[3]16。
学界充分认识到了教师个人故事、个人生活史对教师教学的影响。遗憾的是,已有的教师个人生活史研究却主要是一种教师研究论范式,主要用于教师个人素质培养和实践智慧的研究提升:“生活史是接近教师教育教学经验的一扇窗户”,“探究教师个人生活史就是教师自己对生活与教育中所发生的事件的反思,是对‘教育的生活世界’的感悟与体验。这些经历往往会成为教师原初教育信条,对其以后的教育教学产生深刻的影响。”[5]换言之,教师个人生活史是教师自己对本人生活的一种反思、描述,是用以自我认识的工具,与教学没有直接关系,这是教师论的、认识论的,而非教学论、课堂论的。笔者认为,既然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个人故事”走向讲台,既然教师个人故事并非与教学尤其是文学教学毫无关系的东西,甚至还以隐性的形式制约着课堂教学的效果,那这些故事就可以在适当的时机从“隐性”走向“显性”,让其“浮出历史地表”,“偶尔露峥嵘”。事实上,完全排除个人叙事的课堂,可能是不存在的。许多老师,在公开课时完全排除自己,而在个人授课时,多多少少涉及个人故事。我们所谓教师个人叙事,其实就是指教师在课堂上对自己个人故事的这类选择性讲述。它和当下学界所谓的教师个人生活史探究不完全相同。它不是教师对个体生活经验和教育经历的课下反思并达到自我认识的工具,而是课堂实践中教师个人生命故事的临场叙述,这属于是教学实践论范畴,而非教师论的问题。
经笔者观察和实践,教师个人故事由“隐”及“显”的显现,或者说教师个人叙事的恰当运用,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的教学效果。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6],与此相似的另一广为流传的说法则是,“教育本身就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从学生/年轻人的心灵来说,教师自身的故事,显然更能成为推动他们成长的“树”“云”。因为比起历史长河中的其他人的灵魂,比起文学文本中的那些虚构的灵魂,他们对站在他们眼前的这个活生生的教师的“灵魂”更感兴趣。而教师的灵魂,就来自于教师的故事。当你敞开心扉“说出你的故事”时,不仅可满足学生的好奇心,而且还会使之感到一种信任感,平等感。韩愈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早闻道者,有专攻者便为师。教师之所以为教师,就因为比学生有着更多的经验阅历、知识储备,有着更为多样、丰富、精彩的个人故事。知识源于生活,经验就是故事,如若不将知识还原于真切可感的日常生活故事之中,而仅仅将之当做一个客观的对象,生硬、呆板、机械地告诉学生,知识就会变得面目可憎。而且,文学中的许多体验、体悟,是理论性的概念或者概念性的讲授所无法传达的,必须借助于举例、现身说法等。有时一个观点的了解,一段文学作品的领悟,怎么解释都说不清,说一段亲身经历的故事,学生立马就懂了。一些与知识相关的故事,尤其是个人亲身经历的故事,不仅可以带入课堂,还可以起到活化课堂知识、活跃课堂气氛的效果。
就文学史课堂教学来说,教师个人故事的由隐及显,还有着更强的必要性、更多的合理性。文学史课堂姓“史”名“文学”,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属性。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尽管文学史本身是客观的,但文学史的书写和讲述却无疑具有主观性。西哲有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心灵史”。任何历史阐释,都必然带有“当代”人的主观视域,都是阐释者心里的一种心灵重建。这时,阐释者自身的历史故事及其主体情绪,就必然介入。事实上,同样一个历史故事,不同时代的人以及同一时代的不同个体来讲述,之所以具有不同的魅力,就在于叙述主体的介入维度和情绪涂抹不一样。而叙述主体介入方式与情绪倾向就来源于主体个人生活史的漫长积累。文学史的课堂教学,本质上就是教师作为一个“当代”历史、故事的参与者而与过往文学史对话、沟通、融合、共鸣的过程。对一个文学史问题的理解,老师若能将自己之所以这么理解的“个人故事”讲述出来,会让学生认识到文学史学习的过程, 不仅是一个知识识记的过程,也是一项视界融合的过程。换言之,教师作为叙述主体自身故事的出场,既有利于学生对文学史关节点及其各种细节之逻辑的理解,也能告诉学生教师学习和理解历史的基本方式、方法。
从文学史课堂的文学属性来说,也需要教师个人故事的适当进入。如果说一切文学都是人学,那文学教学包括文学史教学也同样是人学。俗话说,太阳底下没新事物。人类自诞生以来,许多的心性模式、情感构型、行为机理都是恒久不变的。20世纪30年代有关文学人性论的论争中,梁实秋等人早就指出,人与人之间或许有“遗传”“教育”“经济的环境”“生活状态”的不同,但“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7]鲁迅等人则曾精辟地指出,文学固然要以人性基础,但人性的实现形式和表现方式却不免具有阶级性。“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比如“‘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8]事实上,阶级、阶层之外,不同的时代、民族、地区,人性的表现形式也会不尽相同。这就造成了文学理解和文学接受的“障碍”与“困难”。文学说到底,其实就是普遍而永恒的人性在不同时代、阶层、地域中的表达。而学生,因为作品中那些非常时代化的、阶级化的、民族性、地域化的原因,而无法真正或充分进入文本内的普遍人性的体悟与把握。这时,老师若能按照自己对作品中深层人性的体认,将之置换为一个自己所曾亲身经历过的故事,学生便会因为和老师的同时代性、面对面的近距离性,而迅速穿越文本中那些“历史”“时代”“地区”“阶层”等的迷雾,直接进入到对恒久人性的理解和体悟,从而快速掌握文学史文本的真谛和奥妙所在。
二、教师个人叙事的出场时机与调度原则
如前所述,在叙事化教学的视野中,文学史课堂的教学内容,主要由文学史故事和文学文本故事两大类构成。前者是指大的时代背景和小的作家个人身世经历,后者则指作品自身包含或隐含的故事。在此意义上,文学史课堂上教师个人故事的出场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如何将之嵌入文学史故事和文学文本故事的问题。更准确地说,就是一个如何处理教师个人故事与文学史故事、文学文本故事之关系并将其有机嵌合在一起的问题。对此,笔者曾经指出,“文学史课堂以讲述文学发展脉络和文学现象演进为主要任务,因此文学史故事是纲,是第一序列的故事,它构成了课堂故事叙述的中心情节。如果说它像一根藤,那文本故事就像这跟藤上的瓜,它是嵌套而不是并联在文学史的藤上的,是次一等级的故事。而个人故事则是更小的藤蔓或瓜蔓,它嵌套在文学史故事和文本故事的相应之处,是次级或更次级的故事。它的嵌入点,可以是在文学史故事的叙述中,也可以是在文本故事的分析中。”[1]
具体来说,在文学史故事的叙述尤其是大的时代背景与作家个人思想、作家身世经历与作品风格之关系时,教师个人故事便可以出场。历史本身奔涌向前,从不停息,但人在历史中的许多行为模式、思想方式却是基本不变的。人在历史中的一些常态、常情、常德,对我们理解历史相当重要。这时,教师主体以当下历史中的活动者的身份,对历史上作家们的情境做出设身处地的思考,以自己类似的亲身经历或个人故事为基础,对历史进行“同理心”的阐释。在情理相同的情况下,既能让“两个故事”——客观的文学史故事和主体的个人故事之间形成一种对话关系,也能让学生瞬间理解当时的情境。例如作家生平介绍或者身世经历的问题,许多老师总是将其当做猎奇的对象,变成了作家八卦的讲述或者风流韵事的集锦。学生固然听得饶有兴味,却没有任何“营养”。事实上,作家生平或身世经历的讲解,必须注意和大的历史时代背景(大时代故事)以及具体的作品特征(文本故事)之间的双重联结。或者说,作家个人故事和大时代故事、文本故事之间的三重对话与互动,才是讲解作家生平和身世经历故事的重点所在。文学是时代的产物,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而时代和文学之间的那个中介,就是作家和作家的内心。但因为审美观念等的不同,作家的内心也许是“镜子”,也许是“灯泡”,也许是“熔炉”。这样,大的历史时代对作品的最终影响,就会显得比较抽象、复杂。这时,作为教师,便可以将自己的个人故事有机嵌入进来,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其中的复杂性。
文学史故事同理心体验(外文本的同理心嵌入)之外,文学文本故事或者说介绍文本中具体场景时(内文本的同情心介入)也是教师个人故事出场的合适时机。米兰·昆德拉说,“小说是关于存在的诗意沉思”,其实文学都是。教师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就是要带领学生经由“诗意”的叙述,进入对“存在”的把握和“沉思”的领悟。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不同的教师因个人故事的不同,对文学文本存在和沉思的可能会不尽相同。有论者便因为有着“与于勒故事类似的生活经历”,于是对《我的叔叔于勒》做出了不同于传统“阶级观点”的新解读:“信是解读全文的‘钥匙’;菲利普夫妇是因为无法承受事实而不想面对;而莫泊桑并未在小说中表达任何批判,只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展示了人世沧桑中小人物的无奈。”同样地,因为有着“从家乡到北京的奋斗历程”以及此一过程中“父亲出于疼惜对她出去闯的阻挠、同伴留在家乡的感叹、自己不断更上层楼的体验”,让她从《五小鸭》这篇童话中也“读出了不断追求‘好’的人生境界的意义”。甚至于得出结论,语文课堂上的文本解读或者说教学解读“其实教的是自己”:“语文老师调动全部生命的体验和经典文本接触,读出属于自己的东西,课文就不再是教材和知识点,而成了生命的血液、智慧的泉源!教书其实教的是自己!”[9]个人故事确实决定着教师对具体文本的把握与理解,若将生成这种“自己”的具体个人故事直接说出来,则更能帮助学生设身处地的理解文本的意涵、场景、思想主题。如讲到巴金《寒夜》中婆媳关系的复杂性时,亦可嵌入自己的亲身观察和体验以为例证。许多学生毕业多年后仍然记得这一节。
抓住了教师个人故事的嵌入点,也就抓住了个人叙事的调度核心。但除此而外,还必须注意“相关度”与“叙事量”的把握。所谓“相关度”,是指教师个人故事和课堂主要教学内容和知识点之间的相关性和结合度,至少有两点需要切实注意。一是切忌“霸王硬上弓”。不能为了所谓课堂效果,便“为赋新词强说愁”,强行硬凑、加塞一些可有可无甚至与教学完全无关的个人故事。作为课堂教学的叙述者,教师必须时刻谨记:文学史故事、文学文本故事,才是教学的主要内容,教师的个人故事只是用来帮助理解这两个主要故事的。也因此,只有与主要故事具有紧密“相关度”、确实有利于帮助和理解教学内容的个人故事,才可以讲述。反之,关系不大,相关度不强,或者本来就可有可无的故事,就不能讲述。二是切忌“无主题变奏”。有些个人故事,一开始确实和教学内容紧密相关,但讲着讲着就很容易变成漫无边际的“脱缰野马”,甚至越扯越远,以至开口千言、离题万里。比如有老师讲解“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因学生不知雎鸠为何物,便讲起自己目睹并抓捕雎鸠的“个人故事”。这立马引起了学生的兴趣,连睡觉的学生也都顿时醒来。但接下来的叙述,本应是他亲眼所见之雎鸠的形状、大小、特性等。而这位老师却从如何看到、为啥去抓,如何抓讲起,并由此叙述起过往种种抓鸟的趣事,讲了整整大半节课。有趣固然有趣,但把课堂变成了和教学内容风马牛不相及的胡扯。课堂的中心是完成教学任务,任何教师个人故事的“旁逸斜出”,都必须回过头来为知识传授服务。否则,就是逾越了课堂教学的“红线”。
“相关度”的把握之外,“叙事量”的掌控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学是一门时间的艺术。在叙述流程的设计中,教师还必须清醒认识到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永远都是一对大矛盾。一部文学史,长则几千年,短则几十年,而一门文学史课程,也就是一个学期,48-56学时,至于一堂课,则只有40-45分钟。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掌握好叙述的速度和节奏。”[1]有限的时间里必须传达完教学任务,这就决定了教师个人叙事只能是帮助理解文学史故事和文学文本故事的催化剂或边角佐料,决不能变成了主食或主餐。即便是与教学内容非常相关的个人故事,也不能无限发挥,只能点到为止,千万不能把课堂完全变成个人故事的说书场。尽管不能硬性规定个人故事该占多少比例,但不超过三次,不多于课程时间的三分之一,应该是最起码的要求。严控教师个人故事的叙事量和时间性,这就好比炒菜中必须适当控制调料一样。一方面,适当放点调料是可以的,可以把菜做得更香,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放得太多,不能把佐料当成主食或主餐。就如一盆羊肉,没有佐料,还是羊肉,还可以吃,营养丝毫不少,只是味道不怎么样而已;而如果只有佐料,完全没有羊肉,这盆菜就失去了营养价值,而且也是难以下咽和令人作呕的。
总而言之,在传统的课堂教学实践中,影响制约教学方式和教学效果的教师个人故事是“隐性”的,它“时刻在场却又始终缺席”。但“在今天,课堂已经开放了它自身的‘疆域’,不再是‘象牙塔般的禁锢地’。课堂教学在时空的视阂中不断扩张,己成为一个复杂关系的网络空间,‘在场’与‘缺场’因素的交叉影响以及历史传承的累积性不断繁衍和维持”[3]7。至少对文学史的课堂教学来说,教学主体或者说教师的个人故事,是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由隐性走向显性,由“缺席的在场”变为“真正的在场”。它或许“并不必然属于文学史课堂教学的内容,但自然、恰切、巧妙地运用,却会让整个文学史课堂的叙事,更为生动、有趣和丰富,并有利于对文学史故事和文本故事的理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