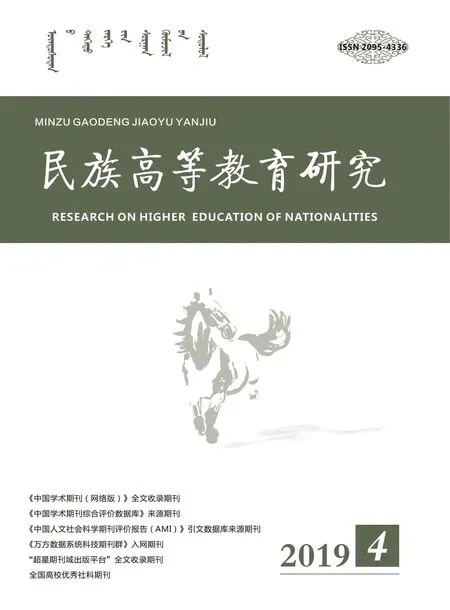英雄传说故事的“社区教育”功能
——以卫拉特英雄嘎勒登巴传说故事为例
萨日娜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民间传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主要以散文形式的口头传承为流传方式。民间传说描述的多为某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物、事件、各种风物的起源,具有一定的教育和审美功能,是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英雄传说是民间文学这一大类别中将英雄人物进行神圣化叙事的散文性传说故事,其主旨为传颂英雄精神、歌颂英雄功德事迹,有时还会与“风物传说”相融合,以一定的物质表现形式即自然景观和风景名胜“寓教于乐”。
换言之,英雄传说故事具有“社区教育”功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里使用的是“社区”的概念,而不是“民族”的概念。“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1]。“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原意是“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关系”。“社区”在具体指称某一人群的时候,“共同文化”和“共同地域”是它的两个基本属性,而“地域”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实际上是产生共同心理图式的基础,并且潜移默化地不断强化着社区的共同文化。
“卫拉特”是Oyirad的音译,即元明时期的“斡亦剌惕”“瓦剌”,在历史文献中也被称为“厄鲁特”。明初起,瓦剌人口达到四万户以上,逐渐形成并且建立了“四卫拉特联盟”,“四卫拉特”中的“四”其实并不指四个部落,卫拉特的部落构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差异很大,“四”是指最初的这四万户人口。卫拉特蒙古人自明代之后至今的主要活动区域集中在我国新疆,因此笔者认为“新疆卫拉特”应该被称为一个“社区”或者“共同体”,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因为它是聚集在“新疆”这个“共同地域”中有着“共同文化”根基的联系紧密的群体。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更是陆上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联系中西文化和经济的重要纽带,各民族、各部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在长期历史沉淀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交流、战争、融合不断积累,产生了绚烂多彩的文化图景,进而产生的少数民族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也是非常珍贵并且丰富多样的,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
嘎勒登巴是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领袖即和硕特首领鄂其尔图车臣汗与其第三夫人苏勒门哈屯(“哈屯”是蒙古语中汗王妻子的称号)的次子,1635年出生,1667年秋逝世。在短暂的一生中,他不仅从十七岁起就率领卫拉特蒙古人与外族侵略者作战并且取得胜利,帮助卫拉特人民保卫了领土,而且在卫拉特大内讧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维护了卫拉特地区的政治和平,他不断为人民争取和平生活的形象深得人心,是人民心目中的“和平英雄”。嘎勒登巴的英年早逝让人们对他的敬仰和怀念之情不断加深,也正是由于卫拉特蒙古人民失去了一位心系百姓的人民英雄的伤痛遗憾和对嘎勒登巴的怀念崇拜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时代环境的变迁愈发强烈,民间根据他的真实身世而形成了英雄传说故事。卫拉特蒙古人将嘎勒登巴神化为“斩妖除魔”的“人民保护神”的传说故事代代相传,直至今日,卫拉特民间仍然广泛传唱着赞扬嘎勒登巴的歌曲。这些传说故事也因此成为卫拉特蒙古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它折射着过去、现在、未来的卫拉特人民的文化精神面貌。
一、作为民族志的英雄传说故事
民间传说故事口头传承的特点具有的特殊历史记忆功能。口头传承的起始时间先于书面记录,有时可以与客观历史真实无限接近,口头传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嘎勒登巴的英雄传说故事在卫拉特蒙古人聚居地广泛流传,他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新疆地域范围内许多自然景观的风物传说(例如赛里木湖、博格达峰的传说等)也都与他有关。然而,这位英雄人物在正史中却极少被提起,正史对这一真实存在并且对卫拉特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几乎没有记载。
关于这一点,蒙古国科学院院士楚伦·达赖先生在《蒙古国的卫拉特研究》中论述道:“1755年至1758年,满清皇帝为讨伐卫拉特蒙古多年不降之罪,采取了斩尽杀绝,迫使他们背井离乡等手段……为民族的自由而进行不懈斗争的卫拉特蒙古因为遭到失败,所以其功绩一概被抹煞,在史籍中被冠以‘叛徒’‘逆贼’‘乱匪’等罪名。对其领袖人物噶尔丹巴(Galdambaa)、策妄阿拉布坦(Tseveenravdan)、噶尔丹策凌(Galdantseren)、舒奈(Shunai)、达瓦齐(Dawats)和噶尔丹(Galdan-Boshogt)、阿睦尔撒纳(Amarsanaa)等人更是除了‘猪’‘狗’之类的词外没有其他称呼。深受卫拉特人民爱戴的英雄噶尔丹巴和舒奈在历史上几乎没有记载。”[2]我们从这段论述中可知,也许历史是可以被销毁或者被扭曲改变的,也进一步说明了嘎勒登巴英雄事迹的真实性以及他在正史中没有留下记载的原因。
民间流传的所有嘎勒登巴英雄传说故事之中,最为著名的是“嘎勒登巴的下凡”“萨尔特格在赛里木湖不小心丢了脑袋”(在赛里木湖智斗萨尔特格)和“嘎勒登巴的爱马洪乎祖尔”(卫拉特民俗“吃肉时要丢弃羊的肱骨肉”的来源)。嘎勒登巴在传说故事中幻化为有神力有魔法咒语的、天神腾格里唯一的儿子,被指派到卫拉特为人们消除灾祸。我们可以看出,传说故事强调了嘎勒登巴高贵的出身,这一点与客观事实是具有相互指涉性的,现实中的嘎勒登巴也是整个卫拉特盟主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儿子,相当于卫拉特的王子,同时又是多场重要战争的首领。在“萨尔特格在赛里木湖不小心丢了脑袋”(在赛里木湖智斗萨尔特格)这个传说故事之中,“萨尔特格”在不同的流传版本里呈现出不同的身份,有时是频繁在蒙古族神话传说中出现的怪物“蟒古思”,有的版本将萨尔特格描述为其他中亚突厥民族的侵略者或者勇士。这个故事主要影射的应该是历史上嘎勒登巴十七岁时带领卫拉特士兵抵抗异族侵略者并且取得胜利的那场战争。传说故事中的嘎勒登巴是以魔法咒语和极快的反应速度取胜的;在历史实际战争中,嘎勒登巴在对战人数方面也是以少胜多的,说明他确实具备一些过人的军事韬略和作战天赋。
我们由此可知,传说故事不仅填补了一些正史中忽略和被销毁的内容,以口头传承的记忆方式保留了当时发生的历史,表达了卫拉特百姓对嘎勒登巴的怀念,是一种活形态的民族志,许多与嘎勒登巴的传说故事相关的当地景观和风俗禁忌也被流传下来。传说故事的存在,使民族历史的细枝末节显得更为清晰和确凿。
二、作为指导当下的“社区文化生存手册”
民间文学来自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经验,与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伦理习俗、审美心理等全方位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构是紧密相连的。民间文学既来源于民众生活也作用于民众生活,影响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轨迹,传说故事尤其如此,不仅具有文学性和历史性,更具有文化审美功能,也以节日仪式和民俗禁忌的方式影响着处于共同社区的人民的生活,其本质具有教化功能。
传说故事虽然无限接近客观历史真实,但是也存在着对历史客观真实的背离,尤其是其中的神话化幻想成分。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成分虽然本身没有现实意义,但是其存在背后的根源以及它被创造出来的精神内核与心理机制,对人们当下的生存状态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从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文化历史研究角度出发,所有文明的发展都遵循一定的规律,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不同时代的挑战,一种文明是否可以继续向前发展则主要依靠这一“共同体”中的精英人物是否能够应对并且战胜挑战,从而说明了精英人物对于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英雄传说故事的主旨在于传颂英雄精神,“英雄精神”不仅涵盖了保护领土安全、保护人民生活祥和安宁的武力行为,更包含了不同时代迎接不同挑战所需要的摒弃小我之私欲而以大局为重的胸怀和大智慧。英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民族精神,如何评价和记忆英雄,反映的是这一社区的核心价值观,对这一共同体光辉历史的铭记、对历史英雄的怀念和崇敬,其实是对现实的一种鞭策和激励,对人们当下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始终具有指导意义。
传说故事中还存在着大量的生存经验,隐藏着充满浪漫主义的警示。民族精神传说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强化,社区中的每一个个体以传说故事为神圣范式,遵循其中传递的生活习俗以融入社区共享的文化宗教信仰,进一步加强了社区中个体之间的联系和社区文化本身的独特性。一方面,个体得以进行身份认同和自我确认,社区内部成员的精神层面的结构更为紧密;另一方面,社区文化也得以继续保持活力。
嘎勒登巴的传说故事,不仅有口头传承形式和民俗禁忌的仪式,也有以景观风物作为物质形态,对卫拉特这一社区本身特有的历史文化心理不断进行强化,成员之间也在英雄传说故事口耳相传的过程中进行共有价值观和身份的认同,成员心理层面对共享文化的依赖也被潜移默化地强化了。因此,传说故事对当下的指导意义在于人口数量较少的社区如何在时代剧变的潮流中保持自身文化历史的独特性存在的意义和活力。对每一个社区成员的具体生活来说,传说故事的存在是一种更偏向于价值观追求的意识形态样本,是自我身份存在的证明。
总体来说,传说故事作为指导当下的“生存手册”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传说故事以非物质和物质的形式强化了社区内部共同的审美心理和价值观结构,强化社区精神内核以抵抗时代剧变带来的各种文化侵略与影响,帮助社区成员进行身份认同和形成一定的文化归属感与安全感。
其次,传说故事本身具有的鲜明地域性和历史性给社区带来了宝贵的生存经验,给人们了解某一区域的地理、历史、文化习俗等基础知识提供了一种有趣的途径。
再次,传说故事激励和鞭策着社区成员战胜日常困境,使社区成员更加清晰地看到社区自身的文化样貌。传说故事作为社区成员传播思想的一种简单易行的形式,也掌握着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不断完善价值观体系的灵活性和主观能动性。
三、作为投射未来的意识形态镜像
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人类在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之后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下和未来可能会遇到的挑战,我们也能够从这样的历史发展规律中找到未来发展的趋势。也就是说,过去与当下也是未来的组成部分,人类文明的记忆也有投射未来精神样貌的功能和作用。民间传说故事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固定的传播区域,这一固定的传播区域是依靠共同的语言、民俗、文化、历史与心理机制、思维模式而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沉淀,被口耳相传的传说故事、地方风物景观、不断强化的民族精神,形成了一个社区不变的意识形态内核,是任由时代洗礼都不会改变的,它具有一定的凝视性,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投射未来的意识形态镜像。
正如嘎勒登巴传说故事中体现出的那样,即使是同一种族内部也会产生分歧纠纷,完全不同的文化之间也会相互交流融合。文化多样化不仅仅是新疆这一地域的也是世界各地的客观事实,更是未来的趋势。科技的发展虽然已经使地球村的生活形式变得越来越同一化,但是当每一个个体了解自己来自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信仰、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社区、经历过不同的历史变革时,也就进一步说明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生命个体思想的不可复制性,对于个体进行自我身份的确认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我们通过对民间文学例如英雄传说故事和相关风俗禁忌的研究可知,时代的变化淘汰了哪些旧观念、迎合了什么样的新时代主流思想。人民大众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的,当具有传播本质的民间传说故事根据民众的心理需求和时代政策的改变而改变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对社区群众发挥教化作用。当这一地域在过去的传说故事中呈现的样子是多种文化交错相融时,人们在未来也会以某种记忆方式对不同的文化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宽容、理解、接受。
因此,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过去文化的多样化传统也映射着未来更宽容温和的意识形态。对此,传说故事的存在对多种不同的文化采取尊重理解并且主动进行学习了解的态度养成,具有一定的“社区教育”功能。正如2001年出版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对文化多样性作出的描述:“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的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3]
综上所述,笔者经过文献搜集和梳理,从自身文化背景和田野调查的结果出发认为,首先不可否认,英雄传说故事是一种活形态的民族志;其次,英雄传说故事对当下的社区文化生存具有不可忽略的指导意义;再次,英雄传说故事还具有投射未来意识形态的镜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