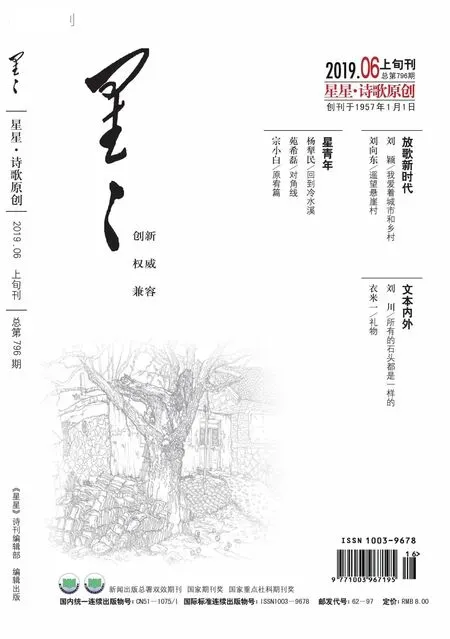哀册:父亲纪(三首)
聂作平
1967:婚姻
天作之合呀!木匠的女儿嫁给剃头匠的儿子
宛如坡地上间种的高粱和大豆
那么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当然值得公社书记也表达鼓励和赞美
但我仍要感谢作媒的刘幺娘,是她
率先捅破了这层纸。我的父亲与母亲
订亲,看期,结婚。尔后
才有了我,才有了我在五十年后
坐进阳光明媚的冬天,写下这组
回忆之诗
父亲和母亲,只隔着两匹小山
四方水田,和一根鹅肠般的山路
春天的马桑花和油菜花,一直开到
两家的篱门下。啁啾的燕子
悠游于同样烟熏火燎的屋檐
它们婴儿般的鸣叫,让每一个春夜
都变得温暖而泥泞。当母亲麻利地
从池塘浣衣归来,沉默的父亲
坐在瓦房前,读一本掉了封皮的旧书
全大队惟一戴眼镜的人,他那瓶底厚的眼镜
他那天然的卷发——更重要的是,他那穷得
把门板拆下换高粱的家庭,都是婚姻
而爱情,它如同燕子嘴角的春泥
再勤劳,也无法堆出一条通往春天的花径
幸好,我的母亲只上到二年级,只能歪歪斜斜地
书写她的名字。这个半文盲
一生敬重知识,敬重那些认字多的人
一如她的父亲,一生敬重菩萨,敬重能够带来灾难和惩罚的
高高在上的神灵。老木匠八个女儿中最小的那个
外公花了整整两年时间,为她打制一张
沉重而繁复的楠木床。他企图用这座移动的小宫殿
迎来小女儿的幸福和安稳
最终,他却失望地看着,迎亲的队伍
把它抬进年久失修的赵地主建造的旧瓦房
……
四十年后,老去的父亲和母亲
回到四十年前的洞房,那早就卖给了张家的祖居
他们清楚地指认现场:这里是楠木床,这里是装衣服的柜子
这里是摆放油灯和书本的木几。最后,母亲总结说
哦,这里,你在那个秋夜来到人间
发出第一阵明亮的哭声。接生的刘幺娘把你裹进襁褓
小小的襁褓,用你父亲的汗衫缝制。你的父亲
他踏着凌晨的霜露,到你外公家借米
……
1984:蚕桑
众多的蚕儿一齐啃食桑叶,造成了一场
春夜的雨声。但那时,潮红的月亮
高高悬于盆地和我家屋顶之上
整夜啼叫的子规,被月光映红了鸟脸
像是关公,派驻人间的使节
1984年,岁月平坦,风调雨顺
父亲从林业转入蚕桑,他的工作对象
由遮天蔽日的林子,由松树、柏树和苦楝
转变成田间地头,低矮而碧的桑树
当然,还有白胖的蚕儿。它们小小的身子
被雨后的桑叶,神奇地放大,点亮
为此,父亲必须做一个蚕桑专家
母亲也必须做一个养蚕能手
夜半醒来,我看见屋子里燃着炉火
父亲一边抽烟,一边翻检《养蚕指南》
母亲一边说话,一边为蚕儿换垫,添叶
他们相互纠正,又相互赞美
如同一对同门师兄妹,正在修炼
秘洞里偶然获得的失传的剑术
暮春,桑叶渐老,细长的锯齿锯断暖和的雨水
父亲和母亲站在蚕房里,恍似两个
与幸福初次遭遇的孩子。作茧自缚的蚕儿
亮着身子,爬上草堆
晚来的风,摆动它们嘴里的丝。父亲和母亲慢慢坐下来
他们平静的目光,透过窗户,也透过那层薄薄的雾气
雨水精心冲洗后的天空,如同一匹刚刚织好的丝绸
2017:丧礼
穿上戏袍似的僧衣,这个姓翟的农民
就摇身一变,变成乡亲们口中的道士
这个此时此刻,凭借咒语和桃符
与亡灵暗中沟通的半神,他满脸神圣
就连叼在嘴角的香烟,也不再抖下
燃烧后的白灰。是的,我清楚地记得
那面银子般的锣鼓,三年前,在同一座庭院
送走了祖母。那个夏夜,你与我坐在
同一株黄桷树下,闻着刺鼻的花香,听着翟道士
用地道的富顺方言,为我的祖母,你的母亲
招魂
你在69岁那年,失去双亲,沦为孤儿
可惜你浑然不觉。你微笑着招呼吊丧的亲朋
递烟,倒水,端凳子,间或和其中的某位老友
开个玩笑。而我,我荒唐地喝多了酒
歪着身子,向祖母的牌位作揖
吐出火舌的纸钱窜上临近的牌桌
三缺一的那桌,三个肥胖的妇人,不耐烦地交头接耳
继而又发出快活的笑声。是的,101岁的喜丧
高寿而去的亲人,于生者,是值得骄傲和炫耀的福祉
我自然想到你和母亲,还要三十多年
你们才会走到祖母寿终的年岁。哦,
漫长的三千多个日夜后,我甚至要比你们
还要衰老。那时,在你的丧礼上,我也会如同你
这般从容,这般淡定
孰料才过三年,翟道士的锣鼓,又一次在我家庭院敲响
似曾相识的咒语,似曾相识的吟诵。如今
已是在为你招魂。你比你的母亲,早走了28年
28年,我们可以喝下几百瓶酒,抽掉几百条烟
或者像天底下大多数父子那样,沉默无言,相对坐到半夜
或是在春花秋月的夜晚,偶尔怀想童年往事……
然而,提前撤退的亲人就是一次猝不及防的车祸
来不及预料,也来不及躲避
惟有用柔软的胸膛,迎接这致命的一击
你沉睡在棺木中,面容沉静
你让我想起三年前,你101岁的母亲;想起你被剪去的28年
如盐如蜜的28年,化作翟道士沙哑喉咙挤出的经文和咒语
化作纸钱的轻烟,和撕烂秋夜的锣声。
这个深秋,黄桷兰还有残留的芬芳,只是
与我对坐并一同敌视长夜的,不是你
而是我修长孤苦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