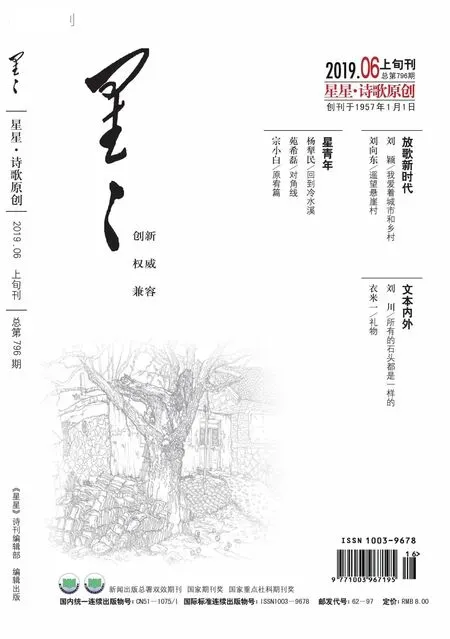刻意,与不刻意(随笔)
刘 川
有时,灵感来了,这家伙根本就不管我身处何方。我赶紧张开手,猛一攥。感觉诗就在其中了。缓缓张开手,复又失之——或者说,诗,从来都在,就是那张开、猛攥带来的空白与透明。我一直认为,写诗,要刻意;而表达的效果,要不刻意。要瞄准它、去捉住它;又要无功利、不强加命题地呈现它。
关于写之刻意,我不认为“诗到语言为止”。诗从语言开始,应该发散出去,到达语言之外的某处,我不问它抵达之处,是感受、是况味、是思想、是情感,还是其他存在。总之,我要诗有所表达,不仅仅是作为语言。我说的写之“刻意”,即创作观不是历史虚无与现实虚无,更不是价值虚无。诗人之为人,在一个具体的社会与时代维度里,是重要的一环。这一环天然具有表达的责任,以证明,这一环没有断脱。
写之刻意,我不认为“诗无用”。诗当然不能工具化。但也不是说,诗就是充闲帮庸之趣。诗,是诗人与社会对话的诉求,是建立另一重维度世界的努力。诗人之为诗,诗是人之灵,是暗夜里的火炬,是生命更高的形态,我说的诗之“用”,就是让人成为能够审美的人。而审美,不仅仅是专注于对修辞之美、对文本的理解、领悟与欣赏,而是一种对人之高贵与优雅的判断与体认,是一种拒绝自我染污与异化的能力。
写之刻意,是在动笔前,即建立人格。以人之格,奠基诗之格。这里的人格,不是平常所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也不是个人的道德品质,而是一种完整的现代人价值,一种进步意义上的人的存在。诗的写作,当致力于一种进步的、开化的、反省的、成长的人格建设。
至于表达的效果,却是要不刻意。
达到灵动、率性、自在的诗意,需要接通人气。表达人生经验,才是接通人气之根本。悬空高蹈的诗,虚伪做作的诗,只能在语言里空转。
达到收放自如、游刃有余的诗意,需要接通地气,本土氛围、日常生活,皆是诗人真实脚踏之地。这块土地的气息,力量远远大于泊来的洋大师二手经验。
本土和日常,是个体、是细节、是质感。生命的纹理、情感的褶皱、精神的刻度,只有通过对具体的人的触及才能得到。本土和日常,即是我们最熟悉的具体的人的总和。因为不能深入地关注人内心、关注已经发生在自己和身边人群身上的这个深刻而丰繁的时代,所有的写作将处在一种“失语”状态里,而遮掩“失语”的做法只能是:刻意、做作,以修辞的形式。
我不反对诗作为语言艺术的所有可能。以人为本、在人之上,我乐见所有形态的语言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