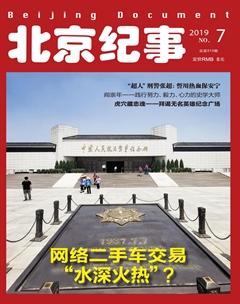“六一”的虎坊桥随想
周六落笔,恰逢“六一”儿童节,遇上各种节日说点应景的话也是常态。自己曾经的儿童节,基本上是在宣南这地界上过的,往具体点说,就是虎坊桥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后面的福州馆小学。把受教育的经历用“人生的衣服扣子”形容,学校确确实实是第一粒扣子,但想扣好也不容易。3岁看大7岁看老,有人居然能洋洋洒洒写本小孩子心理发展演变的书赚钱,所以老话有老话的好处,3岁和7岁虽然只是一个概数,但每每证明是有道理的。童年还没学会伪装,反映出的性格往往是本真。成年人水越来越深,深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做事往往就没了章法,什么时候掉坑里,还搞不清因果。有一个比较通俗的词,叫膨胀;还有一个比较西化的词,叫变形,说的就是现实。
我3岁时上过北京友谊医院幼儿园,正对面是曾经的北纬饭店,后来又改称新北纬饭店,早年间是接待苏联专家,后来是有京味特色的星级饭店。在幼儿园混的日子没多长,唯一可以嘚瑟的是咱也在那儿经历过。最有意思的是,最近这个新北纬饭店已经与时俱进,成了示范性的老年公寓。在老街坊眼里,这改变多少有点让人找不着方向,作为西城最大的养老项目,是由央企、市属国企、厚朴投资联手打造,总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项目分为两部分,其中活力老人居住的“健康生活社区”,就是由新北纬饭店改造而成,而紧挨着的老北纬饭店将被改造成“持续照护社区”,供需要护理和康复的老人居住。老北纬饭店,不管外观是否照旧,内里肯定是面目全非了,据说这地方能被投资人看上,主要是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友谊医院仅一路之隔,附近还有宣武中医院,往远点还有宣武医院。而且,陶然亭公园和天坛公园近在咫尺,从房间里就能看见祈年殿。

说着小的扯到老的,也是当下国人最无法释怀的事吧。说自己,还依稀记得曾经的一个“六一”儿童节,在学校的操场上,“红小兵”的塑料臂章终于戴上了。从我在的小学往东走,几箭之地,有个香厂路小学,1967年11月,这个小学的二年级至六年级共有28个班,以年级为单位成立红小兵连,下设排、班,全校组成红小兵团,红臂章取代红领巾,他们居然搞成惊天动地。好笑的是这种状况也就持续了五六年,我们的脖子上又开始挂红领巾了。红领巾有布的,洗着容易褪色;有人造丝绸的,颜色红得亮眼。无论布的还是丝绸的,戴领巾都是有方法技术的,不讲究的毛躁的就不是戴而是系了,缺点就是戴一段时间边角部分极易破损。
说到这,一个大学同学发了条朋友圈,照片是坐东朝西对着永安路的一个建筑——北京职工服务中心,以前我们俗称它是“劳保馆”,后来演变成“技术交流站”,算起来它和附近的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前门饭店、光明日报社大楼、友谊医院、医科院、中央芭蕾舞团大楼、天桥剧场,还有周边一个模子的居民楼,都属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的产物,具有代表性。那些年除了大干部,平常人家里很少有报纸,想看报有个好去处,就是光明日报大楼下面的阅报栏。这大楼当年特漂亮,黄色瓷砖贴面,对面的前门饭店也是,只不过换成宫墙般的红色。现在再看,大多数都已经陈旧,北京职工服务中心这栋楼基本还是原来的模样,特别是门两边高大的塑像,以前是可以随便上去攀爬的,儿时的乐趣之一,现在肯定是不行了。
我从小在南城长大,家就在虎坊桥路口往南北京市工人俱乐部的后面,至今仍对这一带比较熟悉。虎坊桥的方位,是珠市口西大街与骡马市大街东西相接、南新华街与虎坊路南北相通,虎坊桥原为桥名,后演变为街名。据清朝程穆衡《箕城杂缀》记载:“虎坊桥在琉璃厂东南,其西有铁门,前朝虎圈地也。”在明清时,有条由北向南的沟渠,经过京华印书局西侧一直向南,通到先农坛的苇塘中,虎坊桥就是在这条沟渠上修建的石桥,大概在今天十字路口的西侧。西南角的北京市工人俱乐部是1956年1月建成的,主要是北京京剧团在此演出,每天一大早学校还没开始上课,墙那边已经在吊嗓子了,咿咿呀呀的好不热闹。《杜鹃山》我看过首演的观摩场,应该是全国的剧团被叫来学习。《沙家浜》的主演经常在马路边碰到,特别喜欢。前几年包给四川德阳的一个杂技团,旅游旺季,成天堆满了大巴车,就是彻底走下坡路的节奏。加上旁边的“虎坊桥人才市场”那叫一个乱,找个保姆小时工差不多,其前身为宣武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跟文化特别近的地方,有过去的京华印书局,现在归了中国书店,位于十字路的西北角,因其外形酷似航船,俗称“船楼”。前身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强学会书局官营印刷机构,于1884年始建,1905年被上海商务印书馆买下,改名京华印书局。1954年5月公私合营改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文革”时改称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其次是东北角的纪晓岚故居,雅号阅微草堂,至今已经有240多年。纪大人在这儿住了两个阶段,分别是从11岁到39岁,从48岁到82岁,前后共计62年。还有一个地方就只剩故事了,早先,在珠市口西大街有公共汽车站叫“给孤寺”,老北京人没有不知道的。先说给孤寺的念法,在此可不能“望文生音”,正确的读音是“机古四儿”。此寺原先在纪晓岚故居东200米,相传是在唐贞观年间建的,明代称寄骨寺,清顺治时重建后称“万善给孤寺”。进入民国,给孤寺建起了一个剧场——“第一舞台”。据说这是一座有别于老式茶园、能容纳2000人的新式大剧场,还有转台,当年杨小楼、梅兰芳、九阵风、余叔岩、尚小云、小振亭等京剧名角一起在这儿联合赈灾义演。可惜的是1937年的一场大火,“第一舞台”被彻底焚毁。
清朝在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八旗居内城,汉人居外城。在宣武门以南菜市口、珠市口的外城,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京官、士子聚居的地方,人们称之为宣南。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指出:“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北京老城区的命运从此发生转折,宣南的、西城的,粗放式的拆迁没有了,保护走上了正轨。保护老城,不得不说新中国初创时期的建筑,晚清民国时期的建筑该如何保护好、使用好,也是不可忽略的课题,之前的大拆大建是有遗憾的。1993年,两广大街的拓宽,拆除了菜市口路南烂漫胡同口的黑猴百货店、北半截胡同口的新华书店和人民照相馆。黑猴百货店,店主人养过一只黑猴,机灵乖巧招顾客喜欢,时间久了,人们不说正式的店名,就叫“黑猴儿店”。后来黑猴死了,店主人就照它原来的样子铸了个小铁猴放在门口,附近的老住户,买不买东西,都愿意过来摸一摸它,时间久了居然把猴头摸得锃亮。菜市口东北角,有名的菜市口百货商场,体现改革开放老百姓富裕起来的“黄金第一家”,被迁到了白广路北口,原址变成了国家版权局大楼和沃尔玛商场。鼎鼎大名的西鹤年堂药店为了给地铁4号线让路,也搬离了原址,说清代的菜市口刑场,没了这个地标,一切就只剩下传说。

现在看,西城区是北京营城建都的肇始之地,加强修补刻不容缓,加快腾退迫在眉睫,落实好《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是重要工作。今年西城区“两会”期间,区文委主任孙劲松介绍,除了传统民居外,众多不可移动文物也将得到修缮与利用,绍兴会馆、京报馆、庆云寺等已经进入设计招标阶段,预计2020年亮相。位于骡马市大街51号的福州新馆(林则徐故居)由于房屋老化严重,要加固房屋基础替换房梁,工程量很大,完成后将成为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据林氏后人编著的《林则徐与中国图录》及《林则徐日记》等资料记载,林则徐不仅长期参与“福州新馆”的活动,而且为之筹建出力甚多。如他在日记中提到: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上午“偕同乡诸人往虎坊桥董宅,议买房屋为福州新馆,即于是日成议”;四月十二日早晨“赴万隆号,备福州新馆屋价”;同年十二月十三日“赴福州新馆商议修屋”。这骡马市大街51号福州新馆的历史渊源,据说是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由旅京的福州籍官员陈若霖舍宅而建。陈若霖为陈宝琛曾祖,官至刑部尚书,为政清廉,流传的“陈若霖斩皇子”故事为家乡人津津乐道。他听说建新馆急需要地皮,在辞官告老还乡时,特将其府宅捐赠同乡会作为福州会馆。今年说这些还有层特殊意义,因为2019年是“虎门销烟”180年,想当年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坚决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史例,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禁毒壮举。
(编辑·刘颖)
51498473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