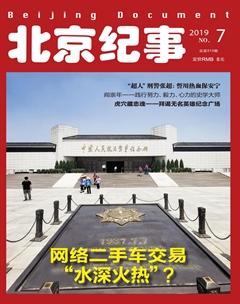那些痴情的狗儿们
翻看《现代汉语词典》,凡带有“狗”字的成语,几乎没有一条不是骂人的。如“狗急跳墙”“狗头军师”“狗苟蝇营”“狗血喷头”“狗仗人势”“狗眼看人”,等等。尤其那条“狐朋狗友”,更是对狗这种一生忠于主人、忠于友人的动物的极大诬蔑!
作家巴金先生在他那篇著名散文《小狗包弟》中,叙述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一位艺术家特别喜爱隔壁人家饲养的一条小狗,时常喂它一些食物,因此他们成了朋友。“文革”期间,艺术家被拖着去游街示众,说他是“里通外国”的反革命,他不承认,专政队棒棍齐下,把他的一条腿打断。他满身血污地趴在地上,认识他的人都一个个转身躲了去。这时,忽然从人丛中跑出那条小狗,一下扑到他身上,到处闻着,并用它的脚爪在他身上不停地抚摸,还用舌头舔他脸上的血污。专政队驱打它,它也不走,最后专政队用木棒打断了它的后腿,它才哀叫着逃去……
艺术家被关了几年,放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上几斤肉去看望那条小狗,主人告诉他,那天小狗负伤跑回后,喂什么都不吃,哀叫三天就死了。
狗,是最通人性、最有良心的。
听母亲说,我幼小时,全家曾在石家庄住过,当时家里养了一条叫花子的母狗。那年,正当全家准备搬去北平定居时,花子却生下一窝小狗。善心的奶奶含着泪花对花子说:“花子,火车上不让带你们啊,我们不能把你带走了,你要带好你的孩子们……”临走那天,母亲还给花子母子做了一大盆食物。聪明的花子好像已经明白了主人的决定,几辆搬家的车子启动时,它耷拉着尾巴,领着几只小狗,低垂着头,一直送到火车站……

两年后,父亲去石家庄办事,顺便去看望邻居,老邻居热情地留他吃饭。那时候,石家庄老百姓住的都是平房,家家都是土炕,吃饭就在小炕桌上。正当父亲坐在炕桌一侧吃饭时,一条溜进屋来的大野狗一下蹿上土炕,把父亲吓了一跳。野狗用两只爪子抱着父亲的双肩,用舌头不停地舔他的脸。等父亲认出这条脏兮兮的野狗正是花子时,这个一生从未掉过泪的硬汉子,也禁不住抱着花子大哭起来……
狗对主人无比忠贞,一旦它在情感上遭到了巨大的伤害,它将会怎样呢?
那是2003年第20期《读者》上刊登的一件真事:台湾一位计程车司机曾在多年前养过一条狼狗,因它后来长得太大,且食量惊人,加之叫声奇响,时常吵得四邻不安,最后决定将它丢弃。他把狼狗装进布袋,开车到一百多公里外的深山放了,狼狗在车后追了好几公里才消失掉。一周后的一个深夜,司机听到碰门声,开门一看,是那条狼狗又回来了,只见它形容枯槁,极为狼狈,显然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艰苦奔跑和寻找。这位司机决心既定,二话没说,再次把它装进布袋,开车到更远的地方——沿北宜公路狂奔到宜兰,一路上狼狗在袋中不停地低声哭嚎。待车停下,打开布袋时,发现袋中到处是血,原来它已伤心至极,将自己的舌头咬断两截,悲壮地自尽了……司机悔恨万分,将它厚葬,并时常专程前去焚香祭拜。
狗,对主人的忠贞情谊,对友人的怀念举动,恐怕是人类都做不到的。
1969年,在大批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期间,北京知青张同学等一行数人去了陕西插队,住在某村村北一排简陋的房子里。因为偏僻,村里又不通电,队长说,养只小狗吧,晚上孩子们外出好做个伴儿。几天后,队长当真送来一只毛茸茸的小狗娃。刚来时,瘦骨嶙峋的它,睁着两只大眼睛看着知青们,孩子们很爱它,大家动手给它垒了一个不错的窝,因一身黄毛,起名大黄。
知青们吃什么就喂它什么,在孩子们的呵护下,一年刚过,大黄就长成一个健壮的“大小伙子”了。不管晚上谁外出,都是大黄保驾。
到了1975年,大批知青返城了。当时,孩子们返城,都是先坐马车到15公里远的公社办完手续,然后乘汽车去火车站。不论哪一批人走,走几个人,大黄都是跟在马车后面跑到公社。只是孩子们归心似箭,到公社后就忙着搬行李、办手续、上汽车,谁也没顾上再看一眼大黄。
等到张同学最后走了,大黄就呆呆地坐在汽车站,望着汽车远去的方向,等啊,等……
从第二天开始,天一亮,大黄就爬出狗窝直奔公社跑去,跑到公社附近那个汽车站,就开始两眼望着汽车远去的方向,待上好一会儿才失望地返回。
就这样,大黄每天一个来回30多公里,天天如此,一直坚持了3年多……
它一直住在原来的窝里,队长几次把它拉回自家,但只要不拴,它就跑回去。后来知青们当年住的房子几处房顶都倒塌了,大黄却仍旧守在那里,苦苦地等待着小主人们的返回。
两年后的一个冬天,大黄老得不行了,它实在跑不动了,连水也喝不进了,但每天还朝着公社的方向凄凉地望着,望着……
几天后,大黄终于死在窝里,队长把它拉出准备埋在后坡。突然,老队长惊奇地发现,大黄身下竟压着3封张同学前年写给队里的信,是要求队里给他补办一些手续的。为这三封丢失的信,队长还跟婆姨发过几次好大的火,怨她没收好,原来竟是被大黄偷偷地衔走了。
20世纪90年代,当老队长来京看病,住在张同学的家中,向他诉说了大黄的感人故事,张同学哭着说,等退休后一定再去陕西,好给大黄的坟上添一把土,为它终生的等待鞠一躬,为自己对朋友的负心深深道歉……

作家冯骥才在法国访问时,曾有机会参观了一座特殊的墓地。这座建在塞纳河畔,叫作阿斯尼埃尔的狗的公墓,到处长满花草树木,一排排整齐的墓碑仅比人的小些,坟墓造型美观,式样极少重复,碑石上一一刻着狗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有的还记载着墓中的狗生前不凡的业绩。一座墓碑上说“墓主”一生中曾荣获“7个冠军”。另一块墓碑上刻着:“这只狗曾救活了40个人,但它却被第41个人杀死了。”
许多碑文甚是感人:
“自从你离开我,我没有一天眼睛里没有泪水。”
“你曾经把我从孤独中救了出来,现在我怎样救你?”
“咱们的家依然有你的位置,尽管你自己躺在这里。”
“想到我曾经打过你,我更加痛苦!”
……
许多坟墓旁还塑造了各类精美的雕像,每个墓碑前的大理石台上,还放着各式各样的陶瓷制成的小狗、小猫、小车、小娃娃、小枕头等,这都是狗主人来扫墓时摆上去的。
那天,当作家夫妇刚刚走进阿斯尼埃尔时,正碰见一位胖胖的老年妇女由一个男孩陪同从里面走出,这一老一少的鼻子都通红,显然他们是刚为爱犬扫完墓后,还处在十分悲痛之中……
近百年来,不知多少有关狗的故事被中外作家、艺术家写入书中、搬上银幕,感动着成千上万善良的人。
1946年,13岁的我,和家人一起在上海沪光影院观看一部叫作《义犬寻主》的美国彩色影片(那也是我第一次观看美国影片),当看到那条名叫莱茜的义犬,从遥远的一个小岛上逃出,历尽千辛万苦,遍体鳞伤,一步4个血脚印地去寻找它从前的穷主人时,全场一片抽泣声,当年5岁的祥麟小侄竟感动得放声大哭起来……
我深深感到,任何一条狗的品格,都比某些人高尚。在文革中,有卖友求荣的“朋友”;有踩着朋友的肩膀“往上爬”的“朋友”;有背信弃义,为了自己飞黄腾达,将朋友置于死地的“朋友”。而在狗中,却没有一条是那样卑鄙的败类。
所以,我便觉得,一个人如果真能结识到一个或几个像狗那样忠诚的“朋友”的话,那他真是再幸运不过了。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