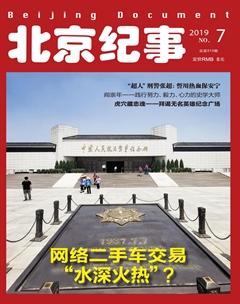“一对一”公益活动发起人岑赫

著名的百色起义的发源地——广西省百色市,是广西内陆面积最大的地级市,拥有“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称号。同时,百色也是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大石山区、贫困地区、水库移民区。在这种环境下,尽管国家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但是仍然还有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因为无法解决基本生活保障而失学。
有这样一位广西百色人,出生于60年代末——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困难的时期,在党和国家的帮助以及自己的努力下,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现在,成为会计师事务所所长的他,不忘初心,反哺家乡,发起并主办了“一对一”资助贫困学生公益活动,帮助了50余名失学或即将失学的少年儿童——他就是岑赫。

岑赫说,他之所以会十分重视教育精准扶贫,并发起“一对一”公益活动,与自己的出身和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1980年代,成绩优异而家里却较贫困的岑赫,被选拔到县里最好的中学就读于“民族班”——类似于后来的“宏志班”,学费、书费、生活费都由党和政府负担。岑赫说:“这一举措,使许多和我一样读不起书或者读到一定程度就辍学了的优秀学生,得以继续留在课堂,接受教育。这说明,党和政府很重视人才的培养。”3年后,岑赫又被选拔到省一级的“广西民族学院预科部”读高中。广西民族学院就是现在的广西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学院预科部”,选拔的都是学习好、家庭贫困的孩子,在这个班读3-4年高中,目的是培养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人才,所有的费用都由政府承担。“我在高中的时候,跟本科生待遇一样,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本科生还要好一点。我们那届选拔的孩子,上本科的有60多个人。这在当年来说还是很难得的。”岑赫回忆道。这六年的求学生涯,使岑赫一直对党和国家,对自己的家乡,怀着浓浓的感恩之心。
除了自身的经历,岑赫的家族也有着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传统。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岑赫的先祖,素有“开明官僚”之称号的山西巡抚岑春煊,在山西创办了山西大学堂中西两斋。山西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堂之一,和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一道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纪元。直到现在,山西大学坞城校区的山西大学堂景点门前,还矗立着岑春煊的雕像,显示着学校百年的厚重历史,显示着岑家先祖对教育事业、教育兴国的深刻理念。1938年8月,百色学院的前身,广西省立田西师范学校成立,岑赫的先祖岑永杰受命为校长。建校时,正值抗战艰苦岁月,首任校长岑永杰提出了“推进边区文化,培养卫国英雄”的办学指导思想,目的是为边远山区培养合格小学师资。

岑赫的父亲,也是一位人民教师。在祖辈、父辈的耳濡目染下,岑赫对教育领域和教育行业也有着很深的感情。秉承着这份深厚的感情,怀揣着报效祖国、回报家乡的愿景,这些年来,岑赫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教育事业尽一份力。近年来,岑赫发现,国家对教育事业越来越重视,形势也越来越好,于是他也着手将自己多年的想法付诸实践。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该如何扶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怎样才能做到精准扶贫?”岑赫告诉笔者,“前些年我回老家的时候,亲朋好友的孩子,谁有困难了,或是生病了、没路费了,我能帮忙的一定会尽力帮。后来我发现,这些帮助只能是临时的,不是长久之计。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我觉得教育扶贫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后来我萌发的‘一对一’扶贫活动的想法,我觉得这应该属于‘精准扶贫’的一部分。”
2009年,岑赫发起“一对一”资助贫困学生公益活动。活动资助的学生都是家庭经济条件非常贫困而面临失学的孩子,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一直扶持到高中毕业。有些资助人,学生到大学之后家庭条件困难的,他们也会出于自愿继续资助。岑赫告诉笔者,一年级的孩子刚开始接受教育,还没有定性,而年纪稍大一些,基本就能看出这个孩子的学习态度是否端正、天资够不够聪颖,学习成绩是否良好。另外,受资助的学生必须品行端正、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在同样条件下,优先考虑少数民族的学生。
岑赫说,活动资助的不仅是小学和初中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而是把高中阶段也囊括其中,这是很关键的。岑赫在家乡看到,很多孩子刚刚初中毕业或初中肄业就到外面大城市去打工了。“一是家庭困难、上不起学,再加上外出打工挣钱,诱惑力比较大,一出去就‘收’不回来了。孩子们过早进入社会,对他们的成长也有一定的影响。一旦不好的影响形成,再想改变就太难了。”岑赫不无担心地告诉笔者。
岑赫认为,从农村来讲,更能体现教育改变命运。他说:“这不仅改变受资助的学生,也会改变他的下一代。另外,受过教育的孩子,对父母、对长辈也会更有孝心。我们现在资助的学生,女孩儿比男孩儿多一些。这是因为,特别在农村,女孩儿受教育的保障性更低。比如我的几个表妹,都很聪明,但她们读完小学家里就不让读了——因为家庭困难。这真的非常可惜——本来她们应该有另一种道路。所以,我们在资助当中对女孩儿更偏重一些。”
“一对一”公益活动,资助人均为品行良好、富有爱心的人士,主要为北京地区的各界人士及教育机构等。岑赫说,从事会计师事务所这个领域,会接触到社会各界的客户,也认识了很多朋友,有国企的也有民营的,囊括各个行业。接触时间长了,岑赫发现,有很多客户都很有爱心,愿意为公益事业作奉献。岑赫把自己发起的公益活动跟大家一讲,很多人都踊跃参与了进来,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公益平台。资助人将资助资金汇款到学生本人姓名的银行卡上,不通过其他任何个人和中介机构。资助钱款随着成长阶段和学习辅导资料增加而增加。一般为小学阶段200元/月;初中阶段300元/月;高中阶段400元/月。活动规定,任何人和机构,包括发起人、各地联系人、教育部门、学校等,不得收取任何费用,确保资助资金全额用于受助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岑赫说,在做“一对一”公益活动的过程中,他一直坚定一个想法——这个活动是“资助”,而不是“承包”。岑赫告诉笔者:“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会资助过多。无论如何,父母、家人对孩子的教育责任是第一位的。我回老家的时候,见到受资助学生的父母,聊天的时候也会跟他们说,除了资助的学杂费以外,若是家里突然有什么困难,咱们再想办法。但你们作为家长,也要努力为孩子创造条件。”“一对一”公益活动目前所定的资助金额,专款专用,基本能保证孩子们顺利完成高中学业。有很多资助人看到自己资助的学生学习很努力,成绩也不错,家里又确实困难,还想进一步再帮孩子一把。岑赫就会建议他们,可以给孩子们买一些课外书或者文具,冬天的时候也可以给孩子们添置些厚实、暖和的冬衣。“我们平台一般都会建议资助人通过实物奖励孩子们,而不是直接给钱——也就是说不能‘承包’。”岑赫告诉笔者,“我还向资助人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比如说一个小学的孩子,你愿意一个月资助400元,还不如资助两个学生,让更多的孩子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另外,资助人一旦决定资助,即表示公开承诺,从小学一直资助到高中毕业。岑赫解释,之所以如此规定,是要给受资助的学生一个长期的希望。岑赫说:“这个‘希望’的意思是说,孩子们能清楚地知道,只要自己专心、努力地学习,资助就会一直延续到高中毕业,而不是只给一两个学期,突然就断了。这种希望对孩子们心理的良性影响,我觉得应该很大。当然,这是我们跟所有资助人提出来的一个建议。”

岑赫告诉笔者:“我和好朋友钟建国先生——我叫他钟哥,还有几个朋友一起,下周要到县里去看资助的孩子们,看看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状况,顺便送一些文具、学习用品。钟哥特别细心,特意给孩子买了新的字典,还精挑细选了笔和画板等一些文具。”岑赫告诉笔者,在公益这方面,他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觉得这件事应该能够一直做下去。
“一对一”公益活动,至今已有凌云县、田阳县、西林县的近60名学生得到资助。岑赫说,这个活动不要求数量,只要求质量——精准教育扶贫的质量。岑赫介绍道:“早年我自己资助的几个学生已经大学毕业了,包括北京林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百色学院,等等。毕业以后就看他们自己的发展了——毕竟接受过高等教育了。”“一对一”活动现在正在资助的学生有50多个,大多数学习都不错。但也有三四个孩子中途发生变化。比如,小学的时候挺好的,但到中学以后,受到环境、家庭或个人条件的影响,孩子不爱读书,成绩也一落千丈。“主要是态度上的问题,不是因为孩子不够聪明、学习跟不上之类的,而是他自己不愿意学习。”岑赫说,“其实我也好,资助人也好,并不指望孩子们学习成绩好到什么程度,非得考清华北大或者名牌大学。只要他们尽自己的能力,能够考上相应水平的高等院校,正常接受教育就可以了。”
“一对一”公益活动要求受资助的学生,每个学期要给资助人写信汇报学习成绩和生活情况。岑赫告诉笔者,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孩子们写信的时候,可以熟悉信件的格式和写法——现在人们联系基本上都用手机或者微信等等,很少有人会写信了。另外,写信的过程中还能够锻炼孩子们的书面表达能力——老师们也说读书还是要勤“写”。除此之外,在受资助的学生在与资助人通信互动的过程中,能够多与外界接触,开阔自己的眼界,还能让这些孩子从小就知道世界是有爱的,自然而然地就能懂得感恩。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比单纯的说教要有用得多。岑赫说:“看着孩子们一年一年地成长,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再到上大学,我就觉得能尽能力做这个活动非常值得。”
慢慢地,“一对一”公益活动资助的学生已多达几十个,岑赫开始觉得单靠个人来维护这个平台,有些力不从心了。他说:“特别是小升初以及中考阶段,孩子们的信息很容易‘断档’。”受资助的学生升学后,之前的班主任只知道孩子考上哪个学校,具体班级基本都不清楚;而新学校的班主任,又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受资助的。岑赫解释说:“农村的学生一般都不是很活跃,也不太爱说话,他们不会主动跟老师讲自己的情况,那么有时候就会和资助人失去联系。”
2017年,北京奔向未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接了“一对一”资助贫困学生公益活动,负责联系资助人和被资助学生。公司董事长任颖博士是岑赫的好朋友,也是一位知名爱心人士。
岑赫介绍,“奔向未来”有丰富的资源,还有专人时刻跟进学生的信息,使这个平台运转得更加顺畅。岑赫和“奔向未来”,全都是公益性质的,不会向资助人或受资助的学生收取任何管理费,他们双方对接以后,平台会始终关注双方的信息,但决不会过多打听、干预他们。岑赫说:“我有这个很好的平台,也有一定的能力做这项公益活动。这个能力不是我个人的,而是通过认识的一些朋友,大家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尽可能地帮助面临失学的孩子。”
2017年国庆长假,“奔向未来”在北京组织了50人左右的团队——主要是资助人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到资助的小学做公益活动。岑赫回忆说:“当地的孩子和北京这些孩子,之前已经结成对,都互相认识了。孩子们刚见面时,无论是自我介绍还是上台表演,都能明显感受到北京去的孩子更加活跃,而当地的孩子基本都很腼腆——坐在那儿怯生生地看。不过,没多一会儿,孩子们就熟了,很快就玩到了一起。”资助人家庭不但参观了当地的学校,还到一些当地学生的家里去拜访。岑赫告诉笔者,北京去的孩子都觉得当地生活很新鲜,包括地里的农作物甚至猪栏里的小猪崽。他们也看到,原来同龄人还有这样学习和生活的——这些当地的小伙伴,即使想买一本书、一个铅笔盒也很难很难。回到北京,有不少孩子写作文的时候都说,这次活动对自己的触动很大。
采访的最后,岑赫告诉笔者:“我们毕竟能力有限,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做一些事——做得不大,但会倾尽全力做到最好。现在有“奔向未来”这个团队加入进来,我们也不打算一下子扩充得太大——这样很容易就会流于形式,而且还会有一定的副作用。我们初步计划,明年继续将这项公益在百色市西林县以及周边地区做扎实,5年之内可能会涉及其他地区,比如贵州等省市。”
(编辑·张子乐)
kelemyt@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