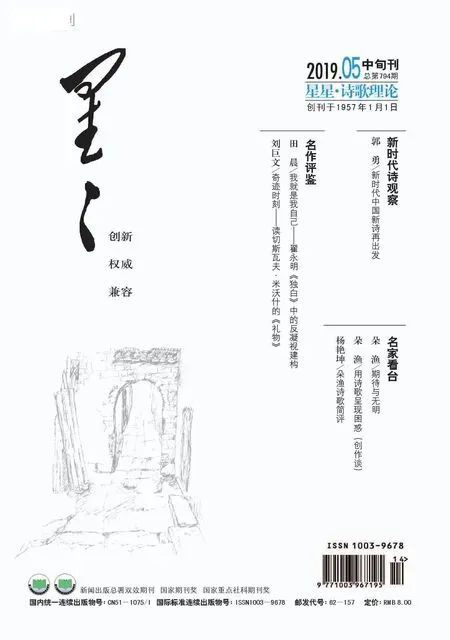我就是我自己
——翟永明《独白》中的反凝视建构
■ 田 晨
独 白
翟永明
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
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
二者合一,你把我叫做女人
并强化了我的身体
我是软得像水的白色羽毛体
你把我捧在手上,我就容纳这个世界
穿着肉体凡胎,在阳光下
我是如此炫目,是你难以置信
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
看穿一切却愿分担一切
渴望一个冬天,一个巨大的黑夜
以心为界,我想握住你的手
但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
当你走时,我的痛苦
要把我的心从口中呕出
用爱杀死你,这是谁的禁忌?
太阳为全世界升起!我只为了你
以最仇恨的柔情蜜意贯注你全身
从脚至顶,我有我的方式
一片呼救声,灵魂也能伸出手?
大海作为我的血液就能把我
高举到落日脚下,有谁记得我?
但我所记得的,绝不仅仅是一生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讨论了全景式监狱中凝视者与被凝视者之间存在着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被囚禁者时刻处于狱警的监督之下,被一种“权力局势”所制约,行为也随着监视而被规训。凝视是权力的象征,是对他人的文化规训和道德引导。而在男性秩序的主导下,社会对于女性的凝视亦是复杂而多变的。女性是被注视的第二性,其肉体和精神在男性凝视之下也将被塑造成社会期待的模样。
《独白》一诗,为翟永明组诗《女人》中第三辑的一首,诗歌中的“我”用一种宣泄式的独白,在多处意指男性凝视。全诗甫一开头,便表明了这个“独白”女人对于自身命运被操控的清醒认识——“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诗人笔下的“我”,虽充满“狂想”,拥有深不可测的魅力,但是,我因“你”而生,继而被“你”命名为“女人”,我的“身体”在“你”的注视下按照“你”的期待不断被“强化”。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认为,女性内在拥有一个“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两个既有联系又截然不同的身份因素。女性作为被注视着的客体,身体受到男性的凝视,也会从内部以男性的目光注视自身。“我是软得像水的白色羽毛体”。诗人对于“我”的身体的观察和描述,实际上是在表现男性对于女性完美身体的一种观看,“白色羽毛体”这一喻体,它轻盈、洁白,柔软似水,相对应的女性身体作为本体不过是男性的一种欲望对象;同时,在《女人》组诗中多次出现的“太阳”意象象征着男性秩序,而在本诗中,“肉体凡胎”的“炫目”亦摆脱不了阳光照射的原因,“我”是因“太阳”而美丽的,女人的美丽源于男人的希冀。因而并非女人自身在欣赏和肯定自己的身体,而是女人内部作为男性的“观察者”在以男性的标准,注视自己。
被男人所“形成”的女人,自然受困于肉身对男性的取悦,同时也无法摆脱精神上的依附性——“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看穿一切却愿分担一切”。男权社会对于女性道德的规约,造就了男性理想中那个“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温驯、服从被当作正统的女性应有的品性。作为女性,“看穿”的是生而为女人的种种现实宿命,“分担”的是社会对女性既定角色的规定。权力凝视对女性的灵魂自由进行着悄然的压迫,基于这种不对等关系,无论女性的觉醒多么充分,无论多么渴望“冬天”与“黑夜”以期对自己的“清醒认识”和对自身“怯懦的摧毁”(翟永明《黑夜的意识》),一旦在男人面前,她的“姿态”瞬间变为“惨败”。觉醒的女人也难逃“惨败”的命运,此时诗人的“独白”已经转为无可奈何的“喟叹”。
除了对男性凝视的意指,《独白》同时以“黑夜意识”为武器进行反凝视的建构。“黑夜意识”是翟永明在创作《女人》组诗之后提出的诗学理论,包含着反抗外在压迫的意识和服从内心真实的意识两个方面。女性首先要意识到自身受到男性标准的影响,以此反抗和摆脱自身既定的角色,还要意识到女性身份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并因其独特的生命体验,而拥有独到的人生见解,即翟永明所说的既“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真实的召唤”。(翟永明《黑夜的意识》)
反抗意识是女性追求独立、脱离男性中心话语的主体意识,“我”渴望“黑夜”和“冬天”就是对象征着男性秩序的“白昼”和“阳光”的反凝视。但是,“真正的‘女性诗歌’不仅意味着对被男性成见所长期遮蔽的别一世界的揭示,而且意味着已成的世界秩序被重新阐释和重新创造的可能。”(唐晓渡:《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翟永明在此诗中“重新阐释”和“重新创造”世界的策略,便是通过女性书写服从自己内心的真实。“用爱杀死你,这是谁的禁忌?/太阳为全世界升起!我只为了你/以最仇恨的柔情蜜意贯注你全身/从脚至顶,我有我的方式”。有别于传统女诗人要么“固守传统美学”而显出的小女人情怀,要么模仿男性口吻、“追逐男性气质”的书写,在这首诗中,诗人是以充满女性特质的方式在书写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爱”却“杀死”,“仇恨”但“柔情蜜意”这种理性世界里的悖论,在女性经验里却是一种复杂激烈的情感方式,是女性的真实反应,所以即便在分别的时刻,“我”仍然在坚持“我的方式”;另外,不同于男性书写的清晰和理性,诗中絮叨式的独白,以及大海、落日这些宏阔而跳跃的意象,造就了一种迷离、悠远又神秘的意境,契合于女性心理的千变万化和捉摸不定。以上种种对女性“内心真实”的服从,亦是对男性书写的反动。
因为服从于内心的真实,女性成为她自己,而不是任何人的附属。“一片呼救声,灵魂也能伸出手?”靠自己的灵魂拯救自己,“我”才能承担自身的命运,而非被规定。“大海作为我的血液就能把我/高举到落日脚下,有谁记得我?/但我所记得的,绝不仅仅是一生”。“日落”之后,属于女性的黑夜来临,那些在黑夜中觉醒而独自美丽的女性,即便因为不再“炫目”而没有人记得,但却因为黑夜的意识,超越此生命运的局限,以女性真实的角度展开对自身、社会、人类的全新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