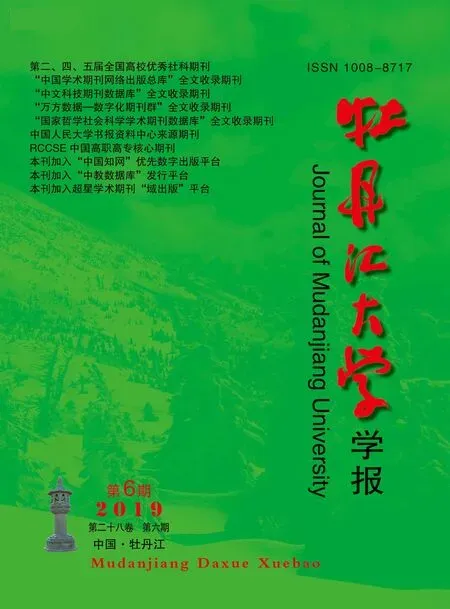《永远的尹雪艳》人物形象新论
何 春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33)
引言
台湾作家白先勇的经典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自1965年出版至今,受到了评论界不小的关注与重视。关于这篇小说的评论文章不胜枚数,在谈及白先勇文学作品时,这篇小说也是必然会被提及的白先勇代表作之一。笔者在读了这篇小说及相关评论文章后,生发了不少有别于此前评论家解读的一点看法。
关于这篇小说的评论大致是从以下几个角度切入:一是时间角度,或谈尹雪艳的不老以及小说中其他人的老去,表现白先勇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与悲悯;或谈尹雪艳等第一批从大陆到台湾的移民今不如昔的怀旧与乡愁,表达白先勇对传统文化堕落的担忧与反思;二是从主人公尹雪艳人物形象角度,或批判地将尹雪艳“非人化”,象征为死亡的化身,是魔,是幽灵,是无常;或将尹雪艳纳入特殊年代里女性弱势群体地位写她的无奈与自我救赎;三是从其他如色彩、意象等新批评角度进行阐释。
但归纳起来此类文章一般都认为尹雪艳是不老的,是非正常人的。本文将从时间和尹雪艳人物形象这两个方面论述笔者重读了《永远的尹雪艳》后的一些观点。
一、尹雪艳并非不老
小说一开篇确实写道:“尹雪艳总也不老”,不少评论文章便是抓住这句看似提纲性的句子生发开去,得出尹雪艳是置身时间流逝之外一个不老去的女人,是一个幽灵,无常。如果将“尹雪艳总也不老”理解为尹雪艳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一直是一个年轻漂亮的甚至“吃人”的女人,似乎窄化了这句话的多重含义,甚至是片面解读了这篇小说,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其实是将“老”写得淋漓尽致的一个巨大的讽刺!
“老”这个字的含义是丰富的,它可以指人年岁大;可以指老年人;可以委婉指人去世;也可以指对某些方面富有经验,如老练、老手;可以指很久以前就存在的,如老朋友;也可以指陈旧的,如翻老账;也可以指原来的,旧有的,如老地方;还可以指(蔬菜)长得过了适口的时期,与“嫰”相对,如油菜长老了;甚至可以指(事物)火候大了,如鸡蛋蒸老了。通过阅读文本,我们发现围绕尹雪艳总也不老,作者恰恰写尽了“老”的多重含义。有人说尹雪艳是身处时间之外的人,众多的男人、女人迷恋尹雪艳是想从尹雪艳这里享有时间。这样的观点读来像看一篇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尹雪艳总也不老”不是一句肯定性的句子,而是以尹雪艳看似总也不老写尽了世事沧桑、人情变化、岁月流逝之下的老去。不读出这一点,单靠文本中几句说尹雪艳总也不老,就得出一系列“时间之外的人”的解读似乎忽视了白先勇作为现代派小说家的立场。
白先勇是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应该是具有现代派的审美追求的。现代派小说与古典小说的一个不同点是,现代派小说尽可能将作者隐藏在文本之后。“现代派小说理论认为小说应该成为舞台,纯粹由剧中的人物自己去表演。博纳科夫在《洛莉塔》中写了亨伯特勾引十二岁的养女的故事。当有人向他说起,‘您深感亨伯特和洛莉塔的关系是不道德’时,他答道,‘深感亨伯特和洛莉塔关系不道德的不是我,而是亨伯特自己。他关心这些,而我不’。”[1]在《永远的尹雪艳》中,也可以说认为尹雪艳总也不老的是剧中人,而不是白先勇。读者在阅读小说时,以旁观者视角不仅看到了尹雪艳的老去,而且尹雪艳所在的那个上流社会在老去,尹雪艳身处的时代也在老去。以尹雪艳为中心的这个群体就像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那个裹挟在时间之流中整体走向毁灭的马孔多镇,看似不老是没有意识到生命的重复性与整体飓风式消逝。
以下我们便具体分析小说是怎样以不老写老的。尹雪艳的年龄大概是三十多将近四十,年近四十的女性算不上很老,但也说不上年轻。十几年前尹雪艳的迷人是“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2],百乐门时代的尹雪艳确实是靠着年轻、美貌、风韵吸引着人,但年近四十的尹雪艳迷人早已不是那风情了,而是尹雪艳这个中年女人广泛的人脉,练达的人情。尹公馆的女主人凭的是干练、周到、妥帖的职场服务和历经世事后人事交际的虚伪、逢迎。“尹雪艳在台北的鸿翔绸缎庄打得出七五折”,“吴燕丽唱《孟丽君》的时候,尹雪艳拿得到免费的前座戏票,论起西町美食、看绍兴戏,尹雪艳又是无一不精了。”[3]“尹雪艳是一个最称职的女主人。每一位客人,不论尊卑老幼,她都招呼得妥妥帖帖。”“她对每一位客人的牌品及癖性都摸得清清楚楚。”[4]这不仅是尹雪艳年龄上的老去,更是尹雪艳经历世事后,在应酬方面的老练,富有经验。
其次,聚集在尹公馆的多是十几年前在百乐门捧尹雪艳场的老朋友以及他们那班太太。“老朋友”们有些头上开了顶,有些两鬓开了霜,太太们也是经历了十几年的往事沧桑,而尹雪艳给他们的感觉是还透着十几年前“上海大千世界的繁华”,“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5],这样的尹雪艳是老旧的,周身透着旧时代气息。认为尹雪艳总也不老的是一批和尹雪艳一起走向衰老而不自知或不愿承认,沉缅于往日繁华的没落官绅和他们的太太们。
主要和这样一群已迈向年老的人打交道的尹雪艳又怎么可能不老呢?就像小说中写道的那样:“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互相宰割。”[6]这是怎样一种苍凉的、老气横秋的心态啊!
再看尹雪艳对待王贵生、洪处长和徐壮图的三种不同方式,王贵生下狱枪毙的那一天,尹雪艳在百乐门停了一宵,算是对王贵生致了哀。一个舞女能为一个获罪下狱的死囚停舞一宵致哀,在该明哲保身,撇清关系时,红遍了黄浦滩的尹雪艳没有过多顾虑自己的名声,百乐门停舞一宵既是表达自己的哀思,也是公开承认与王贵生的事情,应该说是一个年轻舞女有情义的表现了。到洪处长,丢官破产,闲职也没捞上时,尹雪艳带走了自己的全部家当,还带走了一个名厨师两个苏州娘姨,此时的尹雪艳已不是那个年少无知的百乐门舞女了,她知道痴情无用,明哲保身,安排好自己才是主要的。所以尹雪艳离开了洪处长,不仅带走了自己的家当(既然强调自己的家当,是否尹雪艳一直留着心眼将自己的财产单独保存的),还带走了能帮自己创业的三个得力助手。以上两位费尽心血才接近到红极一时年轻漂亮充满风情的尹雪艳。到徐壮图,尹雪艳直接放下身段主动接近,因为她知道自己不再有年轻女子的魅力,而且与人打交道不再像此前一样处于被动局面。徐壮图的不幸遇害没有给尹雪艳造成任何影响,因为此时的尹雪艳已是交际场所吃人不吐骨头、讲求实利、翻脸绝情的老手了。她款款地去给徐壮图遗像鞠躬,跟徐夫人握手,甚至抚摸了一下两个孩子的头,像一个上司去悼念遭到不幸的下属一般。徐壮图的死对尹雪艳来说是无足轻重的,此时的尹雪艳已老辣到无情无义、虚情假意,所以当晚她依然可以笑吟吟的跟别的男人周旋,“干爹,快打起精神来多和两盘。回头赢了余经理和周董事长他们的钱,我来吃你的红!”[7]
这个看起来依旧妖艳美丽的尹雪艳其实情感上越来越苍老,淡漠;处事方面越来越老练,老谋深算;对自己的利益也越来越看重。这个总也不老的尹雪艳其实一直在苍老,和她所在的那个群体一起衰老,这是一个逐渐老练、老辣、老谋深算的从年轻走向衰老毁灭的实实在在的女人。
二、尹雪艳形象新论
对尹雪艳持批判观点的文章把尹雪艳看作“非人化”的负面形象,如欧阳子女士“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8];朱美禄在《斑斓的色彩,丰富的意蕴——白先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色彩与意象分析》中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尹雪艳就是一个活无常”[9];王德威教授也说,“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是‘中国祸水传统里的又一高潮’”[10]。这样对尹雪艳的评价笔者认为是功利主义思想和男权话语的,将尹雪艳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与尹雪艳纠缠的三个男人两死一落魄,评论家在批评尹雪艳时是否可以说是因为三个男人的生死比一个女人的性命重要这种极端功利主义思想呢?评论家们只看到了与尹雪艳有瓜葛的三个男人没有好下场这个结果,似乎完全忽视了尹雪艳一步一步活出自己的价值这一事实。尹雪艳个体生命与价值实现在一些评论家那里似乎比不上那三个男人的身家成败,这是否可以说是一种功利主义批评。鲁迅小说《祝福》中与祥林嫂有瓜葛的三个男人也都死于非命,她的两任丈夫和儿子阿毛。不知有哪位批评家会说祥林嫂不是人,是无常。因为祥林嫂不漂亮吗?
于是我们又需要提到男性话语权。一些文章借用小说中文本原话说尹雪艳犯了重煞,是妖孽来直接证明他们对尹雪艳“不是人”的合理推导,却忽略了小说文本中说出这些话的人物和语境。“犯了重煞”是与尹雪艳同为舞女的女人嫉妒刻薄之辞,“妖孽”之语更是一位谄媚贵妇以骗取钱财为目的的神神叨叨的老妇人的满口胡诌之言。这些观点和《祝福》里边四婶等人的看法一样有多少可信,又是否真是作者本人对尹雪艳、祥林嫂的观点?我们客观去探讨被尹雪艳“祸害”的三个男人的真实面貌:王贵生是财阀王家的少老板,他找尹雪艳是因为爱吗?不是,正如白先勇另一篇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写的那样:“阔大少跑舞场是玩票,认起真来,吃亏的总还是舞女”[11],王贵生的敛财完全是为了尹雪艳吗?贪财、攀比,官商勾结这些都不是好色造成的,是比好色更致命的毒药,他的下狱枪毙有多大程度是尹雪艳造成的?若跟尹雪艳脱不了干系甚至但凡尹雪艳知情,她也就不是“百乐门停了一宵,对王贵生致哀”,而是锒铛入狱了。
再说洪处长 ,“一年丢官,两年破产,到了台北连个闲职也没捞上”[12],在那个战乱年代,昨日是座上王,今日是阶下囚的比比皆是,而大资本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阶级的压迫下破产的更不在少数。十个十里洋场的处长局长与洪处长相似经历的也有。
最后说徐壮图的惨死。徐壮图是台北工业时代下,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四十出头。文中借徐太太的口说:“徐先生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他一向都是这么说:‘男人的心五分倒有三分应该放在事业上’……他每天为公事在外面忙应酬。”[13]事实上,徐壮图被工人用扁钻刺死的原因不仅是徐壮图脾气不好,根本上是劳资矛盾的冲突结果,一个雄心勃勃的企业家总是想方设法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极强的压迫必然导致反抗。曹禺话剧《雷雨》中工人鲁大海也想开枪打死资本家周朴园,和女人没有关系。
综上将三人的死怪到尹雪艳头上是欲加之罪,他们的死是时代,是人的劣根性造成的。尹雪艳和祥林嫂所遭受的命运的捉弄有什么区别?
然而,本文也并不认为尹雪艳是值得我们同情、怜悯的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女性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女性人物谱系中,女性想要独立生存也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样的人生道路仿佛是尹雪艳这样的弱女子生存的必行之路”[14],但尹雪艳到底是凭着自己的优势地位,凭着美丽、风情、才智、交际能力从职场小白一步步成为尹公馆老板。从尹雪艳的“升职”历程来看,就是一部交际社会的《杜拉拉升职记》,“通过对生存环境的选择与改造,实现自己的主体性”[15]倒有点像司汤达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
我们无法否定在中国男性叙事存在着这样一种做法,“抹去女性这一弱势群体在男性强势文化的压制下辛苦挣扎的生命痕迹,从而使女性为生存而抗争的行为失去合理的依据,使女性在挣扎过程中产生的人性变异失去让人悲悯同情的价值,成为单一的恶行恶德”[16],但恶行恶德却不一定永远是消极的。在不公平不民主的社会里,有时候反戈一击,不择手段是出于生存竞争,对现实的不妥协,对实现自身价值的挣扎。
在《永远的尹雪艳》里,和小说中其他太太们等女人相比,尹雪艳可以说一直是胜利者,奋斗者,主动掌控自己命运者。那班依附于丈夫的太太们十几年来历经沧桑,丈夫的不如意导致她们的不如意,反而是这个做过舞女、小妾、交际花,而今孑然一身的尹雪艳对她们“施以广泛的同情”“耐心的聆听她们的怨艾及委曲”。
因为这群太太只会依附于人,耽于享乐却没有生存能力,甚至没有独立女性基本的个人思想。宋太太更年痴肥,形态臃肿,她先生有了外遇而对她颇为冷落。宋太太对这样的局面只会叹息抱怨,哭泣怨怼“我就不信我的命又要比别人差些!”[17]徐壮图的太太是典型的以丈夫为中心的传统家庭妇女,“我看他每天为公事在外边忙着应酬,我心里只有暗暗着急。事业不事业倒在其次,求祈他身体康宁,我们母子再苦些也是情愿的。” “有人传话给我听,说我们徐先生外面有了人,而且人家还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亲妈,我这个本本分分的人哪里经过这些事情,还撑得住不走样?”[18]于是宋太太沉湎于对过去日子的向往,徐太太将希望寄托于神婆的装神弄鬼。相比于这些无知愚昧麻木迷信的旧时代传统妇女,我们不能不说尹雪艳倒是相对独立女性。从百乐门卖笑的舞女到王贵生(可以说是金钱)的妾,王贵生无法依靠后,做了洪处长(可以说是权势)的上位夫人,到洪处长落魄时,尹雪艳已不是百乐门那个只能依附男性的舞女了,她有了钱,有了人脉,见了上流社会形形色色的人情往来,离开洪处长的尹雪艳带着自己的家当、名厨师和两个苏州娘姨,在台北开起了自己的尹公馆,做起了女主人。还是个最称职的主人,周到妥帖,收入可观。再到徐壮图,主动出击争取自己的利益与幸福,当然出事后也及时脱身,仍过好自己的日子。
我们可以说尹雪艳是有点不择手段,不道德,但也应该看到尹雪艳努力活出自己的风采,不至于落得大多数旧时代风尘女子那样可悲的下场。
结语
综上,本文认为《永远的尹雪艳》塑造了一个交际社会活出自己价值的相对独立女性形象。这个女性形象有她作为人冷酷绝情、不择手段的一面,也有她从弱势群体逐渐打拼,功成名就、历经沧桑的一面。我们不能完全批判她的冷酷无情,也不能只看到她的历经沧桑,而是应该看到她作为人的复杂多面,在世俗的角度客观看待这样一个美丽的风尘女子。
——兼谈民国时期上海舞女的职业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