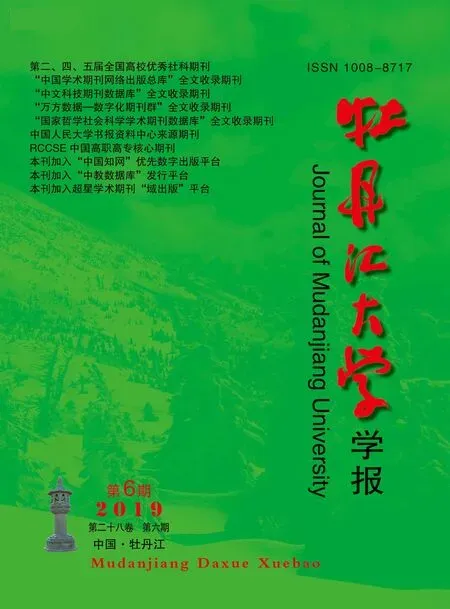从库恩的“范式”理论与阿尔都塞的“总问题”理论比较看现代西方科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
杨 松 雷
(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54)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在古代,哲学是知识的总汇,科学完全包含在哲学之内。自逻辑经验主义兴起之后,人们又把哲学当作“形而上学”完全拒斥,认为哲学不但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反而会妨碍科学的发展。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之后,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反思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作为一名科学家及科学哲学家的库恩提出了“范式”理论,力图证明科学的发展是离不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属于哲学方面的东西。与此同时作为哲学家的阿尔都塞提出“认识论断裂”“总问题”理论,力图证明马克思哲学是“科学”。二者的理论形成一个有趣的对应。
一、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的缘起及内容
从启蒙以来,理性确立了其主导地位,认为只要沿着理性走下去,科学也能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人们便能达到对真理的把握。尤其是近代西方逻辑经验主义兴起以后,更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一个有脉络、连续性的积累进步过程。科学具有确定性、规范性、普遍有效性等特点,科学与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社会背景等因素并无关联。
随着近代科学的飞速发展,科学哲学从十八世纪上半期也发展起来,其发展过程大致可以说是从逻辑经验主义到批判理性主义再到历史主义,也就是从逻辑经验主义的完全拒斥形而上学发展到历史主义向哲学的回归。库恩是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一派创始人。库恩通过“范式”理论指出,科学的发展不是纯粹理性和纯粹逻辑的指引下的连续积累进步过程,科学的发展是与社会、历史因素紧密相联的。他指出,人们坚持的某种科学,是“科学共同体”所共同信仰的“范式”。什么是“范式”呢?库恩指“这些著作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在于它们共同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它们的成就空前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1]如牛顿物理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都可以称为某种“范式”。而“科学共同体”是指“其成员都是从相同的模型中学到这一学科领域的基础的,他尔后的实践将很少会在基本前提上发生争议,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库恩认为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并不是由其中的内在逻辑、是否合乎理性来判断的,而是建立在能否成为 “科学共同体”信仰的“范式”。
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并不是单向的连续的知识的积累与提高。而是新的“范式”的建立,旧的“范式”的破除。新旧“范式”之间是本质的区别而不是量上的自然过渡,“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它们之间没有公约数,只有质的差别。范式的变革不可能是知识的直线积累,而是一种创新和飞跃,一种科学体系的革命。库恩认为科学发展脉络是: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时期。其中常规科学时期就是科学知识的渐进积累过程,这时“范式”还能对当下问题作相对较好的解释,“科学共同体”成员只是对“范式”补充完善。但如果在发生反常与危机的时候,旧有“范式”始终无法给予解决,人们会审视旧有“范式”,进而发生科学革命,建立新的“范式”,这个新“范式”“能较好地解释导致老范式陷入危机的问题。对新“范式”来说,“如果这一主张能够合理的实现,那么它通常可能就是一个最有效的主张。”[3]从而成为相应“科学共同体”成员所信赖的新“范式”。
二、阿尔都塞“总问题”理论的缘起及内容
在理性主义兴起以后,在认识论问题上大部分哲学家总认为认识是直线型的,是在继承中取得发展,借用柏格森的说法,时间是一个绵延的过程,生命也是一个绵延之流。而认识也是连续性的,即使有否定,也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否定。从以往的认识来看,哲学家们基本上都认为认识的发展是个绵延的、连续的、有本质的联系。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阿尔都塞的老师法国籍哲学家及科学家巴什拉认为,在科学研究中不存在单一的直线性的进化,反而是在同过去决裂、断裂中发展的。他强调,“认识论断裂”是科学发展中最重要的规律,反对 “绵延说”“连续说”,认为“时间不在流失,时间在爆裂”。 作为巴什拉的学生,法学哲学家阿尔都塞进一步发展了巴什拉的“认识论断裂”,并借鉴雅克·马丁的“问题式”,提出“总问题”“征候阅读法”等,并用这些理论来研究马克思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阿尔都塞指出,“确定思想的特征和本质的不是思想的素材,而是思想的方式,是思想同它的对象所保持的真实关系,也就是作为这一真实的关系出发点的总问题。”[4]“‘总问题’的概念与唯心主义地解释思想发展的各种主观主义概念的不同之处,正是总问题的概念在思想的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的各个论题组成的一个客观的内在联系体系,也就是决定该思想对问题作何答复的问题体系……总问题的本质不是它的内在性,而是它同具体问题的关系。”[5]“总问题”的作用是“在思想的内部确定着各具体问题的意义和形式,确定着这些问题的答案。”[6]阿尔都塞为什么要提出“总问题”呢?他指出“因为,说一种思想是一个(有机的)总体,这仅仅就叙述而言是正确的,而就理论而言则不然,因为这种叙述一旦被改变为理论,就有可能使我们只想到毫无内容的空洞整体,而想不到整体的特定结构。相反,如果用总问题的概念去思考某个特定思想整体……我们就能够说出联结思想各成分的典型的系统结构,并进一步发现该思想整体具有的特定内容,我们就能够通过这特定内容去领会该思想各‘成分’的含义,并把该思想同当时历史环境留给思想家或向思想家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7]而且“任何理论就其本质来说都是一个总问题,都是提出有关理论对象的全部问题的理论的、系统的母胚”。[8]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阿尔都塞看来,各哲学家思想之间、理论之间之所以不同,正是由于“总问题”不同而区分开来的。每个哲学家思想深处所藏的 “总问题”不同,也造成了个体之间对“同一对象”的不同解读,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并进一步用这个理论体系解读整个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
三、库恩的“范式”理论与阿尔都塞的“总问题”理论比较
库恩和阿尔都塞要解决的问题恰恰是相反的——一个要证明科学的“哲学性”,一个解决哲学的“科学性”。二者是相反相成的,从相反方向证明同一个问题——科学和哲学相互之间的借鉴、补充和融合。二者存在以下相似性:
第一,在相反的方向上达到殊途同归
库恩首先是一个科学家,但在他对科学史的研究中发现,科学的发展不是纯粹理性和纯粹逻辑的指引下的连续积累进步过程,科学的发展是与哲学、历史等因素紧密相联的。库恩指出,“范式”对“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具有精神支撑调节作用,会影响到科学研究者的心理、情感、信念和思维方式等。阿尔都塞是一个哲学家,他要解决的是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问题。阿尔都塞把“认识论断裂”“总问题”的理论运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因为从1845年开始,马克思开始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人道主义理论彻底决裂了……并重新确立了一个新的理论总问题,一种系统向世界提问的新方式,一些新原则和一个新方法。这种新发现导致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诞生。”[9]这样,阿尔都塞通过“认识论断裂”“总问题”把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和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区分开来,把马克思和其他哲学家区分开来。
第二,理论结构的相似性
库恩的“范式”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总问题”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范式”和“总问题”都可以看作一个相对封闭的结构,都因其特殊性与其它的 “范式”或“总问题”严格区别开来。“范式”之间是质的差别,是不可通约的。而“总问题”之间由于对象、内部结构、提问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理论。有趣的是,二者都曾以拉瓦锡克服燃素说发现氧气作为自己的例证。(这点可参见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136—141页。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 49—53页。)阿尔都塞在举例之后指出,“‘使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的含义是毫不含糊的,那就是改变理论的基础,改变化学的理论总问题,用新的理论总问题来代替旧的理论总问题”。[10]而库恩在举例之后说,“需要有一次重要的理论修改以使拉瓦锡看到他看到的东西,也是为什么普利斯特终其漫长的一生却未能看到它的根本原因。”[11]
第三,理论旨趣的相似性
“范式”与“总问题”的相似性还体现在,二者都会导致新的理论的产生和对事物不同的解释。新的“范式”与“总问题”之所以与旧的 “范式”或“总问题”不同,在于新的“范式”和“总问题”具有两方面的特点:其一,它们能更好地解释、解决旧的 “范式”和“总问题”要解决的问题;其二,它们不但能较好地解释、解决旧的“范式”和“总问题”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还能解释、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库恩指出,在常规科学内,人们利用已有的“范式”,可以解决一系列难题,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如果旧有“范式”不能解决反常问题,发生危机,又会出来新的“范式”取代它,进一步解决新的难题。阿尔都塞认为,正是因为新的“总问题”的确立,才把马克思哲学与人道主义等区分开来,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等区别开来,把马克思与斯密、李嘉图等区别开来,以“剩余价值”学说这个“总问题”实现了理论革命,最终形成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这样,马克思就成为可以同伽利略和拉瓦锡相比的科学的奠基人。”[12]
四、从“范式”与 “总问题”比较看现代西方科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
阿尔都塞把科学主义引入哲学研究,而库恩则把哲学、历史等因素引入到科学研究中。尽管属于不同的领域,他们的思想与作用却是如此的相似,他们对科学与哲学及其研究方法的相互影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上,科学利用自身的发展模式得到飞跃式的发展,有把哲学远远抛在后面之势。哲学也需要借鉴科学的方法,争取自己的“合法化”。一方面,科学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认识,为包括哲学在内的各门学科提供了知识基础;另一方面,哲学本身的研究也需要借鉴科学的研究方法。正如赖欣巴哈所说的,“一种对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仅现在有,而且一直就有,……是要指出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13]
而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把哲学当作“形而上学”完全拒斥。人们在对科学的期望中,总是企图把科学建构成为独立于历史、永恒的对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认识。从“范式”理论与“总问题”理论的相反相成可以看出,哲学和科学之间并不存在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人们认为科学的发展完全与哲学无关,科学应该完全拒斥“形而上学”的观点是错误的。正如另一位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指出的那样,如果人们对科学的期望是要科学提供绝对确定的东西,这种对科学的理解是“直接由神学继承过来的标准加以判定:它必须被证明是确凿无疑的。科学必须达到神学未达到的那种确实性”。[14]
——重读阿尔都塞的《论青年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