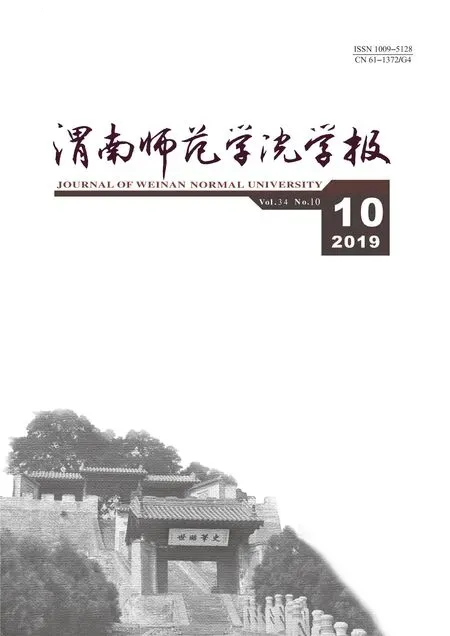《史记·夏本纪》隐喻探析
王 炳 社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夏是中国一个古老的部落,相传由包括夏在内的十多个部落发展而来,大概居于尧、舜时代,后因夏禹治水有功而登上王位。关于夏禹的身世,《史记·夏本纪》是这样记载的:“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1]49这是一种隐喻的叙事方式。一般而言,“历史编纂总是由四种转义——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中的一种而得到充实的”[2]10。司马迁为什么在《夏本纪》的开头要这样叙述呢?显然是有其特殊用意的。这也就是说,夏禹的祖辈虽然有过辉煌,但到他这辈,已经变成了平民百姓。而一个平民出身的人,要想登上王位,当然他身上得有诸多优点,或者应该是接近完美的人。历史叙述注重客观,要尽可能避免个人的针砭倾向,这样才能有效实现其隐喻目的。何以如此?因为“在构造知识以服务于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目的方面,隐喻有着明显的效果。在我们支配把实在转变成人类目标和目的能够接受的世界方面,可以论证隐喻是我们拥有的最强有力的语言工具”[2]16。因此,为了表现夏禹的高尚品德和过人能力,司马迁在其《史记》叙事的时候,注重以隐喻的方式展示夏禹之德、能、绩、勤、俭诸方面。显然,如何将这多个方面有效传达给读者和后人,而且要让他们喜欢阅读、乐于接受,甚至付诸行动,如果采用机械僵化的方式去说理或训诫,显然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因此,采用活灵活现的、生动的事实或故事,也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使事物活现在眼前”[3]179,或者说“是用一类事物理解和体验另一类事物”[4]76,即“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建构我们的现实”[4]76,也就是采用叙事或者讲故事的方式,便可达此目的。
一
中国人重“德”,常常把“德”作为选人用人的第一标准,这从黄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黄帝(轩辕)当初立,是因为其“有土德之瑞”[1]6;颛顼帝(高阳)所以立,是因为其“有圣惪焉”[1]10;帝喾(高辛)所以立,是因为“其德嶷嶷”[1]13;帝尧(放勋)所以立,是因为“其仁如天”[1]15;帝舜(重华)所以立,是因为其能“行厚德”[1]38,且“天下明德自虞帝始”[1]43。也就是说,从“德”的方面来考察,虞(舜)帝是最为全面和经典的,因而成为中华传统美德的典范。由此溯源,从黄帝到尧、舜,都是同一姓,只是改了国号,以彰显各人的美德,即所谓“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1]45。也就是说,当时的国号也就是每个人“德”的隐喻。
对于夏禹的“德”,司马迁很少有直接赞扬的语言,而是采用客观叙述或讲故事的方式,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夏禹道德的高尚,从而使得抽象的东西形象化、“陌生的东西熟悉化”[2]15,进而实现了“引导我们依据较熟悉的系统去看不那么熟悉的系统”[2]16,即“把陌生的东西熟悉化”,以达其隐喻之目的。古人尚德,是因为唯有德高方能孚众望,才能得到众人的拥护和爱戴,这样天下才能太平,老百姓才能有好日子过,因而“德”便成为历代帝王选择接班人的首要标准。对于夏禹高尚之德,司马迁主要通过五个方面来予以叙述和印证:
第一,夏禹德高望重,深孚众望。
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1]51
司马迁,重点关注的是夏禹的德,而德则具体体现在夏禹的为人处世和言谈举止上。司马迁说,夏禹为人敏捷勤俭;他的为人,一切行为都符合道德规范,仁爱可亲,说话诚实可信;他的一切言谈举止都符合规范:说话快慢有度、符合律吕,进出屈伸合于法度;他的内心高尚,一切皆能宜于事理,而且勤勉敬谨,可以作为纲纪。司马迁采用客观叙述的隐喻手法,通过对夏禹非一般人能够做到、能够具备高尚品德的叙说,隐喻夏禹继承帝位的合理性。
第二,人的道德是否高尚往往体现于对祖宗长辈的尊重、孝敬和对事业的敬畏上。为此,司马迁采用了对比的隐喻手法重点记述了夏禹对己与对祖先神明、于私及于公之态度,从而实现了非直接表达的隐喻: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1]51
这里,司马迁以隐喻的方式记述,首先说夏禹对自己严苛的要求,他在饮食起居方面,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从不讲究吃喝穿戴,而对于祭祀祖先神明,他却能够尽可能地做到使祭品圣洁丰厚;其次说夏禹自己住着简陋低矮的房子,可是对于农田水利工程却愿意花大价钱尽力地去做好。这两件事情,虽然叙述简洁,但却足以说明夏禹品德的高尚与做事的公而忘私。从隐喻思维的工作机制来看,隐喻“是通过选择和突显喻体和本体的某些因素,并使喻体中的因素‘映射’(mapping)到本体,从而达到认识本体的目的”[4]93-94,因此,司马迁通过对夏禹对己对神、于己于公故事的叙说,隐喻夏禹道德的高尚。
第三,夏禹在处理公务、管理百官中也表现出高尚的职业道德。
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国赐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1]75
这里,从表面上看,司马迁是说帝舜安定九州,实为一种艺术隐喻(借喻)形式,这也是艺术隐喻常见的一种形式。而九州安定的前提是夏禹治水的成功,因而舜帝的诸多政绩,或者说“德”的修竞,其实主要是由于夏禹的努力辅助而实现的。也就是说,夏禹“能成美尧之事”[1]50,即所谓“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1]77。所以,舜帝政绩的伟大,恰好是夏禹德能的隐喻,当然也是舜帝权力的隐喻。中国自舜帝而夏禹,天下基本稳定,其核心表现就是以夏禹治水为核心的天下大治之功绩。这种趋于一统的过程恰好就是一个隐喻,即以“德”为核心的融合和感化天下。“这表明隐喻作为一个过程,它的完成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引导;作为一种结果,它体现或蕴含了一定的意识形态。”[4]95这里,为了使得《史记》的记述更为简洁和具有说服力,在述说夏禹治水的专注和功绩的时候,司马迁甚至采用了《尚书》中的诸多原文,不仅增强了《夏本纪》的信度和行文的简洁性,而且增强了其简洁之下的隐喻性。
第四,夏禹高尚的道德还表现于他对道德标准的研究和制定上,也就是人的“九德”。
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皋陶述其谋曰:“信其道德,谋明辅和。”禹曰:“然,如何?”皋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长,敦序九族,众明高翼,近可远在已。禹拜美言,曰:“然。”皋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难之。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知能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宽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日严振敬六德,亮采有国。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肃谨。毋教邪淫奇谋。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天讨有辠,五刑五用哉。吾言厎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绩行。”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赞道哉。”[1]77-78
这是舜帝时期君臣之间一段很有趣的对话,它不是为经济、为社会,而是为人,对话的主体是夏禹和皋陶。皋陶作为舜帝时期的一个重要谋臣,他有足够的智慧和计谋,因此他与夏禹的对话便成为《史记》中关于道德体系建设的经典片段之一。此对话一方面隐喻夏禹开始为管理国家做准备,另一方面隐喻夏禹更看重用道德体系的制定来约束人、教化人的意识形态作为。皋陶认为,对人的治理,关键在道德建设,只有全社会的道德水准提高了,人才会有诚信可言,这就需要人人都去谨慎地修身,要从长远着想,要厚待周围的亲人,这样,众人拾柴火焰高,国家就好治理了。显然,这里面有歌颂舜帝面对“父顽,母嚚,弟傲”[1]21,“常欲杀舜”[1]32,而舜却仍然“能和以孝”[1]32的高尚品德,舜帝可为学习榜样、道德楷模。但显然,光靠像舜帝这样极少数的人是难以改变社会整体道德面貌的,要想改变,唯有建立起完备的道德体系,不再有“父顽,母嚚,弟傲”的现象,人与人之间才可和睦相处,社会才能够长治久安。因此,夏禹与皋陶讨论的问题,可谓是一个宏大的社会道德体系构想,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亦隐喻夏禹的高瞻远瞩。因此,皋陶认为,人的行为有九种道德:宽大而能敬谨,柔顺而能自立,忠诚而能供职,有治理的才能而又能敬谨,驯顺而能果毅,正直而能温和,简易而能辨别,刚健而能笃实,强勇而能好义。人能够坚持这九德,可以说就是完人了。此言既隐喻舜帝的美德,亦为暗示夏禹继承帝位以后应该做好的九个方面。因此这段对话就是一个完整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伦理道德既是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因此,皋陶与夏禹的对话形成的“隐喻不仅简化了复杂的政治,更重要的是包装了无形的政治,给予抽象问题以生命力”[4]99。
第五,“德”作为衡量人之正与邪的首要标准,这也是虞舜和夏禹时代的首要标准。对此,司马迁并未采取直接叙述的方式,而是采用了对话的方式,这样更加切身和有对比性,进而实现隐喻说明的作用。
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辅之。余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绣服色,女明之。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来始滑,以出入五言,女听。予即辟,女匡拂予。女无面谀,退而谤予。敬四辅臣。诸众谗嬖臣,君德诚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即不时,布同善恶则毋功。”[1]79-80
这是夏禹治理完九州以后和舜帝的一段对话,从对话中可以看出,舜帝和夏禹在选人用人方面都是主张道德标准第一的。随着帝舜年事渐高,寻找合适的接班人就成为摆在他面前的一件重要事情。对此,夏禹的观点是“辅德,天下大应”,也就是一定要选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这样,天下的老百姓才会顺应,社会才能进步和发展。司马迁通过夏禹将此作为一个建议给舜帝说出来,其隐喻价值在于:一是明确“德”是人的根本;二是表明夏禹用人和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三是这与舜帝希望众臣举荐道德高尚的人管理国家的理念是一致的;四是提醒舜帝要提醒众臣不要把像鲧、丹朱一类的人推荐到治理国家的阶层中来。
当然,关于夏禹的美德,还有谦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他把治水立功的机会首先让于契、后稷、皋陶;舜帝驾崩后,三年守孝期满,他把帝位让于舜之子商均,在众诸侯的一致支持下,他才即天子位;他去世前,就安排益继承帝位,而非自己的儿子启,等等。这些,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夏禹高尚品德的一个方面。这其中,让贤、让位之举,也都是司马迁为了突出夏禹的高尚品德而特意强调创设的隐喻情境。
正因为夏禹有无比高尚的品德,“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舜德大明”[1]81。反言之,虞舜之德即是夏禹之德的隐喻。
二
就一个完美的人而言,高尚的道德固然重要,但要想成就一番事业,还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尤其是像治理国家这样的能力。从《夏本纪》之记述来看,夏禹就具有这样的雄才大略,这也是舜帝最后选定夏禹作为接班人继承帝位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于夏禹的能力的记述,司马迁采用的也是隐喻的方式,也就是突出其行为和事件的客观性和“被给与”[5]22性,从而实现了对事物“认识论的还原”[5]37,即隐喻性的记述。
帝舜谓禹曰:“女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难禹曰:“何谓孳孳?”禹曰:“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刊木。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1]79
司马迁通过夏禹和舜帝、皋陶的对话,以对话记述的方式,显示出夏禹的能力和美德:他治理水患,陆行乘车,水行乘船,遇到泥泞的地方就乘坐泥橇行走,遇到山路就脚穿带齿的檋登山,并以木橛作为标志;遇到饥民,他和伯益就用稻粮鸟兽救济他们;他率领众人去除九州河川内的壅塞,使之流入海中,又挖深田间的水道,使之流入川中;他还与后稷施与民众谷物;对与食物短缺的地方,他就想办法调剂,使人民安居乐业。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使天下太平。表面上看,司马迁记述的是舜帝和夏禹、皋陶的对话,实际上是为了表明夏禹工作能力的强大,这是一个隐喻。因为对话往往是人内心情境的一种表现,因而它是心灵的隐喻。表面上看,以上对话是舜帝要夏禹说些美好的事情,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事实上夏禹也说得很轻松,甚至是“轻描淡写”。但人们可以想象,治理九川,让人人都有饭吃,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是何等的不易!对话之弦外音,便给人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这本身就是一种隐喻。由此可以看出夏禹能力的无比强大,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这样的叙事非常巧妙,但他却隐在地为舜帝选择夏禹作为接班人提供了“行动的建议”[4]117。这样的隐喻性叙述,使得夏禹的形象甚为崇高和伟大[2]19,从而使得司马迁的记述亦更为真实可信。
同时,为了使得夏禹继承帝位能够顺理成章,司马迁借用舜帝之口说出了夏禹治理国家的理念:
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1]51
这样的叙述,看似很简单,然而它却蕴含着夏禹等人大量的工作,而且要完成得令舜帝非常满意。从隐喻的角度来看,“隐喻属于启迪思想的方法”[6]24,所以司马迁在这里描述夏禹带领益、后稷等人十三年治理九州的过程:用科学的方法测量山水的平、直、高、低、远、近,记录在案,一年四季从不休息;划分了九州,并且开通了九州的道路;在九州的陂泽兴修水利储水,以防止旱灾;按照九州所生产的物品,制定贡赋的标准;夏禹依据地形和土地特征,命令伯益教给人民在低湿的地方种植水稻,命令后稷教人民种植旱作物庄稼;有效调剂各地食物的平衡;依据各地的出产和交通情况制定贡赋标准等。这里面涉及土壤、交通、水利、种植、测绘、行政等诸多学科,但夏禹都能够处理得有条不紊、科学有据,这显然隐喻夏禹能力的强大。这里,司马迁用了“左”“右”“载”“开”“通”“陂”“度”等动词,增强了叙述的动感性和故事性,从而造就了隐喻语境。以快节奏的跳跃叙述方式,使得关于夏禹能力的目标语境得以淋漓尽致地显现。更为可贵的是,这样快的节奏,极其简洁,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叙述的隐喻价值。这种方式,其实正符合“隐喻是以具体事物的特点描绘抽象性质”[6]44的事物的特点。司马迁这样的叙述,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而这丰富内涵的核心就是夏禹超人的能力。
为了突出夏禹的能力,司马迁还记述了夏禹对各地缴纳税赋标准的制定:
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1]75
这是夏禹完成治理九州、九川、九山之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甸服(王城五百里以内的地区)之地缴纳赋税的标准为:一百里以内的百姓缴纳带秆的谷物;二百里以内的百姓缴纳带穗的谷物;三百里以内的百姓缴纳去掉秸芒的谷物;四百里以内的百姓缴纳带壳的谷物;五百里以内的百姓缴纳纯米(麦)。侯服(王城外五百里以内的地区)之地的分封管理体制为:甸服一百里以内的地区,是天子封卿大夫的采邑;二百里以内的地区,是封男爵的地域;三百里以内的地区,为封诸侯的领域。对待绥服(侯服外五百里以内的地区)之地一百至三百里的地区的百姓,主要以礼乐法度、文章教化为主;三百里以外、五百里以内地区的百姓则主要担负保卫天子的任务。要服(绥服以外五百里以内的地区)三百里以内的地区为夷人居住的地区,另外二百里则是流放违犯王法的犯人的地方。荒服(要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三百里以内的地区是荒凉落后的地区,另外二百里则是流放一般犯人的地方。这五百里一个区域,便于层级管理和设防,是相当科学的。因此,在这道行政命令中,其隐喻意义在于:一是隐喻夏禹制定不同地区标准的科学能力;二是隐喻夏禹对国家的管理能力;三是隐喻夏禹的行政执行力;四是隐喻夏禹对事态的掌控能力。
为了表现夏禹的工作能力,司马迁还采用了对比(衬托)的隐喻方式,也即禹和父亲鲧的对比: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1]50
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鲧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四岳眼里,天下再也没有能超过鲧之能力的人了,故而四岳请帝尧允许鲧去治水。然而,九年时间过去了,鲧却毫无建树,水患仍然很严重,因而夏禹是作为为父亲将功赎罪而去治水的,最终夏禹取得了成功。一般而言,艺术比较更偏重于对对象隐喻价值的挖掘和发现,因而司马迁的对比记述方式更多体现的是其意向和意图,这是司马迁的独到发明,也因此更加突出了夏禹治水的能力。
三
要想全面考察一个人,除了“德”和“能”以外,还应从政绩的角度去看。对此,司马迁大书特书。在《夏本纪》中,司马迁用了几乎二分之一的篇幅来记述夏禹带领人们治理九州、九川、九山的过程。
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致功,致于衡漳。其土白壤。赋上上错,田中中。常、卫既从,大陆既为。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1]52
夏禹对天下的治理,首先治理的是冀州(包括现在的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河南省、辽宁省、陕西省全境及内蒙古自治区),从现在辽宁、内蒙古、北京一带南下然后到黄河的壶口,再就是梁山、岐山、太原、岳山、漳河、常水。经过治理,土地可以耕种了,黄河也发挥了它的航运和灌溉作用,人民安居乐业了,给朝廷的贡品也有了着落。虽然文字简洁,但可以想象,其中的管理、调遣,人、财、物的安排等等,运作起来当然会遇到诸多困难,但司马迁对如此繁杂的事情却用了极其简洁的语言予以叙述,在一种貌似客观的状态下隐喻夏禹的能力和魄力。从隐喻学的角度来看,隐喻式的描写或叙述,往往使得事物“从一个意义领域延伸到另一个意义领域”[6]164,这就是隐喻的奥妙所在。因而,夏禹从冀州到常水,到黄河,其治理的成功,在重结果的隐喻式叙述下,反而突出了夏禹能力之下的政绩,不得不令人信服。同样,对黄河下游的治理亦取得了决定性成功:
济、河维沇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于是民得下丘居土。其土黑坟,草繇木条。田中下,赋贞,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贡漆丝,其篚织文。浮于济、漯,通于河。[1]54
经过十三年的努力,夏禹带领人马治理了兖州:治理了黄河下游的九条支流,湖泊湿地得到保护,使得这里土地肥沃,万物茂盛,为国家增加了税收。对这样重大而又艰巨的工程,司马迁同样采取了极其简约的叙述。简约,其实是艺术家常用的一种构造世界的隐喻形式,它类似于绘画和书法中的留白,也就是“拒绝并净化绝大部分普通事物世界中的实体和事件”[6]16,从而形成“精致的结构”[6]16,也就是隐喻的结构。司马迁这样的“简述”方式,使得夏禹的功绩得到聚焦式的表现。虽然简约的使用如果不够妥当的话,有可能伤害事件本身的表现,然而,如果使用恰到好处的话,它更能凸显作者想要表达的事物。因而,司马迁的表现是很聪明和富有成效的,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夏禹的功绩,其隐喻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后,司马迁对夏禹对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乃至九山、九川治理的叙述也都极其简约精致,达到了充分突出夏禹治理河山功绩的隐喻功效。
海岱维青州:堣夷既略,潍、淄其道。其土白坟,海滨广潟,厥田斥卤。田上下,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维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为牧,其篚酓丝。浮于汶,通于济。[1]55
对于青州的治理,司马迁只用了“堣夷既略,潍、淄其道”八个字,就把一场浩大的工程“轻描淡写”地给“打发”了,但我们相信,“世界不仅仅是用其字面上所言说的东西构造出来的,而且也包括其言说的隐喻意义”[7]19。历史叙述作为一种科学,司马迁没有把叙述的着眼点放在艰难的治理工程上,而是将其放在了治理后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这本身就是一种隐喻,因为“无论是字面的还是隐喻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陈述都可以揭示出它并没有说出来的东西”[7]19,因而司马迁要给我们展示的正是夏禹的政绩。对徐州治理的记述是“淮、沂其治,蒙、羽其艺。大野既都,东原厎平。其土赤埴坟,草木渐包”[1]56;对扬州治理的记述是“彭蠡既都,阳鸟所居。三江既入,震泽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乔,其土涂泥”[1]58;对荆州治理的记述是“江、汉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涔已道,云土、梦为治。其土涂泥”[1]60-61;对豫州治理的记述是“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播既都,道荷泽,被明都。其土壤,下土坟垆”[1]62;对梁州治理的记述是“汶、嶓既艺,沱、涔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1]63;对雍州治理的记述是“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所同。荆、岐已旅,终南、敦物至于鸟鼠。原湿厎绩,至于都野。三危既度,三苗大序。……西戎即序”[1]65。对这些州的治理,突出确保生态良好、社会安定、边境安宁、百姓乐业及朝贡的丰富和满足等方面,这无形中表现出夏禹治理各州的能力和政绩。
治理完九州,夏禹的政绩已足够突出、足够大,这也是最难的治理工程。然而,夏禹并没有停歇,而是继续治理九山、九川,司马迁的记述,几乎是一系列山川名字的罗列,又像是旅行的路线图,而对治山治水的问题、困难甚至人员的伤亡等事项皆概略不记,其实这是“意在言外”,是一种策略,即一种隐喻的策略,这种陈述“可以揭示出它并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并成为关于没有被指示的性质和情感的字面或隐喻的有力例证”[7]19,因此亚里士多德说:“最巧妙的话来自隐喻。”[3]183正是由于隐喻,才使得夏禹的政绩被接受者在一种看似“冷冰冰”的历史叙述中得以放大,因而,隐喻使得历史叙述的蕴涵大大加深和扩展,也使得夏禹成为下一代帝王的不二人选。
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1]75
对于夏禹的功劳,帝舜也有充分肯定: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1]77
历经艰难险阻,夏禹才完成了对九州、九川的治理任务,其中的困难和牺牲可想而知。对此,司马迁一没有抒情,二没有铺陈,而是用了最为简洁的“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和“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天下于是太平治”予以总结,其中给人留下诸多想象和联想的空间,从而无限延伸了叙事的空间,不仅节省了文字,也大大提升了叙事的隐喻价值。
四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夏禹,也是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奠基者之一,勤劳在夏禹身上也得到充分体现。不过,在《夏本纪》中,对于夏禹的勤劳,司马迁也是以隐喻的方式表现的。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1]51
在记述过程中,司马迁几乎没有用一个与“勤”有关的字眼,而是把着眼点放在了夏禹对先人鲧未能完成治水大业的感伤和焦虑上。夏禹焦思焦虑、全力以赴地去治水,甚至能够做到“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是焦虑,还是赎罪,抑或是对治水事业的敬畏。不管如何,总之一点,夏禹做到了常人无法做到的敬业,他“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1]51。为了治水,夏禹和随从下属们一年四季都在奔波,十三年从不停歇。如此勤奋的他,自然会感天动地,当然最终完成“治九州”“道九山”“道九川”的伟大工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也有力印证了司马迁“禹为人敏给克勤”的判断。再看司马迁对夏禹治理“九山”“九川”的记述:
道九山: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道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汶山之阳至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1]67
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嶓冢道漾,东流为汉,又东为苍浪之水,过三澨,入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汶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道沇水,东为济,入于河,泆为荥,东出陶丘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汶,又东北入于海。道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道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北至于泾,东过漆、沮,入于河。道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东北入于河。[1]69-70
在这两段文字中,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还原成夏禹治理山水的画面,然而司马迁却没有明写,而是将画面蕴藏在了一大堆名词、介词、动词之中。试想,治理“九山”“九川”,那是何等浩大的工程,然而司马迁的记述却仅仅只有329个字!而这329个字里面,仅山名就有近40个,水名有近30个,更为奇特的是仅“至于”(“入于”)就有20余个。也许是受到《尚书》简洁叙事的影响,司马迁用词很“节俭”,叙述很简洁,而在节俭和简洁背后,便是其隐喻意向之所在。这些静态的、甚至有些机械罗列的记述方式,其内部却充满着动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内涵,这极其丰富的内涵的核心就是夏禹的勤劳与智慧,也就是它是司马迁头脑中的一种内存在,一种意识对象的存在。因而,司马迁的静态表述、罗列式叙述其实就是一种隐喻的方式。他避开“道九山”“道九川”过程复杂的千头万绪和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不表,而是截取结果的部分,这是典型的以局部代替全部的艺术隐喻的另外一种形式——转喻,这就更给接受者留下了无限个“空白点”或“留白”,从而使夏禹的勤劳与智慧得以最大化。因此说,“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其实还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方式”[8]28。
对于夏禹的勤劳与智慧,司马迁并未停留于治山治水上,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对人民的教诲与引导。
禹曰:“予(辛壬)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1]80
夏禹一心扑在舜帝交给他的光荣而又艰巨的治水任务上,他在新婚的第四天就出外治水了。他舍小家为大家,所以才最终完成了治水大业。在治水的同时,他还辅佐舜帝设立了五服制度,使家庭伦理和礼仪得到强化;在他夜以继日的勤奋工作下,国土面积达到了方圆五千里,而且给每个州设立了十二个师,九州以外达到四海,每五个国设立一个首长,所以他们都能够按照舜帝的要求完成各项任务。对此,司马迁采取了另外一种隐喻的记述策略,即通过夏禹之口说出来。这里的所谓“说出来”,并非夏禹的自我表功,司马迁采取了极其巧妙的方式,他运用的是夏禹、舜帝和皋陶等大臣讨论治理国家这个问题的时候,夏禹现身说法的一种自然流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这种不费劲就能使人有所领悟,富于启发性的表述方式,“对于每个人说来自然是件愉快的事情;每个字都有一定的意思,所有能使我们有所领悟的字都能给我们以极大的愉快”[3]176。所以,夏禹之言的核心是:治理国家就像做人一样,不仅道德要高尚,还要勤奋,还要公而忘私,还要有大局观念。这就实现了“目标情景与始源情景的比较”[9]6,从而造成了德、能、勤诸方面与治理国家的关联,自然形成了隐喻,当然也无形中形成了夏禹与丹朱之间的鲜明对比,这也应验了“内容与表达手段之间的距离越大,它们的对照越是出乎预料,隐喻就越明显和令人惊异”[6]164。这样就实现了表述意义的延伸,也即从夏禹的勤劳与智慧延伸到了另外一个意义领域——治理国家,从而实现了隐喻,这也是司马迁记述历史常用的一种隐喻手法。司马迁没有让夏禹去接舜帝对丹朱不满的话,而是话题一转,从自身说起,这样既不使气氛紧张,也不伤及舜帝的颜面,当然这也符合“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和说明另一种事物的过程”[4]93隐喻生成的本质。而司马迁选择这样的记述策略,实际上也符合隐喻的一般工作机制,即“通过选择和突显喻体和本体的某些因素,并使喻体中的因素‘映射’(mapping)到本体,从而达到认识本体的目的”[4]93-94,当然也是因为“隐喻能使他们避免直接提及而伤及脸面”[4]99的缘故。
五
古人物质贫乏,所以人们对“俭”尤为重视。俭以养身,廉以养心,这是古人的传统美德,也是古人的自我约束机制,这一点在夏禹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对于夏禹的俭朴,司马迁亦采用隐喻之简化方式予以表述。在表述过程中,司马迁没有选择过多的细节,而是采用极其简练的语言,给人们留下诸多联想和思考的空间,从而实现了隐喻式表达之目的。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1]51
夏禹自己在饮食起居方面极其简朴,而在祭祀祖先神明的时候,却能想尽办法使得祭品丰厚圣洁。夏禹自己所居住的房子极其简陋低矮,可对于农田水利建设,却愿意花大价钱尽力地去做好。而且他在工作中没有享受任何特殊待遇。通过对待“鬼神”、农田水利工程和家室、自己态度的比较,司马迁不仅给读者表现出夏禹德操的高尚,而且表现出了夏禹生活俭朴的高尚美德。同时,司马迁也给人们活画出一个清廉之官的形象。当然,夏禹的父亲鲧九年治水无成,也是夏禹尽心尽力治理九州的一个隐喻情境。因而夏禹不敢有任何怠慢,只能“薄衣食”“卑宫室”,夜以继日,努力把治理九州的事情做好,这也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勤奋的人、一个纯粹的人必须要做好的。
所以斯泰宾认为:“隐喻是一种不明说的比较。”[10]93比较其实就是表达者对表现对象的一种艺术性重组,而通过这种重组,表达者便实现了对对象的隐喻性表现,也即隐喻性映射。因此说:“隐喻的特点是意义的转移,它从字面意义映射到某一个隐含意义。”[11]71而且,“它能以已知喻未知,以熟悉喻生疏,以简单喻复杂,以具体喻抽象,以通俗喻科学,从而形成一种抽象思维手段,发挥其思维功能”[11]78。所以司马迁在表现夏禹形象及其功绩的时候,经常采用的策略就是隐喻,或隐喻式思维。他往往并不直接表述,而是采取寻找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或关联性,进而对事物进行重组式的表述,从而不仅使得所表现的人物性格鲜明,而且实现了言此意彼的隐喻效果。按照“选择从属于表达”[12]20的原则,对于要表达什么,表达者心里是明白的,因而当他要表达的时候,他会选择巧妙而合适的对象表达他所想表达的内容,这种选择和思维过程,正是隐喻形成的过程,因而司马迁以最精简而又最精确、以最充分且又最巧妙的方式表现了夏禹的德、能、勤、绩、俭,因为“整体的特征是通过选择它的细节来表达的。选择要求肯定一切与其本身有关的注意、享受、行动和目的。……它是走向与揭示历史过程中目的的统一性的那种实现冲动相统一的一个步骤”[12]110,这也许是更令人信服的一种历史表述方式。因为“隐喻总是根据别的什么事物向我们表明某种事物”[2]78-79,所以“隐喻和历史叙述都展现了这种有意图的性质”[2]79。因此说,“历史学家的任务,并不是向我们提供通过某种翻译规则与过去相联系的关于过去的反思或样式,而是形成某种可以用来理解过去的或多或少自主的手段”[2]79-80。所以司马迁对于夏禹俭朴一面的表现,并没有大书特书,而是表现在一种极其简化的叙述中,这正是一种隐喻的方式,它更加凸显了夏禹人格和形象的伟大。
因此,对于夏禹俭朴的一面,司马迁仅用了“薄衣食”“卑宫室”及其他甚为简洁的文字,叙述精简扼要。这样的叙述,其蕴含却极为丰富、隐喻价值极高。而“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1]51式的叙述,不仅是一种情境的铺设,而且也可以看作是夏禹俭朴的隐喻,但和“薄衣食”“卑宫室”相比,其隐喻内涵就显得更为丰富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