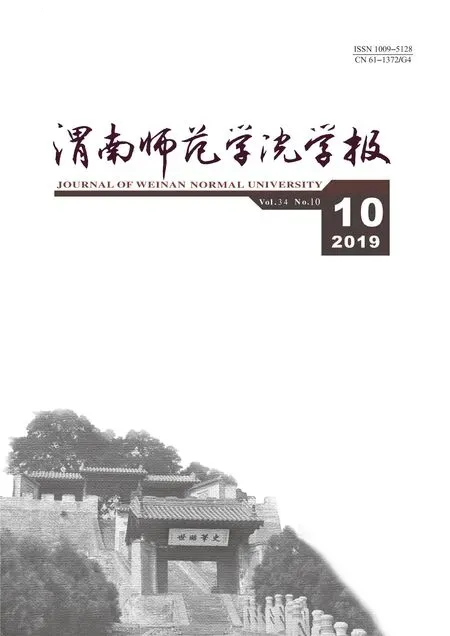从三晋地域文化与司马迁的关联看其出生时间应在前145年
崔 凡 芝
(山西大学,太原 030006)
一、司马迁的出生地与初期学习
《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1]3293此处之“龙门”指地区。司马迁故籍韩城就在龙门地区。此地区的标志物,一为黄河水,一为龙门山。龙门山横跨晋陕两界,黄河水由晋陕峡谷奔流向南,两岸断山绝壁,相对如门,传说为大禹治水所凿,故称禹门,又传说有神龙在此升天,便称作龙门。这里景致奇特,充满神秘,司马迁以之为桑梓之地,当有自豪的情感在内。
古称山之南,水之北为阳;又山之东,水之西亦为阳。龙门山为梁山之余脉,跨黄河两岸。黄河水蜿蜒曲折出禹门口,折而由北向南,把龙门地区分为河东、河西。梁山在黄河之西,韩城正处在龙门山之南30公里之地,在黄河之西,梁山之东,韩城南边是一马平川的一个小平原,称韩原,这就是“迁生龙门”的故里,统称为河山之阳,是一块风水宝地。司马迁祠墓就坐落在韩城南10公里芝川镇司马坡上,靠近黄河。司马迁的出生地,在韩原的华池、高门,在芝川镇西,相距约4公里。
地灵人杰, 司马家族人才辈出。司马迁生于圣地,长于圣地,耕读于故里河山之阳,厚重的河西文化养育着青少年司马迁的成长,当是一种美好的感受,而庄肃地书于《太史公自序》中。
“耕牧”指家业活动。不一定专指司马迁从事耕作放牧,而是指居于乡间生活与成长,家庭从事耕牧业,未必指亲身耕牧为生。古代占有乡间土地者,及其佃户统称耕牧良民,并非专指依赖土地生存的贫民雇农为耕牧之民。韩城处黄土高原丘陵地区,古来就是农业畜牧长足发展的地区。
“诵古文”是童蒙从学的一个阶段:五六岁开始学习,先认读今文写的书籍;稍大后认读古文写的书籍。今文指当时通行的小篆、隶书等,笔画简直,好认;古文指秦以前六国通行的大篆,即籀文,笔画繁复,不易认读。司马迁十岁开始读古文,一个“则”字,可能说明是比较早地进入了对先秦典籍的研读,有几分自得。亦可推测,其家庭对他的培养是很注重的。
这里需要探究的是他在哪里开始自己的学习的?
首先,要确定一下他父亲的行迹,因为他的人生和事业是在父亲司马谈的言传身教下发展的。司马谈生在何年?已无资料可考。只知其于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举贤良对策,出仕为太史丞,被派往茂陵督建武帝陵寝。如司马迁出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则父亲去茂陵时,他已五岁了。司马谈于建元三年(前138)至建元六年(前135)间升为太史令,去京师任职,但家眷仍在韩城,已是十岁的司马迁只能随家人在韩城诵古文和进行深入的学习以投入到父亲指导的著史工作中。直到元朔二年(前127),他家才入籍茂陵,此时司马迁已将近十九岁,之后便是二十壮游,进入游学阶段。所以,他的初期学历,应该是在韩城故乡完成的。而他的家庭和当地的文化底蕴也完全可以提供他学习的一切条件。
二、故乡与家庭条件
(一)故乡情况
韩城在晋、豫、陕的三角地带,这是中华民族的直根之地。三晋文化区是直根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南地区又是三晋文化区的核心部分。
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说:“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至7000年前到距今2000余年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2]又说:“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南方文化的交汇撞击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群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中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发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3]243
从司马迁所撰《史记·五帝本纪》来看,五帝的活动多在运城地区。炎帝、黄帝、蚩尤大战的阪泉、涿鹿之地,一说在河北,一说在运城。从考古发现来看,河北缺乏充分的证据,但晋南运城地区则有较多的传说和考古遗迹。今运城下辖的解州镇,古时曾称作解梁,据《解州县志》记载,解梁古时曾称作涿鹿。宋代罗泌所著《路史》就肯定解梁是涿鹿,“解”字,有解杀之意,起因就是黄帝在这里解杀了蚩尤,民间俚俗亦谓解州盐池有时呈赤色,即蚩尤血所染。俚俗之言仅作备闻而已。而汾西陶寺的发现,考古界认为正是尧舜时代进入父系氏族方国时代的有力证据。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自然环境优越,当平原地区被大水所淹成为泽国的情况下,运城地区是最适于人类居住的丘陵地带,山清水秀,土地肥沃,盛产铜矿,又有生活所需的池盐,是当时最富庶的地方。不只炎黄二部族挺进于此,连东南方的蚩尤部族也前来竞争。大战之后,便是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
之后,进入五帝后期相对稳定的发展生产时期。《左传·哀公六年》孔颖达疏:“尧治平阳(山西临汾),舜治蒲阪(山西运城),禹治安邑(山西夏县),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以运城为中心的晋、冀、豫等地区),统天下四方。”[4]显然,历尧舜禹三代,运城地区都是各方国的中心地带。
进入商代,据考古专家王克文研究,商朝的先人,也是起源于晋南的。辗转定都安阳后,其重要力量依然驻守于晋南,众多的考古发现足以说明这点。
周之先人从晋南兴起,迁徙到陕西后历经磨难,终于灭商。灭商时,其祖根之地由重兵把守,大大助力了武王的成功。国学大师钱穆曾经撰文详细论述了这一历史过程(见《燕京学报》1934年第10期《周初地理考》)[5]。而周人晋源说的观点在近20年来的考古发现中,也提供了坚实有力的证据。
春秋时,晋为五霸之一,而到了战国时,韩、赵、魏又成为七雄之三,这里演绎了争霸称雄最为震撼人心的剧目。而其高度的经济繁荣,灿烂的文明硕果,以及频繁的战争场面,促成了人才辈出的结果。从帝王将相、公卿大夫到平民百姓中,涌现了无数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以及史学家、文学家等。尤其由三晋兴起的法家思想和法家人物,荀子、韩非子、商鞅、范雎等提出的治乱兴衰的思想体系,在法家人物纷纷西进秦国后,帮助秦国统一了六国,促进了中华民族再一次的大融合,三晋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韩城、运城隔河而居。此段黄河古称西河。从风陵渡折向东去的黄河古称东河。运城在西河之东,故作河东;韩城在西河之西,称作河西。俗语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即指韩城在一段时间内所属河东治理,另一段时间内属河西治理的拉锯状态。实际上,秦汉之前,更多时间是由晋与三晋之魏治理的,此地的文化习俗有更多的运城特色,二者几近相同。现今进行的探源工程和探源游中,韩城与运城便视为一体,遗迹与景点并列其中。
黄河水并未阻隔民间的交往,水大湾多,可以摆渡过河,冬天结冰,便成通途。通商贸易不断,语言习俗相近,世代通婚联姻,清明扫墓祭祖,社火看戏观灯,平时走亲访友,人们熙熙攘攘,来来往往,早已形成一种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整体。故司马迁浓厚的乡情中,也满含了对三晋文化的深厚情结。
这一地区的文化积淀,包括了藏于民间的各种文化典籍,也体现在遍布乡镇的私塾乡学中,更有许多乡贤饱学之士。司马迁所处之汉初,遗风犹存,故其十九岁之前在故乡学今文,诵古文、钻研文献,考察史迹,起步著史,是完全有条件的。更何况,作为史官家族的后代,其学习条件更会优越于一般家庭的子弟。
(二)家庭条件
司马迁的远祖世为史官。西周时,其先人程伯休甫曾任官司马,以战功而改姓司马,但仍世典史职。后因政局大乱,王官失守,史官们抱典载籍流落民间。司马氏于周乱时迁入晋,晋乱时又各奔前程,或入卫国,或入赵国,或入秦国。司马迁这一支便定居到了秦国的少梁,即韩城。
韩城在战国后期,逐渐为秦掌控,司马迁的近祖先后当了秦的将军、铁官等,入汉后其高祖做过长安市长,但他们的家眷依然居住在韩城,死后还是要归葬于此地。其祖父司马喜未能任职,用四千石粟捐了个五大夫的爵位,可以享受一些特权,但其家业仍以耕牧为主,是个殷实之家。
农业社会重农抑商,视农耕为根本。“敦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是治家的格言。农耕传的是敦厚家风,诗书传的是文化积淀。
司马迁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而其世典史业的家世,又赋予了他献身修史的历史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从其先人,尤其是其父亲司马谈的培养和教育中传承下来的。
三、司马谈培养儿子立志著史
司马谈早有著史之志,他曾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废,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诚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1]3295因此,他自幼向学,成地方饱学之士;还曾设帐讲学,培养地方人才。由于他的学识和人品,再加上史学家世,被举为贤良,授作太史丞。升为太史令后,入京师供职,得以全力以赴地进行著史工作。
著史工作是艰巨的,司马谈深知其任重道远,故非常注重对儿子的培养。认今文,诵古文,研读文献,考察史迹,收集民间传说等工作,从青少年时已经开始。青少年时期有着更强的吸收能力,受父亲影响,他笃定了著史的志向,当父亲临终嘱托他要完成自己未竟的著史工作时,他泣泪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3295当触犯龙颜做生死选择时,他宁肯蒙受耻辱也要争取活下来,得以完成著史的重任。司马迁的使命重于泰山,是从父亲笃定的著史之志中传承下来的。
司马迁20岁以后,其学业开始了大转换,即受命父亲,开始大规模的游学活动,第一次游历江淮等东南一带考察史迹,搜集史料,以补充秦汉以来史料的不足。二三年后回来,又多次陪侍汉武帝巡视西北地区。还奉使巴蜀以南之云贵川地区,搜取更多边远地区的史料。
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全部游历中,很少提到去三晋地方,尤其是缺少到运城地区活动的记载。但苏辙曾在《上枢密韩太尉书》文中说:“与燕赵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5]381他自己也说“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货殖列传》中,对三晋地区的民情风俗也有很多精彩的描写:“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1]3271没有对世俗民情深入的体察,是不会有此深入描摹的。
可以推测,其在青少年时期,在立志著史思想的指导下,是会对祖根之地的历史和社会风貌做出考察与探访的。其对此地史事如数家珍似的稔熟,对英雄人物的由衷钦佩,流露的正是深厚的故乡情结。
故乡情结是一种人之常情。与司马迁同姓同为龙门地区河东夏县的史家司马光,在他的《和促通追赋陪资政侍郎吴公临虚亭燕集寄呈陕府祖择之学士》一诗中亦有同样的表述:“吾家陕之北,陕事吾能说。”“能说”是一种稔熟,如数家珍。他在《送促更归泽州》一诗中又说:“太行横拥巨川回,三晋由来产异才。”“产异才”是对故乡人才辈出的赞美,是满满的自豪。
史家之乡情流露在笔下,则其文更能感人至深。《史记》中所写三晋地区的史事与人物,往往是长篇巨著,浓墨重彩。
所以司马迁父子在故乡的生活、学习、著史,与三晋文化对他们的濡染,是密切关联的。既培养了他们美好的情操,又从多方面成就了他们的著史事业。现在我们回到本文开笔所引《太史公自序》的四句话:“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字面意义无疑是说司马迁年十九之前“耕牧河山之阳,二十南游江、淮”,步入社会按父母指引行万里路,做文史考察。“年十岁则诵古文”是一句插入语,指司马迁年十岁时的学识状态。所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对“年十岁则诵古文”前后均施用句号,表示是一个独立的句子单元。“迁生龙门”四句话导入司马迁两个生年假说,前135年与前145年。导入前135年,则司马迁九岁以前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只能解决为十岁的司马迁在京师诵古文,“诵”也只能解读为“开始学习古文”,与“则”字意义不吻合。“则诵”,即为学习古文,更含有能诵读古文。再说,“九岁孩童”怎么“耕牧河山之阳”?“迁生龙门”四句话导入前145年说,则司马迁十九岁以前“耕牧河山之阳”,才合于情理,合于字面意义的解决。更有两条文献支撑。其一,元朔二年汉武帝大移民十万口置朔方郡,迁家资三百万豪富实茂陵,游侠郭解、司马迁于是年家徙茂陵,司马迁正年十九,在茂陵见郭解。其二,《报任安书》云:“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这“长无乡曲之誉”明白无误地说司马迁在故里已经成人,没有得到地方官的荐举入仕,亦当指年十九。本文着重挖掘三晋文化对司马迁的熏陶,则有助于对“年十岁则诵古文”的正当理解,即司马迁年十岁诵古文在故里而非京师,可为司马迁生于前145年之旁证。对此,我们还应做更多探讨,因为这是十分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