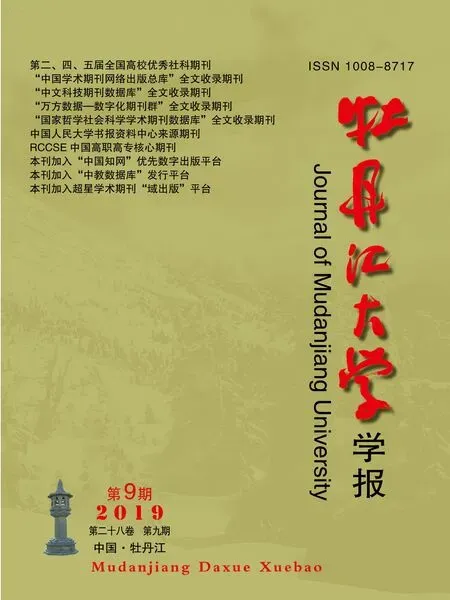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朱英诞《眼睛》赏析
娄 秀 娟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朱英诞,一位曾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诗坛上散发出耀眼光芒的诗人,一位曾在北大讲授诗歌的学者。耗尽毕生心血创作了三千余首新诗和一千三百余首旧体诗,却是一名“诗坛沉匿者”。其诗歌艺术成就有目共睹,废名评价“在新诗当中他等于南宋的词”[1]。但由于与时代环境的错位,使他隐匿在自己的“诗园小筑”中,为后人留下一座丰富的诗歌“宝库”。近年来,朱英诞逐渐被揭开神秘面纱,一步步地走近大众,开始散发自己独特魅力。本文从诗歌《眼睛》出发分析朱英诞五十年代的诗歌创作特点,以及探寻他为何在建国后隐匿于诗坛。
1948年是朱英诞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他在《华北日报》副刊上发表译诗及《吴宓小识》)。自此之后,朱英诞的作品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刊物和报纸上。然而这样的沉匿,并非诗人自觉自愿的抉择,其在五十年代初创作的以朝鲜战争为主题的诗歌——《眼睛》,可视为是他融入新时代而努力的成果。从具体诗歌内容便可看出,诗人在努力与时代对话,但遗憾的是:尽管他做出了新的尝试和努力,却并没有真正地走进时代。在被革命话语笼罩的时代环境中,他是那么的不合时宜,以至于“应时之作”(《眼睛》)都因“感情纤细”被出版社退回。这使他明白自己的尴尬处境,于是他回到自己的“乡下”,将自己的诗歌“埋葬”。
一、 日常化审美意象的坚持
王泽龙教授曾提出:“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影响最大的就是象征主义诗潮,几乎中国现代主义诗人中没有一个不与象征主义诗歌发生联系。”[2]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活跃于三四十年代北平诗坛的朱英诞与象征主义诗歌有联系且受到过影响,是合情合理的。象征主义诗人重视意象,尤其重视意象在表达上的重要作用,喜欢通过叠加组合意象来传达诗意、表露诗情。朱英诞的《眼睛》正是通过叠加组合“女孩”“眼睛”这两个意象,并结合隐喻象征手法,赋予诗歌新鲜的诗意。
“纯”与“美”——女孩
《眼睛》中的“女孩”象征着美丽纯洁,是作者特意选取的用以寄托主观情感的意象。在诗人早期的诗歌中“女孩”这个意象并不少见:“这是一条冷清的小巷,/美丽的女孩仿佛是光明”(《小巷》);“我携带着女孩 ,/像太阳携带着月亮”(《过司法部街》);“啊孤独是太阳,/这里朴素的女孩像花像月亮”(《孤独与侣伴》);等。在诗人的眼中女孩如花似月,不但是美的化身,更是理想人性的化身。故在具有“时代意义”的《眼睛》中,他选取心中最美、最理想的“女孩”作为诗歌的情感载体。用“女孩”来象征美好纯洁,在三四十年代的象征主义诗歌中比较常见,由朱英诞笔下的女孩不难联想到戴望舒笔下“像丁香一样的姑娘”。意象“女孩”虽在三四十年代备受现代诗人青睐,但建国后的诗歌创作却逐渐被忽视,甚至被攻讦。
1950年初,《文艺报》开设“新诗歌的一些问题”的笔谈专栏,就新诗如何能更好地适应社会与时代展开讨论。《文艺报》编辑部在《新诗歌的一些问题》中对1949年底天津《进步日报》上刊登的一首小诗做出严厉批评,以此说明当时诗歌存在的一些问题。小诗:“小姑娘/赛天仙/花花俏俏走当前/头上梳了几根辫/根根辫子鲜花簪”(宁以:《锣鼓声》)。编辑部批评作者在诗歌中没有深刻体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更没有表露出自己的阶级意识。
不少诗人对表露“阶级意识”各抒己见。王亚平提出:“‘政治立场不清,那就是成为严重的立场问题’,同时要求广大的诗人要‘深入工农兵”,从思想上转变自己’,‘变自己的思想、情感成为人民大众的思想情感。’”[3]郭沫若认为:“写诗歌的人,首先要求他有严峻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为政治服务的意识。”[3]而何其芳在《话说新诗》中强调:“我们必须知道,社会生活也好,时代精神也好,诗的情绪也好,都是变动着的。在阶级社会里,都是有阶级的区别的。”[3]而诗人该如何在诗歌中表现自己的阶级意识呢?方法之一便是攫取宏大崇高意象。
同样以抗美援朝为诗歌主题,王亚平开篇便是“起来,全中国的人民/抗议美帝的暴行!”(《抗议,美机的暴行》),艾青更是高声呐喊:“挺起我们的胸膛/我们要做自由人/亚洲人团结起来/和美国强盗厮打”(《亚细亚人,起来!》)。臧克家也不甘示弱地吼道:“胜利的箭头,射出去/射出去,从“三八线”的弦上/用了朝鲜人民的权利,射出去”(《胜利的箭头,射出去》)。当同时代诗人都在呐喊“全中国的人民”“亚洲人”“朝鲜人民”时,朱英诞低吟:“孩子们都愿望参加志愿部队啦/只我们‘史沫特莱班’就有六个女孩签了名/这些美丽的女孩都还在十五岁以下/虽然她们不能如愿地跑到前线去,却不能不受到赞美:最纯洁、光明的/毛主席的优秀女儿!谁能不赞美呢?”对比同时代同主题的诗歌,便可知朱英诞这首诗歌被拒之因——“女孩”这个意象显然并不符合当时的时代语境和创作要求。更重要的是,在表现阶级意识面前,“人民”显然比“女孩”更有力,也更能为大众所理解接受。
“窗”与“镜”——眼睛
眼睛,被誉为“人类灵魂之窗”,透过它可以透视人们内心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和隐秘的精神世界。顾恺之曾说:“传形写影,都在阿睹之中”。“睹”指的便是眼睛。从“眼睛”的“窗”与“镜”的特征出发解读“眼睛”意象,有利于挖掘诗歌中蕴含的情感。
达·芬奇说“眼睛叫做心灵的窗子”(《笔记》)。透过眼睛窥探去心灵,是一件多么美丽的事。正是这样诗人才能写出:“这些美丽的眼睛怎样看着红旗噼啪噼啪的飘扬,/就怎样看祖国的边疆和人类的心脏,/就怎样看你们,英勇的人民战士啊!/她们看着你们出发,战斗和凯旋,在和平的春风里。”这样美丽的诗句。女孩用自己美丽的眼睛看英勇的人民战士出发、战斗、凯旋,诗人把她们“看战士”的目光同“看红旗、看祖国边疆、看人类心脏”的目光等同起来,赋予人民战士以崇高伟大。而在女孩们灼灼注视的背后,诗人也在看女孩们,他透过这些美丽的眼睛,看到女孩们内心中对战士的崇敬、赞扬以及美好祝愿(祝愿他们能平安归来)。
眼睛同时又是一面镜子:“但是,眼睛都是美丽的,都是美丽的;/每一对眼睛和另一对眼睛一样;/而我们的祖国和山河大地就整个的坐落在/任何一对美丽的眼睛里;/我们的祖国有多么美丽,/我们的美丽的女孩的眼睛就有多么美丽。”诗人利用眼睛的镜像特征来表示眼睛之所以美丽,是因为祖国美丽,借此传达出对新中国的赞扬。诗人借眼睛来倾述对祖国的深情,通过一对对美丽的眼睛折射出新生活的美好。
诗人通过组合、叠加及重复“女孩”“眼睛”来传达诗意诗情,这带有明显的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意味。在同时代诗人强调诗歌的责任,在诗歌中不断树立宏大崇高意象时,朱英诞坚持将日常化意象入诗,坚持在日常化意象上建立现代主义的象征和隐喻,用一种“清新婉约”的方式隐约抒发个人感悟。仅从意象的攫取上,便可知建国后朱英诞沉匿是必然——做不到“随波逐流”必然被浪头淹没。
二、曲折隐晦的主题呈现
《眼睛》可算作朱英诞勉力的“应时之作”,虽然这首“应时之作”并不符合建国后新诗的审美旨趣。在诗歌中诗人通过学校中一群青春女孩对美帝侵略者愤怒的眼睛,来表露国人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怒,但在具体诗行中,看不到愤怒控诉,听不到激亢呐喊,字里行间皆是清新温婉。诗人另辟蹊径创作出的清新战争诗,不仅秉承其田园式创作风格,更与其当时身处的环境脱不开关系。建国后,朱英诞从唐山回京,先后在北京贝满女中、北京三十九中学任教。这六个纯洁美丽的“史沫特莱班”女孩极可能就是他的学生,由这些女孩最纯洁、最光明的眼睛里他看到了她们对国民的热爱,正是这份热爱点燃了他的灼灼诗情。
大隐隐于市。朱英诞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来关注世事,来坚守自我。在诗歌美学上他始终与主流话语保持距离,坚守着一种疏离和偏移。而这种疏离和偏移由其对“晦涩”的坚持上可以看出,在“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号令下,在诗歌中坚持“晦涩”是危险操作,这不仅“脱离群众”,且“立场模糊”。通过《眼睛》这首政治型的战争诗歌,更能看出他不自觉的坚守——即使是赞扬祖国和人民,也是含蓄曲折,而非直接高声告白。
诗人通过“胜利的白鸽飞起像夏天的白云”“直到你们回答她们美丽的眼睛的注视里”“她们看着你们出发、战斗和凯旋,在和平的春风里……”隐晦暗示人民战士定会旗开得胜,打败美帝侵略者。但他不像王亚平那样直白“垂死的美帝主义者/有什么方法能够抵抗?”更没有艾青的决绝“叫醒我们所有土地/为敌人准备下坟墓/让那些流氓海盗/不准有一个生还!”在《眼睛》中除“野兽”外,再找不到其它情绪词。多么可爱的朱英诞!仿佛“野兽”便是他能想到最能代表罪恶的词,他没有直接表露出对美帝侵略者的憎恶仇恨,而是通过书写“美丽”反衬“丑恶”,情感的隐晦表达赋予诗歌深度抒写的空间。
诗歌中穿插的疑问句:“毛主席的优秀女儿!谁能不赞美呢?”“为了它们,我们能不竭尽力量保卫山河吗?/能叫野兽跑过鸭绿江来玷污这些美丽的眼睛吗?”既可看做是诗人与自我的对话,也可看做是他与读者的对话。这三重疑问强调“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点明为何“抗美援朝”势在必行,打败美帝侵略者刻不容缓。“志愿部队”“美帝暴行”“野兽”“胜利白鸽”“朝鲜诗人咬牙切齿的声音”“凯旋归国”等词语可以明确诗人意在歌颂“抗美援朝”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正义之战。
诗人在第五节笔锋一转:“但是,眼睛都是美丽的,都是美丽的/每一对眼睛和另一对眼睛一样/而我们的祖国的山河大地就整个的坐落在/任何一对美丽的眼睛里/我们的祖国有多么美丽/我们的美丽的女孩就有多么美丽。”从这里诗歌开始分层,由控诉美帝暴行转向赞扬祖国山河大地。看似第五节独立于其它诗节之外,而这正是诗歌巧妙之处,当其他诗人都在诗中以口号式的呐喊贯彻诗歌头尾(“和平是人类希望的化身/和平是中朝人民力量的铁证/时间如果没有使侵略者长点智慧/那么,也一定叫他们尝到了要命的苦痛”[4])来强调“援朝”之战必胜时,诗人选择用祖国山河大地的美丽来暗示这份美丽来之不易,而一旦美帝侵占朝鲜成功,那美丽山河将会再次面临支离破碎的威胁,映衬美丽山河的眼睛也将变成含着血泪的眼睛。看似断裂,实际上是有内在的血肉联系。虽然朱英诞竭力想与时代发生联系,为时代发声,但他不盲从时代风尚,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来抒写时代,来与时代对话。
三、无邪清净的诗情
郭沫若在50年代初讨论“新诗歌的一些问题”时提出:“诗歌应该是最犀利而有效的战斗武器,对友军是号角,对敌则是炸弹。”[3]何其芳强调:“诗要求更强烈的情绪。”[3]不少诗人在创作中自觉地践行:冯至宣告“我们写诗——//歌咏英勇的人民,/有最崇高的语言,/但诅咒无耻的恶棍,/要用最丑恶的字眼。”王亚平呐喊“我们站在鸭绿江上,/声援朝鲜人们的抵抗,/赶走美国帝国主义,/消减侵略者的武装。”在这类诗歌中,不难读出大众召唤语调:“我们要雪耻,复仇,/粉碎帝国主义的阴谋。”“他们为了要称王称霸/想把我们推进火坑/我们应该齐声怒吼:/‘这是一万个不可能!’”汹涌豪迈扑面而来,当同时代的诗人都在齐声呐喊时,朱英诞轻声低喃“我曾看见她们悲愤的眼泪和指血,/不曾听见她们欢呼和鼓掌的声音;/我也曾和她们在一起流泪,欢呼,/现在,我们正听着朝鲜诗人咬牙切齿的声音/欢呼着,知道你们凯旋归国/直到你们回到她们美丽的眼睛的注视里……”这样内敛含蓄的情感表达,难以表现党和人民的英勇豪迈和突出工农兵群众生活。确切地说,诗歌中更多的是主观个体的抒情,而非大众语调的传递。
当诗歌逐渐被当做政治宣扬的“工具”时,朱英诞不接受这样的转变,他明确表明:“我只是‘诗人’。逃人如逃寇。一向只是为自己写诗,然而我对于诗歌却永远是虔诚的。人生经验是什么也不爱分析,也不能解说,什么都马虎,什么都置之度外,我所珍惜的是纯粹的情感。其实诗也毫无秘密,我愿意说诗只是生活的方式之一……诗是精神生活,把真实生活变化为更真实的生活。”[5]正因如此,在其诗中读者才能感到在激情澎湃的时代里难能可贵的“和静”之美,这份“和静”源于诗人独特的诗学品格。他坚守诗歌的清净,不赞同在诗歌里有明显的目的性言说。在诗歌中他以普通人的视角出发,秉持着一个“沉默的冥想者”的姿态,将普通人的所感所想熔铸进自己的诗歌中。
《仙藻集》题记“在我们的大传统里,诗本来是提倡生活的一面,平平无奇,故也无所用智。”[5]并复引夏芝则“在高唱理由与目的时,好的艺术是无邪而清净的”佐证。不仅如此,朱英诞更重视诗歌的蕴含,“诗不能像一阵风吹马耳朵似的就吹过去了。或者是‘骆驼见柳,渴羌见酒’,那样也不行。”[5]他说“窗外石榴树盛开着谎花,并静静落下,我在窗下作诗,我感到理想与现实几乎密不透风地分不开,然而,诗绝非谎花;它应该是同时开花而又结果的。”[5]诗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比,说明理想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是不能永远被抛弃或压制的。
纵然他坚守在自己的诗园小筑里,但内心里还是有一股要与世界建立新联系的欲望,故勉力创作《眼睛》。尽管是“应时之作”,他还坚持“不喜官样文章的臭味”,不屑标语口号式写作的创作原则。正如他晚年在自传中所说“废名先生的桥随风飘去了。我以小小的野渡“纵然一夜风里去,只在芦花浅水边”。这是他甘愿自处文坛边缘的自白,在这场孤独诗歌之旅中,他秉承自己的美学理想和追求,不在乎是否被时代接受,是否被大众遗忘。虽然他也有过短暂迷失,但所幸他很快就清醒了。他宁愿做一个有思想的“沉匿者”,也不愿做一个空洞的“传声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