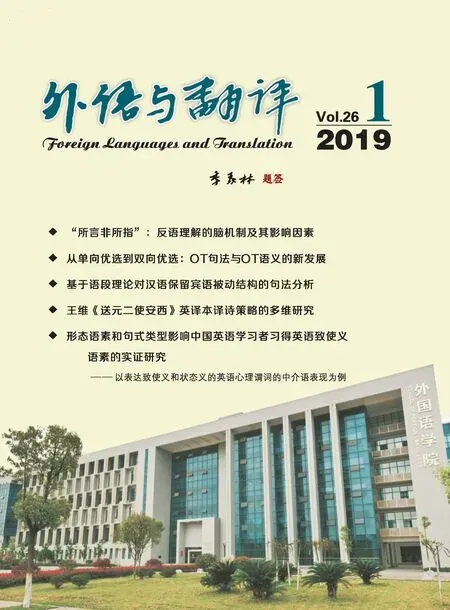当代美国白人作家的生态“失乐园”情结研究
——以查尔斯·弗雷泽的印第安生态书写为例
周弘毅
空军航空大学
【提 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印第安文艺复兴”让美国文艺界意识到了印第安生态哲学对美国社会的治愈价值。然而,始于“西进运动”的印第安生态文明衰颓已无法挽回,这成为许多白人作家心中的隐痛,这种心态即生态“失乐园”情结。查尔斯·弗雷泽是少数在作品中深刻体现这一情结的美国白人作家,他的生态书写描述了印第安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对抗与交融,反映了文艺界对失落的印第安文明的缅怀和反思,在美国独树一帜。
1.查尔斯·弗雷泽——为印第安人发声的白人作家
美国文学史上,印第安作家一直受到主流文化的压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皆处于失语、半失语状态,其绚丽、诡谲的文学作品未能引起评论家和读者的足够重视。而在作品中涉及印第安文明,尤其是“西进运动”中印第安部落血泪史的美国白人作家,则大多站在入侵者的立场上,对印第安人进行不切实际的丑化,将其描述成野蛮、冷血、愚昧的异类,如Margaret Hill McCarter所著《草原的代价》(The Price of the Prairie) 和 Steward Edward White的《长枪》(The Long Rifle)皆属于这类作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印第安文艺复兴”标志着“印第安文学”从隐没走向繁荣,印第安文学,以及涉及印第安文化的白人文学受到越来越多批评家,特别是生态批评家的关注。1999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第三届会议专门就这一论题进行了讨论,印第安文学俨然已成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流派中最富有活力和革命潜力的一支。一方面,以Scott Momaday和James Welch为代表的印第安作家在文学界迅速崛起,为印第安文明的保存和发展摇旗呐喊;另一方面,作为美国文学主流的白人文学界,仍鲜有作家能主动消解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隔阂,对印第安文明进行客观和深刻的书写。查尔斯·弗雷泽(Charles Frazier)是这少数白人作家中的一个。
在1997年出版小说《冷山》(Cold Mountain)而大获成功后,弗雷泽成为当代美国最受关注的作家和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并分别于2006年和2011年出版小说《十三月》(Thirteen Moons)和《夜林》(Nightwoods)。因其特殊的家庭背景,以及在冷山(位于北卡罗莱纳州西部一带,曾属于印第安切诺基部落的领地)上长达十几年的隐居生活,弗雷泽的三部作品中带有浓郁的印第安土著情结,其对印第安文化,尤其是印第安生态文明的深刻感触和独到见解在作品中得到了体现。同时,由于西方工业文明在弗雷泽的身份建构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他的作品也折射出西方文明与印第安文明之间的激烈碰撞和一定程度上的融合。在他的三部作品中,《十三月》被收录于美国“切诺基土著博物馆”(Cherokee Indians Museum)的“切诺基文学计划”(Cherokee Literature Initiative)中,成为第一部被译成切诺基语言和音韵的美国白人文学作品。
2.隐匿在印第安生态书写中的“失乐园”情结
作为一位与印第安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白人作家,弗雷泽在叙事风格上对印第安的“长老口述”形式多有借鉴,如《冷山》中对印第安“击棍球赛”和“世外桃源”的描述,又如《十三月》里主人公威尔·库伯和酋长“熊”之间大量的对话和独白。这种刻意弱化现代文学普遍采用的叙述手法,而加大对这种并不常见,甚至稍显怪异的“口述”模式的使用到底出于何种目的?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哲学家Claude Levi-Strauss在《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中论及“原始思维”(the Savage Mind)时,继承了意大利法理学家Giambattista Vico关于“原始人类”非但不野蛮,且具有其独特的“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的观点,并进一步研究了前工业(pre-industrial)族群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情况下,“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对社会的建构作用。Levi-Strauss(1966:93)认为,由“诗性智慧”和“口述传统”所创造和流传的“神话体系及其表达方式使得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同源关系得以建立,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使得在以下各个不同层面上的差异得以等同对待:地理、气候、动物学、植物学、技术、经济、社会、仪式、宗教和哲学”。 Levi-Strauss 指出,“书写系统”(writing system)间接性重构了人类社会,它虽然极大地拓展了人际联系,却也使得这种联系变得“不可信”(unauthentic)。在美国当代小说的语境中使用印第安“口述”模式,认为,一方面弗雷泽试图用这种非主流的、异域性(exotic)的话语系统重构美国当代社会;另一方面,他在进行小说创造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反思当代小说的主流写作模式和主流文学语言对“作家-读者”关系,乃至人与人之间关系可能存在的不利影响。
就小说的故事情节和精神内核而言,纵观弗雷泽的三部作品,从《冷山》中印第安“丛林法则”的异变,到《十三月》中资本主义对土地的侵蚀,再到《夜林》中的“乐土”丧失、人心不古,弗雷泽对北美大陆上两种文明交融对抗的理解越发深刻,对印第安文明的缅怀也越发沉痛。鉴于弗雷泽小说中广泛采用的印第安口述模式独特的象征意义,以及小说中大量关于印第安生态智慧的描写和贯穿小说始终的生态追求———事实上,弗雷泽借鉴“口述”模式的目的之一便是出于生态方面的考虑可将弗雷泽的三部作品称为“印第安生态书写”。通过对弗雷泽三部小说进行整体性研究,笔者得以窥见隐匿在印第安生态书写脉络中当代美国白人作家的“失乐园”情结。
2.1“乐园”丧失——“丛林法则”之异变
著名的生态主义学者White(1996:6)在论文《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中,对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生态危机进行了精神层面的剖析,认为“人类对生态所采取的行动取决于他们对自己与周围事物之间关系的理解……简而言之,取决于人类的信仰”。White(1996)指出,圣经声称上帝依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并赋予人类管理和支配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以及地上所有牲畜与昆虫的权力,这使得一种思想在西方人心中根深蒂固——人类高于其它一切生物,并对世上万物具有管理权和支配权。后文艺复兴时代的启蒙运动虽然冲击基督教文化,却进一步强化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加深人类与自然的决裂。一方面,工业文明的发展将机械论自然观推向高潮,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达到空前程度;另一方面,Darwin“进化论”中“适者生存”的法则在西方资本主义语境下被曲解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为人类对其它物种的暴力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同的是,印第安人遵从着“平衡共生”的丛林法则。深层生态学哲学家 Naess(1995:28-29)说:“深层生态学的基本规则之一是,每一种生命形式原则上都有生存和繁衍的权利……没有足够的理由,我们没有权利毁灭其它生物”。这与印第安人几百年来秉承的自然观是契合的。印第安人没有宣扬人类至高无上地位的宗教;相反,他们一直秉承“生命之网”的宗教信念,认为万物与人类同根同祖,休戚与共。显然,弗雷泽对这两种观念及其影响有着深入的思考,并在其作品中对两者进行了对比。在《冷山》中,一方面,作为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南北战争”演绎着残酷的竞争,人类毫无节制地自相残杀,目的是获取对敌人命运的控制权;另一方面,逃离战场的英曼在大自然中经历诸多磨难,像印第安人一样捕食猎物,同时也躲避着猛兽的攻击。战场上的杀戮让英曼的灵魂“几乎已经燃尽”(弗雷泽2004:15),而在大自然中生存的经历却使其重新获得了对生命的热爱与尊重,以至于在故事的最后,当英曼面对追捕者时,放弃了杀死敌人的机会。在后续作品《十三月》中,印第安文化中的“平衡共生”原则得到了更好的诠释。在西方入侵前,印第安土著人将所有生命体和非生命体视为与人类同根的“其他的人”(the other people):在捕杀猎物前要进行虔诚的祷告,因为捕猎并不是人类对其它生命的征服,而是动物为了人类的生存心甘情愿地奉献出自己。这种“感恩”使得印第安人从不过度捕猎,因此,自然便能保持微妙的平衡。西方人眼中残忍无比的土著部落战争在印第安人看来不过像一场“击棍球赛”。在这场“比赛”中,死去的人为活下的人和动物腾出生存空间,自己则进入轮回,生命如同“十三个月亮”一样流转不息。这种生存方式与西方人所崇尚的“安全”、“理性”等原则格格不入,却一直维持着当地的生态平衡。不过,这种“平衡共生”的丛林法则最终免不了被西方的“弱肉强食”理论所取代,走向衰亡。至此,“乐园”也不复存在。
弗雷泽在小说中对印第安“平衡共生”法则消亡的思考实际上代表了二十世纪末以来,具有生态良知的美国白人知识分子对“西进运动”所带来的印第安生态文明消亡的反省。西方文明入侵期间,白人屡战屡胜,土著死伤惨重,战争已经不再是维持生态平衡的游戏,而是带来种族灭绝的资本扩张。商品贸易传入印第安部落后,狩猎也不再是为了获取食物来维持生命,而是为了换取经济利益。如此,印第安人与世间万物相依共存的状态随之被西方式“物种统治”所取代。在《十三月》中,弗雷泽通过老酋长熊(Bear)晚年时期的忏悔“口述”表达了自己对这种变化的遗憾:熊也不例外地有那种自我悔恨。他最后几年常回想死在他手上的许多动物。他说为吃饱肚子而杀死动物他倒不后悔,但他希望没有为了买卖而出去打猎。这个世界还没老的时候,曾有动物祈祷词,为野外的这些住客祈祷,祈求它们原谅自己出于无奈为充饥而杀死动物,特别是熊和鹿,让它们流血。动物身上有很多血,令人惭愧,如同杀人。可后来,就在不久之前,杀戮突然能换钱了。鹿皮甚至成了货币……一块鹿皮正好值一元(弗雷泽2010:236)。
2.2回归“乐园”———“奥德赛”式英雄旅程,还是印第安式寻根之旅?
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冷山》与《奥德赛》之间的关联,将英曼充满艰险的归乡之路与Odysseus的英雄归途做比较。例如,南开大学的熊培云(2017)曾结合“漂泊/还乡”这一文学母题,比较《冷山》与《奥德赛》之间人物设置和精神内涵上的异同。在访谈中,弗雷泽也提到了《奥德赛》对《冷山》这部作品创作的影响。但是,从弗雷泽三部作品中一直延续的“乡土情结”以及怀旧和叛逆的文风来看,与其说《冷山》是“荷马史诗”在美国的再现,不如说它是借“英曼归乡”这一叙事解构《奥德赛》所代表的西方神话,动摇新大陆上业已稳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随着这一书写而来的是一种比英雄崇拜更原始、隽永和深刻的情感:乡愁。除此之外,《冷山》的“奥德赛”还有另一层意义:它象征着弗雷泽潜意识里对回归“乐园”的渴望。
从《冷山》的故事情节上来看,弗雷泽将英曼的归乡之路写成了典型的基督教式“救赎之旅”——在旅途中洗净手上的血污,为灵魂疗伤、给躯体驱魔。然而,这场救赎的精神内核却是崇尚非西方文化的。首先,“英曼归乡”的精神内核是“反英雄”的。作为西方文化核心的古希腊神话和基督教文化崇尚英雄主义,这种文化内的救赎是英雄的救赎,其过程和结果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和征服意志;相比之下,作为非西方文化重要支脉的印第安文化从不赞美人类的欲望,但对人和土地之间血脉亲情的珍爱却从不掩饰。英曼是个“逃兵”,其归乡的目的是出于灵魂的安宁和对故土与爱人的眷恋,具有一定的“反英雄”倾向;或者,用深层生态学的术语说,“英曼归乡”是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其次,“英曼归乡”是印第安式的“出世”。《冷山》中,一个外乡人——可能是印第安人,但原文中并未明确说明——通过“口述”的方式向饱受战争之苦的村民讲述了冷山之上一个世人难寻之地:“开阔的田野,还有一条河,河边是富饶的土地,种着大片的玉米……人们在广场上跳舞,远远地可以听见鼓声”;而要通往世外桃源,必须先“去村会堂斋戒七天,在此期间不能出去一步,不能发出战斗的呼声”(弗雷泽2004:194),最后从一个叫做“光明岩”(the Shining Rocks)的狭窄之处进入。这一难寻之地暗指的是现代“印第安保留地”。它与《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以及《道德经》中所描述的“小国寡民”图景是否存在关联?弗雷泽对印第安生态智慧的理解是否融入了些许“禅意”?对此,笔者只能从《冷山》扉页中引用的中国唐代诗僧寒山子的一句禅诗中窥见一二——“人问寒山路,寒山路不通”。对“世外桃源”的描写映射出英曼救赎之旅的真正目的:回归到“生态栖居”(ecological inhabitation)中去。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英曼是白人,但“乡土”这一符号对他而言已经有了土著内涵,这点单从他的回忆中便可看出。与美国白人不同,乡土在印第安土著人眼中并不是记载于书面文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的资本或产业,而是与部落神话和图腾融为一体,承载了部落历史、先祖遗骸和自我身份认同的神圣土壤。1854年,印第安酋长Seattle在被后人称为《西雅图宣言》(Chief Seattle’s Manifesto)的演讲中说:“我们一直记得,大地不属于我们,而我们属于大地,世间万物如血肉亲情般连接为一体……我们只懂得,我们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他对大地无比珍视,亵渎大地就是对造物主的极度蔑视”(Lisa&Jon 2004:23-24)如今,印第安人所支配的土地不到四百年前的百分之三,正如秦苏珏所(2013:112)说:“失去承载着部落和家庭历史的土地、生存环境的巨大改变必然从精神上造成土著人的情感创伤,导致他们个人身份认同的危机”。作为白人作家的弗雷泽不仅敏锐地察觉到印第安土著人现在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更是发现印第安乡土情怀中的生态意义。他告诉世人,回归印第安式“生态栖居”,是解决当前战争、环境等问题的有效途径。
2.3“失乐园”情结的发展路径———从“美丽的念想”到“沉痛的反思”再到“绝望的控诉”
以时间为轴,我们不难发现在弗雷泽的三部作品中,他对于“失乐园”的反思有着明显的变化。“乐园”作为三部作品中的核心意象,不仅仅代表着印第安生态文明,更是象征着弗雷泽在创作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探索与追求——弗雷泽企图通过“乐园”的失而复得来对现代文明进行重构。当然,和许多作家、批评家一样,他在重构的过程中发现了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难以逾越的鸿沟,即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二元论”所带来的文明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弗雷泽在不同层面上对认识和超越这一鸿沟做了一些尝试,这就导致了三部作品中的“失乐园”情结各有不同。
在《冷山》的结局中,英曼面对追杀自己的仇敌时最终选择了宽恕和谅解,走向自然和死亡,二元对立看似得到消除。这时,弗雷泽心中的“失乐园”情结表现为可实现的“美丽念想”。但是,在克服二元对立时,摒弃一方而全然接受另一方,或者完全脱离理性而奔向感性都是治标而不治本,必然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冷山》中的“乐园”之寻并非是生态的、圆满的。
在《十三月》和《夜林》里,小说历史背景下的主要冲突不再是《冷山》中的南北冲突、忠奸冲突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而是更深层次的对立: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思维方式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对立。《十三月》中,印第安人古老的生活方式在西方的大举入侵面前尚能抵抗一番,但主人公库伯错误的策略直接导致了抵抗的失败。借此,“失乐园”情结表现为“沉痛的反思”。弗雷泽的反思一方面揭示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西方的殖民扩张中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也为印第安文化的没落史提供了自己的解读。小说主人公库伯可被视为弗雷泽本人,因为在库伯身上,西方文明和印第安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体现得尤为明显,他追求的目标和遭遇的困境与弗雷泽本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相同的:一方面,库伯致力于和白人政治家周旋,在历史的浪潮中竭力保全印第安部落的土地和文化;另一方面,他又渴望着用西方文明改造印第安旧世界,寻求新的出路。然而,在西方工业大发展的历史语境中,以“口述”、图腾和神话等形式作为载体的土著文化和以书写系统为载体,以法律、机器、规则为代表的工业文明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关系(即便是在二十一世纪,又有什么办法能彻底消除两者之间二元对立的鸿沟?)以“口述”为交流形式的原始社会有着更为紧密和具体的人际关系、亲缘关系,而现代社会赖以建立的书面文件和“行政机器”却使原本紧密的人际关系、亲缘关系流于形式,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是疏远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没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库伯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为了解决部落与西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库伯引进了书写系统和法律系统,企图通过全盘西化、现代化的方式保护族人、保护自然。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自作聪明反而加速了族群的瓦解和自然的损毁。他痛苦地发现,自己所引进的法律系统使得土著族人之间矛盾激化,原有的亲缘关系四分五裂;而且,被库伯发扬光大的商品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用于记账和拟定合同的书写系统将树木、动物变成了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土著人的动物伦理观念荡然无存。库伯晚年时期一段沉痛的“口述式”独白正好反映出弗雷泽对这一段历史的反思:
铁路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现在终于得到了。
它带来了什么?成群的游客,伐木业。
它带走了什么?其他的一切。(弗雷泽2010:305)
不过,库伯的无知恰巧反映弗雷泽对所谓“文明-野蛮”这一对立之理解和反思的逐步加深,同时也提出了如何化解这一二元对立的命题。
在《夜林》中,“失乐园”情结展现出它的第三种形态。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值“印第安文艺复兴”前夜。当时,美国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原有的价值观被颠覆,吸毒、滥交等现象层出不穷,自然环境也在剧烈恶化。与《冷山》和《十三月》不同的是,印第安文明在《夜林》中并没有明确出现,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印第安文明已经几乎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它赖以延续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岌岌可危,美国人在精神上和生态上都已失去自己的“乐园”。于是,在小说中,“夜林”——一个印第安古村落遗址——只是作为一个传说中的地点存在于主人公记忆的最深处,以“潜意识”的形式留存下来,象征被美国人遗忘的“乐园”,在现代化大都市的一个角落里控诉着白人对自然和非主流文化的压迫。”面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坚不可摧的堡垒,弗雷泽的生态追求走向绝望的深渊。此时,这种“失乐园”情结表现为如同《西雅图宣言》一般“绝望的控诉”。不过,在故事的结尾,随着矛盾的解决,“乐园”开始从隐蔽走向光明,希望死而复生,这也暗示弗雷泽心中尚未完全消泯的信心,预示着印第安文明即将迎来的复兴,为小说增添了几分明亮的色彩。
纵观三部作品,尽管叙事方式变化不大,但随着“失乐园”情结展现出不同的形态,弗雷泽的印第安生态书写中蕴含的情感愈发深沉,思考愈发深邃,这也反映从1997年到2011这段时间内弗雷泽的心路历程。
3.结语
弗雷泽作为一名美国白人作家,其对印第安文明,特别是印第安生态文明的热爱和提倡,在美国文学界实属难得。使弗雷泽的小说更具社会意义的是,他对消亡的印第安文化的反思反映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具有历史责任感和生态意识的美国白人作家在文化和生态两个层面上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来?到哪去?”的思考:作为美国白人的自己,到底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还是野蛮的入侵者?我们的文化根基于何处,精神家园在哪?如何才能拯救这片被欲望腐蚀的大陆?这种“胜者为寇”的失落感和愧疚感笼罩着像弗雷泽一样有良知的美国人。在不断发掘那些曾经让北美大陆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古老文明的同时,他们也在重建业已失去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