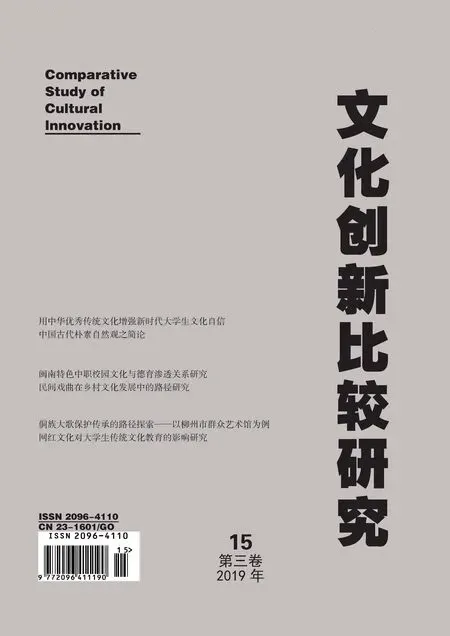历史叙事视角下的大江健三郎与莫言
吐 雅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引言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以下简称大江)与中国作家莫言分为于1994年和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都是享誉全球的亚洲作家。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并不仅限于此,这两位作家之间还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众所周知,在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大江就提到了莫言:“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我得以植根于我边缘的日本乃至边缘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到了一起。”(大江健三郎,2005)2002年,大江还曾亲自采访莫言,并在莫言的陪同下到山东高密县度过春节。并且,大江2006年在中国演讲时,更是称赞莫言是中国最有实力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大江和莫言之间有如此多的联系和互动,这种力量来自于他们文学上的血缘关系。在与大江的对谈中,莫言说:“你能千里迢迢飞越大洋,来到中国偏僻的农村高密东北乡,这种力量肯定是来自于文学。也说明我们两个人的人生起点和文学的起点有很多相似之处。”(大江健三郎、莫言、庄焰,2004)纵观莫言与大江的个人经历和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多个共同特点。其中之一是故乡情结。二者的文学作品都根植于他们的原始故乡、古老而偏僻的东方大地——大江笔下的日本四国地区的峡谷村庄,莫言笔下的中国山东的高密东北乡。他们通过对乡土与命运的不断书写,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学王国。另一个是历史叙事。大江经历了日本在二战中的惨败和战后复兴,莫言经历了中国的文革和改革开放。他们都体验了时代的巨变,带着异质的伤痕,站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交界线上,把个人的记忆分别纳入中日近代史的长河中,以历史主体的身份,历史地讲述民族的传统文化,思考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因此,深入地比较和分析莫言与大江的作品之间的“默契”,是一个极富意义的研究课题。
目前,无论是大江文学研究,还是莫言文学研究,国内外学界都有很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针对二者的对比研究相对较少。国外学界多关注莫言与福克纳、马尔克斯,有关莫言与大江的文学的对比研究则很少。日本有很多莫言作品的译介,但关于莫言和大江的文学的对比研究也很少。国内,有关二者的对比研究,有代表性的是张文颖所著的《来自边缘的声音:莫言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张文颖,2007)。该专著从二者的乡土情结即“边缘的声音”出发,对大江与莫言小说在“民间信仰”和“历史建构”等方面的叙事技法进行了研究,开辟了二者对比研究的新领域。此外,李红(2014)总结大江与莫言的文学特性,指出“鲜明的历史性、社会性、时代性”是二者共同特质之一,为二者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历史叙事这一新视角。但尚处于整体把握,对于二者的叙事技巧的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为了深入探讨二者在各自的文学创作中,如何历史地书写了不同国度的近代史乃至现代人的生存境遇,本文将从叙事学角度出发,结合具体作品,对大江与莫言的小说的“历史叙事”特质进行探讨。
1 战争题材
大江和莫言的作品中都有对战争历史、战争体验的书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大江的《饲育》(1958)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1987)。这两个作品的叙事空间都是在作家的故乡,分别是四国森林的“峡谷村庄”和“高密东北乡”;都是借助少年儿童的视角对战争历史的民间审视;而且都是交替运用多重叙事视角,从而达到了强化作品主题的效果。
《饲育》以二战时期的四国森林的峡谷村庄为背景,讲述少年主人公“我”和被村民逮捕的“黑人俘虏”之间的故事。“我”和小伙们在给这个俘虏送饭、监护的过程中逐渐和他成为朋友。但是,因为“大人们”的原因,生命受到威胁的俘虏把“我”作为人质绑架了。最终,黑人俘虏在这场冲突中被村民打死了。战争带来的暴力和死亡让“我”感到恐惧和愤怒,留下了心理阴影。
在《饲育》中,大江借助儿童视角来呈现现实世界,揭露战争带来的残忍、暴力和死亡。儿童特有的敏锐的直觉和丰富的想象力、异于成年人的思维,为审视现实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种叙事视角,为读者构筑了两个相互对峙的空间——孩童心中的理想世界和被战争异化的现实世界。“大人们”在战争背景下被合理化的那些行为,在儿童视角的透视下,显现出其荒诞、残忍的本质。同时,作品的叙事视角并不是单一的。兰立亮(2009)指出:“《饲育》其实是成年叙述者借儿童之口和童年的记忆对当下的‘我’内心的宣泄。这样,叙事声音和叙事眼光不再统一于叙述者,而是分别存在于故事外的叙事者‘现在的我’和故事内的聚焦人物‘当时的我 ’这两个不同的实体之中。这两种话语系统交织的叙事结构,显然使叙事文本在充满内在叙事张力的机理中生成了超越现有文本的他种意义,从而拓宽了叙事的空间。”像这样,叙事者除了 “当时的我”,背后还存在一个已经成年的“现在的我”。这两种视角的并存,呈现了文本和现实的联系,隐含了“现在的我”对过去那段战争历史的尖锐批判和深刻反思。
莫言也是一个很重视叙事技巧的作家,他在《红高粱家族》中也使用了多重视角的叙事方式。《红高粱家族》以抗日战争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高密东北乡的民间生活为背景,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故事和传奇的一生。“我爷爷”既是土匪又是抗日英雄,“我奶奶”也是一个充满抗争精神的女性。小说通过描写自由而混沌的战争年代,塑造了祖辈们的顽强生命力和充满血性的民族精神。为突出这一主题,莫言在这部小说中不仅运用了狂欢式的、天马行空的语言风格,还给叙述者“我”赋予了多重叙事视角。莫言在《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中曾指出:“将近二十年过去后,我对《红高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写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内心世界可以很直接地表达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这在当时也许是一个创新。”(莫言,2011)正如莫言所言,这部作品的男女主人公“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不仅通过第三者“我”的外视角来讲述,在许多场景中还使用直接描写人物内心活动的内视角,让他们自己讲故事。这种外视角和内视角的交替使用,使叙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给读者更丰富的体验和想象。外视角的客观描述保留一定的客观性和距离感,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同时,内视角把历史现场和人物更直接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多重视角的交替,实现了多维度的历史重构,从而使作品描绘的自由混沌的红高粱世界进一步立体化。
2 家族题材
大江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与莫言的《丰乳肥臀》(1995)都是站在民间立场,通过书写一个家族的命运来折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讲述的是在现实生活里受挫的“根所”兄弟蜜四郎和鹰四,为了寻找自我,一起回到的自己的故乡——四国森林的峡谷村庄。在这里,鹰四效仿百年前领导农民运动的祖先,组织了一支足球队来抵抗地方政府,并最终自杀身亡。蜜四郎被弟弟的死所触动,最终决定走出森林,开始新的生活。在这部作品中,“根所”兄弟二人回乡寻根的故事勾勒出他们祖父一辈的历史,几代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根所”家族从1860年到1960年的百年家族史。这与日本的近代史是相呼应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的“万延元年”指的是1860年,这一年日本封建幕府第一次向美国派出特使,开始打开国门走上近代化道路。百年后的1960年则是“安保之年”,战败后的日本在这一年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确立了美国在日本的军事特权。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对安保条约的运动。并且,大江创作这部小说的1967年前后,正值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一百周年。日本国内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掀起了回顾百年近代史、赞美明治维新的思潮。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无论是“根所”兄弟在现实中遭遇的迷茫与挫折、寻根问祖的经历,还是蜜四郎最后的“重生”,都隐含了大江对日本百年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
莫言《丰乳肥臀》中的“上官家族”不是传统意义上由男性主导的家族,而是“我”的母亲上官鲁氏与不同的男人所生的八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构成的家族。上官鲁氏和她的女儿们构成的庞大家族与各种社会势力产生错综复杂的联系,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小说的时间跨度从鲁氏出生的那一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串联起日本侵华战争、解放战争、文革、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勾勒出了近代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上官鲁氏这一苦难而伟大的母亲形象,象征着生生不息的土地和民族。她的一生就是一部宏大而悲壮的百年史诗,折射了中国屈辱的近代史。
这两部小说在叙事手法上也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在讲述历史时,都是将过去拉回到现在,在共时点上展开叙事。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大江多次将历史凝结在一种共时形态中呈现在读者面前。例如,在小说的第8章“说出真相吧”中,某个雪夜,蜜四郎进入老屋的仓房中,准备吊在有百年历史的榉木大梁上自杀。这时,他看到前院的雪地里赤身奔跑的弟弟鹰四,突然被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包围。“一秒钟的状态可以无限地延伸。声音被雪层吸收了去。时间的方向性也被飘降的大雪吸收进去,消失得杳无踪迹了。这无处不在的‘时间’。赤身裸体奔跑着的鹰四是曾祖父的弟弟,也是我的弟弟,一百年来所有的瞬间都层层重合成这一瞬间。”在这里,时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过去入侵现在,现在回到过去,历史和现实凝结在眼前的一瞬间,融合成了一个永恒的整体。莫言在《丰乳肥臀》中也有使用了类似的叙事手法,让现在和过去融合为一个画面,呈现在读者眼前。在小说的第16卷中,上官鲁氏为保护女儿第一次反抗她的婆婆吕氏。此时,曾经被婆婆拿来殴打她的那根擀面杖,“好像一个成了精的活物,自动跳入母亲的手中。这根枣木擀面杖被上官家几代女人粗糙的手磨得像瓷一样,紫红颜色,坚硬沉重而润泽。”当上官鲁氏手中的擀面杖打在婆婆头上的一瞬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天旋地转,尊卑颠倒”。在这段描写中,那根坚硬又有光泽的擀面杖,是封建家庭中一代又一代女人们命运的见证者。它的存在就像玉石或化石一样,让历史以可直接感知的形式存在于现实当中,让过去与当下交织在一起,并列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艺术手法,淡化了时间的先后顺序和连续性,让叙事在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循环往复,从而描绘出一幅生生不息的民族历史画卷,强化了宏大的史诗主题。
3 小说中的戏剧
莫言的《檀香刑》(2004)是一部极具民俗特色的小说,整部小说以地方戏曲——猫腔贯穿始终,通过戏剧与小说的创新性融合,让民间艺术在当代小说的写作中发挥了独特的叙事效果。《檀香刑》分为“凤头”、“猪肚”、“豹尾”三个部分,讲述的是二十世纪初胶东人民反抗德国列强的故事,其中包含了刑罚文化、战争风云等沉重悲壮的悲剧元素。并且,这些悲剧主题,是嫁接在猫腔这种狂欢式的戏剧形式上展现出来的。猫腔本是流传于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常用于哭丧,唱腔悲壮苍凉,催人泪下。在《檀香刑》中,“凤头”部和“豹尾”部的各章都以猫腔作为引子,出场人物内心道白也采用唱猫腔的形式,猫腔成为重要的叙事手段。不同的曲子和唱词充分表现了人物情感,实现了情节与人物关系的高度戏剧化。特别是,在猫腔班主、抗德英雄孙丙游街受刑的场景中,众多猫腔艺人和百姓齐唱猫腔为其送别的壮观场面,将整个小说推向高潮。戏台上尸体横陈,血流成河,猫腔悲怆又震撼人心的声音奏响了最悲壮的民族哀歌,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在这部小说中,猫腔在塑造人物形象、推进故事情节、深化悲剧主题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江的《水死》(2009)与《檀香刑》相似,在小说的叙事中导入了戏剧元素。《水死》讲述了主人公长江古义人探寻父亲溺水身亡的真相及其思想根源的过程。“我”的父亲生前曾参与右翼活动,并且临死前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因此他的死似乎是为天皇殉死,但“我”对此心存质疑。为探讨这一问题,在《水死》中,古义人以“朗诵剧”的形式引用了夏目漱石的小说《心》,并让作品人物对其展开激烈的讨论。在日本,长久以来,《心》被解读成是主人公“老师”为以明治天皇为中心的“明治精神”的殉死,并且被收入国语教科书,用以教育青少年。但是,《水死》借作品中人物的质疑和讨论,颠覆了人们对《心》根深蒂固的认识,赋予其批判性的新解读。即,“老师”的自杀不仅不是为“明治精神”殉死,甚至可以说是对“明治精神”的否定和反抗。并且,通过对《心》的重新解读的深入和推进,古义人对父亲的死也有了新的理解。像这样,《心》中“老师”的死与《水死》中“我”父亲的死,构成了两个文本的内在呼应,从而揭示了他对于天皇制度下的日本近代史的审视和反思。同样是导入戏剧的元素,《水死》对《心》的引用和讨论,旨在凸显大江对日本近代史、乃至当下现实的思考,这与《檀香刑》借用猫腔来塑造历史的悲壮感略有不同。
4 结语
大江文学与莫言文学的艺术魅力在于其宏大的历史主题。他们从各自的乡土、家族的历史出发,以个体的命运来折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他们在时空的交错中挖掘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纽带,通过对历史的重构来关照时代现实,关注人类命运。这使他们的文学超越了地域性、民族性,具有了更普遍的现实意义,从而走上了世界文学的舞台。同时,大江与莫言的共性不仅表现在他们的文学理念和作品主题上,也表现在他们开拓性的创作手法上。本文以历史叙事为切入点,从战争题材、家族题材、小说中的戏剧三方面探讨了大江与莫言在叙事艺术的相似之处;并选取三组有代表性的小说,分析了这些叙事手法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发挥的效果。在这些作品中,多重叙事视角、共时性描写和戏剧元素的运用,成为深化作品主题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