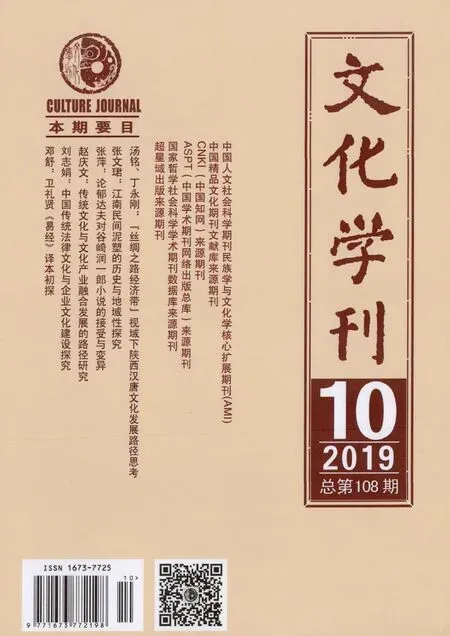电影理论视域下的痖弦诗歌
李世鹏
当代诗人痖弦是台湾创世纪诗社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创世纪》诗刊的主要撰稿人。痖弦、洛夫、张默等重要诗人的出现,兴盛了台湾地区的现代主义诗歌。痖弦有过专门的戏剧学习经历,不仅熟悉中国古典戏剧,而且接触过莎士比亚、易卜生等西方戏剧名家的作品。痖弦在访谈录中谈到:“我是戏剧的科班出身,但我既不会演也不会导,我觉得这是一个欠缺,所以就把戏曲的很多手法放在诗里面,这可能是一种将功折罪。”[1]戏剧与电影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对于戏剧来说,电影的镜头拍摄和剪辑方法带来的视听语言的革新已是一种叛离和超越。痖弦的部分诗歌用戏剧理论很难做出合理解读,用电影学的知识去阐释却恰到好处。戏剧受限于表演空间的相对封闭性,对一些过于跳跃和繁复的意象很难下手,电影镜头却可以通过各类剪辑方法做到。
一、闪回与现实的蒙太奇
痖弦的诗歌《上校》只有短短十行字,却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文本。若用电影理论去阐释,可以生发出至少两种解读方式。其中一种解读是把诗歌中写到的两个情境看成两个独立的叙事片段,这两个片段遵从线性的时间发展,串起上校的前后生活状况。这种理解方式抹去了人物心理活动的可能性,将上校剥离成一个机械的审美客体,这个客体只在诗人设定好的场景中僵硬地做着规定的动作。在这种理解方式下,诗人与诗歌中的上校很难共情,诗人之眼这台摄影机只是一架冰冷的复刻仪。但如果按照闪回和蒙太奇的理论去理解《上校》这首诗歌,不仅诗中的上校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而且诗人自身容易与上校共情,从而使诗歌具有了厚重的人道主义色彩。
电影学中的“闪回镜头”又称“闪念”,是表现人物心理活动和叙述已发生事件时常见的剪辑方法。莫林·特里姆认为:“闪回出现于影像从现在转入过去的时候,可理解为一种故事叙述或主观回忆的方式。”[2]美国著名电影理论家路易斯·贾内梯则认为,闪回是在当下时间节点的事件基础上,插入对于过去事件的叙述[3]。不管怎样表述,闪回镜头遵循的一个原则是:闪现的场景和事件要与人物当下所处的境况有内在逻辑关系,不能把两个毫不相关的事件牵强附会地剪辑在一起。按照闪回镜头的理论,如果我们把上校当下所处的生活境遇看作真实,那么第一个关于战争的片段就是此刻上校脑海中闪现的回忆镜头。按这种理解方式,上校这一主角具有了极强的主体性,镜头深入了他的内在。诗人之眼这架摄影机不再只是冷冰冰地复刻客体活动,而是能够窥探主角的心理世界。
“蒙太奇”是电影中的一种剪接技巧,通过人为地拼接镜头,造成富有深意和冲击效果的叙事。在作品中表现出蒙太奇技巧的文学现象有迹可循,更早的上海“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作品《上海的狐步舞》就借鉴了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蒙太奇造成的叙事冲突并非由每个独立镜头带来,而是这些镜头剪接在一起所产生的效果。上文按照闪回镜头的理论,将《上校》分为了现实镜头和闪回镜头两个部分,在诗境中产生了强烈反差,这在蒙太奇的分类中属于“对比蒙太奇”。第一部分的闪回中,镜头探入上校回忆中的脑海——从前的他是一个自火焰中诞生的战斗英雄,曾数次浴血沙场。闪回的时间是一九四三年,镜头给了上校因战致残的肢体一个特写,这是峥嵘岁月里一种玫瑰般的人生。镜头猛然拉回到第二部分的现实,“上校”这一标签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他作为一个被柴米油盐左右、饱受病痛折磨的小市民形象。对比蒙太奇的技巧发挥了结构性作用——曾经的人生有多曲折、多激情,现在的生活就有多平淡、多琐碎,前者的存在是为了反衬后者。闪回镜头在这里表达了一种转瞬即逝的无奈感、难以捕捉的缥缈感。荣光岁月与赤裸裸的现实相比处于一种失真状态,当下平淡和琐碎的生活片段才是真实,也就是痖弦在诗中所指称的“不朽”。除了对比蒙太奇外,现实镜头内部还包含着其他蒙太奇结构。在描述上校当下的小市民生活时,痖弦用了一组“隐喻蒙太奇”手法剪接的镜头。诗人把摄影机对准咳嗽药、刮脸刀、缝纫机、房租条等生活化意象,这些意象如果单个出现,并不会带给读者强烈的情感冲击力。然而,痖弦将这些单个意象填充的镜头剪辑到一起,就具有了一种隐喻意味——这组隐喻蒙太奇镜头象征的是琐碎、凡庸的生活本身。曾经在血与火中生存下来的上校,如今却被家庭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物件围困,且在这种困境中无法突围。至此,一个闪回加两个蒙太奇的电影学解读串起了《上校》整个文本。诗人用史诗性镜头关注上校心中所想,用特写镜头拉近了与上校生活的距离,在这一过程中达到了审美活动主客体之间的共情,也使整首诗歌包孕了绝妙的反讽性。
二、从新浪潮和新现实谈开去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法国掀起了“新浪潮”电影运动。这场运动肇始于影评人和《电影手册》杂志,《电影手册》主编安德烈·巴赞成了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新浪潮运动团结了弗朗索瓦·特吕弗、阿伦·雷乃、让-吕克·戈达尔等一众知名导演,这些导演都提倡导演个性,是“作者电影”类型的狂热追捧者。尽管新浪潮电影运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拍摄纲领,但对比这些导演的影片可以发现一些共通之处:第一,走出摄影棚,走向街道,拍摄真实的外景;第二,反对拍摄静态镜头,倡导运动的镜头,革新视听语言;第三,鼓吹“非连续性哲学”,否定集中的戏剧性情节。这些新浪潮影片的特征在痖弦诗歌中都可以找到对应,从而使痖弦诗歌具备了世界性的艺术广度。
《一般之歌》第一节以诗人的第一人称视角开场,这一视角捕捉到的镜头为诗人视野内的主观镜头。诗人拒绝封闭的空间,主动走上街头,捕捉真实的外景。在描述这一外景时,诗人不是用剪接的方法静态地串起各个画面,而是借身体的位移做着肩扛摄像机式的连续运动摄影。镜头对准铁蒺藜旁的国民小学,再挪远一些到锯木厂,而锯木厂隔壁是种满莴苣和玉蜀黍的园子……像特吕弗的《四百击》开场时主角安托万在车上努力地连续捕捉巴黎街景一样,痖弦在《一般之歌》中运动地捕捉这些画面时,镜头也同样从未间断。就主题层面上讲,《一般之歌》遵循了新浪潮的非连续性哲学原则,隐去了高度紧张和顺畅的戏剧性情节,取而代之的是平缓的叙事和无情节的意义空间。如果没有可供解读的情节和矛盾,那么诗人捕捉这些镜头的意义何在?其实答案就在文本中——诗人反复述说的“安安静静接受这些不许吵闹”[4]。诗歌中,镜头捕捉到的画面寓示着平淡无奇、了无波澜的生活流,它不制造惊险的矛盾和情节,但对我们而言却是一种绝对性的存在。我们在这种看似平淡如水,实则隐匿着巨大力量的生活流面前无能无力,只能如诗人所说的那样安静地接受一切。
在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之外,意大利电影界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享誉全球的“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这一流派的拍摄方法也为痖弦诗歌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中有一对著名的黄金搭档——导演德·西卡和编剧塞萨·柴伐蒂尼。他们两人编导的电影聚焦于人的生存状况,习惯将镜头对准人的真实生活场景,拒绝伪造任何情节,从而自觉地倾倒出写实性情感。如德·西卡和塞萨·柴伐蒂尼的镜头那样,《如歌的行板》关注的亦是人之生存,诗人拍摄到的是一个个写实性的生活细节——餐桌上的酒和木樨花,报纸上的欧战和红十字会,散步、遛狗和上班,盘尼西林和法兰绒长裤……这些画面表现出的诗学内涵与《一般之歌》大不相同——运动摄影消失了,审美对象不再是人处于缺席状态的场景,镜头因专注于人的日常和困境而添了人道主义关怀。《如歌的行板》侧重与读者的“共鸣和回响”,诗人织就的语言不再居高临下,不再故意放大语言的晦涩程度和偏执地设置叙事迷宫,这一点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的平民化立场和纪实性亦相一致。
三、镜头技巧的狂欢曲
痖弦的许多诗歌都可专门用于讲解电影摄制方法,其暗含的镜头技巧之熟稔能够频频看到一些世界级电影大师的影子。这些技术层面的解读使痖弦诗歌背离了华兹华斯诗歌般纯然的感性流露,达到了以技巧镶嵌哲思的层次。他一反自己早年的浪漫主义诗风,走向探寻更深层次的宗教、存在等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些镜头技巧的运用。
(一)平移的推轨镜头
“推轨镜头”是指让摄影机在器材上移动的拍摄方法,这里的器材通常是拍摄前铺好的轨道,摄影机可以在轨道上平移。随着摄制技术的发展,如今的推轨镜头也指平滑、顺畅的手提摄影机拍摄的移动镜头。这种推轨镜头通常能够带来震撼的视觉效果和心理聚焦作用,受到诸多电影大师的喜爱,如英国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和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等人。希区柯克的《迷魂记》用推轨镜头与变焦手法带来了眩晕多姿的视觉效果,库布里克在《发条橙》和《闪灵》中用推轨镜头是让观众聚焦于画面中的主要角色,而痖弦的诗歌兼采两者,动用推轨镜头达到了他独特的诗学追求。诗歌《妇人》的焦点是一幅拉斐尔·桑西的油画,油画的中心位置是一位妇人。油画本是静止的,痖弦却说画中的妇人肖像般的走来。若要达到这一效果,需要在头脑中借助推轨镜头的手段。摄影机平移的过程中,妇人不仅始终居于油画的中心位置,同时一直处在镜头的中心,读者的注意力自然会一直集中在妇人身上。推轨镜头的移动会在视觉上造成油画在移动的错觉,但妇人的表情不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任何改变,因此,妇人看上去是肖像般的走来。有了推轨镜头奠定的基础,诗人才能在下一节诗中对画中的妇人顿生爱慕之情。妇人在镜头下呼之欲出,又因如肖像般表情始终未变,所以比寻常女性多了一分静穆的神性,这一形象使诗人难以自持。但诗人明白,画中妇人是一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存在,若生出歹念,便会打破这种想象的真实,向诗人走来的妇人会重新隐遁回画中。这种真真假假难以辨别的情形,很像《红楼梦》第一回太虚幻境牌坊上联写到的“假作真时真亦假”,反映了痖弦诗歌创作中对存在与虚实命题的启悟和哲思。
(二)深焦摄影与交叉剪接
“深焦摄影”是与特写镜头相对的一种拍摄技巧。在拍摄一场戏时,深焦镜头不是给演员的脸部以特写,而是拉远与演员的距离,将演员和周遭环境放在同一个画面中。这样既可以照顾到演员的镜头,又能让环境入镜,烘托演员的情绪,甚至起到补充情节的作用。美国著名导演威廉·惠勒、约翰·福特等人的电影中,经常用深焦镜头表达一些言外之意。“交叉剪接”是指将发生在同一时间的两个镜头剪接到一起,这种剪接方法能够起到对比或辉映的作用。交叉剪接看起来很像对比蒙太奇手法,但交叉剪接的条件更为苛刻,必须满足“发生于同一时间”这一限定条件。痖弦的诗歌《神》只有短短的三行字,却融合了深焦摄影与交叉剪接两种电影技巧。诗人先将镜头对准教堂里被供奉的神,深焦镜头下的神不是被信徒簇拥的形象,而是孤零零地坐在教堂的橄榄窗上。橄榄窗在教堂里代表着被边缘化的位置,把这样一个边缘化的环境与神放在同一个画面中,更能凸显神之孤独。第二个深焦镜头对准了祭坛及其周围簇拥着的牧师们,镜头中的画面俨然充满了热闹、祥和的气氛。祭坛的位置在教堂内部中心,本来应是神的休憩之地,祭坛的空间被挤占和充塞,神只能被迫退到边缘地位。诗人将两个深焦镜头交叉剪接到了一起,热闹的牧师们和孤零零的神形成对比,颇有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乐景衬哀情”之意。在这些解读的根基上,诗歌的主旨浮出水面——神之意志名存实亡,人的宗教信仰缺失,神坛成了无意义的名利场。
(三)正逆向建立镜头
电影中的“建立镜头”一般指开场时给出远景或大远景镜头,目的是引出后面较近的镜头,远景由此变成环境背景。痖弦的诗歌《怀人》就有如建立镜头,由远及近、剥丝抽茧地描述画面。诗人开场设置了一个夕阳和锦葵花、北方古老的宅第相交织的远景镜头,这是后文画面所处的大环境背景。接下来,诗人的镜头专注于捕捉大环境内的小细节——算命锣、啄木鸟、书斋、窗纸、松影、藏书、蛀虫……镜头展现的画面越来越细腻,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了开头大远景镜头的基础之上。痖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能够用诗歌展现出建立镜头的技巧,亦能用诗歌颠覆这种技巧,做到别出心裁。诗歌《鼎》开头先展现了三个近景镜头,拍摄的画面依次是九个衔着铜环的狮子头、十二条缠绕着的眼镜蛇、弹七弦琴的二十八个盲裸女。等到展示完近景镜头之后,诗人才给出远景——一个古老的希腊鼎。不同于建立镜头的一目了然,这种逆向建立镜头的优势是打破了读者的心理预期,读者在阅读诗歌、想象镜头的过程中会形成阅读期待,渴望在接下来的阅读中揭开疑问、剖出谜底。在诗歌逐渐淡出人们阅读视野的当下,这种技巧也不失为一种吸引读者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