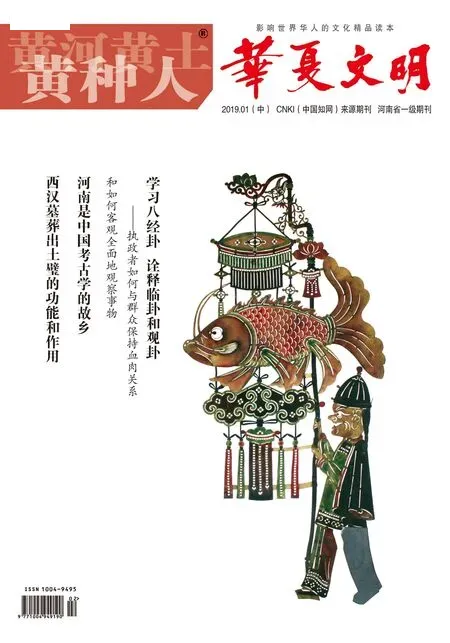河南是中国考古学的故乡
□郑杰祥
河南地处中原大地,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核心地区,也是唯一未曾中断并延续至今的华夏文明地区。若干万年以来,我们的祖先在这里以辛勤的劳动和智慧,创造和遗留下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考古学以古代遗物与遗迹为主要资料,用以研究和探讨人类社会形成、发展的真实状况,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考古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前段考古学称为金石学,又称为传统考古学或古典考古学;后段考古学即现今仍在实践中的近现代考古学。
金石学是以铜质和石质遗物为主要研究对象,考释其形状、纹饰,特别是铭刻文字,用以“证经订史”,探讨它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内涵。该学科正式形成于宋代,清人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序云:“金石之学……专书则创自宋欧阳修、赵明诚、王象之诸人。”近代学者王国维云:“金石之学,创自宋代,不及百年,已达完成之域。”[1]现代学者马衡也说:“五代以前,无专治‘金石学’者。……有宋一代,始有专治此学者,欧阳修《集古录》为金石有专书之始。自是以后,吕大临、薛尚功、黄伯思、赵明诚、洪适辈,各有著述,蔚为专家。郑樵作《通志》,以‘金石’别立一门,侪于二十略之列,而后‘金石学’一科,始成为专门之学。”[2]金石学科的产生,以出现金石学者群体及众多金石学著作为标志,朱剑心《金石学》云:“综计宋代金石学者及金石著作,李遇孙《金石学录》录六十一人,杨殿珣《宋代金石佚书目》列八十九种。”[3]23其学者之众,著作之多,为前世所未有,充分表明金石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这个时期已初步形成。
宋代金石学产生于以宋都东京即今河南开封市为中心的区域,这首先是由于北宋王朝崇尚并复兴先秦儒家礼制,重视收藏大量的古代“金石”礼器等器物资料。宋王朝开国伊始,太祖赵匡胤就下诏重赏“善礼学、通经旨”的太常博士聂崇义,并颁布他所编撰的《三礼图》。《宋史·儒林传》云:“崇义因取《三礼图》再加考证,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俨为序。太祖览而嘉之,诏曰:‘礼器、礼图,相承传用。’……赐崇义紫袍、犀带、银器、缯帛以奖之。”礼制以礼器为载体,宋王朝也大量收集礼器。宋人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云:“宣和间(1119年—1125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又云:“宣和殿后,又创立保和殿,左右有稽古、尚古、博古等阁以储之。”宋人蔡绦《铁围山丛谈》也说:前朝对于出土古器“在上者初不大以为是,独国朝来浸乃珍重……及大观初,乃效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独政和间为最盛,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汉间物,非殊特盖亦不收,及宣和后,则咸蒙贮录,且累数至万余。”储存如此众多器物,当然不是一朝一夕收集而来的,早在宋真宗(998年—1022年)时期已重视收集金石礼器等遗物,吕大临《考古图》云:“咸平三年,好畤令黄郓获是器(仲信父方旂甗)以献。”“咸平三年,同州民汤善德获(太公缶)于河滨以献。”宋人翟耆年《籀史》又云,宋仁宗(1023年—1063年)“皇祐三年,诏出秘阁及太常所藏三代钟鼎器,付修太乐所参较齐量”等[4]。在积累礼器的同时,宋王朝还广开言路,鼓励学者对三代礼制、礼器深入研究,各抒己见,以追求儒学真谛。《宋史·儒林传》记宋太祖赵匡胤就曾下诏对“所进《三礼图》,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三五人,更同参议所冀精详,苟有异同,善为商榷。……《三礼图》遂行于世”。《长编》卷二也云,建隆二年“崇义因取《三礼图》考证同异,别为新图二十卷。丙寅来上,诏加褒赏。仍命太子詹事汝阴尹拙集儒臣集议,拙多所驳难,崇义复引经解释,乃悉以下工部尚书窦仪裁处至当,然后颁行”。《宋史·舆服志》又记云:“宋自神宗以降,锐意稽古,礼仪之事,招延儒士,折衷同异。”从而激励起当时学术界特别是任职于中央政府的官员、学者对礼制、礼器的研究热潮,由此而催生了金石学的形成。
宋代最早的一部金石学著作,当为宋仁宗下诏编撰的《皇祐三馆古器图》。翟耆年《籀史》云,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诏出秘阁及太常所藏三代钟鼎器”,令人绘其图像、隶定铭文,编成《皇祐三馆古器图》。不过此书已经失传,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当即欧阳修所著《集古录》。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宋史·欧阳修传》云,宋天圣八年考取进士,“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并参与倡导古文运动。“庆历三年知谏院”,任该职期间,“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后“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唐书》成,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博士”。嘉祐“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参知政事”,“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本传又说他“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集古录》又称《集古录跋尾》,清代《四库书目》卷八十四介绍此书说:“《集古录》十卷,宋欧阳修撰。修采摭佚遗,积至千卷,撮其大要,各为之说。至嘉祐、治平间,修在政府,又各书其卷尾……修又自云:凡四百余篇有跋。”且“自书其后,题嘉祐癸卯(1063年)”。此书正是欧阳修任翰林学士等官职期间,与奉诏撰著《新唐书》约略同时而写成的。与《集古录》同时成书的金石学著作还有刘敞的《先秦古器记》。刘敞,字原父,宋庆历八年(1048年)进士,曾任职于集贤院,管理图书、档案;后为宋英宗侍读,深得宋英宗器重。《宋史·刘敞传》云:“敞侍英宗讲读,每指事据《经》因以讽谏……帝固重其才,每燕见其他学士,必问敞安否。”因受到北宋中央王朝的影响,刘敞自己也收藏古器,并选出十一器编著成《先秦古器记》,刘氏自序云,将各器“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图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终此意者,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为能尽之”,可说是开创了当时金石学的体例。此书现已失传,书中所记各器已被《集古录》所采用。北宋较早的金石学著作还有吕大临的《考古图》与《考古图释文》。吕大临,字与叔,《宋史·吕大临传》介绍他曾就学于理学家程颐,为“程门四先生”之一。又说他“通六经,尤邃于礼”“元祐中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任该职期间,他选皇宫及私人所藏224件古代礼器,编著《考古图》十卷,《释文》一卷。吕氏自序该书云,所见各器“每得传摹图写……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亦将有考焉。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可知该书完全是遵循宋王朝崇尚并复兴先秦礼制而写作的。吕氏《考古图释文》一卷,是“以《广韵》四声编字,共收八百二十余字,每字各取二三种多至十几种形体”,可称之为我国最早的一部“金文字典”[5]。大约与此同时,还有李公麟所著《考古图》。李公麟,字伯时,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曾任职御史检法。《宋史·文苑传》又记他:“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订世次,辨测款识。”绍圣年间(1094—1098年),奉召为宋哲宗辨识玉玺。翟耆年《籀史》云,李公麟“著《考古图》,每卷每器略为图叙,其释制作、镂文、款字、义训及所用,复总为前序后赞,天下传之”。蔡绦《铁围山丛谈》介绍此书云:“元丰后,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时,实善画,性希古,则又取平生所得及其闻睹者,作为图状,说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图》。”此书现已失传,其体例和内容为《宣和博古图》所传承。《宣和博古图》又称作《博古图录》《宣和殿博古图》,为宋徽宗敕撰,王黼编纂,蔡绦《铁围山丛谈》云:“太上皇(宋徽宗)即位,宪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宗尚。及大观初,乃效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介绍此书云:“北宋大观初年始修,宣和五年(1123年)后成书。著录宣和殿所藏商至唐铜器菁华839件,以器形立二十目,每目有总说,每器均摹绘器形、款识,记录形制、尺寸、容量、重量,间附考证,所定器名,如鼎、罍、尊、爵等,大多沿用至今。”[6]1该书是宋代一部“专门辑录铜器的最大著作”[5]。与此书约略同时写成的还有董逌《广川书跋》一书,董逌曾任宋徽宗时期徽猷阁待制,是当时著名的鉴赏考据学家,著有《广川书跋》十卷,明人毛晋序此书云:“董子政和间鉴定秘阁所藏悉三代法物名器……详论精核。”现代学者朱剑心也云:“其《广川书跋》十卷,皆著录古器款识,及汉唐以来碑帖,论断考证,皆极精当。”[3]28该书是主要根据宋王朝秘阁所藏礼器详加考据写成的一部著作。受当时学术界影响,赵明诚夫妇还著有《金石录》一书。赵明诚,字德甫,宋徽宗尚书右仆射赵挺之之子,少时为太学生,与夫人、礼部员外郎李格非之女李清照久居东京,共同酷爱并收藏金石书画,将其所藏金石2000件拓本,互相切磋,深入研究,以二十年时间,仿照《集古录》体例,编成目录十卷、跋尾二十卷(502篇跋尾),共三十卷。正如赵氏此书自序所说:“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辞,以广异闻,后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读而贤之。……于是益访求藏蓄凡二十年,而后粗备,上自三代,下讫隋唐五季,内自京师,达于四方……因次其先后为三十卷。”明诚早卒,由夫人李清照整理成书,可谓夫妇合作,写成一部颇有影响的金石学著作。
以上介绍的八部金石著述,都是北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金石学著作,这些著作有些是皇帝敕撰,有些则是任职或久居于东京的官员、学者所著。北宋王朝建立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文化也迅速繁荣起来。宋王朝开国伊始,就实行重文教、尚古礼的政策,并收藏礼器作为复兴古礼的资料。《宋史·文苑传》云:“艺祖(宋太祖)革命,首用文吏……宋之尚文,端本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是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择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可见当时的君臣上下,已形成重文氛围,特别是任职于中央政府的官员,多是知名学者,他们集中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首都东京,不少人利用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研究各种金石礼器,写成多部金石学著作。因此,金石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产生于宋都东京应是明确无误的。
金石学到了清朝,发展到鼎盛阶段,同时也面临着重大的转折。首先是清代金石学扩大了研究范围,即“除了传统的青铜器、石刻外,造像、画像石、题名、墓志、度量衡、钱币、玉器、玺印、砖瓦,甚至明器、陶俑、器范也成为著录和研究的对象”,特别是“清朝末年甲骨和简牍的发现”,进一步“扩大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7]59。其次是西方新兴的近代考古学被介绍到中国,为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化也起到了促进作用,西方近代考古学是借助新兴自然科学地质学的地层学与生物学的类型学加以融合、改进,对地下遗物、遗迹进行调查、发掘、整理,用以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大致形成于19世纪中叶,其后不久,即被中国学者所认知。1900年,章太炎所著《中国通史略例》文云:“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7]36这里所说的“洪积石层”,指的就是考古发掘地下出土的遗迹、遗物。1901年,梁启超所著《中国史叙论》文云:“1847年以来,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学,遂成为一学派。”又云:“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现,然物质上之公例,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决不为过。”[7]6这里所说的“层石”,指的亦是地下发掘出土的遗物、遗迹。于是“一些传统的金石学家,受西方近代考古学方法的影响,也有与金石学内在的要求,开始走向田野”[7]59,进行考古调查。金石学家罗振玉通过对出土甲骨卜辞的研究,“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物”;又得知卜辞“发见之地,乃在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8],认为这里应是商王朝故都所在地。于是“1915年春天,罗振玉本人也到殷墟考察了甲骨出土情况,在《五十日梦痕录》里他对这些考察有比较详细的记录。罗氏注意到无字甲骨及其他殷代遗物,包括石刀、石斧、象牙、骨管、贝币、骨镞等,并于1916年编印了《殷墟古器物图录》一书”[7]60。对此,郭沫若先生高度评价云:“罗氏在中国要算是近世考古学的一位先驱者……这种热心,这种识见,可以说是从来的考古学家所未有。”[9]当然,由金石学转化为近代考古学,主要还有赖于西方近代考古学的引进。20世纪初,中国北洋政府为发展工业设立农商部,1914年,特聘请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安特生为该部矿政顾问,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寻找铁矿和煤矿。安氏身为著名的地质学家,同时对考古学也有较高的学术素养,他在田野调查矿藏中,也注意收集石器等古代遗物。“1920年,安特生发表了《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一文,这是目前所知安氏最早的一篇考古学论文”[7]91,此文内容就是他在中国几年来所收集的石器遗物的总结。1920年秋至1921年1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刘长山奉安特生之命赴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调查化石,同时也奉命收集石器600余件,“安氏由此推断仰韶村可能有一个相当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于是“安氏回到北京,征得农商部以及地质调查所同意,又同河南省政府以及渑池县政府取得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于同年10月奔赴仰韶村进行了正式的发掘。发掘从10月27日开始,历时30多天,于12月1日结束,这是安氏在中国进行的最大最详细的一次发掘”,也是在“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村落遗址”。与此同时,“安特生、师丹斯基、袁复礼以及地质调查所的5名中国同事在发掘仰韶村期间,在仰韶村西6公里处的不招寨、仰韶和渑池县之间的杨河村、西庄村相继发现三处史前遗址”,其后又派助手到今河南荥阳市的“黄河南岸发现了秦王寨、牛口峪和池沟寨三个遗址”,“安特生把这些遗址命名为仰韶文化”[7]90。经过对这些遗址所出遗物的整理研究,安氏认为遗址所出“所有兽骨尽属豕类,也有以猪骨做镞刀环玦者,查其种属,当属家畜之猪而非野豕。今之汉族固仍以猪肉为食之大宗”。再者,仰韶遗址“出土的陶鬲与周代的铜鬲及周代金文中的‘鬲’字如出一辙”。有鉴于此,安氏“认为仰韶遗存是汉族的史前文化,因此他称之为‘中华远古之文化’”[7]116,并“强调中国仰韶文化经过商代直到今天,在人种和文化上是连续发展的”[10]。“仰韶文化”,“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11]3,也“是中国第一次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正式发掘,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建立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意义”[11]206。因此,正如严文明先生所说,安特生主持“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那是在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应用近代方法,并且是工作量较大的一次工作,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始”[12]。《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也说:“中国考古学是20世纪初在金石学基础上,受到西方考古学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1921年,北洋政府聘请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对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6]102仰韶文化的发现,证明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和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一样,也存在着远古的石器时代,因而引起国家与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中国近代考古学从此迅速发展起来。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该所成员、毕业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董作宾调查殷墟。经调查,董氏认为这里地下仍应存有大量甲骨,于是同年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任命中国第一位独立从事考古发掘的人类学者李济为主任,这是中央政府建立的第一个考古研究机构,考古组就派董作宾赴河南安阳殷墟首先进行考古发掘。1930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考古学者梁思永回国参加殷墟发掘。他在安阳后岗遗址的发掘中,改造了安特生所用地质学的水平层位分层法,采用由古人类活动形成的自然文化层分层法,并用类型学的方法,将出土有共同形制特征遗物的一些文化层加以合并,从而分出下层仰韶文化层、中层龙山文化层、上层小屯商文化层三叠层。后岗遗址早、中、晚三叠层的划分,“结束了以往人为的水平层位的发掘,开辟了以文化层为单位的发掘历史”,这不仅为当时发现的古文化遗存初步打下年代学的基础,而且大大提高了近代考古学科学发掘水平,“给殷墟以及后来的发掘者树立了典范”[7]236。正如夏鼐先生对梁思永的评价所说:“他是我国第一个接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参加过安阳发掘的旧人都知道,自从他加入后,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大大地提高了。后来许多田野考古工作者都是在殷墟这工地训练出来的。”[13]1932年,李济先生代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河南省政府合作成立河南古迹研究会,就培养出以尹达(原名刘耀)为代表的河南省第一批近代考古工作者。尹达先生早年就学于河南大学国学系,毕业后即参加古迹研究会,从事多项考古发掘工作,晚年的他也深有感触地说:“当时在考古发掘的方法上,思永先生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使中国的青年考古工作者逐渐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中国田野考古的经验。”[14]正是以梁思永先生为代表的我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典范式地辛勤工作,以殷墟为基地,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他们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中,为我国考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综上所述,中国考古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北宋时期,我国传统考古学——金石学就形成于当时的国都东京,进入20世纪初,随着仰韶遗址的发掘,诞生了我国近代考古学。1928年,国民政府建立起第一个考古研究机构,以殷墟为基地进行有规模的考古发掘,在其工作实践中,不断提高考古学的科学发掘水平,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研究资料,并且培养出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河南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的故乡,而且也曾是培养考古工作者的基地,为我国考古事业培养出众多的考古科学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