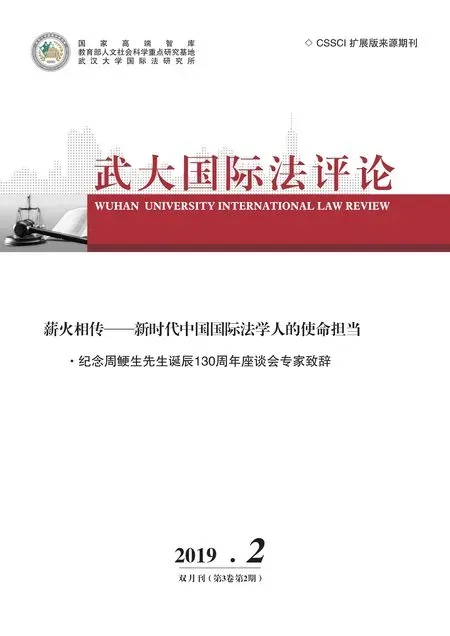论国际投资仲裁中的举证责任
崔起凡
国际投资仲裁已成为私人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端解决的优先选择方式,最近几年也出现了一批涉华国际投资仲裁案件。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沿线国投资法治状况不佳,涉华投资争端存在激增的可能,强化国际投资仲裁的理论研究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举证责任被称为“民事诉讼的脊梁”,是影响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和裁判结果的重要问题,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也同样重要。国内学术界对国际投资仲裁中的举证责任问题尚未给予足够重视,以下基于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对举证责任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以期为“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提供些许有益的理论支持。
一、国际投资仲裁中举证责任含义之澄清
关于举证责任的概念,国际投资协定或者仲裁规则中均未予明确界定。国际投资仲裁中运用的概念通常并非独创,而是借用国内法。当然,由于国际投资仲裁不同于国内司法机构的架构以及仲裁参与者拥有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仲裁中使用的国内法概念,其含义也可能不尽相同。无论怎样,国际投资仲裁中“举证责任”的含义可以从国内法入手展开分析。
(一)国内法中“举证责任”的含义
在普通法国家,举证责任一般分为提供证据责任(burden of production)和说服责任(burden of persuasion)。提供证据责任是指当事人为避免案件直接被法官驳回而承担的必须提供证据的负担;说服责任是指当事人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使得事实审理者(陪审团或法官)相信其主张事实为真实的责任,在证据调查结束后,如当双方证据处于均势,该当事人负担败诉风险。①参见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在大陆法系国家,举证责任包括客观证明责任和主观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是指经法院审理后,当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由其中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风险负担。②参见毕玉谦:《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主观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为了满足其提出事实主张的需要,通过提供证据的方式获得对其有利的裁判所承受的一种必要负担。③参见毕玉谦:《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144页。承担客观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为避免事实真伪不明导致的不利裁判结果,有必要首先提供证据,当证据足以使法官的心证倾向于他时,另一方当事人也会有举证的必要,这种往复转移的“举证必要”就是主观证明责任。
普通法的说服责任与大陆法的客观证明责任功能相当,都属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而且两者在审理程序中始终不发生转移。④See Joost Pauwelyn, Evidence, Proof and Persuasion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Who Bears the Burden?, 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30 (1998).普通法的提供证据责任和大陆法的主观证明责任都属于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普通法的提供证据责任和大陆法的主观证明责任的不同点在于,前者与陪审团的设置相关,当提供的证据不能满足初步证据案件(prima faciecase)这一较低证明标准,案件将会被法官直接驳回,反之,案件事实交由陪审团认定;后者是当事人为避免不利的事实认定而提供证据的负担,与案件是否驳回无关。
(二)国际投资仲裁中“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
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大量仲裁裁决提及举证责任。比如,在Thunderbird案中,仲裁庭指出:当事人对于举证责任的适用原则似乎没有分歧,仲裁庭将适用已经被充分认可的原则,即主张他方违反国际法而产生国际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该主张的举证责任。如果该当事人提交了支持其主张的初步证据,当情况合适,举证责任可以转移到另一方。⑤Thunderbird v.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NAFTA/UNCITRAL, Award, para.95.在Marvin Feldman Karpa案中,仲裁庭援引了WTO美国羊毛衬衫案中上诉机构的观点并指出,提出肯定性主张或抗辩的当事人,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足以确立一项其主张为真的推定,举证责任将转移至另一方,如果另一方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反驳该推定就会承担不利后果。①Marvin Feldman Karpa v.Mexico, ICSID Case No.ARB(AF)/99/01, Award, para.177.上述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体现了这样的规则:提出肯定性主张或抗辩的当事人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这是一项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将在后文另作详述);同时当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确立了初步证据案件或推定(初步证据案件和可反驳的推定往往被混用②Ali Z.Marossi, Shif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 Practice of the 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 28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436 (2011).),举证责任即转移到另一方当事人。
不过,需要特别澄清的是“举证责任”的含义:起初当事人因提出主张而承担的“举证责任”是什么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在该当事人确立了初步证据案件以后,举证责任转移,转移的“举证责任”又应如何解读?这里涉及的两个举证责任是否为同一概念?
其中,前一个依据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分配的举证责任,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相当于大陆法系的客观证明责任或普通法系的说服责任。它的作用在于:当案件经过审理,事实真伪不明,该举证责任为裁判者提供了一个裁判法则,即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不利后果(作出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国际投资仲裁裁决中常常对该举证责任进行分配。比如,在Wena 案中,埃及主张:申请人在订立租赁协议时对一家埃及国有企业的主席进行了贿赂。仲裁庭指出,应该由埃及承担存在贿赂行为的举证责任,不过因举证不足,最终仲裁庭认定贿赂主张未能得到证实。③Wena v.Egypt, ICSID Case No.ARB/98 /4, Award, paras.111-117.此外,后文涉及的举证责任分配均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该术语。
后一举证责任(即转移的举证责任)不是指客观证明责任或者说服责任。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应发生转移,这一点在各国司法制度中普遍被认可。国际司法机构的举证责任分配与一般国内法庭相当,于整个程序进行中并不会转移,而始终由特定当事人承担特定事项的举证责任。④Moj taba Kazazi, Burden of Proof and Related Issues: A Study of Evidence befor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36, 251-253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6).在Alpha 案中,仲裁庭指出:“一旦一方当事人提交了充分的证据支持其主张,举证责任‘转移’至另一方,由它提供证据进行反驳。”⑤Alpha Projekt Holding Gmbh v.Ukraine, ICSID Case No.ARB/07/16, Award, para.236.在该案仲裁庭的这一表述中,“转移”一词被打上引号,是为特别强调客观证明责任并没有转移。
转移的“举证责任”是一种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近似于大陆法系的主观证明责任而非普通法系的证据提出责任。理由在于:首先,在普通法中,原告负有提供证据责任,如果其提供的证据不能满足初步证据案件,其诉请将被直接驳回。而在国际投资仲裁的一般实践中,仲裁庭在程序早期通常不会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驳回仲裁请求,一些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确立的简易驳回制度是针对“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审前异议制度,①参见ICISID仲裁规则第41条第5款。而不是针对证据或事实问题。其次,根据普通法的相关理论,提供证据责任可以在原告和被告之间发生转移,只要满足了初步证据案件标准,提供证据责任即转移给了对方,但是提供证据的责任不可能反复多次发生转移,如果出现证据冲突的情况,该案件应当及时交由陪审团来认定事实。②See Michelle T.Grando, Evidence, Proof, and Fact-finding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8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而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这种在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的举证责任转移可能会反复多次发生,呈现出“弹球”(bouncing ball)现象。③See Ali Z.Marossi, Shif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 Practice of the 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 28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434 (2011).最后,依据大陆法系的证据理论,当一方当事人提供了足够的证据,促使法官的临时心证形成,主观证明责任即转移给另一当事方。另一当事方可以提供反驳性证据,改变法官形成的临时心证,这使主观证明责任再次转移回去。如此可能发生多次反复。国际投资仲裁中举证责任的转移符合大陆法系主观证明责任转移的理论与实践,因此转移的“举证责任”可以看做大陆法系的主观证明责任。④主观证明责任转移的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据。参见毕玉谦:《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170页。而来自普通法的概念“初步证据案件”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可以分别指较低程度和较高程度的证明标准, see Georg Nils Herlitz,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 Prima Facie” , 55 Louisiana Law Review 408 (1994).也有学者认为,在国际争端解决实践中,初步证据案件的确立与否取决于国际司法机构个案中的决定,see Ali Z.Marossi, Shif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 Practice of the 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 28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436 (2011).这种观点意味着初步证据案件作为证明标准不具有确定性。实际上,这里的“初步证据案件”应指较低程度的证明标准(低于优势证据标准),这体现了国际争端解决中强调当事人证据披露的合作义务,是促进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积极举证的“激励”机制。
综上,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存在两种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分别相当于大陆法系的客观证明责任和主观证明责任。争议解决程序之初,两种举证责任均归于同一当事人,该当事人往往是提出主张的原告,不过,当被告提出肯定性抗辩,该举证责任人也可以是被告。在案件审理中,客观证明责任始终不发生转移,而主观证明责任因初步证据案件的确立而转移给另一方当事人,如果另一方当事人不进行反驳,仲裁庭即可认定事实。如果另一方进行了反驳,削弱了仲裁庭的心证,主观证明责任可能再次转移回来,如此可反复进行。两种举证责任各自有其独立的运作空间和机制,同时相互影响。客观证明责任是事实真伪不明情况下的裁判规则,为了避免因该规则产生的不利事实认定,双方当事人都可能有必要履行主观证明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主观证明责任是围绕客观证明责任发挥作用,相比于客观证明责任,它只具有有限的意义。①See John J.Barcelo, Burden of Proof, Prima Facie Case and Presumption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42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33-35 (2009).
二、国际投资仲裁中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理
(一)国内法中的举证责任分配理论
古罗马法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有两项重要规则:其一,“原告负举证责任”。其二,“主张者负举证责任,否定者不负举证责任”。古罗马的举证责任规则体现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两大法系的学者以此为基础对举证责任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形成了具有可操作性的举证责任分配标准。
在大陆法系国家,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理论,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学者罗森伯格所创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该学说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当事人对有利于本方的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第二,通过对法律规范进行分类来区分有利或是不利。他将事实分为“权利发生事实”、“权利妨害事实”、“权利修正事实”以及“权利消灭事实”四种,第一种事实的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其他由被告承担。第三,通过实体法形式上的结构、条文上的关系认定不同实体法规范。法律条文在结构上常采用“本文”与“但书”的形式,其中“本文”部分是权力发生规范,“但书”部分则为权利妨碍规范。②参见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118页。
在普通法国家的举证责任分配学说中,“必要事实说”较具代表性,近些年来为许多普通法学者所认可。比如,Tapper认为,“作为一项常识性的问题,证明对他们的诉请所有的必要事实的说服责任归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或者刑事诉讼中的公诉人”。③Colin Tapper, Cross and Tapper on Evidence 14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Keane 认为,“在民事诉讼中,一般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对于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案件,某些问题是‘必要的’,如果打算赢得诉讼,他必须证明这些问题”。①Adrian Keane, The Modern Law of Evidence 9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除了这些学说,在普通法司法实践和理论中,利益衡量也成为举证责任分配的重要标准,即举证责任分配应当综合政策、公平以及盖然性等要素进行衡量。②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
(二) 国际投资仲裁中举证责任分配理论的适用
有国际法学者指出,古罗马法中“原告负举证责任”中的“原告”(actor)一词并不是从程序角度而是从所涉事项的角度指称真正的原告。③See Cheng Bin,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as Applied by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33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谁主张,谁举证”作为一般法律原则为各国司法以及国际争端解决所认可,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体现于相关规则(比如UNCITRAL 仲裁规则第27条第1 款)和实践中。在AAPL 案中,仲裁庭援引了“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以及郑斌教授对“原告负举证责任”中“原告”的解释。④AAPL v.Sri Lanka, ICSID Case No.ARB/87/3, Final Award, para.56.在SGS 案中,仲裁庭指出:“申请人承担证明其诉请的首要举证责任,而被申请人承担证明其抗辩的责任。”⑤SGS v.Paraguay, ICSID Case No.ARB/07/29, Award, para.80.也就是说,主张一项事实的当事方,无论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应负责提供相应证据。这里所谓的“主张”指的是肯定性诉请或抗辩,如果被申请人仅仅是否定申请人主张的事实,该事实的举证责任归申请人,而且不发生转移。这实际上是古罗马法中“否定者不负举证责任”原则的适用,该原则是大陆法系中“主张消极事实的人不负举证责任”学说的来源,同时它也对普通法国家的举证责任分配理论产生深远影响。⑥参见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谁主张,谁举证”的解释不能停留于字面,因为双方当事人可能都主张或者回避主张同一方面的事实。“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需要结合实体规则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对此,国内举证责任分配理论的适用是有益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是基于一个假设,即当事人应当会且只会主张对本方“有利”或者“必要”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对应的是实体规则中的要件事实,当事人主张这些事实的同时须予以证明。在这个意义上,举证责任分配总体上是实体规则本身预置的,具有派生性的特点。⑦See Andreas Reiner, Burden and General Standards of Proof, 10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330 (1994).这也是一些举证责任分配理论比如“法律要件分类说”的逻辑起点。在这方面,国际投资法和国内法是相同的。在Tradex 案中,仲裁庭指出:“主张者对于所适用的实体法规则的要件承担举证责任以支持其主张。”①Tradex Hellas S.A.v.Albania, ICSID Case No.ARB/94/2, Award, para.74.
作为混合仲裁,国际投资仲裁适用的法律可以是国际法和国内法。②参见ICSID公约第42条。依据国内法提出的事实主张,可以根据国内法中的理论与规则分配举证责任。而国际投资仲裁适用的国际法(主要为投资协定)的内容特点决定了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性:一方面,国际投资协定规定了东道国的投资保护义务,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公平与公正待遇等,投资者主张东道国违反了这些义务,需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鉴于保护人类生命、动植物健康、国家安全、公共政策等方面的考量,在例外情况下偏离投资保护义务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所以投资协定中可能规定例外条款,而且通常在例外条款中对于东道国偏离条约义务规定了一定的条件。东道国援引例外条款需要满足这些条件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仍然符合法律要件分类说中“对有利于本方的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的基本原理,适用普通法“必要事实说”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
(三)国际投资仲裁中“法官知法”的适用:国内法属于免证事项?
依据“法官知法”这项一般法律原则,举证仅限于事实问题,法律上的模糊不清或空白交由法官通过解释来加以解决,法官应熟谙所适用的法律。国际投资仲裁可能适用国内法,此时国内法本身的内容是否落入“法官知法”的范围而无须举证?理论上这取决于对作为查明对象的国内法的定性。如果它被视为法律,那么依据“法官知法”原则,该法属于法官负责查明的范围;如果它是事实问题,则应由当事方负责举证证明。
实际上,在国际争端解决(包括国际投资仲裁)中,当事方主张某一国内法的适用或依据国内法主张权利,必须对其内容予以证明,国内法被认为是事实要素,而不是法律要素,当事方不能期待国际法官或仲裁员知悉国内法。③See Mojtaba Kazazi, Burden of Proof and Related Issues: A Study of Evidence befor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47-49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6).
在Mohtadi 诉伊朗案中,争议焦点是申请人主张其享有权利的财产的法律地位。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应依据伊朗1979年土地授权法(Land Grant Act 1979)证明已经获得争议土地的所有权,而且该财产须在1971年从林地转化为农田或类似已开发的土地,这样在1979年土地授权法通过时该土地不再是林地。仲裁庭不熟悉伊朗法律,无法依据该法确定争议财产的法律地位,也不清楚在1979年土地授权法下“林地”(woodland)的含义。仲裁庭指出,申请人有责任清楚地证明其财产属于该法的调整范围,由于申请人未能履行相应举证责任,仲裁庭最终驳回申请人的权利主张。①Mohtadi Jahangir & Mohtadi Jila v.Iran, Award No.573-271-3, Reprinted in 32 Iran-U.S.C.T.R.124, 160 (1996).
(四)仲裁庭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权
投资协定或仲裁规则缺乏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明确规定,具体情境下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并非总是泾渭分明,有些情况下非常复杂,仲裁庭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对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审查,很少推翻仲裁庭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决定。在Continental 案中,申请人认为仲裁庭错误分配了举证责任。对此ICSID 专门委员会指出:它注意到《华盛顿公约》和ICSID 仲裁规则没有包含举证责任或证明标准的规定。因此,不应要求仲裁庭在决定争议时明确适用某一特定举证责任或证明标准。事实上,仲裁庭没有义务明确指出任何特定的举证责任或证明标准并用这些术语分析证据。②Continental Casualty v.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ARB/03/9, 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 for Partial Annulment of Continental Casualty Company and the Application for Partial Annulment of the Argentine Republic, para.135.
事实上,仲裁庭在分配举证责任时可能基于公平考虑,并且平衡公平性与确定性的关系,须偏离一般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以确保任一当事人不会获得对另一当事人不公平的优势。③See Caroline E.Foster, Burden of Proof in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29 Austral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35-39 (2010).仲裁庭在分配举证责任时可能也会考虑实体法以外的其他因素,比如举证成本、政策因素。有资深学者认为,国际司法机构有权决定哪一方承担举证责任,这是国际法庭适当发挥职能所必需的固有权力。④See Chittharanjan F.Amerasinghe,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Litigation 75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5).实际上,其他国际法庭比如WTO 争端解决机构、常设仲裁法院(PCA)的实践都认可仲裁庭(专家组)对于举证责任分配享有自由裁量权。⑤参见崔起凡:《论WTO争端解决中的证明责任分配》,《武大国际法评论》2014年第2期,第235页。
三、投资协定典型条款下的举证责任
在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中,投资者主张东道国违反投资协定或投资合同中的义务,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东道国可以提出肯定性抗辩(比如例外条款),主张其违反协定的措施具有正当化理由或者协定并不适用,同时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有学者指出,一般例外适用于BIT 项下的所有义务,而特定例外适用于BIT项下有限数量的义务。①See Kenneth J.Vandevelde, Rebalancing through Exceptions, 17 Lewis & Clark Law Review 449 (2013).鉴于一般例外条款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分析对象。此外,国家根本安全例外条款及拒绝授惠条款下的举证责任在实践中引发广泛争议,在此亦予以重点分析。
(一)一般例外条款下的举证责任
大多数国际投资协定的一般例外是以GATT第20条或GATS第14条为蓝本,比如2010年《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投资协议》第16条。一般例外的援引建立在特定要件的满足上,以防止例外的滥用。
“国际投资仲裁庭尚未解释过一般例外条款,仅解释过较为有限的例外,比如美国—阿根廷BIT 中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②S.A.Spears, The Quest for Policy Space in a New Gen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13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062 (2011).不过,基于价值功能和逻辑结构的相似性,投资协定中的一般例外,在举证责任上应当与GATT 第20条或GATS 第14条并无不同。也就是说,应由援引一般例外的东道国承担举证责任,而且可能不仅证明不构成武断或不合理的歧视措施或者未采取变相投资限制措施,通常也须证明不符措施是“必需”的、“有关的”或者其“设计或实施”是为促进条款中所明示的具体政策目标。当然,不同投资协定的例外条款在具体措辞上有一定差别,相应地,东道国的举证责任尤其是待证的要件事实会受到影响。
有些双边投资协定的一般例外对援引方施加了较少的严苛条件,这可以减轻东道国的举证责任。其中一些条款并不要求东道国证明特定措施是“必需”的,而只要求其对于目标实现是相称的(proportional)。③See e.g., Colombian Model BIT(2002), Article 8.还有一些国际投资协定规定了一般例外的程序性要求,比如2002年日本—韩国BIT④其第16条第1 款规定:“……在一缔约方根据第1 项规定采取不符合本协议所规定的义务的任何措施的情况下,该缔约方应当在该措施实施前或在实施后尽可能快的时间内,通知其他缔约方下列涉及该措施的基本要素……”。根据此类规定,即使当事方违反条约义务的措施可以援引例外而获得正当化,它仍应按程序要求进行通知,使其他缔约方尽早获悉其违反义务的相关信息,以作出相应的调整,减少损失。如果违约方未能证明履行了这种程序义务,则不能完全免责。这些要求是善意原则在国际投资法上的体现。数量庞大的国际投资协定(尤其是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一般例外条款的内容具有多样性,甚至有投资协定没有规定一般例外。由于投资协定中对一般例外作出个性化的设计和具体规定,东道国的举证责任(尤其待证的要件事实)也不尽相同。
WTO 争端解决实践中关于“必要性”举证责任的灵活处理值得国际投资仲裁予以借鉴遵循。在巴西翻新轮胎案中,上诉机构指出,申诉方应负责指出被诉方本可以采取的作为系争措施的可能替代方案;如果申诉方指出了可能的替代措施,被诉方可以试图证明被提议的措施不能实现它所选择的健康保护水平,因此不是真正的替代方案;被诉方也可以试图证明被提议的替代方案事实上不是合理可用的(reasonably available)。①AB Report, Brail-Retreaded Tyres, WT/DS332/AB/R, para.156.据此,为证明“必要性”的成立,被诉方不需要通过举证一一排除所有可能的替代措施,因为“即使在数百万次的观察中只看到黑乌鸦,也无法排除白乌鸦存在的可能性”。②[德] 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00-301页。如果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需要穷尽各种可能性并予以排除,那么其需要承担过重的举证责任,甚至不可能。基于举证成本的考虑,由申诉方承担存在某种合理替代措施的主张责任,然后由被诉方证明这些措施并非合理可用或者不能实现本国正当的政策目标,这样才更为便利和经济。
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一般例外条款下的举证责任由东道国承担,这一点比较容易接受。同时对于“必要性”的证明,合理替代措施的主张责任可分配给投资者,由东道国承担这些替代措施并非合理或可行的举证责任。这是一种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
(二)国家根本安全例外条款下的举证责任
国家根本安全例外条款是指一国为保护对本国根本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利益,可以背离条约义务的例外条款。中国签订的一些BIT 中有此类条款,比如2006年中国—印度BIT 第14条。在有些文件中它被称为“不排除措施条款”(non-precluded measures provision)。阿根廷政府为应对21世纪初爆发的经济危机而采取了系列国内紧急措施,导致该国在ICSID 被诉的案件多达几十件。在其中一些案件中,阿根廷援引习惯国际法中的危急情况例外和1991年阿根廷—美国BIT第11条③阿根廷—美国BIT 第11条(“不排除措施条款”)规定:该条约不应排除缔约任何一方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履行其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或安全的义务,或保护其根本安全利益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作为抗辩。
在CMS 案、Enron 案以及Sempra 案中,仲裁庭依据体现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25条①《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25条(“危急情况”)规定: (1)一国不得援引危急情况作为理由解除不遵守该国某项国际义务的行为的不法性,除非:a.该行为是该国保护基本利益,对抗某项严重迫切危险的唯一办法;而且b.该行为并不严重损害作为所负义务对象的一国或数国或整个国际社会的基本利益。(2) 一国不得在以下情况下援引危急情况作为解除其行为不法性的理由:a.有关国际义务排除援引危急情况的可能性;或b.该国促成了该危急情况。的习惯国际法解释阿根廷—美国BIT 第11条。依据国际法委员会的评论性意见,若违反国际义务之行为可归咎于国家,而该国试图依据该草案第五章(“排除不法性的情况”)来规避责任,它有责任为其行为提供正当化理由。②See James Crawford,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s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 Introduction, Text and Commentary 16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在这些案件中,阿根廷为援引该条款需要就“必要性”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采取的措施是应对经济危机的“唯一办法”。不仅如此,阿根廷还要证明自己未“促成该危急情况”。
不过,在LG & E案和Continental案中,仲裁庭作出了不同的举证责任分配。
在LG & E案中,仲裁庭认为阿根廷—美国BIT第11条是“危急情况”习惯国际法的特别法。③LG & E v.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ARB/02/1, Decision on Liability,paras.205-206.仲裁庭没有适用习惯国际法中的“唯一办法”标准,而是审查了阿根廷采取的措施是否合法、必要以及合理的危机应对,采取了类似于欧洲人权法院采取的比例原则标准。④LG & E v.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ARB/02/1, Decision on Liability,paras.239-242.当投资者主张阿根廷采取的措施不是用于应对危机可利用的“唯一方法”时,仲裁庭指出:双边投资协定第11条涉及缔约国必须采取行动、别无选择的情况,缔约国可以有几种应对措施可供选择,以便维护公共秩序或者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⑤LG & E v.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ARB/02/1, Decision on Liability,para.239.可见,仲裁庭赋予“必要性”抗辩的提出者以“自由判断余地”。这类似于《欧洲人权公约》第15条规定的情况。欧洲人权法院对“必要性”采用了较为宽松的解释,允许“为了社会民主的需要”“为了保护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安全,为了保护健康和道德等”,限制基本人权和自由。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必要性”并不意味着“必不可少、绝对必需等”,该词在条约中的含义应由缔约国自己来断定,这就是自由判断余地原则。⑥Handyside v.United Kingdom, 24 Eur.Ct.H.R.(Ser.A) (1976), part II, para.47.显然,相比于CMS案等案件中“唯一方法”的标准,在LG & E案中因仲裁庭的解释方法,关于“必要性”的举证责任明显得到减轻。
关于“促成了该危急情况”这一要件事实,仲裁庭指出,申请人未能证明阿根廷促成该国严重的经济危机。①LG & E v.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ARB/02/1, Decision on Liability,para.256.可见,与先前几个案件的裁决不同, 该案将“促成了该危急情况”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投资者。不过,该案仲裁庭对这种立场转变并未提供充分合理性的解释。
在此后的Continental Casualty 案中,仲裁庭亦接受了“必要性”抗辩,明确认可阿根廷的自由判断余地,②Continental Casualty v.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ARB/03/9, Award, para.181.而且未考虑阿根廷是否应就未促成危急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因为仲裁庭适用的是阿根廷—美国BIT 第11条,而不是习惯国际法。③Continental Casualty v.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ARB/03/9, Award, para.234.
援引习惯国际法对国家根本安全例外条款进行解释,实际上是将前者严苛的条件并入到后者,提高了阿根廷—美国BIT原本设定的“门槛”。将习惯国际法规则用于条约解释的依据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 款第3 项规定的“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有关国际法规则”包括习惯国际法,不过许多仲裁庭在适用该规定时都强调文本解释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在条约未作规定或者内容不确定时才可以参照有关国际法规则。④参见张生:《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条约解释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112页。LG & E 案和Continental Casualty 案仲裁庭将阿根廷—美国BIT 第11条解释为特别法,使其得到优先适用,而且在“必要性”的解释中引入比例原则,认可了国家在危急情况下自由判断的余地。这种解释方法减轻了东道国援引国家根本安全例外条款的举证责任,更有利于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平衡。
“该国促成了该危急情况”是《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25条第2 款规定的不得援引“情况危急”条款的两种情况之一,它的举证责任在CMS案、Enron 案以及Sempra 案中被分配给东道国,而在LG & E 案中分配给了投资者。实际上,“未促成该危急情况”应当被解释为“情况危急”条款的例外,应由投资者主张并承担举证责任。同时仲裁庭需要特别强调东道国在这方面信息披露的合作义务,因为东道国对促成危急情况的详尽信息更为熟悉,获取更为便利。国际法委员会的评论性意见指出,“通常情况下,只有国家才能完全清楚那些可能免除其义务履行的事实。”①James Crawford,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s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 Introduction, Text and Commentary 16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相反,投资者对相关情况几乎难以全面了解。所以,“该国促成了该危急情况”的举证责任由投资者承担,但东道国应善意履行信息披露的合作义务。②合作义务与举证责任不同,当事人履行合作义务是善意原则的要求,并非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参见崔起凡:《论WTO 争端解决中的证据披露》,《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18页。在WTO 争端解决实践中也有强调非举证责任一方的合作义务的情形,如DSU 第22.6条下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对中止减让水平建议提出质疑的被诉方,同时强调申诉方承担提供关于“丧失或减损”计算方法的信息的合作义务。③参见崔起凡:《WTO 争端解决中的证据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131页。
(三)拒绝授惠条款下的举证责任
拒绝授惠条款的目的在于确保投资协定不被非缔约国投资者控制的空壳公司“搭便车”。中国缔结的部分BIT 也包含此类条款,比如2008年中国—墨西哥BIT 第31条。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拒绝授惠条款下的举证责任分配存在争议。
在Generation v.Ukraine案中,仲裁庭指出,作为缔约方的东道国如果认为投资者由第三方所拥有或控制并拒绝给予投资者条约中的利益,举证责任应由援引拒绝授惠条款的东道国承担。④Generation v.Ukraine, ICSID Case No.ARB/00/9, Award, para.15.7.在Petrobart案中,仲裁庭认为应当由东道国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首先,东道国应当证明争议法律实体由第三国公民或国民拥有或控制;其次,东道国应证明该争议实体在其成立所在的缔约国范围内没有实质性商业活动。⑤Petrobart v.Kyrgyz, SCC Case No.126/2003, p.59.
在Plama 案中,投资者一开始即承认它没有实质性商业活动,⑥Plama v.Bulgaria, ICSID Case No.ARB/03/24, Award, para.81.仲裁庭将投资者是否由该国或其他缔约国国民拥有或控制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申请人。⑦Plama v.Bulgaria, ICSID Case No.ARB/03/24, Award, paras.82,89.
在Amto案中,仲裁庭就相关举证责任给出了全面的解读,它指出,依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国际仲裁中,一项主张的举证责任归于提出该主张的当事人。据此,申请人有责任证明它满足投资定义以便获得ECT 协定第三部分规定的保护以及依据第26条进行仲裁的权利,同理,申请人也应当证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它所寻求保护的投资。不过,如果被申请人行使拒绝的权利,主张申请人不属于受保护的投资者,举证责任转移到被申请人。①Amto v.Ukraine, SCC Case 080/2005 (ECT), Final Award, para.64.
针对不同仲裁庭在实践中对拒绝授惠条款下的举证责任分配产生的冲突,有学者指出,拒绝授惠条款下的举证责任由投资者承担比较适合,其合理性在于:其一,投资者为获取协定中所规定的投资保护,存在合格的投资是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其作为申请人提起诉请的基础。其二,投资者相比于东道国,在举证上承担更低的成本。“实质性商业活动”或者权利归属方面的信息对于投资者而言更容易获取和提供,举证成本较低,而这些信息对于东道国而言则难以提供。其三,拒绝授惠条款的目的在于向东道国授权,而将举证责任归于东道国会导致东道国在实践中难以实现其应有的权利。②See Zhang Xiaojing, Proper Interpretation of Corporate Nationality und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to Prevent Treaty Shopping, 6 Contemporary Asia Arbitration Journal 68 (2013).
上述观点不能成立。如果未另作特别规定或约定,那么拒绝授惠条款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东道国更为适宜,理由在于:其一,“证据偏在”的情况在争端解决中并不少见,这不是倒置举证责任的充分理由,仲裁庭可以命令投资者披露相关资料,如投资者拒绝履行合作义务,仲裁庭可进行不利推定。其二,拒绝授惠条款的目的在于向东道国授权,这一判断没有问题,不过举证责任由谁承担不影响“授权”的性质。举证责任由东道国承担仅仅是说明了所授权利的行使需要具备一定条件,包括履行相应举证责任。恰恰因为该条文是授权条款,应由主张该条款权利的一方证明该条款中的要件事实。其三,拒绝授惠条款的性质是授权条款,它使东道国行使拒绝权利具备了正当化的事由,也是一种例外条款,按照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应由东道国援引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投资者提起仲裁要求投资保护,虽然需要存在合格的投资以及具有缔约国投资者的身份,但是只须初步证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相关投资;如果东道国依据拒绝授惠条款提出异议,为此东道国需要承担该条款下的举证责任。
四、国际投资仲裁中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之评述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标准
在缺乏举证责任分配的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国际投资实体法规则的目的和宗旨、条文的措辞、不同条文(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仲裁庭的解释将深刻影响举证责任的分配。这是举证责任分配由实体法本身预置和具有派生性的体现。
如果某一规则明确表明它是东道国偏离投资保护义务的例外或者为东道国违反条约的行为提供正当化理由,那么东道国援引该规则时应该承担该条款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但有些情况下是否构成肯定性抗辩并非清晰可辨,因为不同条文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而且对于同一规则中的要件事实存在双方均主张或均不主张的可能性。这时就要对条文的目的和宗旨进行分析。
比如,有无“实质性的商业活动”既是拒绝授惠条款中的要件事实,也直接关系到投资协定下“投资者”的资格,此时拒绝授惠条款下的“实质性的商业活动”的举证责任分配应当结合条约目的和宗旨进行分析。拒绝授惠条款的目的在于授予东道国偏离投资保护义务的权利,同时“实质性的商业活动”并不是“投资者”概念的必要因素(通常投资协定中投资者的定义无此要求,“实质性的商业活动”也不是影响公司国籍判断的标准)。如果在某一投资协定下,缺乏“实质性的商业活动”使得某一企业不享有该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权利,那是投资协定向东道国授权的目的使然,东道国主张该条款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仲裁庭关于国际投资法包括投资协定的解释对举证责任也会造成直接影响。比如,在阿根廷系列案中,对“危急情况”习惯法及“必要性”的解释直接影响东道国举证责任的轻重。此外,上述CMS 案等案件的仲裁庭对《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 款第3 项的解释,对法律适用进而对东道国的举证责任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仲裁庭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缔约方可以通过投资协定的明确规定限制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比如拒绝授惠条款下的举证责任,投资协定可以明确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一方仲裁当事人,新加坡、日本等国近年来签订的一些拒绝授惠条款就明确要求缔约国证明(establish)投资者被非缔约国国民控制或所有的事实。①参见新加坡—澳大利亚BIT第20条、土耳其—韩国BIT第70条。这种做法提高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可预见性,可资借鉴。
在投资协定谈判和起草过程中,如果没能合理注意条文的措辞以及不同条款(或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可能导致投资协定文本缺乏周延性,仲裁庭不得不行使自由裁量权,举证分配的可预见性会降低。比如,《中国投资保护协定范本(草案)》第1条第2 款第2 项将投资者限定于“住所在该缔约一方领土内并且有实际经营活动的任何实体”,②参见温先涛:《〈中国投资保护协定范本〉(草案)论稿(一)》,《国际经济法学刊》2011年第4期,第175页。同时第10条规定了拒绝授惠条款,适用于该企业在缔约另一方境内未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的情况。①参见温先涛:《〈中国投资保护协定范本〉(草案)论稿(二)》,《国际经济法学刊》2012年第1期,第150-151页。两个条款分别使用的“实际经营活动”与“实质性商业经营”措辞是否同一含义?如果含义相同或部分相同,那么举证责任又该如何分配?条文中要件事实的重叠交叉以及用语的含糊不清无疑增加了举证责任分配产生争议的可能性。②基于目的与宗旨之分析方法,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仍应由东道国承担举证责任,因为即使将相关表述置于投资者定义条款中,仍然作为“投资者”的例外存在,投资协定向东道国授权偏离条约义务的目的没有改变。
(三)举证责任分配标准统一的程序保障:上诉机制的确立
如果国际投资仲裁中出现举证责任分配不统一的情况,现有救济方式存在不足。无论是审查非ICSID 仲裁裁决的国内法院,还是审查ICSID 仲裁的专门委员会,都只能进行程序审查,并不涉及属于实体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如上文所述,专门委员会在Continental 案中对于仲裁庭在此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亦予以明确认可。
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确立上诉机制是统一举证责任分配的程序性保障。有学者指出,没有上诉机构,仲裁庭便没有压力在具体案件说理中提供各种充分理由,但是这些对于确立先例非常重要;由于ICSID受理案件数量大,ICSID框架内建立类似WTO 上诉机构的机制,对条约的解释、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审查,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国际投资仲裁的稳定性、一致性以及权威性。③Louis T.Wells, Backlash to Investment Arbitration: Three Causes, in Michael Waibel et al. (eds.),the Backlash against Investment Arbitration : Perceptions and Reality 349-350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0).的确,WTO 上诉机构在许多案件中对举证责任问题发表意见,④参见崔起凡:《论WTO争端解决中的证明责任分配》,《武大国际法评论》2014年第2期,第213-215页。对于举证责任分配标准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国际投资仲裁中上诉机制的确立已经从设想走向一定范围内的实践,⑤比如,2016年2月1日公布的欧盟—越南自贸区协定规定了“投资法庭制度”,2016年2月29日公布的欧、加之间达成的《综合性经济贸易协议》(CETA)最终文本也明确纳入常设投资法庭及上诉机制。尽管仅仅是一个开始。
五、结 语
作为优选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国际投资仲裁保持着满足不同法律文化背景当事方需要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不同的法律文化互相竞争、互相融合,促进国际投资仲裁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国际投资仲裁应当就“举证责任”等概念形成共识,否则对于仲裁程序和裁判的公正性会产生消极影响。提出肯定性主张或抗辩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个案中需要依据实体规则的目的和宗旨、条文的措辞、不同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判断,仲裁庭也应合理解释规则并分配举证责任。为增强举证责任分配的可预见性,缔约国应在投资协定中周全地制定实体规则,同时确立上诉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程序保障。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法律实务人士应寻求更多机会进入国际法律服务市场并与国际同行进行竞争,为我国政府的外资管理以及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保驾护航。为满足这一需求,在国际投资仲裁中需要妥善应对举证责任问题,包括就此提出本方主张以影响仲裁庭,这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争端解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