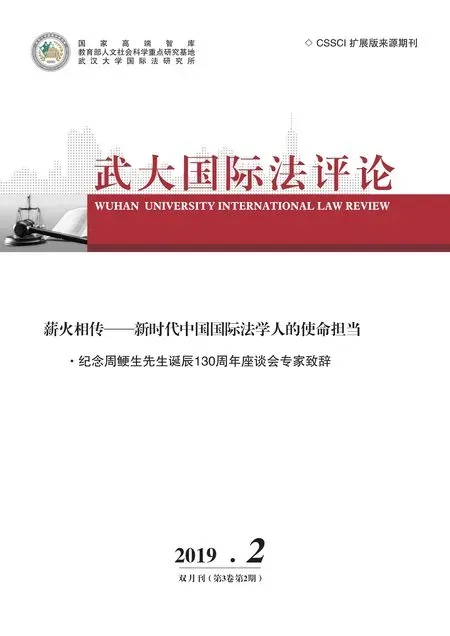怀念外祖父周鲠生
周鲠生先生外孙 陈一周
周鲠生是我的外祖父。我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西迁到四川的武汉大学,出生在外祖父家里,是外祖母抚养了我,在艰苦的抗战期间一手把我带大。在纪念周鲠生诞辰130周年之际,我想表达对外祖父、外祖母的怀念和敬仰之情。
在我的记忆里,外祖父为人十分谦和,平时在家,从未见他疾言厉色,也记不得他曾对家里人包括对我们孙辈发过脾气。出现任何问题时,总是见他和颜悦色,谆谆教导,以理服人。
他从20世纪20年代来武汉大学工作到1950年离开的二十多年里,在学校建立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与学校的师生员工有着密切的脉络。他不仅仅与名教授们并且是不分文科和理工科的先生们,都有着良好的同事关系,对学校的教工也十分友善,对教工的病痛也是关怀备至,例如,一位肖老师患病多年,外祖父去北京多年后还托人给他带药回武汉。
周鲠生去北京后,常有去北京出差开会的武大朋友去家里看望他,这是他最高兴的时刻,不断打问学校的情况,打问老同事、老朋友的近况,深深地眷恋着武汉大学,眷恋着美丽的珞珈山。
到了北京后,外祖父也有一个朋友圈,朋友们常在外祖父的客厅里聚会,他们有时是隔两三周相约来聚一聚,有时是路过家门进来坐坐,一杯清茶。这是哪些朋友呢?有担任过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的李浩培教授,李先生后又任外交学院教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有27 岁就在四川乐山任武大法学院教授的王铁崖教授,去北京后任北大法学院教授;有曾经在武大法学院任教的梅汝傲教授,后也去北京任外交部顾问,是著名的东京审判中国大法官;有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李四光先生,后去北京做地质部长;有文化部长丁西林;国务院对外文委主任清华教授张溪若;有在武大做过教师的外交学院李铁铮教授。常客中还有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帧先生,他20世纪30年代也在武大任过教。看看这个朋友圈,全与武汉大学相关,全是武大校友。他们都是武大的杰出校友!
这说明了周鲠生的亲和力,到哪里都自然而然地把学者们聚合在一起。我在北京度假时,也常坐在客厅里,听着他们回忆武大往事,特别是听他们回忆四川乐山的岁月,听他们讲乐山的那些逸闻趣事和艰苦生活,这也让我涨知识、受教育,并为之感慨万分。在北京的武大校友们经常来看望外祖父,这也为外祖父带来了许多温馨。
那个年代前后二十多年,可以说当时还在从事国际法研究并且著书立说的精英们都在这里了。我在纪念外祖父的同时,也深深地怀念这些已故去的叔叔伯伯们。
最应当向外祖父学习的是他刻苦学习和勤奋工作的精神,20世纪60年代,外祖父已年过古稀,但当时外交部领导建议他写部国际法专著,便于外交干部学习时,他欣然同意。在外交部领导同意下,他辞去一般外事和社会活动,集中力量写书。因视网膜脱落做过手术,视力衰退,当时他的一只眼睛已完全失明,另一只眼睛高度近视,写作时眼睛都要凑到稿纸上了,没日没夜地伏案写作,查阅大量资料,对文献索引一丝不苟。就这样用了三年时间,是他暮年的78岁、79岁、80岁的三年,写成了60 万字的《国际法》初稿。外交部曾派过一位年轻人帮助他整理,他本希望听取各方意见,修改后再出版,但初稿出来后外祖父因过度劳累而病倒,已是风烛残年,从此一病不起,没能再作修改。初稿先是在外交部作为培训讲义内部印发,“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由外交部送商务印书馆出版。首版出来时外祖父已离世五年了,很遗憾,他没有看到自己呕心沥血的著作面市。他就像一支蜡烛,他就像一盏油灯,油已烧尽,但他的思想和他的智慧仍发着光,照亮着后人。
周鲠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是在北京由外交部和外交学会联合举办的,原外交部条法司邵司长发言,称《国际法》这本书是周鲠生对新中国外交事业和发展现代国际法理论与实践所作的一大贡献,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国际法巨著。在这次纪念会上,还组织出版了周鲠生用英文写的在美国首版的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这是一本广受关注的著作,也是对他的一种纪念。
在最后两年,外祖母已先他而去,家里就他一人,一位老保姆给他做饭,照顾他,老朋友们也关心着他,每当病倒,保姆常常是打电话给梅汝傲先生,梅先生立马来家看望并向外交部领导报告,外交部条法司的同事们联系安排医院,每次住院都安排到北京最好的医院,得到最好的医疗。梅先生常在医院看望,把病情报告给领导,起到医院与单位之间的联络作用,当病危时,外交部的副部长还亲自到医院,不是礼节性看望,而是在医院向医生了解病情,认真研究治疗方案,我当时就在病房里,看到这一切,十分感动。我要感谢外交部领导、条法司的领导和同事们,在周鲠生生病期间,给了他最好的医疗和照顾,家人是不会忘记的,感恩于帮助和照顾过他的朋友们!
还要感谢武汉大学、中国国际法学会、外交部、外交学会、武大法学院、武大国际法研究所联合组织召开这次周鲠生诞辰130周年纪念会,让我们得以再次缅怀老校长的风范,学习他那好学不倦、刚正不阿、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学者本色和精神。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