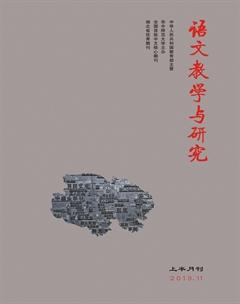从素读、参读到研读
吴国珍
《菩萨蛮(其一)》为《花间集》卷一第一篇,入选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唐诗宋词选读》。
教师的阅读主要是一种教学行为,是教学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教学行为的阅读,显然不是趣味性阅读,那种阅读兴起时拿来就读,兴尽时抛在一边;但显然也不是纯知识性阅读,只满足于了解各种信息、观点和结论。教师的阅读,应当是一种专业性或半专业性的阅读,它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研究。从阅读过程的完整性看,就要经历素读、参读和研读三个阶段。
一、素读,珍视对一首词的最初印象
“素读”是一种基本的读书方法,就是不追求对内容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只是反复有声的朗读,直到把诵读的内容背得滚瓜烂熟为止。这是我国古代私塾常用的读书法。而笔者所言的素读,更强调的是“素”,是指不参考任何资料(必要的字典词典除外)地阅读文本,获得对文本的一种原始理解;对阅读中产生的不解疑问,也不急于寻找资料求证,而是静下心来把文本反复阅读几遍,从文本本身的肌理中获得答案或者启示。
不看任何注释和赏析,直面《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比较明确的有以下几点:这首词是写一个女子的晨起化妆,这个女子比较年轻美丽(“香腮雪”),娇慵(懒起,弄妆,照花前后镜),生活富足(绣罗襦);词中的“度”“弄”字较生动;“照花前后镜”的画面感强,如特写镜头。不太明确的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女主人公为何懒起,词中没有交代;二是“双双金鹧鸪”似有暗示,但不知道究竟暗示了什么。这些不太明确的地方,可以猜测,但不敢保证猜测就是正确的。不明确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字词方面,“小山重叠金明灭”非常晦涩,而“双双金鹧鸪”是如何“帖”上“绣罗襦”的,也有点含糊;二是人物方面,主人公的身份不明,是闺中少女、贵族妇女、宫女娥妃抑或歌妓舞女?皆有可能;三是思想情感方面,温庭筠写作这首词,究竟表达什么思想情感,也看不分明。
从诗歌的特点看,不太明确的部分是诗歌暗示的部分,而不明确的地方是诗歌的空白,而空白的形成不完全是诗人未写到,有的可能是时代变迁等导致认知发生了困难。阅读和教学的重难点就是明晰作者暗示的部分,并将空白予以填充。
二、参读,发现一首词的前世后生
明晰暗示,填充空白,需要教师有广泛的知识背景。所谓参读,就是扩大知识背景,主要通过广泛阅读来实现。没有素读,我们的阅读理解很可能先入为主,被专家的观点主宰;但是,只有素读,我们的困惑依然不能解答,我们的理解也需要求证。文本并不是自足的,它是一个敞开的世界,有很多触角通向四方八方,也接纳四面八方。所以,我们不能仅凭文本获得全部的认知。为了解惑,也为了求证,我们必须搜寻一切有关文本的资料,包括专家学者等对文本解读的文章,进行大量阅读。作为一名中学教师,其阅读的范围可能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网络文章。相对来说,“百度百科”较为权威,因为其说多为前人所说的综合(每段文字后都注明引自何人何书所说,或是综合多家之说)。
二是必备工具书。主要有《古代汉语词典》等。此外,网站“汉典”也较为权威。
三是教材。主要是大家中文专业教材,包括《古代文学史》《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古代文论选》等。
四是史书。主要是《二十五史》,此外,本篇作者还可以参考《唐才子传》。
五是各类解读评析书籍。如唐圭璋等编著的《唐宋词鉴赏辞典》、叶嘉莹的《小词大雅》、葛晓音的《唐诗宋词十五讲》、刘学楷的《温庭筠全集校注》等,依据各人阅读面而不同。
六是温庭筠的其它词作,特别是与《菩萨蛮》密切相关的另外十三首。
通过参校阅读,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一、关于“小人重叠金明灭”有多种理解。《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释此句:“谓画屏与初日的光辉映照成彩。许昂霄《词综偶评》:‘小山,盖指屏山而言。金明灭,形容阳光照在叠折的屏风上,或明或暗,光彩夺目。一说,小山指眉额;金,画眉作金色,亦可通。作者另一首《菩萨蛮》词中有‘蕊黄无限当山额句,即以山喻眉额。”[1]周汝昌持“小山眉”之说。“小山,眉妆之名目,晚唐五代,此样盛行,见于《海录琐事》,为‘十眉之一式。大约‘眉山一词,亦因此起。眉曰小山,也时时见于当时词中,如五代蜀秘书监毛熙震《女冠子》云:‘修蛾慢脸(脸,古义,专指眼部),不语檀心一点,小山妆。又如同时孙光宪《酒泉子》云:‘玉纤(手也)淡拂眉山小,镜中嗔共照。翠连娟,红缥缈,早妆时。亦正写晨妆对镜画眉之情景。可知小山本谓淡扫蛾眉,实与韦庄《荷叶杯》所谓‘一双愁黛远山眉同义。重,在诗词韵语中,往往读平声而义为去声,或者反是,全以音律上的得宜为定。此处声平而义去,方为识音。叠,相当于蹙眉之蹙字义,唐诗有‘双蛾叠柳之语,正此之谓。金,指唐时妇女眉际妆饰之‘额黄,故诗又有‘八字宫眉捧额黄之句,其良证也。”[2]“百度百科”指出有三种理解:“有认为是写室内屏风的,有认为是写女子眉妆的,还有解为是写女子发髻的,歧义纷纷。”[3]
二、关于“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宋刻本),《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明万历本)作“新著绣罗襦”。对于“帖”字,一般认为是“贴绣”,贴绣即贴布绣,其绣法是将贴花布按图案要求剪好,贴在绣面上,也可在贴花布与绣面之间衬垫棉花等物,使图案隆起而有立体感。贴好后,再用各种针法锁边。叶嘉莹认为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熨帖”,“就是熨,熨得很平的。……唐朝王建有一首宫词,说‘熨帖朝衣脱战袍”。[4]
三、关于女主人公身份。今人刘学楷认为:“结拍二句‘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正透漏出女子所著者系舞衣,女子身份为歌舞伎人。飞卿出入倡楼,对此类女子之生活极为熟悉,词中所写伎人早起梳妆前后之情事情態,即其经常亲历者。”[5]辛文房据各类文献编撰的《唐才子传·温庭筠》,记《菩萨蛮》之本事:“出入令狐相国书馆中,待遇甚优。时宣宗喜歌《菩萨蛮》,綯假其新撰进之,戒令勿泄,而遽言于人。”[6]则《菩萨蛮》的写作,是宰相令狐綯假借其手,献给唐宣宗的,那么此词的女主人公以宫女娥妃为当。当然,一般人认为女主人公是一名贵族女子,如“此词写一个贵族女子空虚的寄生生活”。[7]
四、关于作品的主旨。此词主旨,向来也有多种解说,举其要者,有以下几种:
“感士不遇说”。清张惠言持此说。其编撰的《词选》卷一称:“此感士不遇之作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8]初服,与朝服相对,指未入仕的服装,代指未仕。近人夏承焘也基本认同:全词描写女性,这里面也可能暗寓这位没落文人自己的身世之感。(《唐宋词欣赏》)
闺怨说。此说较为普遍,如:“这首词描写女性内心深处的哀怨与柔情。这种感情是通过词中女子晨起梳妆的过程曲折地表现出来的。闺中女子夜来坐待情人不至,因而晨起时既‘懒也‘迟;妆成后虽然光彩照人,但却难掩心中的孤寂。”[9]
艳情说。如近人俞平伯说:“旨在写艳,而只说“妆”,手段高绝。写妆太多似有宾主倒置之弊,故于结句曰:‘双双金鹧鸪。此乃暗点艳情,就表面看总还是妆耳。”(《读词偶得》)今人葛晓音也持此说:“写女子晨起梳妆的慵懒情态,处处只从弄妆的动作着墨,而句句暗点艳情。初日生辉与画屏相映的背景,镜中照花、人面相映的妙思,绣罗襦上贴有双金鹧鸪的暗示,均以明丽辉煌之色出之,却写得婉厚温雅。”[10]
通过参读,我们可以发现,以上四个方面,一、四是很有教学价值的内容,可以据此来设计教学,组织课堂。至于习见“鹧鸪双双,反衬人物的孤独;容貌服饰的描写,反衬人物内心的寂寞空虚”不过是一孔之见,以此“常识”来教学,未免刻舟求剑,胶柱鼓瑟。
三、研读,探寻一首词的最优解
诗词有可定处、未定处、不定处。基于可定处,去解读一首词的未定处和不定处,凭借的是个人的知识背景、阅读素养与生平经历,而知识背景的深浅、阅读素养的高低与生平经历的贫富,则纷纭众说之中必有正误与高低之分。因此,我们参考众人对一首诗词的种种解读,必须有所选择,甚至另创新说。如果说诗词的未定处、不定处正是诗词的问题所在,研读,正是探寻这些问题的最优解。
“小山重叠金明灭”被今人视为晦涩隐僻,但此晦涩隐僻与李商隐《锦瑟》不同,《锦瑟》字句皆可解,但全篇吟咏何人何事何物何情,却不可解,也可以说是李商隐有意将真情真事隐藏起来。但“小山重叠金明灭”主要是字句不可解,推究起来也不是温庭筠故意为之,从全篇看意思皆明确,用语也不稀奇,推至《菩萨蛮》这一组词看也是如此,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小山重叠金明灭”这一句在当时是可解的,意思明白得很。之所以现在不可解了,是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当年那些习见的词语所指称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或者消失了,使我们无处探寻。
那么,如何探寻这些不可解的词句呢?首先是寻找当时的实证、旁证等,包括文字、图片等;其次根据文学写作的原理进行判断;最后,揆之以人情物理:如此,方可约略近之。
“小山”究竟指什么?说是屏风者,其证是温庭筠《菩萨蛮》(其十一)中的一句“枕上屏山掩”,此处“屏山”可解为“屏如山”,如山的屏风,也可解为“屏上的山”,指屏上的金碧山水。这个屏,是放在枕边,又称枕屏。如果解为“屏上的小山”,不可压缩成“小山”,不出现屏字就容易引起歧义。如果解为“屏如山”,从造词方法看,屏山是本体喻体同时出现,是文学手法,不用于生活(下句的“鬓云”“香腮雪”同),而“小山”却只是喻体,除非当时枕屏又称小山,已约定俗成,否则文学作品不可能将本体直接隐去,故作晦语。如小山指屏山,据《菩萨蛮》(其十四)“山枕隐浓妆”,则又可以指“山枕”,一枕一屏,当不同也。将“小山”解为屏风,则“金”又难解,或解为“阳光”,又是隐喻,且无法直接联想到阳光;或解为屏风上的金碧(具体说是“泥金”),似可通,但泥金起钩染作用,在画面上呈现较多,故忽隐忽现的明灭感不强,更多的是金光闪烁。另外,从后面看,此词两句表达一个完整意思,而如果解作“屏风”,那么,开头两句就表达两个意思;再看后面,纯写美人晨起梳妆,一意贯穿,毫无枝蔓,如果首句写屏风,描写周围环境,比较突兀。温庭筠的写作是比较绵密秾艳的一路,开头两句如果一写环境,一写容颜,就显得疏朗清丽,不太符合此词的组句方式。因此,将“小山”解为“屏山”,并不合理。
又有人将“小山”解为“小山眉”。既然“小山眉”是当时十种眉式,省称“小山”是可以被人理解的;再将“金”解为“蕊黄”也是可取的。只是“重叠”实在不可解。周汝昌解“重叠”为“重(zhòng)叠”,义为“深蹙”。小山眉,如何“深蹙”,实难想象;且接下的“鬢云欲度香腮雪”并不与“深蹙”相衬,延至全诗,也无明显的苦怨情绪。如果一定要解为“小山眉”,则是小山眉是用“金”色染料画上去的,经过一夜之后,染料被汗水等浸润,可能堆在一起,不再平整,有点重叠的样子。只是,这幅画面实在不雅致,不是在审美而像在审丑。不像下句,写的虽是鬓丝撩乱,仍以鬓如云、腮似雪突出她的美,从而别有一种风情。或者解为“小山眉”是用金色染料画上去的,染料画得很多,故重重叠叠。但似与“小山眉”这一名称不太像。[11]
当然,网上有资料称,此词开头两句描写女子侧卧,故看上去“小山眉”是重叠的,可备一说。或者头倚向肩(舞女常见动作),两眉也为重叠的,如温庭筠诗句“晴碧烟滋重叠山,罗屏半掩桃花月”(《郭处士击瓯歌》)。[12]
总之,解作小山眉,可取,也存疑。
“小山”不好解,倒不如从“金”字解处入手。温庭筠十四首《菩萨蛮》,除“小山重叠金明灭”外,出现“金”字词句有七句,分别如下:
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其一)(金鹧鸪:金黄色的鹧鸪。)
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其三)(金作股:用黄金作钗脚。)
翠翘金缕双鸂鶒,水纹细起春池碧。(其四)(金缕:金色羽毛。)
画罗金翡翠,香烛销成泪。(其六)(金翡翠:金色的翡翠鸟。)
凤凰相对盘金缕,牡丹一夜经微雨。(其七)(金缕:金色丝线。)
翠钿金压脸,寂寞香闺掩。(其八)(金压脸:金箔等饰物下垂遮住了脸。)
金雁一双飞,泪痕沾绣衣。(其九)(金雁:指绣衣上的金色大雁。)
宝函钿雀金鸂鶒,沉香阁上吴山碧。(其十)(金鸂鶒:钗上金色的鸂鶒饰形。)
闲梦忆金堂,满庭萱草长。(其十三)(金堂:华丽的厅堂。)
山枕隐浓妆,绿檀金凤凰。(其十四)(金凤凰:指枕上金色的凤凰纹饰。)
温庭筠好用“金”字,但“金”字放在其他名词前,往往是金黄色的意思,个别(金鸂鶒)兼有金属之意;只有单用“金”字,指的是金飾。那么,此句中的“小山重叠金明灭”中的“金”是否也是金饰呢?
俞平伯引用的另一个证据是毛熙震《女冠子》:“修蛾慢脸,不语檀心一点,小山妆。蝉鬓低含绿,罗衣淡拂黄。//闷来深院里,闲步落花傍。纤手轻轻整,玉炉香。”从这篇词也可以看出“小山”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妆饰。而对此“小山妆”也有两种不同理解,一种认为指小山眉妆,另一种则认为指一种发型,发髻高耸如小山形。
王子今教授在考查唐代妇女妆饰图像后,认为:“‘小山形容高髻,‘重叠形容‘玲珑云髻生花样。而所谓的‘金明灭则形象地描述了‘玉梳钿朵‘宝梳金钿筐等一类簪饰‘在头发间重叠闪烁情形。至于‘整顿舞衣又‘动摇歌扇时,这些髻饰‘随步且‘逐风,从不同角度反射四面来光而晶莹闪耀的生动景象,也可以想见。”[13]
王子今解说是可以想见出来的,从文学形象看,也是非常美好的,只是缺乏足够的文字佐证。
如将“小山”理解成发髻,与下文的“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也相照应。“鬓云欲度香腮雪”说明发丝有点散乱;“重叠”表明“发髻”经过一夜睡卧,有些堆在一起,所以要“弄一弄”。“弄”字本义指双手玩赏玉器,“弄妆”可以解作用簪饰别住发髻等,使之成型。
接下来,我们可以对这首词的主旨再做一番研读。
“感士不遇说”多被后人否定。清朝张惠言《词选》选词很严,柳永的词一首未选,却将温庭筠十四首《菩萨蛮》全部录入,这就必须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是《菩萨蛮》寄托了思君之情,这其实是认可了《菩萨蛮》是进献之作,是相国令狐绹暗自请温庭筠代己新填《菩萨蛮》词以进献唐宣宗;同时又认为这些词表面上写宫女,实际上写自己,借宫怨以自怨。张惠言将之比拟成汉代的《长门赋》。《长门赋》是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受汉武帝失宠皇后陈阿娇的百金重托而作的。作品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写成,表现陈皇后被遗弃后苦闷和抑郁的心情。它开创了宫怨题材的先河。其序言曰:
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
但《长门赋》有无“感士不遇”的因素?后人可以联想,可以猜度,但就其序言看,应当说是没有这个创作意图的。
温庭筠的《菩萨蛮》组词是不是宫怨词?俞平伯认为是宫怨词,在解释“青琐对芳菲,玉关音信稀”(《菩萨蛮(其四)》)时说:“‘琐训连环,古人门窗多刻镂琐文,故曰琐窗。曰青琐者,宫门也,此殆宫词体耳。”他分析“两娥愁黛浅,故国吴宫远”时又说:“‘吴宫明点是宫词,昔人傅会立说,谬甚。其又一首‘满宫明月梨花白,可互证。欧阳炯之序《花间》曰:‘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此两语诠词之本质至为分明。温氏〔菩萨蛮〕诸篇本以呈进唐宣宗者,事见《乐府纪闻》。其述宫怨,更属当然。”(俞平伯,《读词偶得》)从《菩萨蛮》整组词描写的富丽堂皇来说,说成是宫怨诗是可取的。但由于时间、地点、人物的模糊,就每个单篇词而言,移之一般的闺怨、思乡、怀人,也未尝不可。
即使承认其为宫怨词,词中的女主人公为宫女娥妃,而写作此词时温庭筠也正是屡试不第之时,也不能认为其为“感士不遇”之作,尽管二者情感心理上有相似之处。说到底,是张惠言囿于君臣之义而给《菩萨蛮》贴上的政治标签。
后人对张惠言的“感士不遇说”多持否定,如近人李冰若称:“统观全词意,谀之则为盛年独处,顾影自怜;抑之则侈陈服饰,搔首弄姿。‘初服之意,蒙所不解。”[14]王国维也说:“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15]皋文是张惠言的号,王国维认为张惠言论词太刻板,非要比附君臣大义上去,其实这首词不过是“兴到之作”,一时兴趣,写了一个美女跟爱情的小词,没有什么深意,偏被张惠言深文周纳出一个比兴寄托来,以接上《离骚》的香草美人传统。
如果认定《菩萨蛮》组词是宫怨词,那么,就《小山重叠金明灭》这篇词来说,是否表达了某种怨情?
今人浦江清:“此章写美人晨起梳妆,一意贯穿,脉络分明。论其笔法,则是客观的描写,非主观的抒情,其中只有描写体态语,无抒情语。”(《词的讲解》)那么,人们是如何从中看出怨情的呢?主要从两个词:“懒”和“鹧鸪”。(至于“迟”不是指“迟起”,而是“慢”的意思,指弄妆梳洗很慢。)如清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无限伤心,溢于言表。”[16]对这两个字的解说,人们发挥了很多。我们举叶嘉莹的解说为例:
为什么说“懒起画娥眉”呢?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悦己的人不在她的旁边,我化妆给谁看呢?所以“懒起画娥眉”,就是说她懒得化妆,因为没有她爱也爱她的人在身边,我化妆给谁看呢?所以“懒起”,不过她毕竟还是化了。
衣服上绣的是“双双金鹧鸪”。这是反衬,衣服上绣的是成双成对的鸟,可是她自己的配偶呢?她的那个爱她也被她所爱的人呢?那个人是不在这里的。这是美女,这是相思,这是爱情。[17]
叶嘉莹以女性的心理去揣度,自有其合理处。但问题是,她爱也爱她的人在不在身边,原词并没有交代。这和“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伯兮》)”的情形根本不同。至于“懒起”“新帖”“双双金鹧鸪”,她爱也爱她的人在她身边她也可能这样做。说成“反衬”就掉进“宫怨”的窠臼了,这是和“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不同的。
即使持“山眉深蹙”说的周汝昌,对这两个词的解说也不作过多发挥:“虽曰懒起,并非不起,是娇懒迟迟而起也”“偏偏是一双一双的鹧鸪图纹。闺中之人,见此图纹,不禁有所感触”。至于感触什么,周先生并没有点明。周先生知道有人会问,所以接着说:“若有人必定诘问:所感所触,与全篇何涉?岂非赘疣,而成蛇足乎?答曰:假使不有所感有所触,则开头之山眉深蹙,梦起迟妆者,又与下文何涉?飞卿词极工于组织联络,回互呼应,此一例,足以见之。”[18]周先生说此所感所触正是照应“山眉深蹙”“梦起迟妆”的,是文气贯通的表现,但是对实质内容避而不谈。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既指出它重视辞藻的艺术特征,也指出它暗示的情思:“把美人的睡眠、懒起、画眉、照镜、穿衣等一系列娇慵的情态,以及闺房的陈设、气氛、绣有双鹧鸪的罗襦,一一表现出来,接连给人以感官和印象的刺激。它没有明白表现美人的情思,只是隐约透露出一种空虚孤独之感。”[19]“隱约透露”也只是编者的主观解读。而此前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说得比较刻薄些:“他在词里把妇女的服饰写得如此华贵,容貌写得如此艳丽,体态写得如此娇弱,是为了适应那些唱词的宫妓的声口,也为了点缀当时没落王朝醉生梦死的生活。它上承南朝宫体的诗风,下替花间词人开了道路。”[20]
宫体诗,宫怨诗,一字之别,前者重写色,后者重写情;色中含情,是艳情,情中含怨,是幽怨。而宫体诗,宫怨诗,大多是男子所写,从他们对主人公的态度来看,宫体诗不免涉于轻薄,而宫怨诗多含同情。给《花间集》命名并作序的五代词人欧阳炯说得很明确:
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之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21]
欧阳炯明确指出温庭筠的词作类似李白的《清平乐》(一般称《清平调》),上承的就是南朝的宫体诗,这是时人给予的评价,应当是最贴切的。
据史书记载:“温庭筠者,太原人,本名岐,字飞卿。大中初,应进士。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测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裴度子或侄)、令狐滈(令狐绹子)之徒,相与蒱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22]从太原到长安,温庭筠可能迷失于花花世界,与京城富少厮混在一起,艺术才华献给歌楼妓院,自然不得志。后来浪游外地,也是“与新进少年狂游狭邪”,德行上并没有收敛。以此德行观照,温庭筠倒是自甘沉沦,何求上进?
后人解为怀才不遇,解为思君怨悱,正是“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还是当代学者余恕诚说得比较客观:“温词中,作者倾注的主要情感,还是温庭筠作为情种浪子对艳美世界的流连,对女子不幸的同情。在对女性的同情中,可能折射出了作者某些身世之感,但它不是创作中有意识的设喻或寄托,而是浸透作者全身心的情绪在创作中无意识的流露。”[23]
具体这篇《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笔者认为只是温庭筠对艳美世界的流连之作。抛开歧义纷纷的“小山重叠金明灭”,其他可以看得见的描写,“鬓云欲度”的撩拨,“香腮雪”的肉欲,“懒起画娥眉”的娇慵,“弄妆梳洗迟”的做作,“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自我欣赏与陶醉,“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的内在心愿与暗示,无不指向一个感官刺激的审美世界。
李泽厚指出这种艺术趣味的来历:
从中唐开始大批涌现的世俗地主知识分子(以进士集团为代表)很善于“生活”。他们虽然标榜儒家教义,实际却沉浸在自己的各种生活爱好之中:或享乐,或消闲;或沉溺于声色,或放纵于田园;更多的是相互交织配合在一起。中唐的这种矛盾性格逐渐分化,经过晚唐、五代到北宋,前一方面——打着孔孟旗号,口口声声文艺为封建政治服务这一方面,就发展为宋代理学和理学家的文艺观。后一方面——对现实世俗的沉浸和感叹倒日益成为文艺的真正主题和对象。……并非宋明理学,而是诗文和宋元词曲,把中国的艺术趣味带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境界。这里……更指的是李商隐、杜牧、温庭筠、韦庄的诗词。……这里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主题,……走进了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之中。……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24]
如温庭筠这类知识分子,他们的艺术情趣已经沉浸在感官的世界之中,硬要把他们的词作摆放到治国安邦的殿堂之上,即使是摆放在怨悱的边缘之处,恐怕他们也是忸怩不安的。他们更乐意的,是在绮筵绣幌、歌馆楼台的妖娆世界,在绮靡采艳的声色之中,吟唱这些柔媚轻巧的词句,获得心灵细微的触动和长久的迷醉。
综上而论,《小山重叠金明灭》当为宫体词绮艳一路的代表。
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入研讨,我们打开了文本与世界的各种关联。这样,我们在课堂教学时就可以提供足够的空间让学生驰骋想象,也有了明确的边界把学生留在文学的殿堂之中。这样的课堂教学有一定的宽度,也容易达到一定深度。
注释:
[1][7]朱东润 主编.中国历史文学作品选(中编 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27—428.
[2][18]周汝昌.《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赏析[M]//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40.41.
[3]百度百科.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DB/OL〕.[2019.03.30].https://baike.baidu.com/item/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4][17]叶嘉莹.小词大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69.60.62.
[5]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899.
[6]辛文房撰,舒宝璋校注.唐才子传[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341.
[8]张惠言.词选: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57:12.
[9]徐国良,方红芹注析.花间集[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1.
[10]葛晓音.唐诗宋词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01.
[11]此说并非新说。夏承焘在《温庭筠的〈菩萨蛮〉》中说:“小山”是指眉毛,“小山重叠”即指眉晕褪色。“金”是指额花,“金明灭”是说褪了色的额花有明有暗。见夏承焘《唐宋词欣赏》,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12]friyalv.解溫庭筠词“小山重叠金明灭”之谜〔DB/OL〕.[2019.04.02]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505350&PostID=7511108.
[13]王子今.温庭筠词“小山重叠金明灭”图解[J].四川文物:2005(02).
[14]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2.
[15]王国维著,李科林校注.人间词话·人间词[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124.
[16]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8.
[19]袁行霈 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51.
[20]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206.
[21]欧阳炯.花间集叙[M]//赵崇祚.花间集.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4.
[22]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M]//二十五史(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610.
[23]余恕.论温词“类不出乎绮怨”与对绮怨心境的表现[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3).
[24]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190‐191.